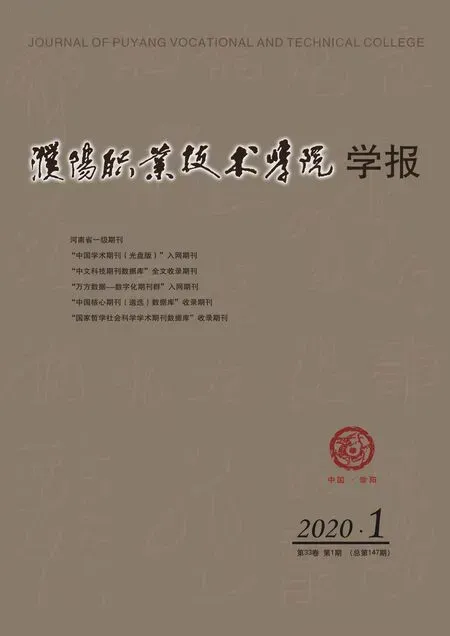《红高粱家族》的“狂欢化”叙事
2020-12-12陈亚
陈 亚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莫言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我觉得一个作家肯定要在创作过程当中追求变化, 每一个作家如果他认为可以用过去的语言、 过去的风格来写新的故事那是没有出息的……应该有这种求变的心, 是一个作家还有可能进步的根本起点。”[1]正是基于这种“求变的心”,莫言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不断超越自我,从而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其《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强烈狂欢化色彩的小说,颠覆了既成的叙事模式和传统的审美原则。小说中“复调”式的叙事结构、“狂欢化”的语言风格以及“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共同构筑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狂欢化”世界,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狂欢盛宴。
一、“复调”式的叙事结构
“复调”理论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一个子理论,复调小说是文学“狂欢化”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与独白小说相比,复调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 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2](29)。 换言之,“复调”小说强调对话性,强调将小说中众多的声音和意识结合起来, 从而使作者与叙述者、 叙述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形成一种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 小说《红高粱家族》便通过运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实现了“现实”与“历史”超越时空的“大型对话”,构成了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叙事结构。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复调”式的叙事结构主要以三种方式呈现。
第一,不同的叙事视角的运用,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小说通过人称的变化自由切换叙事视角,主要形成了“我”与“我父亲”两种不同的叙事视角,创造了“我”和“我父亲”两个叙述者的复杂时空。 小说一开始便以“我”的叙事声音为基点,讲述“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故事。 而在具体展开讲述故事时,又以“我父亲”作为“第一叙事人”,而将“我”这个站在当今来俯瞰历史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隐匿其中。 “父亲”作为事件的参与者,他的叙述经历,可以为作为文本叙事人“我”的叙述提供历史素材及真实性的保障。 而“我”的叙述视角则直接将“我”带入了故事的语境,带到了历史的现场。 不仅如此,“我”与“我父亲”叙述视角的自由切换,使得“我”与“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三代人能够进行对话交流,甚至可以产生一种情感的互通。比如,通过“父亲”的叙述,我可以嗅到“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可以听到“我奶奶”坐在花桥里“心跳如鼓”,可以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体细节;通过“父亲”的感受,“我”可以与“我奶奶”“我爷爷”产生一种情感的互通。“父亲”能感受到“我奶奶”死前的痛苦,“我”同样可以通过“我奶奶”死前的呐喊,体会到“我奶奶”面临死亡的痛苦与不甘。“父亲”以历史的参与者讲述故事,“我”则用今天的视角去追述和评论“父辈”的经历。 在这两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中,“我”渐渐融入了故事当中,仿佛也成为了故事的参与者。
第二,叙事顺序的颠倒错乱,形成了一种“狂欢”式的时间与空间。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采用了诸如倒叙、顺叙、插叙等多种记叙顺序,打乱了故事叙述的时空,形成了一种超越常规生活的狂欢时空。从总体上来看,整部小说的记叙顺序采用的是倒叙。先讲“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去世前的事情,然后再展开叙述“我奶奶”生前与“我爷爷”之间发生的故事。 具体来看, 小说中各个部分又采用了多种叙事顺序。 比如,小说一开始便直接写到1939 年“父亲”跟着余司令去伏击敌人汽车队的场景。在这段场景描写中,作者首先运用顺叙的方法,记叙“父亲”与“我爷爷”出门时、出门后的场景,中间则穿插了“父亲”死后,“我”站在“父亲”墓碑上的画面,然后又借“父亲”对刘罗汉的思念,运用插叙的方式,叙述了刘罗汉被日本兵剥皮前的事情, 最后又转而描写余司令带领大家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过程。 小说通过运用多种不同的叙事手法,颠倒叙事顺序,使故事的时间与空间发生错乱,从而形成一种“狂欢式”的时空。在这种时空中,作者可以将“我”很好地融入故事,使“我”自然而然地成为文本的叙事者。 通过借用这样一种“狂欢式”的时间和空间,将“我”与“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联系起来,更好地表现具有血缘关系的三代人不同意识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话。
第三,两条线索并行,多个小故事夹杂,实现了双声调的并列共行、多声道的共振。 小说《红高粱家族》主要有两条叙事线索:主线是“我爷爷”的抗日史,副线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小说以“我爷爷”伏击日本的汽车队作为开头,通过“父亲”对“我奶奶”死后,“我爷爷”一系列的动作行为,传达出“我爷爷”对“我奶奶”的思念,从而引出“我爷爷”与“我奶奶”的爱情故事。 通过“父亲”对罗汉大爷的回忆以及陶罐头老太太的讲述, 引出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剥皮的故事、“我奶奶”和刘罗汉之间的故事。在讲述“我爷爷”的抗战史时,又在多处插入“我爷爷”苦练“七点梅花枪”,刺杀花脖子的故事以及“我爷爷”与冷支队、江小脚之间的纠葛。 而在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时,又在多处运用插叙的手法,讲述了“我爷爷”与“我二奶奶”、“我奶奶”与黑眼的故事等等。小说通过两条主要线索并行的方式,运用插叙的手法使多个小故事夹杂其中, 突破了原有叙述的一元结构、独白式的单视角模式,形成了一种双声道并列共行、多声部共振的“复调式”叙事模式。
简言之,小说《红高粱家族》在全知与限知两种视角之间来回穿梭, 在叙事过程中通过自由切换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父亲”,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的“大型对话”,从而拉近了“现实”与“历史”的距离。通过采用不同的叙事手法,形成了一种超越常规生活的“狂欢”时空,实现了小说中时空的自由变换。通过形成一种双声调并列共行、 多声道共振的叙事模式,从而实现小说的复调叙事,构成整部小说复调交错的叙事结构。
二、“狂欢化”的语言风格
“‘狂欢化’表现在语言上,即是‘脱冕’式的艺术风格,指为崇高降格、为低俗升格的语言风貌。 巴赫金所坚守的是狂欢化理念, 所奉行的是避雅求俗的旨归,这使平民俗语、百姓口语、幽默讽刺,甚至是下流避讳之词,皆可入文。”[3](97)小说《红高粱家族》的人物语言多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叙事语言又多混杂俚语、俗语、咒语、顺口溜、民间歌谣、齐鲁方言等多种类型的语言,符合巴赫金所倡导的“避雅求俗”旨归,属于名副其实的“狂欢化”语言风格。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语言充斥着粗话、脏话、叫骂等,同时夹杂着小贩们的吆喝,是典型的广场式语言,这些粗俗污秽语言的混杂,达到了巴赫金所说的“语言杂多的佳境”[4](205)。 譬如小说中“我奶奶”在临死前有这样一段呐喊:
天哪! 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认为我有罪吗? 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 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 天,什么叫贞节? 什么叫正道? 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邪恶? 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5](64)
这一段呐喊,是“我奶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对夺走自己生命的“天”的控诉。 从这一声声的叫骂中,“我”听出了“我奶奶”内心的不甘,听出了“我奶奶”对自己一生为追求幸福的所作所为的不后悔,听出了“我奶奶”对压抑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不满等等。作者在这里通过一段充满控诉、叫骂的言辞而不是借用一些华丽的辞藻,表达了对“我奶奶”敢爱敢恨敢想敢做的行为、 蔑视封建道德伦理的精神的高扬与称颂。 小说中“我爷爷”亦可谓脏话、粗话连篇。如在小说第一章第四部分中, 余司令带领弟兄们伏击日本汽车队为队伍提高士气时说:“弟兄们,藏好,等鬼子们汽车上了桥,等冷支队的人把退路封住,听我的号令一齐开火, 把畜生们打到河里去喂白鳝喂蟹子。 ”[5](21)又说:“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 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 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 我还想改编他呢! ”[5](21)等等,小说在刻画余占鳌这个人物形象时,其人物语言屡屡使用“老子”“王八蛋”“畜生”等等语辞,通过这些粗俗的语言,将一个粗野豪放、 蛮横倔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而小说中类似于“杂种”“婊子”等骂辞更是比比皆是。另外,小说中众男人下流污秽的话语更显粗俗不堪。如小说第一章,余司令手下的队员们说:“豆官,我想你娘。 ”甚至还有“想和你娘困觉”等下流的话。 再如小说第四章中第一部分郎中在向黑眼介绍药的功效时说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小说中像这样一些粗俗不堪的下流话比比皆是,正是“狂欢化”语言风格的体现。
小说中的叙事语言亦体现出了“狂欢化”的语言风格。 小说中描绘的肉体、生殖器、粪便等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俯拾即是。 如小说中屡次描写了男人撒尿的场景,其中一次提到了“我爷爷”往高粱酒的篓子里撒尿, 却阴差阳错地酿成了上等的高粱酒。 由“被清凉的尿液浇过的高粱酒”变成上等醇香的高粱酒,这一转变,类似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降格”。同时,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还有多处提到了“乳房”、男性生殖器等肉体下部形象。 如描写“我奶奶”被子弹射中时写到:“枪弹射穿了奶奶高贵的乳房,暴露出了淡红色的蜂窝状组织。”[5](59)另外,在巴赫金看来,“夸张、夸张主义、过分性和过度性,一般公认是怪诞风格最主要的特征之一”[6](351-352)。 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狂欢式的夸张”亦主要通过叙述语言表现出来。如对“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的“野合”场景有这样一段描写:
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 ……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 ……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喑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过去了。[5](62)作者运用铺陈夸张的辞藻将“我爷爷”“我奶奶”“耕云播雨”的壮观场面跃然纸上,这段描写类似于狂欢式的场景描写。 通过这段“狂欢式极度夸张”的描写,将“我爷爷”与“我奶奶”生命本能欲望的迸发描写得淋漓尽致,讴歌了“肉体的低下部位”和“肉体的物质性原则”,歌颂了“我爷爷”与“我奶奶”勇于冲破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精神。同时,小说中通俗易懂的民间歌谣、节奏分明的顺口溜、咒语、“吃拤饼”等不同类型的语言多得数不胜数。
总之, 作者借助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将社会杂语嵌入小说话语体系之中,将俗语、民间歌谣、方言等多种类型的语言夹杂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之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狂欢化”语言风格。 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北京的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语言是庞杂的混合体,有乡间土语、有纯粹口语化的、有文革流行的政治化的术语、有来自古典的经典的书面语,像个化妆舞会,像狂欢节,牛头马面都有,眼花缭乱。”[7](18)正是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看似粗俗不堪的“狂欢化”的语言风格, 使读者不仅能感受到高密人民原汁原味的“粗俗”, 而且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三、“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创造了一种观察世界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即以狂欢的眼光观察世界,以颠倒的视角审视现实人生, 并将这种审视人生的特权授予了一群特殊的、 不平常的边缘人物——傻瓜、小丑、骗子等。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亦塑造了一大批以“痴”者、“狂者”为代表的“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红高粱家族》中“我父亲”便是莫言笔下“痴”者形象的代表。 小说展开的背景是在“我父亲”十四岁多一点的时候。而整部小说中故事的展开皆以“我父亲”的叙述为主,这样一来,整部小说的叙述采用的便是一种“童年视角”。 换言之,整部小说故事的展开、整个故事中人物的活动都以“我父亲”这位“儿童”为中心。在“我爷爷”“我奶奶”等成人统治的世界里,“我父亲”作为一个“儿童”成为了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一书中提到的“不理解”的转义载体,担负着与巴赫金论述的狂欢节中的傻瓜等角色相同的功能。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相较“我爷爷”“我奶奶”等成人而言,“我父亲”这个“儿童”就相当于一个边缘角色,由于对成人世界有诸多的不理解和不适应,于是便被作者赋予了“傻”“痴”的面具。比如,“我父亲”不理解“我奶奶”死后“我爷爷”的种种行为,不明白“我爷爷”脸上两行泪水背后的含义;不理解“我奶奶”对“二奶奶”的种种咒骂,因为在“我父亲”的记忆里,“二奶奶”对他还算比较亲切。然而这诸多的不理解却传达着“我父亲”这位“痴”者视角所映射的人之世态,展现着狂欢式感受的“第二种生活”。
“狂欢化”的人物形象除了“痴”者外,还有“狂”者。 “狂”者的人物形象不同于那些屈从于传统道德伦理的人物形象,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反抗者、破坏者和追求理想的行动者。 这类“狂”者的人物形象是对传统人物形象的颠覆, 他们是源自于民间诙谐文化中的怪诞人物形象, 他们的观念与传统伦理道德中宣扬的观念格格不入。 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对于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狂”者则以“我爷爷”“我奶奶”为代表。
“我爷爷”余占鳌的“狂”首先表现在对人伦秩序和礼教制度的蔑视上。 “我奶奶”在轿子里的哭声唤起了“我爷爷”的怜爱之心,于是不顾周围人的眼光、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说教,抓住“我奶奶”的小脚将它送回轿内;因为对“我奶奶”一见倾心,于是不顾人伦纲常直接将回门的“我奶奶”掳进高粱地;为了让“我奶奶”能够脱离苦海,果断地杀掉单家父子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对封建礼法的公然践踏,余占鳌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封建权威, 任凭生命的原始冲动打破以“礼”为最高标准的法则,在天地之间宣示着性爱的力量和美丽。其次,他的“狂”还表现在对权势的不屈服与反抗上。 为了报“我奶奶”被土匪花脖子掳去的仇,“我爷爷”苦练“七点梅花枪”,最后单枪匹马杀掉以“三点凤凰头”著称、称霸一方、让官府闻风丧胆的土匪头子花脖子。对待各种政治势力的拉拢,他一概拒绝,凭借自己的胆识拉起了一支土匪队伍,与日本人周旋抗争等等。 这些都体现出“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的“狂”。 而“我奶奶”的“狂”则主要表现在其对“三纲五常”封建制度的漠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夫权、父权的反抗。 在“我奶奶”的眼里,花轿里的一切都污秽不堪,整个花轿就像一具棺材,这种心理反映了“我奶奶”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她的心里一直有对美好自由爱情的希望, 所以她毫不避讳地用小脚掀开轿帘去看轿夫宽阔的肩膀; 当发现将自己掳进高粱地里的人是“我爷爷”时,她“暗呼苍天,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激得奶奶热泪盈眶”。不同于传统女性,整部小说中“我奶奶”丝毫没有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欲冲动。不似传统的“淑女贤妇”,“我奶奶”敢于反抗以男性为中心的夫权、父权。嫁进单家不情不愿,于是新婚之夜手握剪刀保护自己。对父亲的所作所为百般怨恨,于是在当家后,用二十个包子决绝赶走自己的父亲等等。 作者对“我奶奶”这些行为的描写,将“我奶奶”这个敢于反抗礼教制度、不屈从于命运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总而言之,小说《红高粱家族》对“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这类“狂欢化”人物形象的刻画,一方面在于实现对传统人物形象的颠覆, 另一方面则在于实现对“我爷爷”“我奶奶”这类平凡人物的“加冕”。小说中“我爷爷”是个不同寻常的英雄。 不同于传统“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我爷爷”是个“杀人越货”、满口污言秽语、 土匪气十足的英雄。 不同于传统将“三从四德”奉为圭臬的“淑女贤妇”,“我奶奶”是个“越规”、自由开放的女性。作者对“我爷爷”“我奶奶”的刻画颠覆了传统的人物形象, 这类人物形象散发着浓郁的狂欢气息。 以“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为代表的这群偏离社会秩序、道德规范的边缘人物,在非理性视野的观照下, 能窥见他人所未能见的世界,触及中心人物所未能及的新领域。
莫言曾说:“我只能用低调写作,因为低调,才是真正贴近生活的。 ”[8](184)莫言一贯提倡低调写作,却又在写作中不断探索求变。莫言的“低调”,让我们在《红高粱家族》中真切地感受到了高密东北乡民浑朴自然的生活,感悟到了高密东北乡民的“真”性情。莫言“求变的心”,让我们在《红高粱家族》中看到了一个“狂欢化”的红高粱世界。 小说中“复调”式的叙事结构,让我们见证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狂欢化”的语言风格, 让我们听到了高密乡民的呐喊;“狂欢化”的人物形象,让我们感受到了高密乡民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自由张扬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