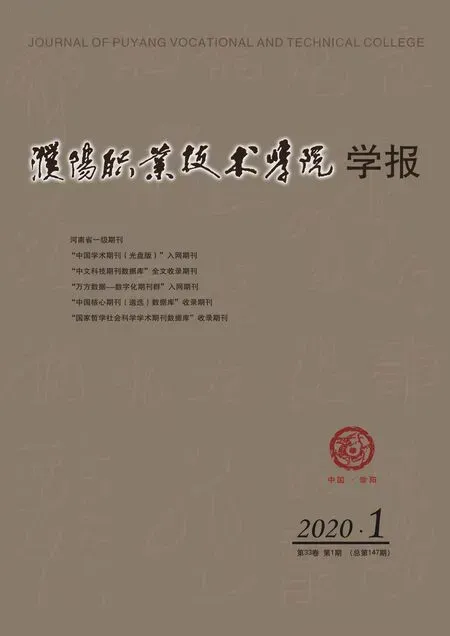从演义小说中军师形象看中国民众的崇智心理
2020-12-12张潮寒
张潮寒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2)
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出现并取得成功以来, 继之而来的诸多演义小说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军师形象。 这类军师形象作为人民群众心目中智慧的化身, 反映了明清时期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和情感取向。但是,目前学术界多致力于研究诸葛亮等单个著名军师形象, 或将两位军师进行对比研究, 即使有把军师形象作为一种类型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 也多着眼于探讨方术文化及传统儒道思想对军师形象的影响, 鲜有考虑到落魄文人不独要风流自赏,还要取悦下层民众使作品得以流播,这样就不得不照顾下层民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趣味,自觉站在下层民众角度,尽量写出他们心目中的军师[1](62)。 军师形象之所以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就是因为他们反映了人民大众理想中“智慧”的面貌,成为人们心目中“智慧”的代言人,进而引起人们崇拜。文学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多方面的[2](318),因此我们可以从一类文学形象中了解中国民众的精神追求。 这种从读者接受角度探究军师形象中蕴含的受众文化心理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一、伦理本位——智慧的依附性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的军师能够成为智慧的代名词,为广大民众所传颂,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崇智心理。 然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评价人和事物的标准都或多或少受到道德因素的影响。 孟子称“仁义礼智”为四端,则把“智”看作伦理道德的一部分。 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眼中的智慧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的, 而是依附于伦理道德而存在。 具体来说,则表现为强烈的道德至上性和宗族血缘性。
(一)忠君报国,道德至上
“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乃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3](275)。小说中塑造了诸多军师形象。而作为智慧化身为人所崇拜和传颂的对象, 其共同特征是他们将超群的智慧“用于正道”,即忠于明君,帮助明君一统天下或治理国家。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坚持大汉正统,为报刘备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替天行道,扶周灭商,都是忠君报国的典范,因此被世代传颂。即便是作为小说中的反派或失败一方的军师,如闻太师、哈迷蚩、范增等人, 他们虽立场不同, 其结果也是以失败收场,但他们的报国忠君之心仍然值得肯定,因此在小说文本中也给予他们一定的肯定与尊重。 相反,如《说岳全传》中的秦桧,有谋略却甘作金国奸细,陷害忠臣岳飞,徒有不忠之智,只会被万世唾骂。 小说以道德为标准将军师分类, 一方面是在传统的儒家文论“文以载道”思想指导下,作者有意强调和塑造的结果。 小说中对军师爱国尽忠的高尚品德的极力歌颂,正是受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寄寓了作者对于以天下为己任,不辞劳苦,积极入世,为国为君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人格的崇拜之情[4](23)。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民众在儒家思想长期熏陶下,也形成了以道德品评人事的思维方式。 因此中国民众虽然对智慧极为推崇, 但这种崇智心理显然不够独立。中国人所崇拜的智者是有道德的智者,忠君爱国的智者;值得尊敬的智慧是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而不是害民误国的奸谋。 演义小说中着力塑造和歌颂的智慧化身许多都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 有着高尚的人格,而不是单纯地强调“智”。军师之智慧必须用于正途,否则就遭人唾弃或沦为笑柄。
(二)家族传承,血缘纽带
“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入文明社会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体系。 ”[3](226)因此中国人极重血缘纽带,重视家族传承,这在中国民间社会尤甚。 因此演义小说中不仅出现了许多将门世家,还出现了许多军师世家。《说唐前传》中的徐懋功是军师形象的典型, 在瓦岗寨和唐军中都曾出谋划策;而在《薛刚反唐》中,他的孙子徐美祖担任了薛刚兴唐军的军师, 另一个孙子徐孝德亦担任了李旦汉阳军的军师。 此外还有《说岳全传》身为诸葛亮后人的诸葛英,也是精擅扶乩请仙之法,担任岳飞麾下军师。 其子诸葛锦更是梦中直接得祖先孔明授予天书,成为岳雷扫北的军师。 这种军师世家的出现,正是中国人强烈的家族观念的反映。 家族中长辈都希望子孙能够继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将来光宗耀祖,至少不能辱没先人。家族中出了一位才智之士,其后人也必才智过人。 因此一部小说出现了才华卓绝的军师,其他小说家在创作小说时需要塑造军师形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就将其设定为某著名军师的子孙后代。但是智慧真的能够家族继承吗?首先中国古代就没有相关的遗传学研究作为佐证, 更何况一个人是否有智慧还受到后天培养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仅凭家族遗传很难将智慧世代相传。但小说家这么创作,无非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这种心理就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家族传承就是虎父无犬子, 人们都希望他的后人有能力继承自己甚至胜过自己。 这种军师世家出现在小说中, 就是中国人家族本位思想在小说中的反映。 这种思想对中国民众崇智心理的影响体现在智慧的家族传承性上,与其说崇拜某一个智者的智慧,倒不如说是更希望将这种智慧以家族的形式代代传承,后人能够延续祖先的辉煌。 在家族观念影响下,民众的崇智心理也就带上了浓厚的家族血缘色彩。
由此可见, 中国民众的崇智心理带有很大的依附性。它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品格被人颂扬,而是依附于伦理道德和家族血缘, 在满足了特定条件的基础上才会成为人们所崇拜的对象。 这种依附性是中国民众崇智心理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尚奇倾向——智慧的非理性
自先秦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起,理性精神便贯穿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但中国文化中始终有着源自楚汉浪漫主义的非理性因素。 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多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故而信鬼神者少;而广大民众受自身认知水平和眼界所限,加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谶纬神学和宗教迷信等思想的影响, 难免会对这种超现实、非理性的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和崇敬之情。因此,对于军师智慧中的超现实因素,则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
在传统巫文化和方术文化的影响下, 小说中的军师形象也不免带上了术士的色彩, 孔明、 吴用等“军师型”英雄都是集中了各种智者的特征之后创造出的近乎于神的“智”的化身[5](35),有着极大的超现实性, 各类奇门道法也就成为了军师高超智慧的一个重要体现。 具体来说,有观天象之术,诸葛亮以此预测自己的生死寿数,刘伯温以此发现帝星所在;有奇门阵图,布阵者如孔明所布八卦阵,击退司马懿;识阵破阵者如神机军师朱武,大破奚胜所摆之六花阵;有占卜之术,孙膑庞涓便以之斗智;“红袍将”周德威用占卜预知敌军黄巢的动向;更有种种奇门妙法,如姜子牙作法冰封岐山击败鲁雄大军, 诸葛亮于赤壁战前登七星台借东风, 公孙胜用五雷天罡正法破高廉……此等方术,都是军师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家塑造此类术士化的军师形象, 正是抓住了民众的尚奇心理,以此吸引读者。古人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一般人往往终老于故乡,视野不够开阔,对于各种罕见的奇闻异事表现得极为好奇。 加之生存环境恶劣,天灾人祸横行,无能为力的下层民众往往求诸鬼神。 在他们心目中,鬼神是万能的,吉凶灾祥尽在掌握,人们对它们既敬且畏。这种好奇心与敬畏心也影响到了民众对智慧的看法。 军师们以通神彻鬼的术法, 能常人之所不能, 因此博得人们的尊敬与崇仰。 这反映出人们理想中的智者在才能上一定要具备常人没有的本领,能够窥尽天地阴阳奥妙。
小说中军师的术士化与其说反映了人们对军师的智慧的崇拜, 倒不如说是对神异事物和不可预料未来的恐惧与敬畏。 这是英雄祟拜和道教信仰双重心理作用的产物,反映了一向遭欺受压、软弱无助的下层民众希图藉助超人的智慧和道教的神力去克敌制胜的幼稚幻梦[1](62)。尽管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近乎神仙的智者, 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位这样的智者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这类军师形象的出现也就应民众的心理需求而生。因此,中国民众的崇智心理带有极大的非理性色彩。
三、事功原则——智慧的功利性
先秦诸子就十分重视智慧。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要求人应当领悟自然的规律, 才能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兵家重视战争中的智谋,以智谋取胜。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孙子·势篇》)法家强调的法、术、势则是君主治国驭人的智谋,而且还主张要重用“智术之士”。墨家的机关术是科学智慧的体现, 名家的诡辩术则是语言智慧的结晶。 纵横家在掌握天下时局的基础上游说诸侯,其智亦有过人者。各家各派对智慧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一个共通之处是,他们多把智慧当做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 而不像古希腊先哲那样追求纯粹的形而上的智慧。因此,人们所崇拜的智慧就体现出明显的事功原则。虽然,儒家的道义原则始终居于正统地位, 但墨法的功利原则亦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其中,二者相反相融,赋予传统价值体系以复杂的形态[3](320)。
(一)重道轻器的处事智慧
除方术外,军师智慧还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精擅兵法。 智多星吴用“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水浒传·第十四回》),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为梁山出了无数妙计。 其次能准确把握天下时局形势。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有著名的天下三分之计,周瑜也有个天下二分之计;《说唐前传》里徐懋功能够在瓦岗军覆亡之际率先投唐,也是建立在对天下大势明确把握的基础之上。至于诸葛亮舌战群儒, 则是军师口才和语言艺术的表现。 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军师智慧的内容。 但是,一个突出特点是, 墨家的科技思想在小说军师形象中甚少被提及。 诸葛亮虽有木牛流马和诸葛弩的发明创造, 在笔墨塑造上和读者印象中却远不及其观天象、排阵图、借东风那样鲜明突出。在《水浒传》中,代表了宋代科技最前沿的火炮被作者安排给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凌振,而梁山三大军师——吴用、公孙胜、朱武均没有科技方面的突出才能。 至于《说岳全传》《说唐前传》中体现军事科技的铁滑车、铁浮屠及千斤闸,皆为反派势力所有,正派一方仍是靠军师的策略和武将的勇力与之对抗,可见此等“小道”为智者所不齿。此外许多小说中都有的神仙授艺情节,所授者不外乎法术与兵书, 民众对于科技的轻视可见一斑,带有明显的重道轻器的倾向。韩愈《师说》曾言:“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小说中着力歌颂的军师往往强调其兵法韬略、神通法术、辩才纵横等“道”之学问,而非机关器物之学。反之机关器物往往为反派所利用,用来对付英雄志士,使人痛恨;且最后仍然为正义一方的智谋武勇所败,落于下乘。不仅文人士大夫, 这种倾向在底层民众的思想中亦复如是。人们将器物科技视为小道,不堪大用的奇技淫巧,正人君子不屑为之。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在人们心中未能登入智慧之堂, 而为人所认可的智慧都是在“道”的方面。但可笑的是,中国人追求和崇拜的“道”的智慧亦是以“事功”为原则,以此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问题, 终究未能达到纯粹的无功利智慧的境界。
(二)知行知止的为人智慧
道家的隐逸思想也渗透到小说之中, 使得许多军师都具备了隐士的特征。他们早年躬耕陇亩,时机成熟便待时而飞,成为一人之下的军师,辅佐主公建立不世功业,而后飘然归去,回归山水田园。《西汉演义》中张良佐高祖刘邦定天下后飘然归隐;《英烈传》中刘伯温命运同张良类似,受封后归隐江湖。 《水浒传》中公孙胜谨尊师命,“逢幽而止,遇汴而还”,因而得以保全性命。 另一位军师朱武亦出家做了全真先生,投奔公孙胜,云游四海。 如果说方术、口才、兵法等是做事的智慧, 那么这种看破尘世的归隐情结更多的是一种做人的智慧,知行而更能知止。中国社会尤重人伦,因此除了做事的智慧外,做人的智慧亦必不可少。 军师从开始的隐居生活到出山辅佐君主再到最终归隐,几乎成为了许多小说的固有模式,我们需要探索这条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开始时的隐居是因为时机未到,未遇明主,因此躬耕陇亩以躲避乱世;出山则是时机成熟,凭自己的本领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最终的归隐意味着功成身退,不为俗世名利所羁;且远离权力中心的斗争,亦是一种明哲保身。 这种隐居—出山—归隐的模式反映的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即知行知止。人们羡慕智者能够因时而动,把握时机做大事,很好地实现了人生价值。而对于最终的结果,他们往往又能够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及时放手,不贪恋权位和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真正做到全身养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方是做人的大智慧。只是很少有人能达此境界,许多人不是赍志以老,就是功高被戮。 所以,演义小说所写的这些功勋盖世而又能明机识退的军师们,就分外让人感叹、崇敬[1](63)。故而此类模式广泛地受到人们的欢迎。 但真正代表道家纯粹的叩问天道本原的大智慧并未在小说中得到体现和尊崇, 小说这种看似超然的道家隐逸思想实际上也止步于为人处世, 作为避祸和远离纷争的手段而存在, 仍未脱离我国传统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窠臼。
由此可见, 小说中军师形象所体现的重道轻器的处事智慧和知行知止的为人智慧都是以事功为原则,其根本特征仍是为现实生活服务,带有极强的功利性。 可见中国民众的着眼点绝非抽象的形而上的智慧, 其崇拜的也只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性智慧。
综上所述, 军师形象是演义小说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典型之一,其作为智慧的化身,以小说这种通俗的文学体裁为载体, 从中体现了中国民众的崇智心理。本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结合古典小说中一些典型的军师形象, 将军师智慧包含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结合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进一步探讨军师形象身上所反映的民众的崇智心理,最终发现了其具有依附性、 非理性和功利性三大特征。然而明清小说林林总总,涉及到的军师形象还有很多。本文的研究尚停留在粗浅阶段,无论是对于演义小说中军师形象的研究, 还是从读者接受角度对小说中所蕴含民众文化心理的研究, 都有待于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