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活生生的人
2020-12-11侯德云
侯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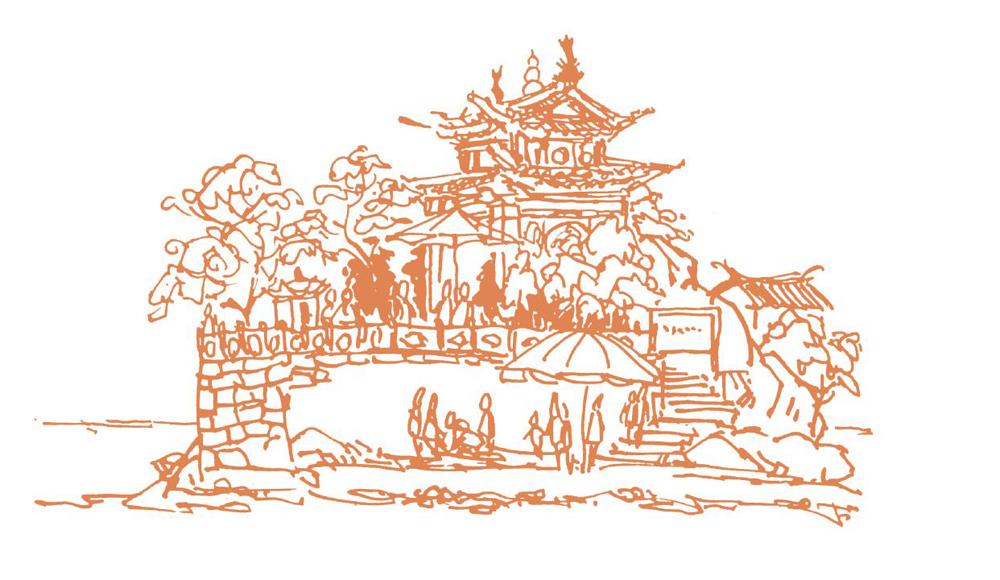
认识相裕亭已经很多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微型小说颁奖会上,最近一次见他,是去年年底,还是在微型小说颁奖会上。
从第一次见他,到最近一次见他,时间相距二十几年。当年他是小相,现在我叫他老相。同样,当年的小侯,在老相眼里也变成了老侯。
这么多年,老侯已记不清老相究竟获过多少微型小说奖项,只大概记得,有《小说选刊》的奖,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奖,有《微型小说选刊》的奖,有《小小说选刊》的奖,此外还有其它各种名目的奖。就在几天前,听说他又获了一个啥子征文的一等奖。
一个作家,写了二十几年微型小说,写出二十几部作品集,还在孜孜不倦地获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位作家对微型小说的痴情,已经痴到不可救药的境地了。说他不忘初心,绝不过分。
老相对微型小说痴情如斯,且大有从一而终的迹象,這让老侯颇为惊诧。在这方面,老相跟老侯,性格上的差异极为明显。老侯本人的创作情思至今还在游移,跟微型小说之间的离合,也不是一次两次,完全信马由缰,走哪算哪。
但老侯对老相,一直都另眼相看。我相信还有很多微型小说的热衷者和从业者,也都会对老相另眼相看。
老相的《威风》,老侯是早就知道的。我曾经写过两篇短文谈它。我认为这篇为老相带来极大声誉的作品,是由细节做种子生发出来的。“说话间,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发丝,猛弹进靴子里,指给陈三:‘你看看这是什么?”种子就在这里,它依附在那“一根花白的发丝”上面。生活中,你把一百根花白的发丝埋到土壤里,你再等上一百年,它也绝不会长出哪怕一根花白的发丝。可是你把一根花白的发丝埋在微型小说里,它就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长成一篇《威风》。
以《威风》为主打篇目的作品集《盐河旧事》,老侯也是知道的。2018年7月,它与冯骥才等几位作家的作品结为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内容简介中有这样的话:“盐河人海口,原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偏偏在这盐河两岸,盐商巨贾,才子佳人,达官显贵云集而来,造就了数不尽的风流传奇。本书创作背景,放在了晚清、民国年代,每个故事的篇幅虽小,却极尽渲染,并把力道积攒到最后,令人回味无穷。数十个精彩篇章,焦点汇于一处,如众星捧月,让《盐河旧事》浑然一体,容量非凡。”
说不清从哪天开始,老相陡然沉浸于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以微型小说的方式,打捞陈年的喜怒忧悲。不过很显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搭台,将这些旧事集结起来,无疑为老相提供了一次精彩的亮相机会。这部作品集中,除了《威风》,给老侯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嫁祸》《忙年》《赛花灯》和《赌城》等多篇。
以《看座》为主打篇目的盐河旧事之二《看座》,老侯当然也知道。2020年7月,它与谢志强、赵淑萍、颜士富等几位作家的作品结为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老相在书籍问世之前,好心好意给老侯发来电子稿,我在内容简介里看到这样的说辞:“作者在同一背景下,围绕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民俗掌故、世事变迁,一口气创作了数以百计的篇章。由一鳞一爪,到片段组合,貌似拙朴,实则匠心独运。本书收集了其中的四十几篇精彩华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拍案叫绝。”
老侯对这部电子书稿的阅读,持续了十几天时间,其中包括我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或狂奔或漫步的间歇。老侯忘不了草原上一片连着一片黄白相问的花坪,忘不了一朵连着一朵徜徉在低空的白云,忘不了觅食的马群、牛群和羊群,忘不了远山柔美的线条,忘不了弯曲而清澈的溪流,同样也忘不了盐河旧事第二卷中的名篇佳构。
老侯在这部新作里看到了一群活生生的人。
老侯固执地以为,小说的美德之一,是让虚构人物活起来,成为芸芸众生中独特的这一个,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和祥林嫂。
盐河旧事里的人物,有不少是重复出现的,大盐东沈老爷、大盐东吴老爷,各家商号的大东家、大太太、管家陈三及丫鬟兰叶、兰枝、小翠等等都是。
老侯喜欢活着的虚构人物,甚于小说的“意义”。老侯觉得,小说的“意义”是次要的,人物才是主要的。老相的杀手锏,是用细节雕刻人物。
与作品集同名的《看座》,首先点燃了老侯的阅读兴趣。这篇作品写活了三个人,一是打鱼人汪福、二是大盐东沈万吉、三是沈万吉的大太太。
汪福在盐河人海口处的一个河心岛上打鱼摸虾,大盐东沈万吉路过此地时,停了马车,看他打鱼。沈万吉这一看,把汪福吓了一跳。河边便是沈家的秫子地,在汪福看来,这河心岛很可能也是沈家的,自己未经沈老爷允许,便在河心岛上搭起草棚扯起网绳,于情于理,显然都说不过去。为了弥补过失,汪福赶忙扔了手中的捕鱼工具,将一对刚刚捉到的莲花鱼抱在怀里,膛水送过河岸,塞到沈老爷的马车上,还一边作揖一边说着小话:“托沈老爷的福,小民汪福,在此混口饭吃。”
一个送鱼的举动,一句告饶的话,让汪福的卑微,一下子灵动起来。而在沈老爷那边,先是支吾了一声,好像没当回事,后是看着惊慌惊恐的汪福,又居高临下地,施舍般地说了一句:“那个小岛,送给你啦!”这漫不经心的一句,让河心岛的“主权”有了不言而喻的意味,并由此换来汪福对沈家持续多年的感恩戴德。沈老爷的城府,可谓深不可测。
汪福感恩戴德的表达方式,是不断给汪家奉送农产品,各种新鲜菜蔬、鱼虾、鸭蛋鹅蛋,按不同季节,源源不断地送去。
情节走到这一阶段,沈家大太太就该出场了。
沈家的窗明几净和大太太的一身绸缎,让汪福的卑微又一次灵动起来。他蹲在沈家的餐厅外边,听大太太问话。沈家小丫鬟礼节性搬来的那把亮锃锃的小椅子,他“没敢坐”。
有了这第一次,自然而然就有了后边的很多次。汪福再到沈家,“先把青菜、鱼虾啥的送到后厨去,再到大太太这边来道安”,且“始终蹲在门外”,不坐那把小椅子。
作为道具,这把小椅子太重要了。
后来,“说不清是哪一天”,汪福听大太太问话时,竟一时忘形坐到那把小椅子上了。
此举在大太太看来,完全是颠覆性的举动,等于是对现有等级秩序的挑战,于是她喊来管家,说:“去把汪福开垦的那块荒岛收回来吧,省得他以后再往这边跑了。”大太太在作品中只说过这一句完整的话,但只这一句,就把人物性格在刹那间凸现得棱角分明。
大太太的这句话,客观上,还拥有一箭双雕的妙用,既疏解了心中的愤愤之气,同时也将原本不知归属的被汪福拾掇得有模有样的湖心岛,收归己有了。其心地之阴之恶,让老侯不知如何措辞才好。
《看座》曾经获得《小说选刊》2016至2017年度双年奖,颁奖词里说,汪福的卑微低下和小心翼翼,“深刻而生动地展现了旧时代的社会现实和阶级形态”,而汪福丰富的内心活动,也让小说“充满戏剧化的张力”。老侯对此没有异议,不过老侯最看重的,还是作品中的三个活人。
在老侯看来,老相的《看座》比他的《威风》还要威风。
《银凤》描述了一个下等人的命运。大盐东吴老爷的二姨太死了,二姨太的丫鬟银凤,被大太太许给了捡煤渣的阿贵。银凤不忘旧情,时常将自家产的瓜果蔬菜,让阿贵给吴家送去。有时银凤也亲自到吴家去,尤其是二姨太的祭日,她是非去不可。每次去吴家,银凤都打扮成“贵妇人”的样子,“很体面地叫一辆黄包车”。但每次回程时,黄包车一出城门,她便下车步行。二姨太三周年祭日那天,很不幸,在步行回家的路上,银凤被日本人的货车给轧死了。这篇作品用五个细节——打扮成贵妇人,叫黄包车,出城后下车步行,丝绸手套,指甲里的乌黑炭泥,共同构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叫人欲哭无泪,欲说还休。
我确信《头柜》中的大先生德昌就活在我们身边。活在老侯身边,活在老相身边,也活在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身边。那是一个不学却有术的人,坐诊把脉不行,媚上欺下却无所不通,栽赃诬陷更是强项。此文最让老侯心动的一个细节是,黑夜里,德昌一个人在吴家大院行走,脸上也挂着微笑,他是担心突然遇到什么人,来不及摆布表情。一个人把心机用到如此程度,事随人愿也就不在话下了。
与上面提到的三篇作品类似,《换画》中的郝逸之、《夜宴》中的吴家大太太、《赌客》中的安虎和陈麻六、《奴才》中的大成、《墨杀》中的刘顺昌、《断仇》中的张康,在老侯眼里,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讓盐河旧事有了别样的鲜艳和别样的妩媚。
此外我还觉得,盐河旧事的体量,完全够得上一部很厚的长篇小说,是老相别有用心地将它捣成了碎片。这种碎片化叙事,是当下这个快节奏时代最接地气的写作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最被青少年阅读群体所青睐的写作方式之一。
(侯德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寂寞的书》《那时候我们长尾巴》等专著、文集十五部,获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等多种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