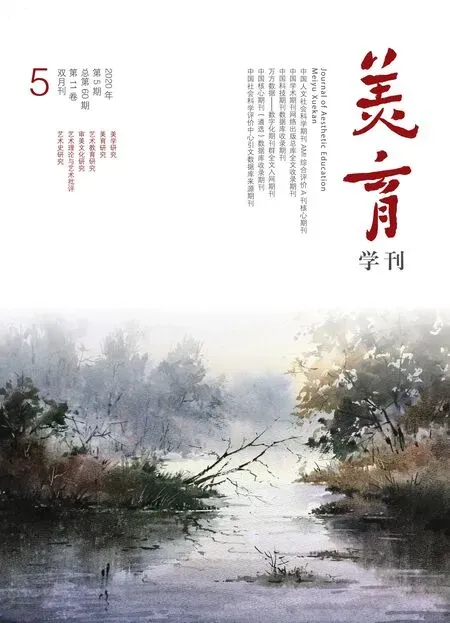苏辙“人情说”的审美理想建构
2020-12-11黄瑞
黄 瑞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所谓审美理想,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根据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习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关于美的看法,所体现的是审美主体或者时代的审美需求。顺着这一思路,本文拟以“人情说”为切入点,探讨苏辙构建的审美理想世界。
一、审美理想的核心:人情为美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曾言:“华夏艺术和美学是‘乐’的传统,是以直接塑造、陶冶、建造人化的情感为目标。”“华夏文艺及美学既不是‘再现’,也不是‘表现’,而是‘陶冶性情’,即塑造情感。”[1]也就是说华夏审美文化是一种情感体验型文化。这在“礼乐”和“诗”中是得到阐发的。
历史文献中,有关“情”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论语·子张》:“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2]《尚书·诰康》有“民情大可见”[3],《礼记·礼运》载:“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4]《左传·庄公十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5]这里的“情”有事实和情感的意思。其实,在先秦时期,一般对“情”的讨论,常常与“性”联系在一起。《荀子·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6]《毛诗序》有“吟咏情性”的说法。这种现象,徐复观认为:“情与性,是同质而常常可以互用的两个名词。”[7]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8]将“情”“性”与“道”相联系,具有本根性的意义。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曰:“人之情性,共禀于天,天不差忒,则人亦有常。”[9]亦将“情性”的根源归于“天”,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道”和“气”。这些论说无疑为苏辙“人情说”的审美理想奠定了基础。
宋儒对“情性”的关注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欧阳修曰:“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10]王安石说:“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又:“圣人之为道也,人情而已矣”。[11]苏轼提出:“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12]程颢曾言:“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13]这种较为自觉的观点,标榜圣人之言,是宋代儒学复兴的体现,也使心性理论成为一种时尚。
苏辙亦多次谈论“情性”问题,不过其所谈论多名以“人情”。苏辙云:“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14]又说:“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15]1020探讨了道与人情以及礼与人情之间的关系。六经所载之道,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下来,是因为道与人情相近,而礼是顺着人情而制定的,才会人情安,天意顺。换言之,在形而下的层面上,道和人情是相近的,而礼是作为中间的桥梁。考虑到苏氏兄弟学术思想的相似性,我们从《东坡易传》(1)据《栾城遗言》记载,《东坡易传》为三苏合撰,其学术思想应具有一致性,可作为参考。中也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曰:“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辩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2)焦竑:《两苏经解·东坡易传(卷一)》,明万历二十五年毕氏刻本。将情、性和命置于同一层面加以论述,也使得“情”具有了情本论的意义,自然也具有审美的意蕴。
具体看来,苏辙的“人情为美”,主要包含主体之情和生活之趣两个方面。
首先是主体之情。苏辙将“人情”与“道”“性”等范畴相提并论,这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苏辙在《诗集传》中阐述道:
诗之所为作者,发于思虑之不能自已,而无与乎王泽之存亡也。……天下未尝一日无诗,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先王之泽尚存,而民之邪心未胜,则犹取焉以为变诗。及其邪心大行,而礼义日远,则诗淫而无度,不可复取。故《诗》止于陈灵,而非天下之无诗也,有诗而不可以训焉耳。(3)苏辙:《诗集传》(卷七),引文据宋公使库本。
这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解释诗歌创作起源于人情,是诗人思虑情感迸发不能自已的结果,无关乎王泽教化,完全是“吟咏情性”的表现。
《春秋集解》中,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将帅诸侯以尊事天子,而不敢合诸侯于京师,故召王于河阳,而以诸侯见。其情则顺,其礼则逆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然而其情不可不察也,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使若巡狩然,尊周,且以全晋也,故为王讳之而足矣”[16]70。苏辙从礼和情的角度诠释“天王狩于河阳”,认为晋文公率领诸侯去朝见周王,本准备在京师觐见但又害怕惊扰了天子,于是让天子在河阳召见诸侯。而“召”是上对下说的,这里晋文公“召王于河阳”,是不符合礼法的,但是于人情则是合理的。而“天王狩于河阳”,既照顾到君臣之间的礼制,又能体现晋文公等人的尊王之心。这确实使得注解简洁且符合常理。苏辙以人情解经,其看重的虽是《春秋》“推王法以绳不义”[16]147的教化意义,归根结底仍是胸怀天下,完善人的心性,做一个精神自由的人,回到有温情的社会。
在《老子解》中,苏辙亦言:
夫欲先而恶后,欲明而恶暗,欲贵而恶贱,物之情也。[17]432
忠信而无礼则忠信不见,礼立而忠信之美发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间,夫妇朋友之间,其外灿然,而中无余矣。[17]443
盖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爱恶之情忘,则虽报怨犹报德也。[17]465
这些仍是在强调“人情”理想。“欲先而恶后,欲明而恶暗,欲贵而恶贱”,这本是一种人情物性,似乎不应该加以评价,但是,苏辙认为假如我们忘却“爱恶之情”,以德报怨,这样一来,按照人情所制定的礼法,能够使忠信这样的美好品德呈现出它的光芒,世间的伦理秩序也就得到匡扶,人性人情也是愈发自然。
其次,人情之美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趣味之中。这种趣味,很多表现在民俗生活与风土人情方面。如苏辙《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踏青》:
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桥没水不胜重,野店压糟无复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鸟渐嘤鸣。洞门泉脉龙睛动,观里丹池鸭舌生。山下瓶罂沾稚孺,峰头鼓乐聚簪缨。缟裙红袂临江影,青盖骅骝踏石声。晓去争先心荡漾,莫归夸后醉纵横。最怜人散西轩静,暖暖斜阳著树明。
苏辙对踏青风俗作了较为全面的描绘:春回大地,冰雪消融,草长莺飞,三五好友相约踏青游玩。有含苞待放的寒花,渐渐嘤鸣的幽鸟,也有临江倒映在水中的倩影,人们满怀喜悦之情,开怀畅饮,喝醉了酒,晃荡着回到家中。最让人难忘的则是人散去之后,静静的西轩,一抹斜阳挂在树梢,由喧闹趋于宁静。对踏青的风俗描写由景及情,由外入里,若是没有对生活的审美体验,这样的情感还会这样深刻吗?
再如《蚕市》:
枯桑舒牙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随手败,今冬衣着及春营。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筐供妇女,亦有姐博资男耕。空巷无人斗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异方不见古风俗,但向陌上闻吹笙。
在苏辙眼中,故乡风俗纯朴,人与人关系融洽,人与人之间热情相待,完全一副祥和之态。对“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的风俗能够保存至今更是充满了自豪。关于生活之趣的描写,在苏辙的诗歌中还有很多,如《次韵文务光秀才游南湖》这类的闲适诗,《竹枝歌》这样的乐府名曲等。
总而言之,苏辙的“人情说”的审美理想,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它从现实出发,力求将“情”与“道”和“气”相联系,使这种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形式具有丰富的本体论美学思想的气息,也使得这一审美理想核心也成为苏辙整个美学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审美理想的机制:复性归道
以“人情为美”为基础,苏辙将“人情”与“情性”联系起来。如前所述,苏辙的“性”的概念也是属于本体的层面,这与《性自命出》篇的论述极其相似,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强调“人情为美”,其核心的理解自然离不开“性”。
有关“性”的论述,苏辙云:
视色、听音、尝味,其皆出于本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缘五色、耳缘五音、口缘五味,夺于所缘而忘其本,则虽见而实盲,虽闻而实聋,虽尝而实爽也。[17]412
朴,性也。道常无名,则性亦不可名矣。[17]436
视之而见者色也,所以见色者不可见也。听之而闻者声也,所以闻声者不可闻也。抟之而得者触也,所以得触者不可得也。此三者,虽有智者莫能诘也,要必混而归于一而后可耳。所谓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与物搆,然后分裂四出,为视、为听、为触,日用而不知。[17]414
人的视觉、听觉和味觉,这些都是本来就有的,是不可以言说的,只是后来有了可以依赖的条件,才开始分裂四处,人们日用而不知,但也因此丧失了其原来的本性。
苏辙进一步解释了“性”的特点,曰:
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损,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玉,凡物莫能患也。[17]413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盖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劳而成之矣。[17]451
性无生死,出则为生,入则为死。[17]453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谓大威也。[17]473
性之大,可以包络天地。[17]473
性之为体,充遍宇宙,无远近古今之异。古之圣人,其所以不出户牖而无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内为身心之所纷乱,外为山河之所障塞。见不出视,闻不出听,户牖之微,能蔽而绝之。不知圣人复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弥远而弥少也。[17]451
苏辙所言之“性”的特点就是“纯朴”,是独立于个体的人,不受生死限制,它又是现实存在的,存在于宇宙之中,天地之间,坦然无所惧。这样一来,关于“性”的认知,即跟“道”一样是本体的存在,只是它的着眼点在于从“人道”——主体的人的视域来观照,所以苏辙又曰:“性之妙,见于起居饮食之间耳。”[17]443我们也只能通过日常起居饮食的表现才能体会到“性”的奇妙。日常起居的“性之妙”可以言说,而“性”作为本体意义的存在是不可言说的,这就又形成了一对矛盾,为了解决“可道”与“不可道”之间的矛盾,苏辙曰:
道无形也,及其运而为德,则有容也。故德者道之见,自是推之,则众有之容,皆道之见于物也。[17]425
道非有无,故以恍惚言之,然极其运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17]425
作乐设饵,以待来者,岂不足以止过客哉!然而乐阕饵尽,彼将舍之而去。若夫执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而况得而恶之乎?虽无臭味、形色、声音以悦人,而其用不可尽矣。[17]439
苏辙将“道”与“德”“容”“象”相联系,找到一个中介。“道”通过运动,进而显现为具体的“象”,而这可以帮助人们去把握“道”这个抽象的东西,去解决这个矛盾,也使得这个审美机制能够运转开来。此外,苏辙还提到“言”与“道”的矛盾,曰: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尽,则听言而足矣;可以事见,则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尽,事不能见,非舍言而求其宗,遗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盖古之圣人,无思无为,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则思虑之不及,是以终莫吾知也。[17]472
对于“道”的理解(也是对美的理解),苏辙并没有采取直接的言说,而是深刻认识到其中的矛盾,转而借助“言”“象”的中介作用,进而认识“道”,也正因为是这个矛盾,“恰好指向无限丰富的感性空间,它与同样指向无限丰富的感性空间的审美活动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18],这也就避开了传统心性论关于价值偏好的讨论,转向更深层次的审美想象,为审美范畴的转向提供了内在可能。
在具体的操作中,“古之圣人”“古之君子”为苏辙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这一类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思无为”,他们的心境是澄明的,故而能接近审美超越的境界。而在实际生活中,苏辙感慨道:
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为见,爱身之情笃,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疾之变攻之于内,宠辱得失之交撄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达人之性之无坏,而身之非实,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尽去,然后可以涉世而无累矣。[17]413
现实中,人们沉迷于身体的欲望,内心又被生死疾病所忧,被宠辱得失所控制,迷失了人的本性,为外物所累,是心中存在执念,苏辙将其称之为“妄”。只有去妄,才能复归本性,不为外物所累:
夫惟圣人知万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画牛马,如刻虎彘,皆非其实,泯焉无是非同异之辨,孰知其相去几何哉!苟如此矣,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足怪矣。[17]423
圣人与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为常,驰骛于争夺之场,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圣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复性,待其妄尽而性复,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责之而自服也。然则虽有大怨怼,将涣然冰释。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无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则亦老而无功矣。[17]478-479
圣人和人一样都是出于“性”,也都会为妄念所执。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其“去妄复性”,回归婴儿般的纯朴之性。而这纯朴之性与道是合一的,圣人据此可以察觉万物之理。所以“古之圣人,去妄以求复性,其性愈明,则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则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则其归愈大”[17]432。圣人坚守本然之性,所以内外圣明,本性一也。凡人若是能依此而行,自然也是能够复归纯朴之性,体察至简人格之美。苏辙借用《易传》来说明具体的实践方法:
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则不可言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圣人之学道,必始于穷理,中于尽性,终于复命。仁义礼乐,圣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义礼乐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后行之,君子也。此之谓穷理。虽然,尽心必穷理而后得之,不求则不得也。事物日构于前,必求而后能应,则其为力也劳,而其为功也少。圣人外不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免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应,此之谓尽性。虽然,此吾性也,犹有物我之辨焉,则几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谓复命。[17]417-418
苏辙以“命者,性之妙也”将《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与老子的“复命”之说相联系,其实质是用儒家的“复性”置换道家的“复命”。对于“去妄”,苏辙所用的办法是“损”,曰:“去妄以求复性,是谓之损。”[17]452所谓“损”就是从具体事物出发去把握道,这也是主体把握本体的一个重要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悟的办法:“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复性,则此三者,人皆足以尽之矣。”[17]430这是一种近似于禅宗的顿悟的方法,“一日复性”是直接的内心的体悟,也是直接体验本体的重要方式。苏辙又说:“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则得之矣。道无功罪,人患不知,知则凡罪不能污也。”[17]465道本身存在人这个主体之上,并且道本身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只是主体不去追求,不了解。这就又回归到主体的人本身,进一步说就是“心”。苏辙认为“性”存在于心,“妄”生于心,曰:
明白四达,心也,是心无所不知,然而未尝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则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镜之于物,来而应之则以,又安得知而应物者乎?本则无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17]411
道无形体,物莫得而见之也,况可得而伤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后有形,有形而后有敌,敌立而伤之者至矣。无心之人,物无与敌者,而曷由伤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无心也。[17]458
人们对“妄”的执念,还是认为万物是真实的存在,只是认识不到它的本然之性。只要破除执念,人之本性是可以恢复的。在此基础上,苏辙提出“心”的概念,认为有心的存在,人才有形的存在,进而才有了对立面,会受到伤害。若是能做到“忘心”,做到物我两忘,就能做到道性合一,真正实现“复性”。相较于“忘身”的“去妄”,“忘心”则是“无思”。苏辙曰:“心之用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及其至也,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于无思,则复于性矣。复于性,则出于五事之表,此圣人所以参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圣。”[15]1227-1228其实,这种“去妄”和“无思”的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的“坐忘”和“心斋”。苏辙这里是采用“夺胎换骨”的笔法,将儒道两家的义理作了勾连,其目的还是复归于性,道性合一,从而达到最高的修养境界,进而进入审美超越的领域,积极地追求美之理想。
三、审美理想的标准:不离仁义
虽然北宋时期疑经之风盛行,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和美的表达方式呈现极大的包容性,苏辙在这场运动中也是敢为人先,大有离经叛道之意,但是事实上,苏辙是主张“《诗》要入于仁义”,其《诗论》曰:“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14]1273又曰:“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由此,其“人情”之说,自然亦离不开“仁义”,换言之,就是将“仁义”注入“人情”。《论语拾遗》载:
巧言令色,世之所说也;刚毅木讷,世之所恶也。恶之,斯以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无求于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为是者,将以济其不仁尔。故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15]1216
不仁而久约则怨而思乱,久乐则骄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然则何所处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则不仁者约而不怨,乐而不骄。[15]1218
仁者无所不爱。人之至于无所不爱也,其蔽尽矣。有蔽者必有所爱。无蔽者无所不爱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以其无蔽也。夫然犹有恶也,无所不爱,则无所恶矣。故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其于不仁也,哀之而已。[15]1218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人而至于不仁,则物有至于害也。“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非不违仁也,外物之害既尽,性一而不杂,未尝不仁也。[15]1218
以上材料,大致可以概括为:仁者直道而行,不会有谄媚的言行举止,外表看起来难以亲近,而内心温润仁厚;让不仁的人长久处于节俭的状态,容易心生怨念而想作乱,让他长久处于快乐的境地,则会产生骄纵而忘记忧患,只有将仁者置于他们中间起模范作用,才会使他们改善。因为仁者爱人,去除蒙蔽心性的障碍,内心坦荡,如水之清澈,火之明亮,通透无蔽,不为外物所妨害,内心无喜恶,对于不仁的人,也只是哀叹而已。由此观之,苏辙的意思是强调仁者“反求诸己”的内在修养,加强自我修身,摒弃利害纠缠,从而走向一种淡泊名利的审美化的人生。
又,《孟子解》中曰:
梁惠王问利国于孟子。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王之所以为其国,未有非利也。孟子则有为言之耳,曰“是不然”。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为利也。惟不为利,故利存。小人以为不求则弗获也,故求利而民争,民争则反以失之。[15]948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反求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审操之,的虽在左右上下,无不中者矣。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居于人上,而一为非礼,则害之及于物者众矣!诚必由礼,虽不为仁,而仁不可胜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谓也。[15]951
苏辙认为,圣人亲身实践仁义而利益得到保存,其主观上并不是去牟利。而普通人去争夺利益往往却丧失其利益。仁者时刻保持自己的操守言行,使其符合礼的规范,这样一来,社会变得井然有序,趋向于仁的境界。而仁者居于普通人之上,一旦其行为举止不符合礼的规范,就会影响到普通大众。所以通过礼来规范其行为,由礼致诚,即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仁的功效也显现出来了。换句话说,礼是通向仁境界的一种手段,也是达到仁境界的一个表现。而“礼沿人情”,礼与人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人情不离于仁义”亦是自然而然。
此外,《老子解》中亦说: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后可常耳。今夫仁、义、礼、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为义,而礼不可以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后在仁为仁,在义为义,礼、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变,不可道之能常如此。[17]401
苏辙此论是将“仁义”与“道”相联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他的立足点在“人道”,因此对苏辙来说,以“情”或曰“情性”“人情”为出发点的论诗、论文,认为其出于斯又表现于斯,一是为他的“人情为美”的理论张本,还有一个现实目的不容忽视,就是文艺的审美教化功能,苏辙曰:
良医之视人也,察其脉而知其人之终身疾痛寿夭之数。其不知者,以为妄言也;其知者,以为犹视其面颜也。夫国之有诗,犹人之有脉也。其长短缓急之候,于是焉在矣。(4)苏辙:《诗集传》(卷一),引文据宋公使库本。
苏辙认为,一国之诗,正如一个人的脉象,反映国家兴衰和民生疾苦。这与苏辙家学有着莫大联系,苏氏蜀学重经世致用,追录圣贤之遗意,言必中当世之过,偏重外王之学。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辙为什么一直强调礼制,在儒家看来,礼乐制度依据人情而设置,并可以反过来陶冶人的性情,彰显圣人教化之功。进一步说,苏辙的“人情为美”是将儒家的审美教化融入其中并付诸实践的。如,苏辙对杜诗评价颇高,在《和张安道读杜集》中,他说:
杜叟诗篇在,唐人气力豪。近时无沈、宋,前辈蔑曹、刘。天骥精神稳,层台结构牢。龙腾非有迹,鲸转自生涛。浩荡来何极,雍容去若遨。坛高真命将,毳乱始知髦。白也空无敌,微之岂少褒。论文开锦绣,赋命委蓬蒿。初试中书日,旋闻鄜畤逃。妻孥隔豺虎,关辅暗旌旄。入蜀营三径,浮江寄一艘。投人惭下舍,爱酒类东皋。漂泊终浮梗,迂疏独钓鳌。误身空有赋,掩胫惜无袍。卷轴今何益,零丁昔未遭。[19]
这里苏辙是化用了元稹对杜诗的评价,综括了杜甫艰难的一生,肯定了杜甫的诗歌成就。在《诗病五事》中,对李白则是较为苛刻。他说: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酒奉明皇,遇馋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汉高帝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岂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发于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诗反之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老杜赠白诗有“细论文”之句,谓此类也哉。
苏辙批评李白主要是从其性格和个性等方面,认为李白喜好声名,华而不实,不能理解义理的真正内涵,性格上又好勇逞强。当然,苏辙的批评可能有失偏颇,但是我们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似乎并不困难,苏辙的这种评价一方面是自己处于宋人学杜甫的巅峰时期,自然难以置身事外,对质朴之气的追求,是整个宋代学术的一个缩影;还有就是他自己的性格特点趋向沉静,与李白的豪放浪漫相左,与杜甫的沉郁之气相合。进一步说,杜甫的诗歌创作契合了他的审美理想,顺乎人情,不离仁义,忠君爱国。苏辙崇杜抑李,“不能说苏辙的文学修养不高,或者说没有鉴赏力,而是应该认为,他所在的这个时代,审美标准真的变了”[20]。
“人情说”是苏辙论文论诗的出发点,也是他审美理想的精要表达。面对时代的新风尚,苏辙自我定位,顺应时代的疑经风气,指出释道两家思想的精华,以疑经来证经,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开辟新的视野,挣脱了前人或者时人僵化的思维束缚,追求美的理想,构建起“人情为美”“不离仁义”“复性归道”的审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