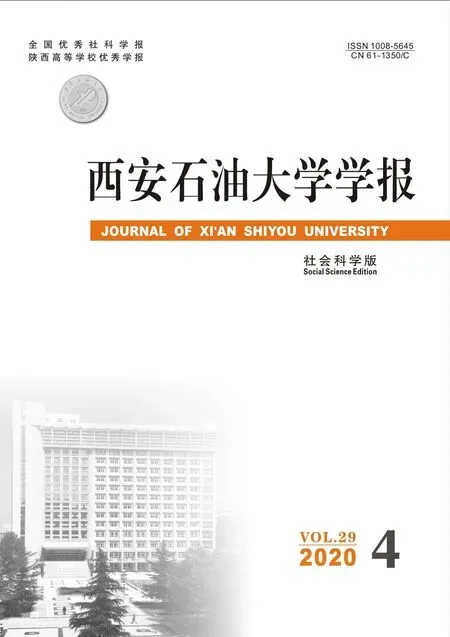温故而知新:伽达默尔诠释学理解的历史性要义
2020-12-10韩苏桐
韩苏桐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0 引 言
“温故而知新”出自《论语·为政》。目前人们对它的解释有四种:一是温习旧的知识,从中获取新的知识;二是既要温习旧的知识,同时又要学习新的知识;三是随着人年龄的增大和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对以往学习过的知识有了更深的体会;四是通过回味历史,人们可以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伽达默尔作为哲学诠释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解的历史性是其哲学诠释学的精华。那么,“温故而知新”为何会成为伽达默尔诠释学理解的历史性要义?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明了“温故而知新”与理解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即探究“温故”与传统和历史的理解、人的现实生命诉求与“知新”以及“温故而知新”与诠释学循环之间的关系。
1 温故:传统与历史地理解
人们对“温故而知新”的四种解释包含着时间上的先后,也就是历史和当代、传统与现在。“温故”的“故”字所表现的是过去的一切的总和,也就是历史和传统。“温”字则表现了人对历史和传统的回味,同时,它也隐含了人的立足点:现在。“温故”就是人立足于现在自觉地回味传统、回味历史。它表明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人能回味传统、回味历史而不能回到历史;二是人以现在为立足点回味传统、回味历史,他的回味有着当代的鲜明特征也就是独特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由历史与当代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赋予,也就是某一社会历史阶段与人融合的结果,而人回味传统和历史的落脚点仍然是现在。相应地,“温故”透露出两种向度:一是历史向度;一是现实向度。这两种向度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理解的历史性中同样存在。伽达默尔将历史向度表述为传统的、历史的存在,将现实向度表述为当下的理解,认为人只要有所理解,就是在运用传统、运用历史。这与孔子所讲的“温故”不谋而合。
首先,人对传统的自觉融合彰显了“温故”。人对传统的融合并不表现为人被动地接受传统的灌输,而是表现为人自发、自觉地融合着传统。对此,伽达默尔讲道:“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Anverwandlung)。”[1]364在伽达默尔看来,人的理解活动先在地受到传统的影响,人们从来都不曾远离和摆脱传统,而是经常处于传统之中并自觉融合、运用着传统。人只要有所理解,就是在自觉运用其所吸收到的传统在理解,人与传统之间的融合因人的理解活动而无法割舍,具有持存性并伴随人生命的始终。对此,伽达默尔以现代历史研究为例继续讲道:“现代的历史研究本身不仅是研究,而且是传统的传递。”[1]367在他看来,“传统的传递”并不仅仅指在研究过程中,各个研究者被历史流传物所揭示出的自身的传统意识,它同时也指向被研究者的传统意识所理解到的历史流传物本身所具有的传统。这种传统因被研究者自身的传统意识所理解而被人意识到。人意识到传统也就自觉与传统进行着融合,它乃是由人开放的理解结构所决定。
但是,人对传统的自觉融合并不是将人完全地置身于过去、以传统消解人的现在,相反,当代作为历史的延续,传统以适合当代人的方式存在于当代,当代仍然是人所生存的时代。这就是说,人要想在当代存活,必须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入当代的传统相融合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而人对传统的融合使得当代人从出生起就已经被烙上了传统的印迹。因此,人对传统的自觉融合使人拥有独特的历史性,人只能存活于当代而不能置身于过去。人对传统的自觉融合过程及其特点与人们对“温故”的解释所表现出的“两方面内容”相吻合。从这一点来讲,伽达默尔所说的“人经常处于传统之中并单纯地吸收、融合着传统”彰显了孔子的“温故”。
其次,人对传统的自觉融合产生“历史地理解”。“历史地理解”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性。关于“历史性”,伽达默尔认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1]383,“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1]387在伽达默尔看来,当人运用自己的历史思维理解历史流传物时,人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由人所存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带有这一社会历史阶段的鲜明特征,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赋予人不同的历史性。因而,人的理解活动受制于社会历史环境。但是,社会历史环境不是凭空出现的。伽达默尔认为社会历史环境与传统密不可分。当代作为历史的延续,传统以中介的形式流变于过去与现在,组成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人于社会历史环境中存在就是于传统中存在。人与适合当代人的传统的自觉融合产生了由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人的历史性。
人的历史性一旦产生,他所进行的理解活动就是历史地理解活动。“历史地理解活动”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人的历史性存在和传统的融合是理解得以发生的基础。[2]605-618历史性的本质是传统的流变,人的理解充分显现了与他相融合的传统的特征与教化;第二,历史流传物充当某种介质使人的历史性凸显出来。伽达默尔认为,当人接触历史流传物时,他就是在与历史流传物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人的历史性或与人融合了的传统的某些属性就被历史流传物激发出来。这样,与其说人在理解历史流传物,不如说历史流传物充当了某种中介或诱因,使人的历史性或某些传统因素被凸显出来,呈现出现在与历史的碰撞;第三,人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只是人自身的历史性或某些传统因素的张扬与显现,他所理解到的东西不是流传物本身的全部内容,而是传统所教导的东西。
这三方面内容乃是人与传统相融合的人的历史性理解的产物,而人与传统的融合又彰显了“温故”,所以人的历史地理解也就由“温故”产生。事实上,“温故”所表达的人立足于现在回味历史、回味传统恰好表现了历史与当代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没有“当代”就谈不上“温”,没有“历史”和“传统”就谈不上温“故”。历史与当代的连续性使传统一直活动于时间之中,传统从历史流淌至现在而奔向未来。
那么,人为什么“温故”呢?或者说,人在自觉融合传统之后所产生的历史地理解的作用是什么呢?
2 现实生命诉求与“知新”
在孔子看来,“温故”能够“知新”。“温故而知新”是人立足于当下回味历史、回味传统,最终又返回到当下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温故”与“知新”同时隐含了理解与人的当下生命的联系。冯梦龙在《论语指月》中评“温故”时写道:“‘温’字最妙,忘却冷,助则热,惟‘温’乃是一团和气;千红万紫,都向这里酝酿出来。”[3]21千红万紫于“温”中酝酿,即是表现了“温故”所带来的蓬勃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与人的现实生命诉求息息相关:人总是因为自我在当下的现实生命诉求要求“温故”、要求“知新”。“温故”的结果就是“知新”,它表明人受到历史与传统的启发已经回答好自我在当下的现实生命诉求问题,并且在当下获得了新的存在。相应地,人的历史地理解所要解答的也是人的现实生命诉求问题。
首先,当下处境促使人以自我理解的方式表达人的现实生命诉求。人的自我处境往往引发人对现实生命的诉求。关于处境,伽达默尔认为处境包含了人的视域。伽达默尔指出:“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1]391在伽达默尔看来,处境包含了人的立足点及其所能看到的一切,人立足于处境就是与当下构成交织,这种交织总是蕴含了人对自己所看到的文本的思考和提问。而人对当下处境中自我存在的疑问表现了人的现实生命诉求。这种诉求促使人寻求某种方式回答好人在当下的自我存在问题。这种方式就是理解。伽达默尔指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1]383伽达默尔认为,人的理解总是与其所存活的时代息息相关,在此时代中,理解既是与人相融合的传统的产物,同时,人也被历史流传物所吸引,试图在历史流传物中理解自身,人试图理解自身就是表明人寻找自我在当下的生命价值。但是,人以时代的方式进行理解并不是说人必须拥有着相同的理解,而是指人的理解活动无法逾越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在社会历史阶段之下,伽达默尔更强调人的自我理解。“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1]383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理解并不能被统一或被规范,人因自己的当下处境进行自我理解,他的理解就是自我在当下的生命解答与关怀。不同的历史时代造就不同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有什么样的理解。因而,不同生活经历与生活状态的人,就以不同的理解回答了各自的生命诉求,其中包括“极端的方式”——批判、反思时代——来回答自我甚至是他者在当下的存在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伽达默尔认为人的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在他看来,不同的理解彰显了个人独特的生命历程和现下处境,它表明不同人的理解与某个人在生命不同阶段下的理解没有优越性之分,因为人的生命无优越性之分。理解作为解答人的自我存在问题的方式,它较之之前的理解总是表现了人在当下的遭遇与思考,并带来之后的生命预期。换言之,人在理解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塑造。[4]50-65因而,人的自我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它创造的就是人在当下的生命解答与未来的“生命延续”。
但是,人的一生中总处于各种各样的处境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生命诉求,这也造成了理解的多样性与相对性。那么,在多种理解之中,人的现实生命诉求是随着理解不断波动,还是在被解答之后拥有着长期的稳定?这就与伽达默尔提出的“文本意义”相关联。
其次,文本意义作为理解的结果,它回答了人的现实生命诉求,并成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走向的“引领者”。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总是使人理解到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文本意义。“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1]383从人的处境而来的理解,它的结果或者表现形式就是它所创生出的文本意义,文本与处境的联结表明文本意义与人的现实生命诉求相联结,即“文本具有的意义是它在我的具体情况里为我而有的意义。”[5]116因此,文本意义作为理解的结果,它回答了人的现实生命诉求,使人的生命有了合理的寄居之所。它相当于引领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又或者,它是人内心某种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准则。人接受自己所领悟的意义就处在意义的引领之下,而人的其它生命诉求也围绕着相对稳定的意义而展开。
文本意义的产生,突破了人在此前的生命阶段并在之后一段时期内引领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走向,使人进入到一种新的生命阶段中,是人的自我生成活动的展现。[6]36-40这就与孔子的“知新”所表达的意思相符合。因此,“知新”源于人的现实生命诉求,同样也是为了解答人的现实生命诉求。
3 “温故而知新”与诠释学循环
人借助传统和历史回答人的现实生命诉求的过程彰显了“温故”与“知新”的循环:人对文本的理解由当下处境中的事情引发,由与人相融合的传统予以回答,所以“温故”与“知新”的循环是历史与现在的循环;当下事情引发理解,却由传统回答问题,这表明人借助部分历史经验解决当下困境,所以“温故”与“知新”的循环是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处境与人的存在状态及其生命诉求相联结,多种处境引发多样理解,人走向未来的过程就是人在理解中生命体验得以上升的过程,所以“温故”与“知新”的循环是生命体验的循环。这三种循环形式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中同样存在。
首先,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是理解与前理解的循环,也就是历史与现在的循环。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理解都包含着某种前理解,人的理解活动经历着理解与前理解的循环。他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描述这种循环:“对本文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1]379前理解的先行把握使理解拥有了某种预期,人只要有所理解就是在前理解的规定下理解。但是,前理解之于人的理解永远是变动的,这种变动与事情相关联。“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1]380-381人对事情的理解总能从前理解中得到相似的经验,它说明之前的理解有着与此相同或相似的事情。[7]286-303当人完成了理解活动,它就成为前理解而进入历史中,并产生理解经验。那么,当人被某些相似的事情触发了理解,之前的理解经验就作为前理解应用于当下的理解中。这样,理解与前理解、历史与现在就构成了诠释学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理解与前理解的循环始终与事情本身和人的处境相牵扯。它表明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事情参与进理解活动中,理解与前理解才能真正构成一种诠释学循环。人的理解固然是从前理解而来,但理解却是由事情触发。此事情与形成前理解的事情相关联。这就是说,没有与之前的事情相关联的事情发生,前理解就不会应用于当下的理解中,当下的理解就不会形成。二是引起人的理解活动的事情总是被包含在不同的处境中,处境规定了事情只能相似而不能相同。事情只有相似,由事情而来的理解才不会完全地复制前理解,理解才会是一种创造性地理解。从这一点来讲,理解与前理解、历史与现在的循环不是一种封闭的圆圈式的循环,而是开放的螺旋上升式的循环。
其次,前理解与理解的循环表现了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在理解和前理解、历史和现在的循环中,由于当下的事情与引发前理解的事情有所关联,当下理解才会形成,所以,人的当下理解表现为部分,它表明人正在进行某种陌生却又熟悉的活动。[8]19-35这种感觉正是前理解应用于当下理解活动的结果。从这一点来讲,前理解在理解活动中担负着整体这一角色,前理解之于当下的理解就是整体之于部分。但是,理解是一种历时性活动。当下的理解活动结束后,它作为部分的身份就消失掉而成为了整体,也就是成为了前理解。当人进行之后的理解活动时,将来的理解就成为部分。这样,人的理解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整体与部分的循环,更进一步讲,在历时性之下,某一时刻的理解活动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
最后,历史与现在、整体与部分的循环中又包含人的生命体验的循环。由于事情总是被包含在处境中,处境则与人的当下生活状态及其现实生命诉求相关联,所以,不同的处境和事情引发的理解表明人的生命体验进行着一种循环。这种循环由历史与现在、整体与部分的循环所表露。在历史与现在的循环中,相似的事情触发了理解和前理解的循环:前理解活动是过去某个时间点的人以理解的方式表达其现实生命诉求的活动;当下的理解活动则是人在当下以理解的方式表达其现实生命诉求的活动。当前理解应用于当下的理解,人不仅能学习到之前的经验,而且能唤起之前的关于事情的记忆、体验当时的情境。因而,理解的过程就是人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9]35-39,也就是生命体验的循环。
在人的生命体验的循环过程中,人的当下生命与他过去的生命发生了融合。伽达默尔认为:“我们的历史意识所指向的我们自己的和异己的过去一起构成了这个运动着的视域,人类生命总是得自这个运动着的视域。”[1]394“异己的过去”是相对于此时此刻的人而言,它并不排斥某个人的过去,相反,它包含着过去的一切。所以,人的当下与他的过去永远进行着生命的融合,融合的结果就是人突破了当下的生命桎梏却又包容着以往的生命。而人的当下生命也只有与他在过去的生命进行融合,才能沿着过去生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另外,“温故”与“知新”的循环表明了历史经验的往复过程:人为了“知新”而“温故”,借助部分历史经验回答现实生命诉求,而“新”在时间的磨砺下又成为“故”的一部分并继续应用于之后的“知新”中,所以,“新”与“故”同时被包含在人类经验中,“温”与“知”就是人自觉地应用历史经验的过程。朱熹曾对“温故而知新”进行如下解释:“不是离了故的别有一个新,须是常常将故的只管温习,自有新意:一则向时看与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则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则因这上面却别生得意思。”[10]153-154“向时看与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与“别生得意思”就是指在“温故”与“知新”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历史经验的不同应用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同时,它也说明人并不追求“故”的客观性却关心“故”应用于当下的有效性,即人始终以当下的自我存在为主导,选择具体的、有效的“故”来回答他在当下的诉求。相应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也有类似的特征。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表明理解是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组成部分。伽达默尔指出:“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1]4在这里,伽达默尔并不把诠释学看作某种方法或技能。“方法”与“技能”的特性表明它们只属于部分人,而理解则是所有人都掌握的“方法”,方法一旦被所有人掌握,它就不再是方法,而是成为了经验。因而,理解不是方法和技能,而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统一体。从理解的归属上讲,理解永远属于历史和传统,也就是属于生活实践和生活实践经验。历史作为人类在过去的实践活动的总和,传统则以某种方式使人意识到它所保存的人类在过去的实践经验。这种方式就是前理解对理解的应用。前理解由于代表着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所以“应用”就是历史实在对当下的开放,即人总是在过往的人类生活实践经验中理解。二是当下的理解活动被完成后,它既成为了前理解而被纳入到历史中,同时它又产生了某种理解的经验而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人的当下理解由于总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所以当下的理解产生了“创造性的经验”。这种经验既是对过往的经验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当下理解活动的肯定,具有辩证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人虽然借助历史经验解答当下困惑,但是,他们较少或完全不关心历史内容本身的客观性,相反,他们更在意历史经验对当下的有效性。“有效性”与事情紧密相关。相似的事情在连接起理解和前理解的过程中,对当下有用的历史经验已经被事情预先挑选好。这就是说,事情具有挑选历史经验的功能且服务于人的当下存在。
简而言之,理解在人类生活实践经验中进行着循环运动:理解既来源于以传统为载体、以前理解为表现形式的人类生活实践经验,同时,当下的理解也产生了经验,并使经验被纳入到人类生活实践经验中,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一点讲,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展现了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循环,也就是“故”与“新”的循环往复。
4 结 语
“温故而知新”表明人为了解答当下生命诉求而要求“知新”,“知新”的途径是“温故”。人的多样生命诉求引发了“温故”与“知新”的循环。在循环过程中,人既寻求到历史经验解答了自我的生命诉求、领悟了自我的生命意义,同时人也在意义的引领下走向未来。相应地,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既是历史地理解,又是现实地理解,它既着力于借助历史和传统解答人的现实生命诉求,同时又以“意义的创生”引领人在之后的生命活动和生命走向。如此,历史、传统与当下构成了循环,它展现历史与现在、整体与部分以及人的自我生命体验的循环。这样的循环使得理解成为人固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组成部分。从这三个方面来讲,“温故而知新”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理解的历史性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