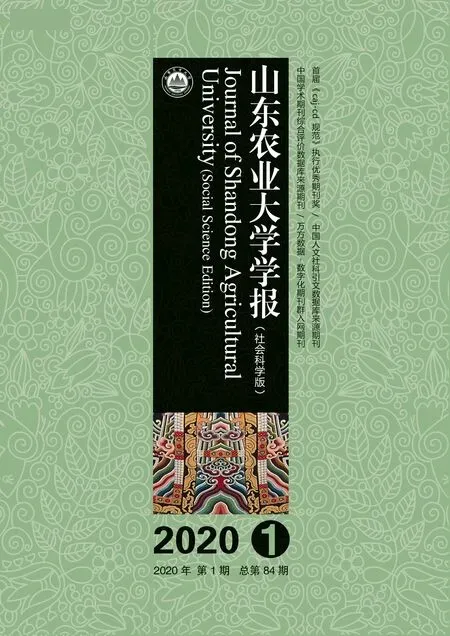论伍尔夫小说《幕间》中人与动物共生的生态思想
2020-12-09仇小萌
□仇小萌
[内容提要]与传统仅仅从男女两性关系的视角解读小说不同,文章尝试用德勒兹的生成动物理论来探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幕间》中人与动物共生的生态思想。小说通过描写人类对动物的压迫,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物种歧视与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内在联系。作者通过一幕由动物做主角的历史剧演出,使主人公们经历了“生成动物”的状态,艺术地展现了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共性和流动性,解析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作品还表达了动物性的多元态思想,主人公们最终成为一系列人类动物,回归自然和生命的本真状态。《幕间》启示我们,人类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不应忘记自身的动物性,人类只有与其它物种和谐共生,才有真正的未来。
1939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炮火笼罩了整个欧洲,在英国乡下避难的伍尔夫此时正在酝酿她的新作品。整日与动物为伴的生活,让作家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动物相依为命、血脉相连的情感,同时她也目睹了人类对动物的虐待和残害,开始从人与动物关系的角度,思考父权社会将人与动物、男性与女性、民族与民族二元对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作家在《三个基尼》中写道: “战争的罪魁祸首不仅在德国,也在英国……纳粹主义根植于父权文化之中。如何制止人们对动物的伤害?如何停止国家间的相互残杀?”[1]带着对战争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她完成了小说《幕间》。这是一部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故事以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前的英国乡村生活为背景,分为两条主线: 一条叙述波因茨宅奥利弗一家和动物的故事,另一条讲述拉布鲁特女士指导村民和动物表演露天历史剧的经历。学者们一般从作品中的动物意象对伍尔夫的女权和生态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吉莲·碧尔(Gilian Beer)分析了书中幕间剧开演前出现的史前动物形象,认为作家借助这些已经灭绝的史前巨兽表达出“女性被男权社会压抑的主体意识”[2];朱莉亚·布雷格(Julia Brigg)相信伍尔夫将动物作为幕间剧主角,是为重温人与动物、人与人相互友爱的岁月,“是对英国历史充满怀旧之情的最后一瞥”[3]。德里克·瑞恩(Derek Ryan)则以奶牛意象为例,认为作家借助动物的表演展现出“人类历史所蕴含的文明和自然双重属性”[4],意在唤起人们远离战争、回归自然的美好愿望。
《幕间》这部小说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了伍尔夫从前期作品中关注女性和自然的独特价值逐渐过渡到探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后现代思想。本文力图运用德勒兹的生成动物理论对《幕间》进行系统解读。 西方的动物研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统治,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动物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对西方文明史关于动物的思想进行了反思,提出生成动物理论,徳勒兹认为西方传统文化中动物都是“克分子动物”,这样的克分子动物不是动物原本的形式,而是被人类社会构建出来的,用以巩固人类的中心地位。自然界动植物的真实状态是“分子动物”,它们不由特定的形式、器官和功能界定,而是纯粹由共通的情感和感受所构成。人类和动物拥有共同的生命,没有优劣之分。人们应当尝试“生成动物”[5],体验动物的喜怒哀乐,从而在内心获得动物和自然的强大生命力。小说《幕间》艺术地展现了人类生成动物的状态,揭示了人类与动物共有的多姿多彩的生命,主人公们最终成为一系列人类动物,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回归生命本真,承认、接纳并拥抱自我的动物性,最终建立人与人、人与动物和人与宇宙万物和谐的期盼。
一、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下失语的动物
传统的人类文明一直将动物作为他者对待,动物被冠以低劣、野蛮、不具理性、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等名称,并被人类视为“我们所不是的物种”。西方文化在建构人与动物分界的同时,将这种界限逻辑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内部的等级划分,女性及其他弱势民族都被与动物性联系起来,排除在大写的“人”的范畴之外,成为压迫和暴力的对象。小说中,伍尔夫通过描写人类对动物的残害,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揭示了物种歧视是隐藏在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歧视等背后的深层思想根源。
德勒兹认为,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动物都是“克分子动物 ”,这种克分子动物不是动物的原本形式,而是被人构建出来的,他们承载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象征意义,代表我们不愿意纳入“人”这一范畴之内的一切。在西方文化中,动物一直是“人”极力排除、否定的“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世间有三种灵魂:“理性灵魂,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理性灵魂代表思维和判断能力,是人类身上最高尚的部分,动物灵魂比理性灵魂低级,代表人和动物的本能需求和情感需要,人类必须克服自身的动物灵魂,致力于发展逻辑思维和判断力,才能成为一个伟大、高尚和文明的人”[6]。亚力山大·科耶夫进一步划分了人与动物的界限,指出:“人能够像动物一样自由地活着,但只有他否定这一自然或动物的给定事实时,他才以人的方式活着。”[7]巴塔耶赞同柯耶夫的观点,他认为:“一切动物性形式都要被一个意味着人性的光明世界排除在外”[8]。本雅明批判了人与动物的这种界限逻辑,他认为动物和自然处于“深切的悲伤”[9]之中,因为人用自己堕落的语言为它们命名,不仅没有传达出人自身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传达出它们的精神实质。
德勒兹将“克分子动物”分成两类:一种是国家动物,即从属于种属、分类的动物,它们往往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人类神话学中的 “系列或结构,原型或模型”;另一种是“俄狄浦斯式的动物”[10],它们属于与人类关系亲密的宠物,是人类情感寄托的对象。在《幕间》中,马、狗和蛇就是三种具有代表性的 “克分子动物”。马作为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工具,是奥利弗家族唯一“允许和男主人一起画入肖像画的动物”, 对马的统治意味着对大自然、对殖民地和对异族的征服和统治,将马和男主人一起画入肖像画,更能体现家族先辈“驰骋沙场、辉煌一生”的崇高地位。蛇在《圣经》中是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魔鬼撒旦,代表着诱惑人类堕落的邪恶力量,小说中当男主人公贾尔斯在花园中看到一条蛇艰难吞咽它的猎物蟾蜍时,他对这只畜生感到愤怒和恶心,立刻“抬起脚,朝它踩下去,那团东西立刻就被踩烂了”[11],他的网球鞋上沾满了粘稠的鲜血,在场的每个人都对他投来英雄般赞许的目光。与马和蛇代表了德勒兹所说的“国家动物”不同,书中的猎狗则被男主人公们当作娱乐和消遣的“宠物”,动物学者格瑞塔·嘉德表示:“成为宠物,就是让所有关于生命的决定交由他人控制,无法表达自己的自然本能,与奴隶无异”[12]。作家写道:“这是一个让心灵黯淡无光的地方……,那些书在发霉,……夜莺不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带龟纹壳花纹的蝴蝶拍打着窗户的玻璃一遍又一遍,直到死去……”[11]。
工业化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进一步抬高了人性,而其反面则是对动物性的进一步贬低。在工业社会之前,人与动物具有直接、真实、亲密的关系,即使在狩猎或祭祀过程中,人对动物也充满敬意,不会滥杀。在伍尔夫早期的作品《伦敦佬的农场经历》中,她描绘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伦敦郊区农民约翰对动物态度的转变:早年,他经营农场,奶牛、猪和马等动物是他平日爱护有加、依仗其生活的朋友,但将农场转变成牲畜公司后,牛和猪作为买卖的商品,变成了他“牟取经济利益的手段”[13]。在 《幕间》中,将动物作为食物生产的工业化养殖场进一步取代了传统的牲畜饲养公司,这种工业化养殖不仅影响了城市居民对动物的态度,甚至在和动物亲密接触的英国农村地区,人们也仅仅将动物当成可以买卖的食物。奥利弗先生虽然生活在农场, 却习惯于从市场或肉牛饲养厂订购新鲜的小牛肉,对他来说,牛没有生命价值,只是可食用的肉类, “生来就要成为牛肉”。伍尔夫表示,动物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具有情感和意识的独立的生命主体,而不是人类的宠物或食物”[14],动物的价值不应通过对人类的益处来衡量。将动物当成商品和肉食,意味着动物已经被排除在一切生命享有的基本权利、道德和保护之外,完全任由人类的喜好屠戮和宰割。
西方哲学和文化通过建构人与动物的分界,表明了“对亲属关系的认可或否定”,女人、黑人以及其他弱势民族都被与动物性联系起来,排除在大写的“人”之外。生态女性学者亚当·吉姆指出:“ 女性被视为动物,是父权制权力施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它通过将女性动物化,实现对女性的合法统治和剥削。[15]”小说中,贾尔斯和妻子伊萨初次相遇、相爱的情景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被动物化的卑微处境:“当时,贾尔斯正在钓鱼,她看着他甩竿,再甩竿,直到一条鲑鱼跳了起来,被他捉住,那一刻,她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她”。这里作者暗喻伊萨被贾尔斯物化成“一条鲑鱼”,让他充满征服的满足感。贾尔斯的情妇曼萨瑞太太则完全被物化为一个没有生命的“肉食”,满足他一时兴起的淫欲,“鲑鱼、鲣鸟和喜鹊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把事办了,吃饱再说”。将女性动物化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和虐待事件层出不穷,书中写到“白厅街上的皇家骑兵像赶马一样,诱骗、并轮奸了一位少女”[11],而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侧,“犹太人正在被剥夺正常生活的权利,他们像动物一样被屠杀”。动物研究者卡里·伍尔夫指出,只要有关物种的人文主义话语存在,它就“永远会被某些反对另一些人的人利用,支持对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社会他者——或是性别、或是种族、或是阶级、或是性征差异——实施暴力”[16]。
二、生成动物,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
生成是德勒兹提出的一种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新方式,指个体生命不断地通过生成差异,拥有新的感受和认知。生成动物是以动物的眼光去感知和看待世界,从而获得动物的生命体验,以增强人自身的认知和生命力。在小说《幕间》中,伍尔夫通过一幕由动物做主角的历史剧演出,使主人公们经历了“生成动物”的状态,赋予主人公新的体验和感受,重新认识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解析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
徳勒兹认为,生成动物是要与动物建立临近区域,从而让动物所具有的生命力穿越人自身,让人具有动物的诸种感受。生成动物不是生成西方传统哲学范畴里的“克分子动物”,而是生成“分子动物”,这种动物是一种“感受动物”,纯粹由主动和被动的感受构成,不由形式、器官和功能界定,如考尔·布鲁克所说,“将自己想象成一只动物, 想象它会怎样看待这样的世界,会有怎样的知觉,会怎样行动,从而让自己拥有动物的情感、运动、知觉和生成”[17]。生成动物是要在传统人类和动物的范畴之间创造一条逃逸路线,将人与动物解域化,从而让人逃离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社会思想和以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和等级价值为标准的价值体系,重新接近“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因此,尝试生成动物,以动物的眼光去感知和看待世界,不仅能帮助人类获得动物的能力,增强自身的生命力,“还能打破权利、等级和差异的界限,发现人与动物、人与人共生的真实状态。”
如果说在前一部小说《希弗勒——一只狗的传记》中,伍尔夫将 “人的喜怒哀乐赋予勃朗宁夫人的宠物狗希弗勒”[18],那么在小说《幕间》里,作家更加关注人类如何体会动物的情感,力图从动物的视角去看世界,这正是德勒兹所说的进入“人与动物的邻近区域”[19]。在这部小说里,伍尔夫通过一部由自然书写、动物做主角的历史剧演出,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起临近区域,她让大自然和动物自始至终参与了人类历史剧的表演。舞台上,由英雄人物演出的英格兰历史和动物的表演同时进行,伊丽莎白女王、哈兰登勋爵夫人等贵族和英雄人物悉数登场, 演绎英国历史的各个伟大时代;而在舞台另一边,奶牛、毛驴等动物悠然自得地走入走出,人类的演出不时伴随着奶牛嗷嗷的叫声、毛驴的走动声和燕子飞来飞去的情景”[11]。演出最后时刻,人类的表演再次以大自然的方式谢幕,“一群琼鸟飞向舞台旁的大树,整棵树伴随着鸟儿疾飞的呼呼声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似乎每一只鸟都在弹拨琴弦,呼呼声、嗡嗡声从那棵充满鸟鸣的大树上升腾起来,大树变成了一首狂想曲,小鸟用不和谐的声音按着音节歌唱生命、生命、生命,没有节制,没有停顿……”。动物不再是人类舞台上的陪衬,不再是被动、无声的他者,他们是舞台上鲜活跃动的演员,向我们讲述它们自己的故事。
德勒兹认为,《爱丽斯漫游奇境》的作者卡洛尔是第一个尝试表达人物“生成状态”的作家,他借助将爱丽丝的身体在幻境中变换成动物、植物等多种形态,赋予小说主人公新的体验和感受,成功地展现了爱丽丝“生成动物”的状态[20]。在伍尔夫的这部小说中,贾尔斯等人如同爱丽丝一样,在观赏幕间剧的过程中进入了某种幻境,他们的身体没有变形,却失去了被定义为人的两种重要品质——理性思维和判断力,像动物一样凭借听觉、视觉等感知能力去认识世界,抑或是他们在精神世界里已经变成了动物。 贾尔斯发现自己能听懂大自然的语言,他能听见“树叶的沙沙声,奶牛地打嗝声,甚至燕子掠过草地的声音”,“猫头鹰冲着他叫,常青藤把他的骄傲嘲笑,”他成为了一头沮丧的鹿,“世界上最粗鲁的蔑视,已将刺扎进他瘦小的身体”;受人尊敬、高高在上的牧师特菲尔德变成一只 “秃鼻的乌鸦跳上一根显眼的秃树枝”,“一个笨蛋、一个笑柄 ”[11]滑稽地预测未来。在生成动物的过程中,不仅小说男性放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女性也从人类文明语境下妻子、母亲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她们仅仅是自然之子。伊莎变成一只雪鹿, “在丛林中飞跑着,跟着带斑点的鹿群”,斯威辛太太的心随着燕子自由飞翔,时而“漂浮在云彩中间,没有身体”,时而从“一根椽木飞到另一根椽木”,她感到自己“飞越非洲、飞越法国,早在有海峡之前、早在这片土地张满杜鹃花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幕间剧建立了人与动物的临近区域,使主人公进入了生成动物的状态,能够像动物那样感知世界。
伍尔夫还借助描绘主人公们生成动物的过程,展现人类与动物共同的生命,启迪人们平等地看待动物生命和人类生命。德勒兹在《千高原》中将人与动物共同的生命称之为一种“非有机、非个体的生命”,它存在于千千万万有机体和无机体之中,并在构成个体一生中所有时刻始终存在。这种非有机、非个体、无器官的抽象的生命往往以个体生命的形式出现,伍尔夫借助幕间剧的形式巧妙地让个体的生命在短暂的瞬间让位于纯粹的生命。舞台上 “燕子随着乐曲起舞,绕着圈子,飞进飞出,飞向舞台两边的大树;那些树顿时充满鸟儿嗡嗡的鸣叫声,在风的吹拂下,仿佛活过来了,像教堂里有一定间隔的廊柱,把鸟儿的乐曲隔成小节,积累并收集音符……”[11],动物们纷纷走出失语状态,展现出一种纯粹生命的力量,奥利弗先生终于找到了自我生命与动物生命的共鸣,“摇摆的树枝和旋飞的小鸟仿佛受到召唤,走出它们的私生活,接受安排来参加舞会.....一阵阵丁零当啷、嬉笑怒骂的声音,奶牛也加入了这场喧嚣!大家都在跳舞,后退又前进......”,“那些本该用来区分人类和野兽的障碍消失了”,动物和人类都褪去了人类语言赋予他们的特定身份,“所有人都得到了解放,每一个人都是自由人,每一个人都是人格完整的人”。傲慢的奥利弗先生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11],人类和动物都拥有共同的生命,动物生命并不比人类生命低级,而征服印度的事业,以及帝国军队和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比照顾、关心动物的斯威辛夫人更伟大。
三、成为人类动物,回归大自然和生命的本真状态
伍尔夫不满足于督促人们从动物的角度观察世界,更启发人们进一步认识人类自身所蕴涵的动物性。她在《幕间》中写道:“绵羊、奶牛、野草、树木,我们都融为了一体”[11],正是这些本质上独一无二的动物生命形式所构成的连续多元态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小说结尾处,作家将主人公们描绘成一系列“人类动物”,他们通过想象、回忆和梦境重归大自然和生命的本真状态,展现了作者为人类树立一个新的理想生存模式的探索和努力。
尼采在《快乐的哲学》一书中发问“ 动物从哪里结束,人又从哪里开始呢?[21]”在他看来,人性中蕴含着动物性,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本是一体。德里达表示,“在非人类的世界中,有多姿多彩的各种活生生的事物存在着,它们的多元性不可能用一个和人性对立的动物性形象来承载”[22]。他将多元态动物性命名为animot,这个词与animal相区别,体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动物性而非个体的动物,但“它的发音与法语animaux(“动物”一词的复数形式)相似,又表达了动物性存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23]。德里达认为,animot是对传统人类语言的挑战,这个词恰恰显示出动物是在其自身话语之中的存在,它独立于人类话语之外,即是自主的存在,又具备多元的状态。人类生命的本真即是动物性,仅仅让自身暂时与动物互换角色,体验、同情动物作为“他者”的遭遇,无法改变男权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以及动物、女性受压迫的现状。这位哲学家设想人类“重新回到动物的初始”——一种“人类动物”的理想生存状态,承认、接纳并拥抱自我的动物性。
伍尔夫力图通过描绘主人公的梦境,展现出人类自身蕴含的动物性。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指出,男权社会通过“让人类忘记自己的过去——即自身的动物性存在,来维持理性和道德的统治”,但个体被压抑的过去不会消失,而是以梦境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之中,人可以“在梦境中重新寻找到被压抑的动物性”[24]。小说中,阅读史前文明史——这些根据男权社会的语言、逻辑和理性书写的历史,无法让主人公们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多元动物性的存在,如尼采所言“唯有纠正文明对人类自身动物性的压制和遗忘,在动物的梦想、幻觉和激情中才能恢复生命的圆满。”[21]幕间剧结束之后,奥利弗先生坠入了梦乡,他仿佛回到了遥不可及的过去,那时“英格兰是一片沼泽,浓密的森林覆盖着大地,在永恒,交错的树枝上,有鸟儿歌唱……” ,自己变成了一个史前人类,“半人半猿,皮肤抖动着,像一只狗抖动皮毛,他从爬行的地方站立起来,举起了巨大的石头……”[11]。梦境彰显了人类与动物生命之间的种种联系,凸显出人性中的动物性,也否定了后者的他者地位。作家借助梦幻的形式表现了奥利弗先生的动物性,醒来后的他和阿富汗猎犬成为了情感相惜的伙伴,不再有人类和动物、主人和仆人的等级关系,两个好朋友轻快地跑过地毯,跑进卧室,一起入眠。
书中的主人公们还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界生命的多元态,自我生命是自然界多元动物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开始从动物的视角看待自我和世界。在小说《幕间》中,爱护、同情动物的斯威辛太太不相信理性和语言对人类和动物的定义,与奥利弗先生仅仅将池塘中鱼儿们定义为交配和繁衍不同,她认为动物性先于人性存在,并创造性地用动物生命来解释人类自身:漂浮在池塘中的叶片和小鱼被她创造性地命名为“欧洲、印度、非洲和美洲,它们混杂在一起,银色、粉红色和金色,有带斑点的、有带条纹的、还有带彩色斑块的、光亮而质厚”[11]。借助斯威辛太太给池塘中的小鱼命名这一独特的方式,作者表达了人类作为动物的多重存在:大自然是任我们漂浮的大海,人类的世界就是鱼儿的世界,每个人都是独特和多元的,因为爱和恨互相追逐,因而具有美、力量和荣耀。水中的鱼儿、空中的飞禽、陆地的走兽,包括我们,都是大自然多元态生命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本质上无差别的动物生命形式所构成的连续多元态构成了生命的总体。
伍尔夫认为,人们应当倾听自己身上的非人类呼唤,最终实现自身多元动物存在,重塑自己的本真状态,达到德里达所称的animot状态。小说结尾,主人公们被描述成一系列“人类动物”,他们从人类语言的世界中退出,像动物一样用心而不是理性和逻辑敏锐的感知这个世界。这个人类动物离人类的本真状态只有咫尺之遥: “那些花儿,用红色、白色、银色和蓝色发散着光芒,那些用多种语言和多种音节发音的树木,用绿色和黄色的叶子推搡着我们,调遣着我们,像对待琼鸟和秃笔乌鸦一样,让我们聚集起来”[11]。 男主人公最终完全放弃了自指的人类语言,重归动物本性和非人类的自然生态,他的存在就是事物和环境本身:他能听见树叶的沙沙声,奶牛地打嗝声,甚至燕子掠过草地的声音,自然人的自然愿望控制了他,他不再需要词语了。露天戏剧将主人公们与动物和大自然的情感融为一体,贾尔斯、奥利弗和伊莎化身为自然的一部分,“乌云化成了雨水倾盆而下,从面颊上流下来, 是所有人的泪水,为所有人流淌,仿佛全世界都在哭泣。眼泪,眼泪,眼泪”[11]。当人类语言褪去之后,主人公们与自然割裂开来的身体也随之褪去,从而达到完整统一的本真存在。作家充满感情地写道:“世界回到了还没修路盖房的夜晚,这是穴居先民从某个高地的巨石之上审视世界的夜晚,波因茨宅也失去了荫蔽的功能,贾尔斯和伊莎,这对夫妻就像公狐狸和母狐狸,在这黑暗的中心,在这夜幕下的田野里,拥抱在一起”[11]。当人类社会彻底摒弃人与动物、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思想,而将自我和动物看成彼此相融,共生共荣的整体时,男人与女人、人类与动物才能获得新生,过上和谐、平等、互助的生活。
在人性与动物性的关系问题上,伍尔夫与德勒兹、德里达和尼采等人秉持相同的看法。她认为,动物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具有情感和意识的独立的生命主体。在小说《幕间》中,作者通过让主人公们经历“生成动物”的状态,赋予主人公新的体验和感受,重新认识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小说结尾,主人公们被描绘成一系列“人类动物”,重归大自然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表达了作者为人类树立一个新的理想生存模式的探索和努力,即在理性世界中为人类的动物性留出一片天地,将自我想象成一个作为动物的人,和其它物种一样存在于广阔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小说《幕间》启示我们,人类在追求生存发展的同时不应忘记自身的自然性和动物性,人们只有与自然和其它物种和谐共生,人类才有真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