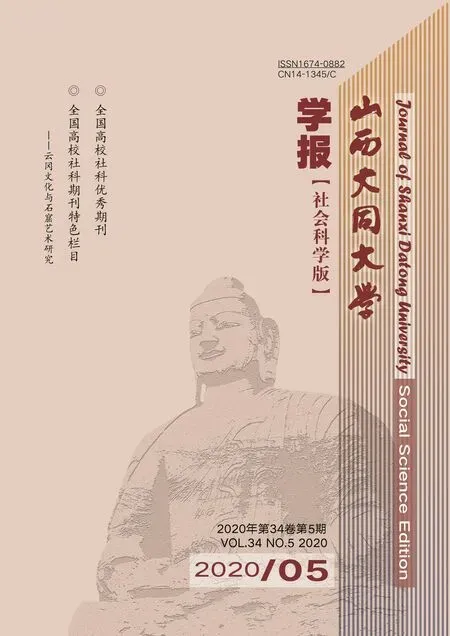明成祖史迹考证
2020-12-09宋松华
宋松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32)
关于《明太祖实录》所载的四道敕书,至今争议很大。上世纪40 年代,王崇武先生提出,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明太祖下达给燕王的敕书“疑为馆臣所伪造”。[1](卷1,P9)上世纪60 年代著名史家黄彰健,以《毓庆勋懿集》所收录的两道敕书作依据,提出《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初九明太祖下达给燕王(明成祖)的敕书及五月十二日下达给郭英的敕书,皆为伪造而成。但是,在并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黄先生进一步推想,同年五月十二明太祖下达杨文的敕书及五月二十九下达给燕王的敕书也为伪造。[2]两位大家的观点,已为学界广泛接受。但是,同一道敕书仅凭三五字的差异,否定另一道敕书的真实性,有些势单力薄。当代史家南炳文先生并不认可黄彰健及王崇武两先生的观点。[3]南先生通过对几则传统史料的重新解读,认为太祖晚年与燕王关系正常,燕王仍领命出征。南先生认为《毓庆勋懿集》所收录的两道敕书,可能版本出现问题,出现了脱文,漏记了燕王。南先生最后总结,《明太祖实录》所载的四道敕书,有很高的可信度。
为了更好地向以上诸位大家学习,也为了使研究建文朝史的事业进一步发展,笔者使用新发现的史料,对《明太祖实录》所载的四道敕书,以及有关成祖其他有争议的事项,提出了新的见解,或许离历史的真实能更近一步。
一、关于建文帝伐燕诏书及分析
燕王称帝后,凡与之相抵触的建文朝档案文书几乎销毁殆尽。[4](P1-3)建文朝纂修的《明太祖实录》必有大量与燕王不利的材料,尽毁原本,敕令臣下两次重修。①又大肆屠戮建文朝臣,建文帝长子文奎年方七岁也被诛杀。[5](卷140)②人证物证几尽灭绝,建文朝历史几成空白。存留至今的明朝国史尽是成祖及子孙的一面之词,自不能轻信。纂修《明史》经历百年,修成乾隆年间,持论当公。但《明史》本之实录,《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夹杂大量精心编撰的虚假材料,对于涉及建文朝前后的史事,当小心甄别。凡此种种,为疏理镂析那段朦胧的历史制造了极大的困难。所幸,一则建文皇帝讨伐燕王的诏书还是存留于世,为今人拨开胧罩在建文朝的团团谜雾提供了重要线索。建文元年(1399)八月,建文帝下诏书讨伐燕王,诏曰:
朕奉先皇帝遗诏,纂承大统,宵衣旰食,思图善政,以安兆民。岂意国家不幸,骨肉之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皆与同谋,朕以亲亲之故,不忍暴扬其恶,止治橚罪,余置不问。今年齐王榑谋逆事觉,推问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柏同谋大逆,柏知罪自焚,榑已废为庶人。朕以燕于亲最近,未穷其事。今乃忘祖逆天,称兵构祸,意欲犯阙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骇闻。昔先皇帝时,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私印伪钞,阴结人主,朝廷穷极,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海内闻知,莫不痛忿。今不悔过,又造滔天之恶。虽欲赦之,而获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太庙,废为庶人。遣长兴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万,往讨其罪。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宜怀忠守义,奉职平燕,与国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6](卷11,P805)③
据方孝孺传:“燕兵起,庭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7](卷141,P1152)此诏书当为孝孺所拟。有明一代,孝孺堪称第一忠介之士。这份伐燕诏书是否属实,可从侧面分析推理。观《奉天靖难记》,成祖凡所责难诋毁建文者,污言秽语,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独无此诏书的只言片语。上书建文帝,或诏告天下,气势汹汹,咄咄逼人,颇似诬枉冤屈。诏内言“燕庶人父子”本指燕王及子高炽高煦高燧,成祖乃故谬为指己及太祖。[1](序,P7)区区五字不能隐忍吞声,犹哓哓不休,诡词狡辩。帝王心理如出一辙。清代雍正年间,坊间流传世宗“十大罪”,④为替自己正名,世宗亲撰《大义觉迷录》逐一驳斥。如诏书所言,成祖多行犯法谋逆之举,及至谋父,则成祖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暴虐之徒。成祖以英豪自许,以忠孝标榜天下,若是诬篾捏造之词,成祖安能无动于衷,不发一语?诏书的部分内容,也可通过其他史籍得到映证。钦修实录已明言“周齐岷代,在先帝时尚多不法之事,何况今日”,[8](卷1,P6)但是另一则材料指出燕王亦参与其中,与周齐湘岷代等王通谋。[9](P311)建文元年八月,即将兴兵讨伐燕王,齐泰奏请布告天下,削燕属籍,声罪致讨,明斥燕王为贼,[7](卷141《齐泰传》,P1152)又曰:“执其有异图,孰信其诬?”[1](卷1,P17)是燕谋不轨,尽人皆知。故发其谋逆,无人不信。[1](卷1,P18)此诏书,《奉天靖难记》不载,《明太宗实录》亦削除。此中原因,不言而喻。成祖及其子孙自知理亏词穷,心虚愧疚,无力翻案。诏书所述的内容,是属实不容篡夺的。
“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7](卷141,P1152)孝孺文中必有大量可揭示事件原有的真实档案文书,然悬为禁厉,已湮没无传矣。南先生言:“在洪武后期,其与明太祖的关系亦未见能确证有不和谐之处的记载。”[3]还未注意这份讨伐燕王的诏书。拿这则史料作参考标准,《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奉天靖难记》中许多伪造的史料将不攻自破。
二、史迹真伪考证
(一)关于《明太祖实录》中的四则史料 《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明太祖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甲寅即初八圣躬不豫,⑤一月后即闰五月初十驾崩。太祖因何故不豫升遐,正史并无记载。此伐燕诏书道出原由,因燕王所致:“昔先皇帝时,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私印伪钞,阴结人主,朝廷穷极,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显然从初八致疾到闰五月初十去世这段时间明太祖与燕王父子关系已非正常。但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以后,太祖向燕王连发三道敕谕:
甲寅,上不豫(五月初八)。 ……
(戊午) 敕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候,余皆选拣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地屯驻隄备。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10](卷257,P3715)
戊午,敕左军都督杨文曰:“兵法有言:‘贰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应敌,为将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拣精锐马步军士,随燕王往开平隄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慎无贰心而有疑志也。”[10](卷257,P3716)
乙亥(二十九)敕今上曰:“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等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朕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10](卷257,P3717)
据诏书,五月初八太祖震怒不豫。五月初八以后,太祖当必欲惩戒燕王。但据《明太祖实录》太祖反而连发三道敕谕,俱令燕王北征。其真实性,委实令人生疑。太祖对诸子管教甚严。小过辄发旨训斥,[11]大过辄召还京师,严厉督斥,待其悔改,方令归藩。据《明史》诸王传可知。
《秦王传》:
二十四年,以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明年命归藩。[7](卷116,P1116)
《晋王传》:
在国多不法。或告棡有异谋。帝大怒,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二十四年,太子巡陕西归,棡随来朝,敕归藩。[7](卷116,P1116)
《周王传》:
二十二年,橚弃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使居京师,世子有炖理藩事。二十四年十二月敕归藩。[7](卷116,P1117)
《潭王传》:
妃于氏,都督显女也。显子琥,除为宁夏指挥。二十三年坐忽惟庸党,显与琥俱诛。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谕,且召入见。梓大惧,与妃俱焚死。[7](卷116,P1117)
由以上观之,太祖对犯有严重过错的诸王,处理手法一以贯之,就是召还京师,拘留很长时期,再作处置。据伐燕诏书所言,燕王因多行不法之事,太祖震怒,致五月初八气极不豫。燕王当犯大罪。仿秦晋周潭四王违法事例,太祖亦当召燕王回京师,⑥然后予以严厉制裁。五月之前,燕王既已被弃用,按例当令南返,则实录所言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令燕王北征当为伪造。秦王晋王先后故去,燕王成为强藩之首,雄居北方。据诏书,燕王骄横跋扈,多行不法之事。虽太祖尚存,但对燕王已不可枸曲,势难图制。[12](序,P10)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与燕王已势同水火。以太祖的多疑雄猜,断不可能再对其委以重用,寄予厚望。太祖临终之际,燕王已成为太孙极大的危胁。临终警谕太孙“燕王不可不虑”。[6](卷10,P783)据《明太祖实录》在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初九)太祖向燕王下达了另一道敕书:
敕今上(时为燕王的明成祖)曰:“迩闻塞上烽火数警,此胡虏之诈,彼欲诱我师出境,纵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堕其计中。烽起之处,人莫宜近,虽望远者亦须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虏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度其人马不下数万,岂可不为之虑。可西凉召都指挥庄德、张文杰,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辽东召武定侯郭英等,会兵一处。辽王以都司及护卫马军悉数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军须十五万,布阵而待。令武定侯、刘都督、宋都督翼于左,庄德、张文杰、都指挥陈用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使彼胡虏莫知端倪,则无不胜矣。兵法示饥而实饱,精而外钝,尔其察之。”[10](卷256,P3712)
五月初八太祖不豫,则太祖察觉燕王不法之事,当在四月或四月之前。若在在四月初九之前,则《太祖实录》所载四月乙酉(初九)太祖令燕王统兵出征的这道敕谕也必为假造。同五月十二日太祖下达给郭英的敕书一样,四月初九的这份敕书,也是由宫中所藏的原敕书改篡而来。[2]
建文朝编修的《明太祖实录》必详细记有燕王种种不法之事,必有太祖晚年与燕王失睦的记载。故夺位后两次重修太祖实录,掩盖真相,同时捏造事实。四道敕谕中的当事人郭英老死于永乐元年(1403 年),[7](卷130,P137)杨文死在永乐四年(1406 年),[13](第72 册,P273)辽王在燕王夺位后,“永乐元年入朝,帝以植初贰于己,嫌之”,屡受成祖打压,委曲自保。[7](卷116《辽王传》,P1116)此种情况下,馆臣无所顾忌制造伪证,编入实录。
据朝鲜《李朝太祖实录》卷十四: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日)辽东被掳人金松逃来(朝鲜),告曰:“蒙古军向辽东,燕府王率师攻击,败之,辽王领兵将行,予亦充军而行,中路逃来。”[14]
成祖曾自述“自陛下嗣位以来,臣未尝言及兵事”。[8](卷5,P104)因此,该史料的真实性大有问题。有学者谓“按之史籍,当时燕王不仅与明太祖关系正常,尔且其对军事行动仍在正常参与”。[3]轻信了该史料。
(二)燕王为周王上书说
……
一日朝罢,建文君谓子澄曰:“先生忆昔者东角门之言乎?”子澄曰:何事?”允炆曰:“东角门在尔。”子澄曰:“臣以为他事,若是事,臣固不敢忘也。然此事须密,待臣细谋之。”子澄退与齐泰等私谋曰:“今主少不闲政事,诸王年长,皆握重兵,久将难制。吾辈欲长有富贵,须早计。”泰曰:“此易,但使人诬告其阴私,坐以不轨,削之,削一国,可以蔓引诸国。”子澄曰:“姑更思之。”泰曰:“他事不足动,惟大逆,则不宥。”子澄曰:“善,然则所发何先?”齐泰曰:“燕王英武,威闻海内,志广气刚,气刚者,易挫,加以不轨之事,孰信其诬,去其大,则小者自慑。”子澄曰:“不然,燕王素孝瑾,国人戴之,天下知其贤,诬以不轨,将谁信之。周齐岷代,在先帝时尚多不法之事,何况今日,而于今作过,周王必先,周王易取耳。周,燕之母弟,取周即剪燕之手足。今只俟周有罪,即令议处置,彼必来救,救则可以连坐。是在我取之有名,在彼虽有一国之众,势孤无援,取之何艰?”泰曰:“甚善,甚善。”明日,入白,建文君喜曰:“黄先生善谋矣。”未几,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遂遣曹国公李景隆率兵至河南,围其城。执王府僚属,驱迫王及世子阖宫皆至京师,削王爵,为庶人。迁之云南,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
……
初周王被执,果敕上议其罪。时上居丧守制,忧邑成疾,见敕惴惴,不知所为,乃上书曰:“若周王橚所为,行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具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诚,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其言恳恻深至。[8](卷1,P6-8)
观此段文字,周王获罪下狱,燕王是局外之人,与周王案丝毫牵涉。引诱燕王上书营救,以期一网打尽,是建文朝臣精心所设的圈套。然考建文帝讨伐燕王诏书有“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皆与同谋”之语,可知周王谋逆下狱,供出燕王,二人实为同犯。周王招供,燕王已是噤若寒蝉。燕王苟以上书,也必以为己请罪求死为是。既然燕王上书为周王开脱本无此事,则齐泰、黄子澄前前后后关于此上书的进言当为虚构。编造此上书,意在表燕王忠厚缱绻,堕入圈套。后世学者,多以子澄所述“周王,燕之母弟”之语,作为燕周同母的有力证据。此论据恐难征信。
(三)燕王来京朝见说 明代诸多史籍有建文元年二月来朝一事,[4](P47-53)至今权威专著仍持此说,深信不疑。[15](第1 章,P61-63)《国榷》建文元年二月乙丑条:
燕王棣来朝,绝驰道,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风韶侍班,奏曰:“诸王来朝,殿上宜主臣礼,宫中宜家人礼。今燕王大不敬,当问。”上不报。[6](卷11,P795)
据伐燕诏书,太祖驾崩之际,叔侄早已深结大仇。燕王奔丧,建文令其单骑入城,尤戒慎恐惧,中途折返。[14](上编卷1,P150)又周王齐王谋逆事觉,均牵涉燕王。重罪之人,谈何趾高气昂,“绝驰道,登陛不拜”一说不知从何谈起?对建文帝而言,新恨交织旧仇,必欲除去燕王。周王被逮下狱论死,[6](卷11,P789)齐王被扣京师,[9](P315,P319)于燕王已是前车之鉴。故燕王来朝一事,纯粹是子虚乌有,杜撰讹传。有史料佐证燕王二月仍在北平。[9](P317)
(四)不杀叔父说 明代不少史籍皆记“建文帝有不杀叔父诏”。[4](P317)兹以《罪惟录》为例,惠宗帝云:
昔萧绛举兵入京,令其下曰:“入门之内,自极兵威,不仁之至。”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负杀叔父之名。[16](《帝纪》卷2,P63)
当时的朝鲜使节,在其文集中也有不杀叔父说的记载,显然信其有。[17](《阳春集》,第1 册P37)⑦特别是《明史》成祖本纪也袭“不杀叔父说”。[7](卷5,P854)王崇武先生从燕王几次遇险,惨烈的战况的事实为依据,得出“不杀叔父说”为杜撰之说。[4](P99-102)但王先生的观点仍未在学界达成共识。对“不杀叔父说”的认可仍是明史学界主流。时至今日,“不杀叔父说”还进入中学教科书。[18](P81)此说似已是定论。今对比诏内有“虽欲赦之,而获罪宗社,天地不容”之语,是则诛杀燕王出自建文帝本意。故朝廷将士奋力扑杀燕王。[7](卷142《铁玄传》,P1153;卷144《平安传》,P1156)
(五)燕王所谓自陈八罪之说 建文元年十一月,燕王有自陈八罪之说。为了便于对比讨论,现将“八罪之说”全引录于下:
以前所上书不报 ,复上书于朝曰:……今历三月,……窃闻朝廷论臣有不轨之事八,……
其一,谓臣三护卫官有踰额数者。今臣三护卫指挥不及二十员,比执掌内员额尚不足,镇抚、百户于常额亦缺,千户不过五十员,比额虽多三五员,然皆皇考临御时朝廷除授者,非臣所敢自署。盖祖训职制条有云“王府指挥司官并属官随军多少设置,不拘数目”。当时各王府皆然。非皇考独厚臣棣,此奸臣之枉臣也。
其二,谓臣不当无事操练军马。此事亦在皇考御临之时有之。盖祖训兵卫条有云“凡王教练军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临事有警,或王有闲暇,则遍数不拘”。非臣敢擅为也。然自皇考宾天之后,臣居丧且病,足迹未尝出外庭,而护卫军士,兵部数数调遣备边,存者仅半,而教练久废。北平官吏军民咸所目观。此奸臣之枉臣也。
其三,谓臣不当于各卫选用军官。自陛下嗣位以来,臣未尝言及兵事,亦未尝选用一官。但在皇考时,曾具奏于北平城中散卫选用三五人,亦不曾于外卫选用。盖祖训职制条有云“凡王府武官,千户、百户从王于所部军职内选用,开具各人姓名、实迹,王亲署奏本,不由各衙门差人直诣御前闻奏,颁降诰勅”,当时王府通例如此,非独臣棣,兵部具有文检可验。此奸臣之枉臣也。
其四,谓臣私养鞑靼健卒。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当时赐敕具在,内府必有敕底可稽。其百余人,今死者已四之一,其头目亦已赴京别用,实非臣私养。此奸臣之枉臣也。
其五,谓臣招致各处异人术士,养于府中,日夕论议为非。尤是无根驾虚之说。果如有之,必知是何氏名,出何郡县,指实罪之,谁敢不服?今无指实之人,但冒以空言,天地鬼神,其可欺哉。此奸臣之枉臣也。
其六,谓臣府中守御四门,不当僭儗皇城守御之制,更番甚严,以为关防朝廷。盖祖训兵卫条有云“凡王府侍卫指挥三员、千户六员、百户六员、正旗军六百七十二名,守御王城四门,每三日一次,轮直宿卫。其官军皆三护卫均拨”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钦遵此制,非始于陛下嗣位之后。而陛下临御以来,兵部数调护卫官军防边,宿卫多不及旧数。此奸臣之枉臣也。
其七,谓臣宫室僭侈,过于各府。此盖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益,其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营缮条明言“燕因元之旧有”,非臣敢僭越。此奸臣之枉臣也。
其八,谓臣第二子高煦过涿州,擅笞驿官。此实臣失于教训。然笞驿官,遂指为臣不轨之迹,冤滥之过,何以服天下后世?此奸臣之枉臣也。[8](卷5,P103-106)
“八罪”的陈述以答辩状行式展开,可谓气壮如牛,宣告燕王无罪横遭劫难,为成祖起兵造反推卸罪责,嫁祸于建文帝,争取更多的舆论同情。查阅《明太宗实录》,从建文元年七月初五起兵至十一月,燕王两次上书建文皇帝。燕王七月初五上书建文帝申述起兵缘由,建文帝未予理会。八月建文帝下诏书讨伐燕王(实录未载此诏书,仅言“未几,削诏爵下”之语),燕王于同年十一月再上书建文帝,批驳建文帝在诏书中指斥自己的种种罪过。然令吾人惊讶的是,所谓八罪与伐燕诏书所指斥燕王的种种罪过“与周齐湘诸王谋逆;私印宝钞;阴结人主;藏逆罪人;不忠不孝致太祖成疾升遐”比对,竟然无一相涉。八罪之说显系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为修实录者罗列编造,以混淆视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太宗实录》修成于宣德中期,此时,汉王高煦已身败名裂,身陷囹圄,更无从申诉,所以在此尽指其罪(或许也是捏造)。对己子不护短不隐恶,烘托成祖高风亮节,有人君之度。 愈发使后人对所谓“八罪”深信不疑。王鸿绪《明史稿》成祖本纪虽仅两卷,但却对“八罪”之说详尽收录。[19](卷5,P29)信其为真。《明太宗实录》纂修凡例:“诏书悉录原文,敕书御制文录其关事其所重,有(有脱文)特敕谕臣下抚远人及卹刑宽贷之类,悉录。”[8]是真话吗?
王崇武先生推断虽实录此段文字“固为馆臣所改撰,非当时之原书”,[1](序,P9)但苦于无对立史料作证,无法对其真实性,予以直接否定。王先生又认为此八条罪过是“仅据实际情形答辩,反觉得体。而惠帝所指责之八大罪状:……遂尽吐其详已”,[4](P14)显然是又信其为实了。黄云眉先生谓:“按燕王上恵帝书,并载燕王《令旨》,姜清《秘史》,《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卷四亦载之。惟《令旨》《秘史》所载肆言斥责,不臣之意显然。《靖难记》虽加删润,与原文尚未甚远,至《实录》则但以八事自辩, 而不复以太祖之死故入恵帝罪,语气温顺,若出两人。”[20](卷4,P54)在此黄先生对比发现,同一上书,在不同史籍中内容截然相反,因而对这“八事”的真实性持怀疑的态度。可惜黄先生也没有注意到这份伐燕诏书,未得确凿证据进行根本的否定。
据此诏书所述,因燕王悖逆所为,太祖震怒成疾“至于升遐”,朝野内外所共知。因太祖之死,燕王背负恶名,已成众矢之的“海内闻知,莫不痛忿”。但据《奉天靖难记》燕王反以长篇大论上书朝廷,以太祖之死故,责难建文帝:
……,矧既病久,焉得不来召我诸子见也。不知父皇果何病也,亦不知服何药而不瘳以至于大故也?《礼》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来报,俾得一见父皇,知何病,用何药,尽人子之礼也。焉有为子而不知父病者?……[1](卷2,P75)
此上书也必非原作,当为后来编撰《奉天靖难记》所伪造。
三、余话
燕王长期居藩北平,势力不断膨胀。又多次出征蒙古,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身边的术士幕僚极力怂恿鼓励燕王图谋大位。[7](卷150《金忠传》,P1163;卷299《袁珙传》,P199)私交使臣,为太祖严厉禁止。[4](P128)但燕王经常私自结交路过北平的朝鲜使臣。燕王温良恭谦,待以上宾之礼,颇动情感人。[14](上编卷1,P129)朝鲜使臣觉察出燕王图有大志,不甘久居王位。[14](上编卷2,P209)一则史料说燕王极力结交太祖晚年宠幸的李贤妃,“令赞易储之计”。[16](P1226)洪武二十八三月,能征善战的二兄长秦王朱樉薨世,三十一年三月,同样雄武有智略的三兄长晋王朱㭎去世。燕王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燕王更加有恃无恐,更加心志不安,正如诏书所言“昔先皇帝时,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不轨之举已为明太祖察觉,“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从这篇伐燕诏书分析看,洪武朝末,燕王行为悖乱,已失太祖意。当在明太祖在世之日,燕已下定决心对抗朝廷。以太祖的明察秋毫多疑猜忌,必有应对之措施。故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五月间连发四道敕令,统兵御北的重任,交付其他诸王。只不过明太祖行将就木,对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的燕王已无法亲自铲除。临终,告戒皇太孙燕王是新政权极大的威害,并要驸马梅殷全力辅佐太孙。[9](P361)以太祖的威严,诸王尚多不法之事。年方二十的皇太孙,更是难以驾驭诸皇叔。如此看来,如果假以天年,太祖也必定要行削藩之策。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是实现皇祖的遗志。遗憾的是,建文帝未能实现皇祖的遗志。太祖遗诏中的“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7](卷3,P783)显系防范诸王。遗诏中“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官民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护卫官军王自处分”,[1](卷1,P16)显系为削夺诸王军权,特别是针对燕王。明太祖去世,建文帝速敛速葬,前后仅止七天,也必是出自明太祖临终前的安排。朱国桢亦言:“故即位而葬,同日并举,皆高皇遗命。正以速葬消诸藩入临觊望之心。建文宁敢自为迟速?然自来葬速,未有如高皇者。忧深虑远,何所不至。”[21](第428 册,P620)显见当时情况的危险。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钞本《明太祖钦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太祖发给晋王朱济熺(时朱棡已薨,子济熺嗣立)一道谕旨:
说与晋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隄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里行。[22]
该史料的所透露出的太祖本意,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该史料透露出的本意就是太祖晚年在戒备提防燕王。[23](P242)有学者认为该史料是太祖晚年仍旧信赖重用燕王的有力证据。[3]因燕王悖逆所为,五月初八太祖圣躬不豫。五月十二日父子关系已非正常。很显然,这道圣旨的意思是 要晋王戒备四叔燕王或者有他意。笔者认为,这是在燕王有突发事变时,太祖授予晋王的处置策略。
对于以上史事的考证,还是甚为必要的。正如南先生所言:“关乎对明太祖逝世前夕燕王朱棣政治地位及其与朝廷关系状况之了解,亦关乎对靖难之役发生背景及其当事双方责任之评价,事非小可。”[3]
注释:
① 永乐元年敕令重修《明太祖实录》,历半年成。永乐九年又敕令再修《明太祖实录》,历六年成。
② 张廷玉最后定稿的《明史》(336 卷本)改作文奎“燕师入,莫知所终”,掩盖了成祖的残暴。
③ 关于这份诏书,在流传过程中,屡被删改。《国朝典汇》《明朝小史》《姜氏秘史》《宪章录》等均有收录。比较而言,惟万斯同《明史稿》(416 卷本)与《国榷》收录最为完整详细。但是,本源于万斯同《明史稿》(416 卷本)的《明史》已将“昔先皇帝时,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私印伪钞,阴结人主,朝廷穷极,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这样的字句删去不提,显系史官为成祖隐恶护短。当初布告天下的此诏书,内容可能更加丰富。
④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
⑤ 《皇明通纪》作“四月,上不豫。闰五月十日,上崩,寿七十有一”。与实录相差几个月。
⑥ 《明太祖实录》卷257 所载,太祖临终之际,令燕王南下。果有此令,也必是惩处之意。重修太祖实录,谓太祖临终召见燕王有传位之意,抑或为馆臣篡改了太祖的本意?
⑦ “乃告于庙,乃命武臣总师往征之。且戒之曰:‘蠢兹北藩,其杰骜者,吾宗亲也。其胁驱者,吾良民也。毋敢疾攻,毋庸多杀。临境示威,以致来附而全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