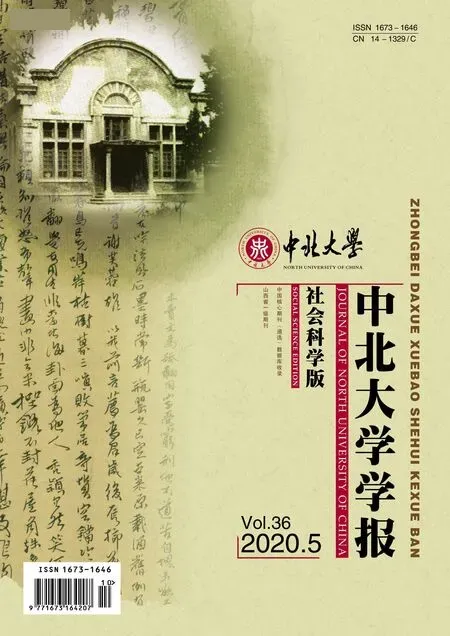论杜甫诗歌的一诗多赠 *
2020-12-09卫玥
卫 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杜甫存诗1 400多首, 其中寄赠诗占不小比重。 部分作品有明确且唯一的寄赠对象, 如《赠李白》《赠韦左丞丈济》《寄高三十五书记》《奉赠严八阁老》等。 部分作品非寄一人, 有多个寄赠对象, 如《奉留赠集贤院崔、 于二学士》《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等。 一诗多赠之作的写作前提是赠诗对象的相关性及时空上的同一性: 诗歌中多个寄赠对象的关系或为同处某地, 如《奉留赠集贤院崔、 于二学士》《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等; 或为共往某处, 如《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寄李白》《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递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等。 寄赠对象的非唯一性使得此类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单一寄赠对象诗歌中主客对话的特点, 在这类诗歌中, 杜甫与多个寄赠对象一一对话, 诗歌文本更具张力。
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此类拥有多个寄赠对象且各人物之间有实质性人物关系的文本。 综观诸研究著作, 如巩本栋《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1]将关注点集中在“唱和”概念的厘清及唱和双方来去的互动关系; 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2]着眼于社会背景下的唱和诗特征; 诸舒鹏的《杜甫与唐代唱和诗演变》[3]则突出了赠诗写作的公共性及其中赠寄互动在体例、 内容上的对照表现; 崔媞《自注“来诗”与诗歌空间的扩容》[4]则注意到杜甫诗中“他人原唱”的影子, 为赠诗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但这些讨论未对寄赠对象的复杂性给予较多关注。 本文所讨论的即此类一题多赠之作, 其寄赠对象的非唯一性及诗歌文本中的“多重对话”, 为我们了解、 审视杜甫的艺术才华及人格魅力提供了又一途径。
1 寄赠诗歌的功能
寄赠作品在作者创作之初, 就有着传情抒志的目的和作用, 此类诗歌亦如此。 将《杜甫集》中赠诗的主要功能进行梳理, 可大略分为送别赠友、 筵席抒怀、 劝勉慨叹、 举荐人才四类。
1.1 送别赠友之作
这类作品在赠诗中占据着不小比重, 主要是诗人在送别朋友时请其传信或者兼寄他人之作。 以《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为例。
该诗为天宝十四载(755年), 杜甫送蔡希鲁归陇之作。 诗歌前四联叙蔡之志雄气猛, “云幕随开府”至“突将且前驱”四联叙蔡归陇之事由, 详述其随哥舒翰一同入京, 后先行归陇这一事件的始末[5]33; 至“汉使黄河远, 凉州白麦枯”则巧用意象, 将蔡适之陇右道与汉之旧郡并提, 以汉使出访之事比蔡归陇右之由, 在景物描写的转换中遥想蔡都尉归陇之景, 此时高适亦在陇地[5]33-34; 末则以“因君问消息, 好在阮元瑜”之句, 因蔡寄高, 将隐含对话者转移到高适身上。 因前文“汉使黄河远”之铺垫, 以汉使出访之典比蔡都尉带信之举, 送别与兼寄之意自然衔接, 诗歌功能更加丰富。
因寄赠对象的多样性, 此类诗歌多使用“叙离别之事, 送寄赠对象甲——地点、 事由之过渡——寄赠对象乙”的结构, 除上文之例外, 如《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寄李白》中用孔巢父“南寻禹穴见李白”之“禹穴”地点作为过渡引出另一寄赠对象李白; 《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 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 因示从第行军司马位》中以“楚宫腊送荆门水, 白帝云偷碧海春”之“楚宫”“荆门”地点, 过渡引出另一寄赠对象杜位, 都可佐证。
1.2 筵席抒怀之作
此类诗歌以记录、 回忆筵席之场景为主要内容, 寄赠对象多身处其间, 作者往往以筵席为契机向好友抒发内心情志。 如《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6]459:
秋日野亭千橘香, 玉盘锦席高云凉。 主人送客何所作, 行酒赋诗殊未央。
衰老应为难离别, 贤声此去有辉光。 预传籍籍新京尹, 青史无劳数赵张。
此为广德元年(763年)杜甫在窦少尹饯别筵上的赠诗。 开篇便是筵席上的自然之景, 颔联则引入章彝, 叙述主人之厚情; 颈联则在欢乐之景中闯入衰老伤离的作者形象, 至尾联乃一转笔调, 以意气风发的窦少尹形象作结。 一篇之中, 在两个寄赠对象之中插入作者的存在, 暂时阻碍了诗歌意脉的流动, 这种“乐—悲” “意气风发—穷老无为”的对比, 使得单一的抒发赠别之情的诗作中, 兼有作者不得任用的复杂心理及不忘好友、 勉励勤政的赤忱之心。
律诗《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 送殷六参军归澧州觐省》[6]989中, 则体现出了主客不同的特点: 即多个寄赠对象之间存在叙述比重的差异, 如:
佳士欣相识, 慈颜望远游。 甘从投辖饮, 肯作置书邮。
高鸟黄云暮, 寒蝉碧树秋。 湖南冬不雪, 吾病得淹留。
开篇两句即以自然之景刻画留别之情, 颔联以“投辖井中”之典烘托蔡侍御留别盛情, 第四句则巧化“殷羡付诸洪乔”之典, 名、 事兼对, 点明托殷传书之实, 颈联则“我—他”相对, “五(句)羡殷, 六悲己”[6]990, 衬托自己离家淹留之无奈。 直至尾联, 作强慰之语收束前文。 黄生白山曰:“公欲托殷寄书, 诗故归重于殷, 蔡侍御则安顿在投辖句中, 与他筵送客详主异宾者不同。”[7]2008此言得之, 这种写作重心的差异体现了杜甫详略得当的安排, 在这些描写中, 杜甫为每个寄赠对象预留了一定的描写空间, 丰富了诗歌意蕴。
1.3 劝勉慨叹之作
此类作品抒发的感情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 行文中采用的艺术手法及感情之间的细微差异更为引人注目。 以《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6]271(以下简称《寄高适岑参》)及《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6]274(简称《寄贾至严武》)为代表, 两作同为杜甫劝勉慨叹之作, 也均在诗作中引入了高岑、 贾严多个寄赠对象。 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 因情感抒发的细微差异, 杜甫在论及寄赠对象的时候分别采用了并叙、 分叙的方法, 现选取片段进行相关论述。
仇注对排律的章法有着这样的论述:“凡排律, 多在首联扼题, 若作长排, 必在首段总挈。”[7]645诗歌背景及感情基调的不同使得两作在开篇部分就显示出并叙、 分叙的差异。(1)前诗中高岑正常迁调, 后诗贾至被贬, 严武也因房琯之事被牵连, 故《杜诗详注》中有“前章寄高岑, 语无悲悯, ……此章寄严贾, 语多感慨, ……同一官职, 而词语不同, 意各有为耳。”之语。 (见《杜诗详注》第654页。 )《寄高适岑参》因为要抒劝勉、 宽慰之意, 开篇便以“故人何寂寞, 今我独凄凉”做慨, 将高岑“并叙”, 将二人与己、 与古人进行对比, 在下一部分中, 并提高岑, “高岑殊缓步, 沈鲍得同行。 意惬关飞动, 篇终接混茫。 举天悲富骆, 近代惜卢王。 似尔官仍贵, 前贤命可伤”, 用前人之迹衬托二人的境遇; 《寄贾至严武》中, 杜甫分叙两寄赠对象, 各述个人坎坷境遇, “衡岳啼猿里, 巴州鸟道边”“长沙才子远, 钓濑客星悬”, 作者分别用衡越、 巴州分指贾、 严, 用贾谊、 严光的典故切二人之姓, 围绕着“故人俱不利, 谪宦两悠然。 开辟乾坤正, 荣枯雨露偏”的中心思想进行烘托、 论述。 两作中都有作者“自我”与“他者”的对比, 前者以作者与二人境遇的差异对比烘托高岑二人的幸运, “荆玉簪头冷, 巴笺染翰光。 乌麻蒸续晒, 丹橘露应尝”, 选取了系列景物描写“他者”; 后者则采用“贾笔论孤愤, 严诗赋几篇”“贝锦无停织, 朱丝有断弦”的描写, 抽象隐秘地揭示了小人构害的危险境遇。 将高岑并叙, 以与前贤对比, 突出二人境遇之佳; 贾严分叙, 各叙个人坎坷之境遇, 以增加知遇之感, 悲悯中寓宽慰之情, 虽均为宽慰之作, 情感抒发实各有侧重。
1.4 举荐人才之作
不同于《杜甫集》中求官的自荐之作或有意为之的荐人之作, 此类赠诗中的荐人之作, 多为杜甫借“带信” “顺路”之契机, 向相亲好友举荐人才, 诗歌整体呈现出自然而不刻意的特点。 在《送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6]546中, 杜甫向好友贾至举荐唐十五; 在《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6]451中, 杜甫向苏使君提到祁录事的“长才”, 暗含举荐之意; 关于《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6]52, 后人亦有“杨必为蜀中诸道使, 而张参其军, 此四十自荐书也”[7]196之点评, 亦见其荐人之意。 此类诗歌中被举荐人、 举荐人、 纳荐人的共时在场, 使得此类诗歌具有了不同与一般“直荐”之作的特点。
以《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6]546为例, 该诗十二句为一层, 末尾八句为一层。 首则以动物作喻, “白鹤久同林, 潜鱼本同河。 未知栖集期, 衰老强高歌”刻叙惜别之情, 次则借“胡星坠燕地, 汉将仍横戈。 萧条四海内, 人少豺虎多”之语叙战后慌乱, 末则引入贾至, 却一反前文哀世全身之意, 向贾至举荐人才, “南宫吾故人, 白马金盘陀。 雄笔映千古, 见贤心靡他。 念子善师事, 岁寒守旧柯。 为我谢贾公, 病肺卧江沱”, “南宫”四句, 叙贾之好贤, “念子”之句明唐之才华, 在对唐、 贾二人进行赞美的同时, 又隐含着二者可互为协助的荐才之意, 末在陈述自己老病的景况时, 不忘借唐之口感谢贾公, 展望贾对唐的起用之恩时, 也表达了对贾至相惜之情的感激。 一篇之中紧抓荐人之意, 兼有对战争离乱的哀叹、 对故交才华的欣赏、 对怀才不遇的无奈, 对身边高节之人的赞赏及对未来的期望, 诗歌内涵丰富深厚。
综上, 因寄赠对象的不唯一性, 此类寄赠诗歌在诗歌功能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以某一功能为主, 间以其他附加功能, “一诗多赠”之作中诗歌功能及情感表达的多样性、 复杂性, 是此类诗歌区别于一般寄赠诗的重要特征。
2 受赠者的多重身份
在多个寄赠对象共时存在的情况下, 诗歌写作以谁为中心、 各对象描写的比重如何进行分配、 作者背后的意图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类诗作的诸多受赠者中, 有些受赠者在诗歌描写上所占的比重很低, 就其在诗歌中的作用而言, 他们充当着“传话者”的角色; 有些对象虽略有着笔但并不是行文叙事的中心, 多为杜甫意图或感情的“旁观者”; 有些对象则被作者大书特书, 处于诗歌的中心位置, 是事件发展的“主脑者”。
2.1 传话者
前文已经提到, 此类赠诗行文成立的前提是时空上的一致性, 这一特点为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 许多寄赠对象因其与另一寄赠对象空间上的一致而被赋予了“信使”的功能, 成为杜甫向另一寄赠对象表情达意的“传话者”。 以《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6]186为例:
不见旻公三十年, 封书寄与泪潺湲。
旧来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诗谁与传。
棋局动随寻涧竹, 袈裟忆上泛湖船。
闻君话我为官在, 头白昏昏只醉眠。
此时许八回江宁省亲, 集中前有《送许八拾遗归江宁省亲》[6]185, 杜甫因与许八相熟, 托其给老友带信, “前六怀旻上人, 末二自叙近况旧事”[7]458, 仅在末二借许八之手, 表达了自己对老友的怀念, 可见此诗中“传话者”的存在。
上元元年(760年)崔五侍御过彭州, 杜甫有绝句托其转致高适[5]62, 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6]330:“百年已过半, 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 何時救急难。” 前两句短短十字刻画出了诗人此刻的窘态, 年老衰病, 更是在收获之季转入饥贫。 末二单刀直入, 发出了“何时救急难”的呼号, 没有丝毫铺垫, 单刀直入, 可见杜甫此时生活的困境, 盖求高适接济生活。 此作中, 崔五侍御的“存在感”很低, 他在文中只起着“信使”“传话者”的作用, 其形象仅为“工具人”。
概言之, “工具人”的存在, 多起着叙述事件始末、 交代背景的作用, 此类“工具人”的被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作者多有交情, 如许八、 崔五侍御、 段功曹等人[8]117-151, 作者有许多寄赠对方的作品。
2.2 旁观者
“旁观者”在此类诗歌中所占的比重不大, 在两个及以上的寄赠对象中, 他们处于次要地位。 如五律《王竟携酒高亦同过, 共用寒字》[6]376中, 杜甫、 王抡、 高适三人同座饮酒, 诗作中前两联点染周边景色, 颈联叙述共饮事件, 尾联以调谑高适之语收束, 王抡这一“旁观者”参与了三人饮酒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 却并未在杜甫对事件的记叙中占据主要地位, 他就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旁观者”, 既不起送信的作用又不是主人翁的地位, 因此显得“多余”。
五律《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6]448中:
旧相恩追后, 春池赏不稀。
阙庭分未到, 舟楫有光辉。
豉化莼丝熟, 刀鸣鲙缕飞。
使君双皂盖, 滩浅正相依。
王汉州、 杜绵州本是此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但未在诗歌中占据主要位置, 前二述房琯旧恩; 对颔联的解释则多有不一, “赵曰旧相言房琯也, 指言于恩追而未行之间, 則数游此湖, 此追道其实也, 又言阙庭未到之间, 且于此游湖而当承恩命时, 则舟楫为有光辉也。”[9]仇注则以为“阙庭未到, 就自己言, 故用分字”[7]1007。 但此联和王、 杜二人无关是毋庸置疑的; 颈联述房湖所产, “三顶恩追, 叹不与房相偕往”[7]1007; 末则点明游赏之主人公。 王汉洲、 杜绵州本应是此次泛湖事件描写的中心, 在实际行文过程中却成为杜甫回忆与房琯友情的“旁观者”。 逻辑上的叙述重点与实际情感中的叙述重点产生了偏差, 产生了极大的艺术效果, 正如仇氏所云:“或将上四句全主房湖说者, 曰恩追, 曰未到, 曰光辉, 为知己之感, 故三致意焉。 但此诗本为王杜泛湖而作, 不应多叙房事也。”[7]1008
在此类赠诗中, 各寄赠对象虽然都见证了事件的发展, 但因写作目的及表达情感的不同, 作者对各对象描写的比重有着一定的差异, 这类诗歌中普遍存在着逻辑主体和情感叙述主体之间的差异, 也正是在这种错位中, 杜甫个人情感的偏向性得到了彰显。
2.3 主脑者
“主脑”为戏曲批评术语, 原意为“一本戏中, 有无数人名, 究竟俱属陪宾; 原其初心, 止为一人而设”即“作者立言之本意”[10], 此处借指杜甫一题多赠诗中的此类人物形象: 行文过程中, 多个寄赠对象间没有明显的主次关系, 在事件叙述或情感抒发的整体中, 他们均占据重要地位, 属于全诗的中心, 为全诗的“主脑者”。 此类代表作有: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缺》《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 武判官弟赴成都府》《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等。
以《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6]800为例, 此诗为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写给郑审、 李之芳的诗作, 二人“时俱在峡外”[11]772。 诗作起即抒怀, 叹己之漂泊, 点咏怀之由, 叙在夔之情景, “吊影夔州僻”起, 述长安战乱往事; “侧听中兴主, 长吟不世贤”为过渡, 称颂郑、 李二公; 至“每欲孤飞去”起, 述漂泊无依, 旋即以“雕虫蒙记忆, 烹鲤问沉绵”等句述郑、 李对己之挂念; 至“借问频朝谒”述己之无官, 旋即以“声华夹宸极”等句勉二人为官; 末明自己欲出峡求禅与二公相晤之意。
在诗歌结构中, 为了表明作者兼重寄赠对象的态度, 全诗中各寄赠对象之间的描写也较为均衡。 此类诗歌中, 作者或“分提”或“并提”(如上文关于高岑、 贾严的论述), 在着笔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别。 程千帆先生曾指出:“一与多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曾被诗人们在布局、 用韵等方面加以运用。”[12]16的确如此, 杜甫在诸如《天末怀李白》 《八哀诗》等赠诗中, 采用了将笔墨明显偏重某人的写法, 而在此类寄赠对象扮演“中心人”的诗歌中, 作者在各寄赠对象之间基本做到了笔墨平均, 不可不说是有意为之。 此外, 就诗歌情感而言, 郑审、 李之芳为诗中隐含的对话者, 表达的感情虽整体较为简单, 但较单一的寄赠诗更添深意。 该诗写作背景为: 李之芳因出使吐蕃被扣留至北地, 至广德二年(764年)得以归国, 任太子宾客[13]346; 郑审为杜甫好友, 且为郑虔之侄[14], 此时官至秘书少监, 其为官也屡遭升迁, 此诗中并置郑、 李二人, 将三人个人之机遇融入时代背景, 慨叹之感更显历史厚度。
3 寄赠者的情感
前文已提及多个寄赠对象对诗歌功能的影响, 寄赠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诗歌的抒情风貌, 寄赠对象的非唯一性使作者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寄赠对象, 这一特点使此类赠诗的情感抒发呈现出自由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3.1 对象的“亲密性”
《杜甫集》中有百余首赠作, 这些诗歌多感情真挚, 其中有不少是杜甫困游长安时的干谒之作, 如《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等。 尽管杜甫尚能做到不移节, 咏“白鸥没浩荡, 万里谁能驯”之语, 但仍不免阿谀奉承。 如《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中较夸张地称赞张垍之才能、 家世之显赫、 皇恩之重, 《旧唐书》卷九十七记载长安沦陷后其兄弟二人“果受禄山伪命”[15]3059, 可见张垍之人品, “杜甫当时向此等小人干谒, 折腰乞怜, 内心必有极其无奈的苦衷。 想必杜甫也承受了自责的内心交战”[16]。
与上不同, 本文讨论的此类诗歌中, 因行文中隐含的他者数量较多, 且托付带信的人多为熟识, 托人帮忙之事即便有“他者”的见证, 反而显得真挚坦荡。 如五绝《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6]330, “百年已过半, 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 何时救急难”, 首二直点己之窘迫, 末二直以“何时救急难”点明文章主旨, 无其他类似作品中象征、 夸赞之语。 《重简王明府》[6]366一诗同为救济主题, 通篇象征, “叶县郎官宰, 周南太史公”分指王潜与作者, 末即以“骥病思偏秣, 鹰愁怕苦笼”为喻, 象征己之窘迫, 不若前者真挚自由。
在普通的干谒诗歌中, 杜甫为了达到希望被援引、 提拔的目的, 多采用“‘开头恭维对方—中间述说自我情况—末尾点出期望援引’三段式规律”[16]。 本文所讨论的诗歌中, 也有不少推荐之作, 但因作者与寄赠对象的“亲密性”, 双方在行文中保持着平等的关系, 感情也更显真挚。 如《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賈侍郎》等诗, 杨侍御、 贾至与杜甫交好[8]142, 因此杜甫在诗歌中强调的也多为杨、 贾二人与自己的匪浅关系及二人的求贤之德, 如“皇华吾善处, 于汝定无嫌” “南宫吾故人” “贤心靡他念”等句。 这类作品在抒发感情时, 尽管也讲求艺术技巧, 但与赠谒诗相比, 多了情感抒发的朴拙和诚恳。
3.2 文本的“公共性”
直观来说, 一诗多赠将原属两人的隐秘情感向第三人、 第四人开放, 这使得诗歌文本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 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 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景中, 杜甫以高超的艺术技巧, 隐秘曲折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 杜甫曾多次在诗歌中告诫对方, 不要随意将诗作进行传播, 如《泛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 因寄岑中允参、 范郎中季明》中, 有“见酒须相忆, 将诗莫浪传”之语;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中, 有“定知深意苦, 莫使众人传”之语; 也因“公共文本”这一性质, 隐晦地向多个朋友提出谨言慎行之诫, 如《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中有“临深莫相违”之语, 可见该类文本在欲说与欲隐之间的张力。
以《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6]481为例: 该诗歌是杜甫离蜀之时, 在饯别筵上留赠章彝及其他幕府诸公的作品。 章彝初为严武之属, 与杜相识后颇有往来, 集中《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 得风字》《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章梓州水亭》《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山寺》《陪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冬狩猎》《桃竹杖引赠章留后》等作见其交往的密切程度。 章彝对杜甫颇厚, 赠其桃竹杖、 资其南下之舟, 杜甫对章之为人虽不敢苟同, 但因受人资助, 仅在一些诗歌中有些隐秘的微辞。 如《山寺》中讥其“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 章彝以桃竹杖相赠,杜甫就规其“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17]342。 在《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中, 杜甫将隐蔽感情在公开场合中进行了展现, “常恐性坦率, 失身为杯酒”, 看似是述己之性, 但背后隐藏着另一层内涵: 蜀地使作者不能心安。 此时严武入朝为官, 章彝待己颇厚, 但杜甫因章彝性格之跋扈(从前文《桃竹杖引赠章留后》及严武杖杀章彝事可窥一二)想要远离该地, 此意图因幕府诸公的见证, 在诗歌中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层次: 其一, 我自知性格太过孤僻(常恐性坦率, 失身为杯酒)(2)诸多论文都曾涉及杜甫的个性特征, 参见贺严: 《论杜甫性格与其诗歌创作》, 《杜甫研究学刊》, 2007年第1期; 刘曙初: 《论杜甫与中国狂士传统》,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吴明贤: 《试论杜甫的“狂”》, 《杜甫研究学刊》, 1996年第3期。, 在这里待下去可能会得罪更多人遭人厌弃, 不如南适吴越; 其二, 我之前曾多次劝谏, 您不纳谏, 我不如离去; 其三, 幕府同僚都在场, 你我今后各自怀念, 不复联络。 因为幕府诸公的见证, 原本很私密的个人请求在送别场合被作者公开, 颇有“决绝”之意。 故王嗣奭有云:“章留后所谓多不法, 而待杜特厚, 公诗屡谏不悛, 想托词避去, 乃保身之哲, 不欲以数取疏也。 不然, 有此地主, 不必去蜀, 又何以别去而终不去蜀耶。”[9]1066足见其情感意蕴。
3.3 人物的“特殊性”
上文提及, 杜甫在同一首诗中对不同寄赠对象的情感表达略有差异, 在人物关系远近及说话分寸上, 作者也展示了自己细腻的情感体察能力和高超的艺术手法。 如《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中, 杜甫与郑、 苏二人交好, 所存《九日五首》等诗记载了三人的情谊。 杜甫与郑虔是“忘形到尔汝”(见杜甫《醉时歌》)的亲密关系, 因此以“戏谑”口吻调谑郑虔醉酒之态, 苏源明“雅善杜甫、 郑虔”[18]5773且当时在国子监为官, 生活不至困顿, 故杜以对苏源明“赖有苏司业, 时时与杜甫酒钱”之陈述收束全文; 《王竟携酒, 高亦同过, 共用寒字》以白描之法述三人饮酒之事, 高适与杜甫交情颇深, 二人年轻之时即有梁宋之游[19], 中年之后交情不减, 杜甫集中就有《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 《奉简高三十五使君》等诗, 高适去世后杜甫有《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之作, 见其交情, 因而末以“头白恐风寒”之语调谑高适。
以《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6]993为例: 此诗是大历四年(769年)所作, 杜甫此时舟居为家与苏涣相交, 适道州刺史裴虬有书至, 杜甫因作此诗。[5]139“久客多枉友朋书”至“使我夜坐费灯烛”(7联)叙道州书札, “忆子初尉永嘉去”至“明公论兵气益振”(7联)叙道州功业, “倾壶萧管动白发”至“阵前部曲终日死”(7联)记苏涣情事, 末“附书与裴因示苏”(2联)交勉裴苏, 结出寄呈之意。 前文已论及此时裴虬有书至, 因此, 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中, 杜甫将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放在答裴虬之书及叙道州之功业上, 至“倾壶萧管动白发”起才点明自己与苏涣的交往及苏之才, 主次分明, 此为结构上的分寸。
就内容而言, 此诗兼有举荐苏涣及告诫苏涣之意。 《读杜心解》云:“寄递其呈苏涣者, 当饯裴時涣亦在坐, 今作此诗, 省忆往事, 遂连及之, 盖公自呈苏非托裴转寄, 涣亦在潭故也, 读者须认清。”[11]327此时苏涣和杜甫同处一地, 杜甫却在寄给裴虬之书中极力称赞苏之才华, 如“宴筵曾语苏季子, 后来杰出云孙比”之语, 在写给某地长官的书信中提及身边才杰, 其荐人之意不言自明; 据《唐书·艺文志》[20]82及《南部新书》[21]133关于苏涣的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苏涣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及一定政治才能的人, 少年时即做过强盗, 被人称为“白跖”, 杜甫与其惺惺相惜[18]335-339却也担心苏涣性格特征招致的祸患, 《杜臆》云:“裴本端人, 借此引苏欲使乱世奸雄转为治世能臣也, 必致身方能致君, 故以捐躯告之。”[7]2019在较大的篇幅中主要答谢了裴虬对友人的关爱并称赞了对方, 在较小的篇幅中用前文所作的铺垫推荐了人才并以裴为榜样委婉地劝诫了苏涣, 兼顾了结构与情感上的要求, 赞美、 荐才、 劝诫均做到了不失分寸。
4 馀 论
要之, 杜甫诗歌中多个寄赠对象的存在给诗歌带来了许多新的面貌。 一方面这些对象的引入有意、 无意地造成了杜甫与多个寄赠对象的对话, 丰富了诗歌的功能, 在杜甫的诗歌中, 诗是推荐人才的载体、 是寻求友朋帮助的书信、 是劝慰他人的寄托; 另一方面, 多个寄赠对象的存在, 给诗歌带来了克制描写与抒情酣畅同时共存的新体验, 这种长处在排律等善于铺叙、 细描的体制中, 更是充分得到了发挥。 此外, 有限文本中多个“主角”的用笔安排也体现了杜甫的匠心之处。
对杜甫这类寄赠诗的研究还有很多挖掘空间: 后世许多诗人受杜甫影响, 有意学杜, 黄庭坚就有许多一题多赠之作: 如《戏简朱公武刘邦直田子平五首》《道中寄景珍兼简庾元镇》《入穷巷谒李材叟翘叟戏赠兼简田子平三首》《送曹子方福建路运判兼简运使张仲谋》《招子高二十二韵兼简常甫世弼》等。 另外, 此类赠诗中很多具有跨体例性质, 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不仅可以作为赠友诗的一个例证进行探索, 同时也可以看成自述体诗歌[22]的一种特殊类型, 这一类型的多元化可以为解读诗歌提供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