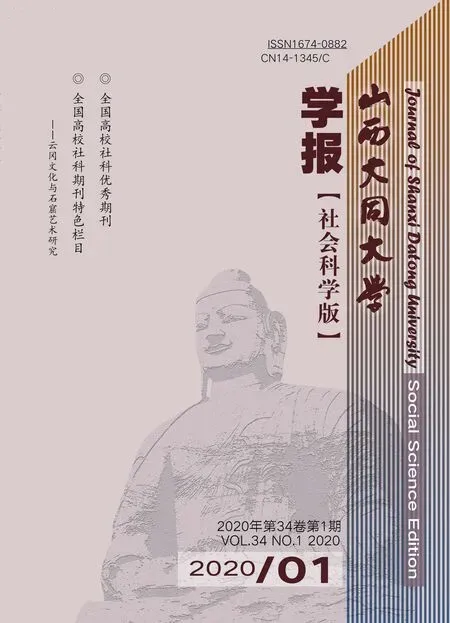丝路文化传播中审美意蕴的衍变
——以云冈石窟雕造艺术为例
2020-12-09闫东艳
闫东艳
(山西大同大学新闻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3)
云冈石窟雕造艺术作为北魏宗教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既体现了平城大同此后作为丝路文化重要节点的必然性,也为隋唐民族交融开启了多样性的可能。云冈石窟造像经历了早期西域风格、中期鲜卑胡风及晚期汉化风格的文化交流融合过程,成为雕刻在石头上的北魏佛教文化传播史。
一、前期:域外西风东渐
汉朝开辟了丝绸之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与沿线各国进行全方位多角度交流互通过程中,佛教经由中亚、东亚、西域丝绸古要塞由印度传播进入我国,佛教雕造艺术随之也传入,至魏晋南北朝进入迅速发展期。北朝鲜卑拓跋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战争,逐步统一了北方,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政权。北魏前期佛教已十分兴盛,太武帝早期灭北凉,深受北凉佛教文化影响、崇信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北方佛教中心始由凉州渐转至平城,西域各国经河西走廊“始遣使来就”,佛教地位不断提升。太武帝执政晚期亲自倡导佛教,王朝出巨资兴建庙宇,至使大量平民出家为僧逃避赋税,严重影响了北魏政权的经济收入,因之王朝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进而产生了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直至文成帝即位才重新开始恢复佛教传播。
道武帝至太武帝间连年拓宽疆域,源源不断把征服地西域及河西走廊各地的能工巧匠迁徙至平城,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储备了大批的人力资源。作为前期北魏的重大国家工程,云冈石窟一期大型窟群的主体建设,主要由来自凉州的僧人和被迁徙至平城的优秀匠人设计,而域外的雕造匠师也为石窟的佛造像活动献计献策。《魏书·释老志》载曰:“太安初有狮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文中“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体现了造像大师们在雕刻过程中对庞大佛像的整体把握能力,“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则反映了匠师僧人们对早期佛造像形制仪轨如何重新建立慎重思考的过程。
云冈石窟一期雕塑艺术受到希腊文化和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希腊文化的审美意蕴体现出崇尚知识、崇尚武力、崇尚艺术的社会价值取向,而北魏鲜卑贵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平城建国初期还没有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厚浸润,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是兼收并蓄,早期佛教沿丝绸之路,经希腊、印度、中亚、新疆等地传入内地,各种异质文化也随之而来。此一时期云冈石窟佛造像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第18 窟造像佛祖十位弟子雕塑呈现出生动写实的美学意蕴,体现出域外浓厚的希腊化思潮,首先整体形象高鼻、深目,充分呈现出域外人种的体貌特征;其次,佛弟子造像背靠石壁,但都采用了圆雕和高浮雕手法,下肢则逐渐隐没于石壁中。这些都呈现出鲜明的希腊雕塑的审美趣味,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中的雕塑及摆放在神庙广场上的雕塑都以圆雕为主,巴特农神庙列柱上的浮雕带也以高浮雕形式为主,且材质多为体积硕大的巨石,有的高达20 米左右。
据《魏书·释老志》载,云冈石窟一期开凿的五窟是由北凉僧人昙曜主持,也被称为“昙曜五窟”。纵观16-20 洞窟佛造像,具有浓厚的域外风尚,窟内主佛体量巨大,造像高度均在 13.5-16.8 米间,大佛高肉髻,方额丰颐,高鼻深目,眉眼细长,大耳垂肩,身躯挺拔、健硕,神情威严、睿智而又和蔼可亲,气度恢弘。佛衣设计为通肩式、袒右、袒右覆肩三种形式,衣内僧祗支饰忍冬纹和联珠纹;服饰体面呈平直式阶梯状,衣料质地柔软而不失厚重,衣纹走向立体,雕刻手法线条纯圆,基本延续了域外犍陀罗风格“服兼厚毡”的思想;造像风格粗犷雄浑、线条流畅,呈现出雄伟健硕的美学风格,这一时期的造像基本是古印度笈多王朝传统佛像形式的赓续,加之东传过程中受到北凉文化的影响,造像也渗透着“凉州模式”中古朴和实用主义的审美趣味。
这一时期的石窟形制也特点鲜明:洞窟主像突出,多为一佛二胁侍菩萨为主,也添加了“故事像”,窟外壁满雕千佛,穹顶和窟门处更雕造了大型护法神像。在寻求本土化审美趣味的同时,也融入了古希腊、古印度、西域传入的粉本雕造技法,新技法融合创造形成了云冈石窟佛造像早期独特的美学韵味。“昙曜五窟”从造像风格到服饰风格都直接受到希腊、罗马、波斯及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广泛影响,彰显出浓重的域外风情。其中第20 窟主尊大佛高13.7 米,形体高大,面容圆润饱满、鼻梁高挺,法相庄严,气宇轩昂,体态肌丰骨硕,因前壁崩塌而被称为“露天大佛”,从任何视角瞻望都能感受到佛的慈悲与宽和,历经千年成为石窟极具代表性的雕造作品,为世人瞩目。
二、中期:鲜卑胡风突显
北魏王朝中期经过几代拓跋王族的治理,统治逐步趋于稳定、经济发展日渐繁荣,帝都平城已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云冈石窟的开凿也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域外艺术元素对石窟造像的影响越来越小,而本地化的鲜卑文化影响越来越明显,体现在建筑、佛像造型、供养人造像、飞天形象、佛像服饰、夜叉发式、部分石窟窟顶塑造等方面。
平城居民主要是鲜卑族和胡人,云冈石窟位于帝都西部,是游牧民族的重要活动区域,鲜卑族和胡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建筑风格穹庐的特点——随意移动、拆迁方便。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穹庐是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也是基本生活空间,其基本形式为:平面呈圆形、圆拱形帐顶呈穹隆状、前部开门,天窗或亮窗开设在易于通风或日照的位置,云冈二期部分洞窟窟顶仍保留有鲜卑胡族特有的毡帐遗风。
鲜卑胡族从东北嘎仙洞而来,累世都有太阳崇拜情结,云冈石窟二期造像的日月装饰体现了其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崇拜敬畏的文化意义。《魏书·太祖纪第二》载北魏皇帝拓跋珪:“母曰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徙,游于云泽,既而寝息,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歘然有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这一期菩萨常戴日月、仰月宝冠,第8 窟窟门两侧神像摩醯首罗天与鸠摩罗天都手持日月宝物,第25 窟窟顶平棊藻井飞天也手托日月。“仰月冠饰或日月冠饰受到了波斯萨珊王朝冠饰的影响”,同时也渗透着佛教文化的影响,因为日月、仰月冠饰在佛教中代表着光明和智慧。
云冈石窟中期供养人服饰也生动体现了鲜卑文化的特色。第6 窟南壁明窗和窟门间雕刻有释迦维摩文殊龛,故事像根据《维摩诘所说经》中的《文殊师利问疾品》雕造而成,维摩诘头戴“尖顶帽”,右手端举麈尾,身穿左衽交领短袖襦袍,双腿自然下垂坐于矮几上,身体向后微仰,身体重心落于向后支撑的左臂上,颌下蓄须,神态轻松。第1 窟内的维摩诘居士头戴胡帽,穿宽袖长衫,外披重裘,右手同样端举麈尾,轻倚隐几,坐于榻上侃侃而谈。造像的“尖顶帽”与鲜卑男子日常戴的“浑脱帽”近似,胡族地域出土的汉画像砖胡族骑手、蒙古墓壁画中的匈奴、北朝出土的陶俑都有“薄毡尖顶帽”形象。第8 、11 窟中三首八臂摩醯首罗天左右侧头、上部莲花中三头四臂阿修罗左右侧头都戴这类尖顶毡帽。学者吕一飞认为“浑脱帽是一种用整张皮(或毡子)制成的囊形或锥形的帽子”。汉族传统服装为交领、右衽,而鲜卑胡族多穿左衽服装,即右压左,左侧衣襟在下。据此,这两尊维摩诘居士造像,容貌和衣着都带有鲜卑胡族的明显特征。
另外,云冈石窟二期雕造的夜叉形象,鲜卑胡族辫发、披发的遗风也生动地反映在夜叉发式上,《维摩诘经·佛国品》:“并馀大威力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悉来会坐。”佛经中将夜叉分为三种:地夜叉、虚空夜叉和天夜叉,并以人的形貌出现。第7 窟和第8 窟出现了多组雕刻夜叉形象,第7 窟拱门西侧塔柱东面第三层所雕夜叉,头部正中梳圆形辫发,辫发中分向两侧弯卷形成“几”字形,头部两侧各有圆形辫发,并呈弯曲状下垂。鲜卑胡族男女皆辫发披发,就是将头发结为发辫、披于背后或肩上,是这一时期平城鲜卑胡族发饰在佛教文化中的重要体现。
中期云冈石窟的开凿依然以皇家为主,其雕造美学风格既沿袭了前期域外东传佛教的美学形态,同时也是佛教造像与鲜卑日常生活的融合,使得佛造像本土化、地域风貌尽显。 具体审美意蕴主要体现为:一是雕造形式“胡风”元素随处可见,穹庐式窟顶、尖顶毡帽、左衽衣领,较之前期“域外风”占主导,样态趋于胡化;二是雕造内容“胡风胡俗”尽显,长腰鼓的高型坐具“筌蹄”、世俗生活中缚裤围裙、长颈琵琶等;三是“胡化”饰品散见,佛菩萨两上臂多有臂钏,五条并列、中串珠、外扎金属箍。生活中鲜卑胡族戴臂钏者甚多且造型奇特。北魏墓葬发掘中常有女性戴首饰、项饰、腕饰等,考古专家也指出“鲜卑人不论男女皆重装饰,尤喜用金银”,胡族装饰品被运用到佛造像中,充分再现了中期石窟造像文化地域性风貌。
鲜卑文化是当时帝都平城重要的文化特征,云冈石窟中期处于西风东渐的发展阶段,雕造风格深受“凉州模式”影响,胡风胡韵浓郁,雕造工匠们凝练纯熟的雕刻技法完整地呈现了拓跋鲜卑族粗犷豪放的生活美学。北魏石窟造像样式从早期“胡貌梵相”逐步演变过渡到中期鲜卑胡风印迹和元素突显,与前期浓烈的域外风相比,中期拥有独特的艺术风韵。
三、晚期:南朝汉风主导
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晚期工程由皇家转向士族、民间,大批留居的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艺术人才,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主要分布在20 窟以西的小窟或小龛,总数达150 余座,也包括在前期开凿的洞窟中增刻的各类小佛龛,营建规模大幅缩减,整体规划难成体系,这一时期的窟式有塔窟、四壁三龛及重龛式三种洞窟形式。这些中小型窟龛数量众多、类型庞杂、式样多变,空间方整狭小;佛造像面庞清瘦、长颈削肩平胸、体态扁平修长,神态清秀俊逸、缥缈虚无;菩萨身形颀长,帔帛交叉,表情孤傲、超尘脱俗。造像服饰多为“褒衣博带”式,衣服下部褶纹越来越重叠繁复,龛楣、帐饰日益繁杂,窟外崖面雕饰也日趋繁缛,造像内容题材日渐模式化、简单化,晚期佛造像的变化深受北魏迁都后“中原模式”的影响。
在南北文化频繁交流互通中,南朝儒家文化对云冈石窟晚期雕造艺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民族传统文化符号体系赋予了佛造像淡雅飘逸的审美情趣。此外,中原汉民族崇奉道教文化,魏晋玄学之风造就了中原士族潇洒落拓不羁的时风,士人所着宽袍大袖的服饰风尚一直赓续至南北朝时期,南朝汉民族追求自由、崇尚无为潇洒空灵的玄学精神。云冈石窟晚期造像与道教文化的“仙化”思想、神仙崇拜思想密切相关,“秀骨清像”式人物造是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思想结合的真实体现。这一时期佛教造像已发展形成了符合当时人们美学趣味的宗教人物形象,并显示出一种通脱潇洒的时代风韵,具有鲜明的汉民族审美趣味的艺术品格。
“秀骨清像”是这时期佛造像最大特色,首先,雕刻技巧与南朝人物绘画技法结合紧密,南朝人物画灵秀隽永,佛造像也普遍呈现出体态修长飘然俊逸的特征;其次,佛造像面部、身躯由早期的饱满丰腴转变为扁平瘦削,神态也由宁静淡泊趋于温和隽秀。另外,衣饰变化也很大,佛像袈裟由通肩和偏袒右肩式改为“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内着僧祗支,胸前佩下垂宽“领带”,下身衣褶层层重叠若菩提叶式,坐佛则出现了“悬裳座”样式,早中期佛衣下摆尖锐的衣角和外侈现象逐步消失。菩萨像头冠低矮,除戴宝冠外,花蔓冠也开始流行;上身璎珞环穿交叉佩于胸腹间,再上绕搭肘,两侧垂下;斜披络腋变为身披帔帛,再交叉于胸前腹际,造型更加宽大,自两肩垂下,绕两臂后向外舞动;裙衣贴身转为裙裾飞扬,宝缯由两侧飘扬转向自然下垂;上身着短衫或袒或内著斜式小衣,下著长裙,衣裙不似前期紧围周身而变为宽敞肥大,大裙下摆呈锯齿状,身形比例明显拉长,颇有南朝士大夫们潇洒飘逸的风度。
晚期云冈石窟的飞天雕刻手法也更为粗犷,头梳高发髻,双足收敛、腰身纤细,姿态更加轻盈,飘逸传神;上着短衫,不露足,裙尾翻卷,大裙裹脚,长巾当风起舞,如羽如翼,身材比例趋于修长,雕刻匠师完美地将飘动的衣带与飞翔的人体结合在一起,形成衣裙与人体间悠然自适的烘托关系。飞天体态夸张,腰部拉长且弯曲度较大,强调变形带来的视觉张力给人以俊逸潇洒、超然出尘的感觉。如第24、30 窟所雕飞天,削肩长颈,面容清峻,身着褒衣博带式汉服,所挽飘带富有动感韵律,整体蕴含高雅洒脱之“中原文化”意蕴。此时期石窟造像还出现了许多贵族供养人形象,小龛供养人造像也有鲜明的南朝汉服特征:V 交领、领结、开襟、偏衫设计,领口加宽,腰线上移系带;供养人衣饰除早期宽袍大袖外,后期更上着及臀短褶、下着宽口裤子、扎腰带,这种轻盈灵动的着装方式也契合了南朝汉文化的审美风格。
云冈石窟后期佛造像的美学意义在于佛教艺术东传后逐步汉化过程中融合了更多魏晋门阀士族审美思想,汉服“峨冠博带”的古风意蕴卓然突出,佛菩萨装向着汉族衣冠服饰转化的倾向,既反映了南朝北朝文化的交融互动,又体现了太和十年后孝文帝实行全面汉化的政治理念,而雕造艺术匠师们也倾注了自己的美学理想和创作才情。至此,云冈石窟造像从早期的“胡貌梵相”演变过渡到晚期“改梵为夏”。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财力所限,云冈佛造像形制基本趋于中小型,雕造技法则大量运用直平阶梯式线条,雕刻装饰平实细腻更贴近日常风尚,佛造像风格趋于常人、身躯瘦削基本接近普通人体比例,更容易被世俗社会所亲近,这和当时平城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相吻合,越来越多的平民希望死后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而佛陀菩萨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精神寄托。
从佛教文化传播角度纵观云冈石窟造像历程,整体呈现自西向东、由北往南的递进轨迹。从石窟造型、佛教题材、雕刻技艺、造像衣着服饰都体现出胡汉融合的渐进过程。佛教石窟造像作为域外东传的“舶来品”,在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后,受到鲜卑拓跋皇室崇奉,再加上西迁而来的僧人、艺术匠师们的大胆创新,佛像雕造的三期过程体现出文化融合与自信。“魏晋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是华夏艺术的瑰宝,也是魏晋风度的理想化表现。从敦煌到云冈,从云冈到龙门,秀骨清像成了至北魏后期以来代表魏晋时期佛教雕塑的风尚和典型式样。成为隋唐以后石窟佛教造像进入繁荣期的先决条件。”佛教文化在北魏王朝传播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域外佛教造像艺术符号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域外、胡族与汉族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新的佛教造像形态,对其后隋唐佛造像造成了巨大影响。研究该时期的雕造美学特征,对于了解汉族、鲜卑族与域外文化融合交流的审美意蕴有很好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