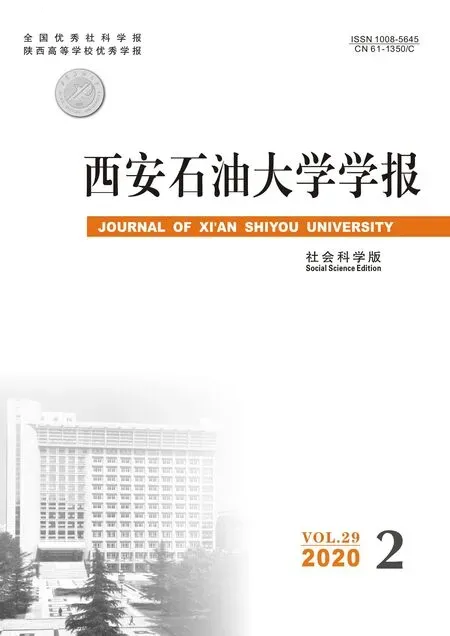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
——重读《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
2020-12-09耿丹青
耿丹青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0 引 言
1946年,中共中央发表《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拉开大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调动了人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推动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意义重大。因此,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小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周立波、丁玲、赵树理这些身处解放区的创作者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笔触伸向了发生在身边的这场土地改革运动,创作出了经典的土改题材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邪不压正》等。在这批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中,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各以其不同的艺术个性,在反映土改运动这一历史性事件上,成为两部互为补充、并耀争辉的史诗性作品。”[1]210同一时期,亲历土改运动的赵树理创作的《邪不压正》也给人们带来很多思考。
通过对这三部经典作品的重新审视,可以看到文本中叙述的土改运动的艰难过程,实际上是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博弈的过程。农民们的圆满结局,土改运动的顺利完成,表现了革命伦理的胜利和乡土伦理的溃败。三部小说选取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这两种伦理的博弈过程,体现了它们独特的价值。
1 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伦理观念一直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对伦理道德的重视是人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一条无形的缰绳。“中华民族是伦理型文化的典型民族,伦理——政治的一体化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2]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特殊的历史时期自然会形成特殊的伦理观念,因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自然形成了革命伦理这一特殊的伦理形态。
自抗日战争开始,整个社会的伦理形态就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革命伦理’主要指的是在解放区时期这一中国现代革命所历经的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并深深地打上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烙印的伦理形态。”[2]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一反前期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民族启蒙的主题,开始大力描写战争、革命、鲜血与炮火,唤醒人们反抗侵略,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在这一历史时期,革命伦理成为了支配解放区的精神主导力量。在战争时期,个人、家庭、血缘、爱情都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切为了革命服务的革命伦理观念。革命伦理强调集体意识,为了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个人要服从于集体。个体意识消失,只存在集体主义,每个人都是革命浪潮中的一员。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潮流中,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再是家庭和血缘的关系而是革命情谊,爱情亲情均已消融在无情的战争中,革命伦理取代了个体伦理、家庭伦理。
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统治中,农村形成了一套自我完善、自我管理的乡土伦理观念。在乡土伦理的支配下,农民一直以来过着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与土地的亲近使他们形成了忠厚淳朴的性格:坚韧、乐观,逆来顺受。乡土伦理告诫农民顺应天命,面对苦难折磨,默默忍受是最好的应对方案。乡土伦理在农村的统治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3]24血缘关系的联结、家族的延续使得乡土伦理的观念随着生命的传承而绵延不绝,宗族意识、人情观念限制着农民的思想。
当革命的号角突破时空界限进入乡村中时,革命伦理就开始了对乡土伦理的突围。在土改小说的描写中,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展开了无声的斗争。革命伦理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和革命武装的保障进入乡村,唤醒广大农民参与阶级斗争的热情。革命伦理通过对土地和财产的重新分配获取合法性,从而使农民接受其观念,自愿为解放战争贡献力量。
2 土改小说中的伦理博弈
在《暴风骤雨》的开头,萧队长带着土改工作队进入了元茂屯,宣告土改运动的开始。萧队长等人此时秉承的是革命伦理的观念,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革命,然而元茂屯中的村民遵从着的依旧是乡土伦理。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邪不压正》中,随着减租清债运动的开展,革命伦理已经开始初步施展威力。在土改工作小组到来之前暖水屯已经进行了一次清算,并斗败了地主侯殿魁、江世荣。张裕民、程仁、李昌等思想先进的农民已经成为了党员,在暖水屯,革命伦理看似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暖水屯的“八大尖”中最尖的钱文贵依旧屹立不倒,部分农民依旧顺从乡土伦理的观念,侯忠全还偷偷地将分到的地退了回去。下河村开展了清算运动,地主刘锡元被斗倒,但是软英的婚事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农会主任小昌分到的果实最多,乡土伦理依旧占据上风。
乡土伦理统治下的农村,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人情、血缘、宗族的种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像是涟漪激荡在水中泛起的层层波纹,给革命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作为乡土伦理代言人的是小说中的地主以及腐化了的村干部。地主韩老六和他的几个“狗腿子”勾结各方势力,长期统治着元茂屯。在危机来临时,韩老六借自己的女儿韩爱贞勾搭分地委员杨老疙瘩。唠嗑会成员张景祥虽然察觉也碍于人情和面子没有说出去。地主钱文贵的女婿是村治安员张正典,他又将自己的儿子钱义送去当兵,并利用侄女黑妮吊着教员任国忠,妄图借黑妮收买农会主任程仁。在暖水屯,他和村里的富农、贫农、村干部、八路军都有牵扯,也因此没有人把他列为斗争对象。下河村中的农会主任小昌,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假公济私,又将得罪自己的聚财一家列为斗争的对象,暗地里想让软英嫁给自己十四岁的儿子。这些人都是乡土伦理观念的忠实拥护者,他们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到革命的进程,因此打倒这些阻碍者是土改工作队的首要任务。
对中国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心中最在意的东西,“老百姓希望得到土地,却不敢出头。他们的顾忌很多。”[4]158。在乡村中,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小部分地主的手中,他们借用各种手段剥夺贫农、长工手中的土地和财富。在乡土伦理占据上风的乡土社会,农民对于这种剥夺是毫无察觉的,他们只是感叹一声自己的命不好,就继续拼命干活,试图获得土地。革命伦理要崛起势必要瓦解乡土伦理。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做保障,借助对土地的重新分配,革命伦理逐渐开始施展威力。为了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身为革命伦理代言人的土改工作者首先要做的是向农民散播革命伦理的观念。和贫苦农民进行交流,组织农会是他们选取的主要方法。这些土改干部将阶级斗争的观念植入农民的心中,将土地分给农民,唤醒了他们斗争的热情。萧队长等人在抵达元茂屯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农民交谈,并由此确定地主韩老六就是主要的斗争对象。通过和土改干部的亲密接触,贫苦的赵玉林、郭全海以及白玉山被革命伦理所感染,勇敢地和地主展开斗争。暖水屯土改工作组成员杨亮也四处走访农民,了解村里的形势,本来已经有些灰心的妇女主任董桂花也因为与杨亮的谈话重新燃起希望。上河村工作团到来后,就将软英叫去谈话,了解村里的实际情况。
在这三部小说里,两种伦理的博弈并非是简单的一次较量,而是反复的艰苦斗争。当村里第一次斗争韩老六时,他主动献出自己的五十晌地以及几头牲畜和几件破衣裳,大伙就心软了。第二次斗争大会,韩老六挨了狗腿子李振江的巴掌,“可是大部分的人,连老田头在内,都不吱声,慢慢地,一个一个地,都走开了。”[5]109暖水屯中的地主李子俊的女人凭借自己的眼泪让上门讨要红契的佃户无功而返。“没有人去接那匣子,他们忘记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完全被女人所演的戏麻醉了”。[4]155地主钱文贵的土地不多,又是抗属,村里没有人想过将他列为斗争对象。身为农会主任的小昌一直掌握着大权,村里没有人敢得罪他。乡土伦理在这几次较量中一直占据着上风。
为了瓦解乡土伦理,作者精心设置了种种突发事件,增强革命伦理的力量。狡猾的地主韩老六突然失去了理智,鞭打小猪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也使得第三次斗争大会胜利召开。在土改工作陷入瓶颈的时候,催化力量章品同志突然来到了暖水屯,他的到来让暖水屯中的农民吃下定心丸,村民坚定了斗争钱文贵的想法,在大会上打倒了老奸巨猾的钱文贵。随着整党会的开展,被错划成分的聚财得以平反,工作团组长让小昌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经历种种曲折之后,土地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革命伦理的势力增强,获得了群众的认可。
当地主跪在台上接受批斗的时候,群情激愤,人们挥舞着手臂,诉说着自己的血海深仇。
“打死他!”“打死他!”分不清是谁的呼唤。
“不能留呀!”又一个暴怒的声音。
“杀人偿命呀!”
“非把他横拉竖割,不能解恨呀。”老田太太颤颤巍巍说。”[5]155
“‘群情激愤’表明人们已然接受或屈从于一种新的伦理——革命伦理,正是这种伦理制造出无数‘群情激愤’的场面。”[2]故事发展到此,土改工作获得了圆满的成功,革命伦理在农村得到了普遍接受,在这场博弈中,革命伦理取得了胜利。然而,虽然这三部小说中的土改运动都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对土改运动的展现是不一样的。
3 不同的叙述重点
在这三部小说中,周立波、丁玲和赵树理各自选取了不同的角度来展现土改运动,他们的叙述重点也落在了不同的地方。
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极力展现的是革命伦理的所向披靡。为了尽可能地消解乡土伦理观念对农民的影响,展现革命伦理的光彩,周立波选择将地主韩老六描述为无恶不作的恶霸型地主。韩老六与村里人没有任何宗族关系,和许多贫农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韩老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连他的兄弟也是土匪,他和日本人勾结,将村中的农民抓去做劳工,想尽一切花招谋取农民手中的田地。赵玉林被逼跪在碎瓷片上,家里穷得连衣服都没有。郭全海的父亲被韩老六引诱着赌钱,输光了所有财产,在寒夜被赶出屋子活活冻死。老田头的女儿裙子因为不愿屈从韩老六被活活打死。
为了展现土改工作的艰难,使革命伦理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作者构设让群众大会进行了三次,前两次的群众大会都被狡猾的韩老六逃脱了。直到鞭打小猪倌这件事的出现,民众的愤怒到达了极点,韩老六才真正被打倒。鞭打小猪倌这一冲突性的事件恰恰表现了《暴风骤雨》的创作缺陷,地主韩老六失去了前期的狡猾和奸诈,行事鲁莽,不顾后果。为了突出革命伦理,乡土伦理的力量在这里被削弱。
为了表现革命伦理的正当性,当代表革命伦理的工作组离开之后,乡土伦理卷土重来,革命的果实被张富英等人窃取。赵玉林牺牲、白玉山调到了县里,元茂屯中只剩下郭全海。由于他势力单薄,被撵出了农会。直到萧队长到来,恢复了郭全海的职务、逮住韩老六、清算了屯里的残余地主杜善人,农民才真正实现了翻身。在《暴风骤雨》中,所有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萧队长这个中心人物,萧队长代表的是革命伦理。《暴风骤雨》将叙述的重点集中在了革命伦理战胜乡土伦理的过程上,实际上这个过程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在周立波笔下,乡土伦理被弱化,革命伦理被增强,这种力量的不对等使得小说失去了真实感,与历史实际不符。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将目光投向了农民,真实地展现了乡土伦理观念支配下忠厚老实的农民形象。与元茂屯不同,暖水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的缩影。在暖水屯中,人情、血缘关系复杂,村里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为土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暖水屯之前进行的清算打倒了江世荣和侯殿魁两个地主,但是革命伦理的观念依旧没有占据主要地位。侯忠全悄悄地把分到的地退了回去,李子俊的老婆一哭,佃户就无计可施。郭富贵等人在去向江世荣讨要红契的时候,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村里的干部张裕民、程仁、李昌心中都还残留着乡土伦理的观念,他们碍于人情和宗法意识无法与地主彻底划清界限,暖水屯中的土改工作无法彻底展开,“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长大的,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唉——,有私情就总难办事嘛。”[4]105
村里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地主李子俊、侯殿魁、钱富贵都与村里的人沾亲带故,他们也不像韩老六那样罪大恶极。丁玲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农村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地主的篇幅不到四分之一。乡土伦理与革命伦理的斗争在丁玲笔下表现的更加真实和复杂。直到故事的最后,随着章品同志的到来,地主钱文贵才被打倒。然而,即使是工作组成员的干部老董也希望自己能够分到几亩田地,娶个媳妇过日子。许多村民更是忙着自己田里的活计,对打倒地主毫不关心。革命伦理虽然战胜了乡土伦理,但是在暖水屯这个地方,根深蒂固的乡土伦理依旧根植在村民心里,比起《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描写更加切合实际。
与周立波和丁玲对土改运动的正面描写不同,赵树理则是借爱情来侧面反映土改运动,将乡土伦理和革命伦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故事借下河村富裕中农王聚财女儿软英曲折的婚事展现了土改干部腐化的现象,为土改工作敲响了警钟。软英喜欢的是贫农小宝,可是父亲聚财反对他们的爱情。在地主刘锡元的威逼下,聚财不得不同意将女儿嫁给刘忠。随着减租清债运动的开展,刘锡元被斗倒,解除了软英的第一次婚姻危机。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农会干部小昌将大部分的田地划给自己,软英的婚事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很快,随着第二次土改运动的开展,本来是中农的聚财却被划为富农,小宝也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小昌列为斗争对象。小昌又利用权力威胁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直到工作团的到来,聚财得以平反,小昌在整党会上被开除党籍,软英的婚事才得到解决。
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借软英的婚事所描写的土改运动将革命伦理和乡土伦理结合得最为圆满。软英的父亲聚财在乡土伦理的统治下,害怕地主的威逼。在乡土伦理的家庭观念下,聚财作为一家之主掌握着女儿的一切,因此软英的婚姻权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在《邪不压正》中,革命伦理没有试图取代乡土伦理,而是与乡土伦理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精神支配力量。软英遭遇的两次婚姻危机都是被革命伦理化解的,聚财被划为富农的不平遭际也是通过革命伦理得到平反。故事的最后,区长对软英说:“我代表政权答复你:你和小宝的关系是合法的。你们什么时候想订婚,到区上登记一下就对了,别人都干涉不着。”[6]82在赵树理这里,革命伦理的正当性通过聚财一家人的遭际得以确立,革命伦理消解了乡土伦理的不合理成分,使两者互相融合,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所以软英的二姨迫切地盼望工作组去上河村工作,期盼他们解决上河村的问题。
周立波、丁玲、赵树理都是著名的解放区作家,三位作家在进行创作时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意在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综合对比这三部叙述重点不同的土改小说,可以看到这场伦理博弈的过程在周立波笔下被简单化,绝对化;在丁玲笔下,乡土伦理在这场博弈中暂时败退,却没有完全瓦解;赵树理展现的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结合则更加真实。三位作家的叙述侧重点不同,但都揭示了这场伦理博弈的结果是革命伦理取代了乡土伦理的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事实。
4 结 语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三部小说在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周立波、丁玲、赵树理通过不同的叙述重点,对土改运动进行了描写。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对比可以看出,隐藏在叙述话语背后的是创作者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土改小说表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是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这场伦理博弈的结果是革命伦理取代了乡土伦理,统治广袤的乡村,成为指导农民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