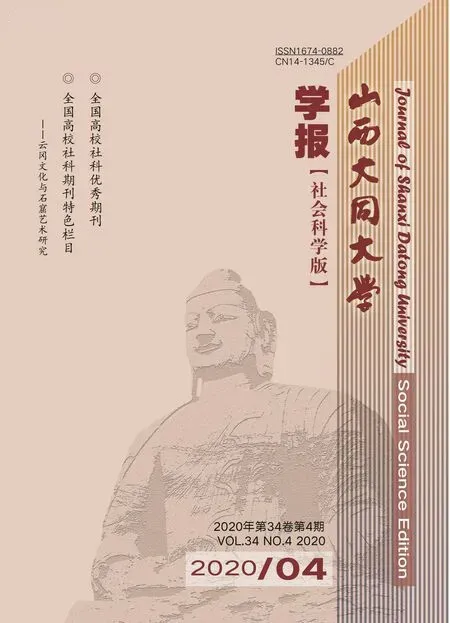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本接受的社会学分析
2020-12-09李婉玉
李婉玉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北京100875)
192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元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此后简称《阿丽思》),这部风靡英美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幻想小说自此开始了它的中国之旅。赵译本在中国非常受欢迎,1922年-1939年间重版4 次,[1]当时甚至有很多小女孩儿名叫阿丽思。[2]赵译本也启发了中国作家,借鉴《阿丽思》的写作风格和技巧,创作出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背景的阿丽思故事——《阿丽思中国游记》(沈从文,1928)和《阿丽思小姐》(陈伯吹,1931)。多年来,翻译学界对赵译本也一直颇为关注,多是在褒奖的基调上,从译者主体性、风格得失、双关语的翻译、文化意象重构等特定角度进行评析。
任何翻译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一方面,从事翻译活动的主体(个人或团体),都处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另一方面,翻译产品的选材、生产和流通,以及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影响。[3]换言之,翻译是一种“受社会调节的活动(socially regulated activity)”。[4]
本文拟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参照社会学路径下翻译研究的三分法,[5]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全面探讨影响赵译本接受的因素。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分析赵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关注文学场域及其次级儿童文学场域的各方行为者的角逐;中观层面,关照参与译本接受的行为者及其互动;微观层面,分析译者个人翻译能力与译本接受之间的关系。
一、译本接受的文学场域助推力
场域是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指“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成”。[6]社会是由不同的场域构成的,场域具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法则,但彼此之间又相互联系和影响。赵译本无论在语言运用还是在内容表现上,都符合当时文学场域的要求。白话文占主导的文学场域和“儿童本位”观占主导的儿童文学场域,为赵译《阿丽思》的接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白话文占主导的文学场域 赵元任以“试验”白话文为出发点译就《阿丽思》,展现了白话文的优势,符合当时白话文推广普及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译作的流通与接受。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文学场域内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较量持续发酵。很多人仍习惯用文言文进行写作,其中不乏林纾等翻译大家。以儿童文学译介为例,虽然早在1898 年就出现了用白话译介的儿童文学作品(即梅侣女士翻译的《海国妙喻》,今译《伊索寓言》,1898年在《无锡白话报》的创刊号发表),但直至五四运动前后,还有大量的文言文译作面世。如191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家麟、陈大镫译《十之九》;1919年,《学生杂志》第6卷第1到12期连载了林纾、陈家麟译《颤巢记》等。同时,各地白话刊物纷纷创建,作品很受青少年学生群体的欢迎。1920年1月,政府通令小学教科书采用语体文(即白话文),提倡统一国语。[7]社会各界对白话文也十分推崇,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最为热烈。
白话文推广的关键正在于“造一可传世之文学……以服古文家之心”,[8]但当时新生的白话文学创作本身存在着很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还未能有很多“可传世之文学”。赵元任以白话文翻译阿丽思的故事,尝试解答这些问题(详见下文),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白话文的普及,[9]白话文大潮也相应促进了赵译本的传播。
(二)“儿童本位”观占主导的儿童文学场域在当时的次级儿童文学场域内,“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和“载道”文学也在相互对抗,前者占主导地位。文学界疾呼真正充满儿童气息的儿童文学品格和风貌,对包括赵译《阿丽思》在内的多部域外儿童文学的译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之前的儿童文学作品基本是以“载道”为目的(先载孔孟之道,后载民主科学之道),服务于儿童教育的现实需求或“成人的政治目的与功利主义的需要”。[10]随着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等西方儿童观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儿童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慢慢得到重视。儿童观发生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翻译观的转变,鲁迅、周作人、胡适、严既澄、魏寿镛、周侯予、郑振铎等一批文人学者,都大力提倡以儿童为中心,为儿童而作、而译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中的童心、趣味性、游戏性得到重视。而《阿丽思》一书全篇贯穿着“没有意思”的笑话和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充分体现了儿童世界的纯与真,正好契合当时盛行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促进了《阿丽思》的广泛接受。
二、译本接受的知名学者支持
“社会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思想的另一重要概念,指“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11]赵译本在客观上十分符合当时文学场域的主导要求,得到了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等知名文人学者的大力支持,增加了赵译本的社会资本。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直接加速、扩展了赵译本的接受。
胡适一直十分欣赏赵元任的白话文和音韵水准,对《阿丽思》的翻译也是赞赏有加,称“这部书译的真好!”。[12]这部译作不仅书名是由胡适拟定,而且赵元任与当时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初次接洽,也是由胡适从中穿针引线。[13]周作人、郑振铎等人从“儿童性”的角度大力推荐这本书。该译作一出版,周作人就在《晨报副刊》撰文发表评论:“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却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所以我推举这部《漫游奇境记》给心情没有完全化学化的大人们,特别请已为或将为人们的父母师长的大人们看——若是看了觉得有趣,我便庆贺他有了给人家做这些人的资格了。”[14]晨报副刊是当时四大副刊之一,具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后来周作人还将该译本收入自己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郑振铎对该书也评价很高:“作者在这里写儿童心理与他们脑筋中所有的梦想,飘忽错乱,若有理,又滑稽,又怪诞,真是一部无比杰出的杰作。”[15]这些评论客观上都为赵译本争取到了更多的读者,促进了译本更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三、译本接受的内在质量保障
通读译者序、凡例,对照译文正文,可以将赵元任的翻译标准总结为兼顾准确和自然。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使用语体文”,[16]“先看一句,想想这句的大意在中国话要怎么说,才说得自然;把这个写了下来,再对对原文;再尽力按照‘字字准译’的标准修改,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国话的时候算危险极度”。[16]
(一)准译及其限度 赵元任按照“先看一句…再对对原文”的方法进行翻译,再尽量按照“‘字字准译’的标准修改”,几乎完全保留原作的叙事风格和写作手法。其中非常有挑战性的双关语、不通的笑话,甚至如阿丽思说话走调(“希汉”、“切怪”)等细节表述也能较为准确地译达。例如,在原文第三章里,老鼠在讲述自己悲苦的身世前讲到:“Mine is a long and a sad tale”,阿丽思将“tale”理解成了它的同音词“tail”,于是接着发问“It’s a long tail,certainly…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赵元任将这一双关语以“委屈”的谐音译出:“你这尾是曲啊!可是为什么又叫它苦呢!”准确译出了原文的双关意味,显示出他精准的语言掌控能力。紧接着,在老鼠讲述自己身世时,原文用阿丽思误解为的尾巴(tail)形式呈现了它的“a long and a sad tale”,字体上大下小,整体上宽下窄、细细长长、弯弯曲曲。译文也很巧妙地保留了这种形式,生动形象。
另一方面,赵元任并未不加变通地追求“字字准译”,而是保留原文意义内核,在不影响主要情节的前提下,适当地调、换、增、删原文字词,以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再现双关或诗文等的效果。同样以老鼠的故事为例。它尾巴状的讲述为:Fury said to a mouse. That he met in the house,‘Let us both go to law: I will prosecute you —Come,I will take no denial; we must have a trial: For really this morning I’ve nothing to do.’Said the mouse to the cur,‘Such a trail,dear sir,With no jury or judge,would be wasting our breath.’‘I’ll be judge,I’ll be jury,’Said cunning old Fury;‘I’ll try the whole cause,and condemn you to death. 赵译为:火儿狗在屋子里头遇着个耗子。狗说‘你别充忙,咱们去上公堂。’我不承认你赖,谁不知道你坏?我今儿早晨没事,咱们同上公堂。”耗子答道,“狗儿,你这爪子手儿,放了我再说话:告人无凭作罢。”火儿答道,“不妨,判官陪审我一人当,全场一致送你去见阎王。”对比原文和译文即可发现,译文作了以下修改:添加了“你别充忙”“我不承认你赖”“狗儿,你这爪子手儿”“全场一致”等内容,略去了“come”,调了“jury”和“judge”出现的位置,将“law”和“death”换成了中国读者熟悉的“公堂”和“阎王”。
在“尽力字字准译”的标准指导下,既保留原文整体内容和风格,又灵活处理各种双关语、打油诗和笑话。这在客观上也使得译文生动活泼,达到了赵元任译此书时推崇的另一标准:自然。
(二)自然地使用白话文 在翻译这本书时,赵元任已经“决定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语言的研究上”。[17]他翻译此书,是为了对“中国的言语…做一个几方面的试验”:一是评判语体文的试验,二是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三是“诗式的试验”。[16]也就是说,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是赵元任检验白话文的首选材料,而他也明白,为了译得“自然”,须使用白话文才行。我们以他提到的三个“试验”为线索,对这个标准进行分析。
第一,赵元任以翻译《阿丽思》为契机,评判白话文是否可以更自然地表意。《阿丽思》一书充满离奇的想象和玩字的游戏,如果用形式规范而且用词用字比较统一的文言,如四六字相间的骈文,很难传达原文明快俏皮的风貌。而白话文通俗浅显,逻辑清楚,描写更为形象具体,容易被孩子接受。在具体翻译时,赵元任对白话文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在叙事部分使用普通语体文,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进行细致真切的描写;在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部分,选用北京方言和语气助词,以更贴近真实说话的状态与人物思维。“例如,在第二章里,阿丽思说,‘啊呀,不好啦!我怕我又得罪了它嘞!’”助词“了”就分别用作“了”“啦”“嘞”三种。[16]赵元任灵活运用白话文,使得故事中的各种形象都鲜活了起来,跃然读者心头。
第二,关于第三人称的使用问题。古汉语只有“他”一个第三人称代词,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但近代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著作的引进,“他”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是否为此创造新字词成为当时学者热议的问题之一。《阿丽思》的故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代名词,比如,在最后一首诗里,出现了多次“he”、“she”、“it”和“they”,只有“他”无法表达清楚原意。当时也有“那女的”、“他女”或“伊”等译法,但若在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里也这么译,就显得生硬别扭,无法表达原作故事与人物的自然灵动,趣味性必然大打折扣。赵元任大胆尝试使用“他们”“她们”“它们”,译本语言显得自然贴近,第三人称代词匮乏的问题迎刃而解。
第三,关于“诗式的试验”。当时,白话文学创作在小说、诗歌等各种体裁中一一展开,赵元任在儿童歌谣方面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白话文的实际运用。《阿丽思》是给小孩子看的,小孩子看书一般会不自觉地念出来,因而原作中的童谣、打油诗等不能译成散文,要译成诗才好听。并且只有译成语体文的诗,才能译得自然。原作中的童谣基本是由一些英语说教诗改编而来,由于历史、文化以及语言的差异,讽刺说教的意味很难译达,但打油诗的内容和韵律基本得到了保留。赵译本里的诗歌读起来仍然押韵,不失儿童性和趣味性。
为了做到翻译准确且自然,使译文既好听又好看,赵元任除了在以上三方面进行试验外,还在语音、形式等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在音韵方面,他强调要关注读诗的节律,以便念起诗来有板有眼。在形式方面,尝试结合视觉效果,比如童谣里如果需要快读两字,在最初的译本里都会“印得靠近些”。[16]第十章最后一只名为骨勑凤的鸟唱着“体面汤”的歌谣跑远,因歌声随清风越听越远,在译文里也印得字体越来越小,可谓更加传神。
四、结论
赵元任《阿丽思》译本自其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关注,接受情况良好,这与译本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和译文质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白话文大潮和“儿童本位”观的盛行,为译本的接受提供了良好的文学场域助推力。其次,场域内多个知名学者大力推荐,通过其社会地位与影响,扩大了赵译本的接受与传播。最后,赵元任本着“给孩子看的书”的原则,准确又自然地运用白话文,翻译了《阿丽思》,译本的内在质量是译本接受的根本保障。
借鉴社会学理论开展译本接受研究,不仅可以看清影响译本接受的外部因素,而且可以进行较为深入的文本分析,对全面考察译本的接受情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