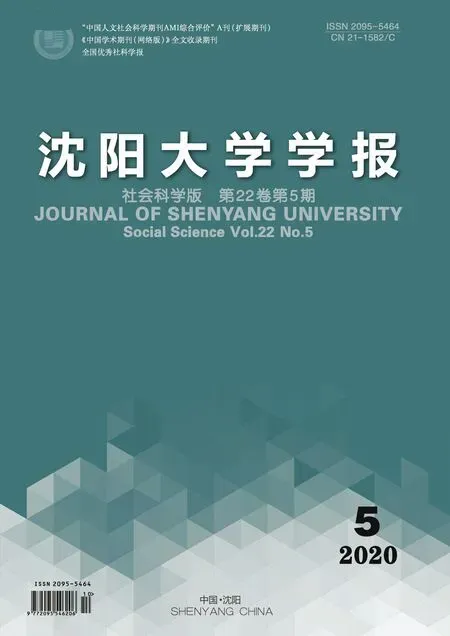青春创伤与工人形象书写
----论“80后东北作家群”的写作
2020-12-08万国欣黄育聪
万国欣, 黄育聪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东北作家群”在文学史上通常指20世纪30年代,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群体。人们早年对东北文学的认识可能都来自于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的作品[1]。虽然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已成为历史,由“文化寻根”掀起的关于东北乡土小说创作的热潮也已不再新奇,而东北文学的创作并没有销声匿迹。新世纪以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80后东北作家”凭借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东北国有企业改制背景的写作,有力地证明了东北文学仍然存有活力和值得关注。近几年,东北青年作家们陆续推出的作品在文坛上引起一定的反响。如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班宇的《冬泳》、郑执的《生吞》等作品均受到文坛的关注。虽然这几位作家踏入文坛的途径、创作风格等有所不一,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有着些许的共同之处。他们在作品中对青春创伤经验的书写,以及对独属于东北地域的、带有东北气息的下岗工人形象刻画的不谋而合,使他们以群体性的方式引起文坛的热切关注。尽管“以一个地域概括几个作家”的分类方式仍然饱受质疑,但质疑无法抵挡一个事实,即在当代文艺领域,一个景观化的东北,正在成为被叙述的对象[2]。
这批生于东北的“80后东北作家群”的青春成长,恰逢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热潮。在作家成长与时代发展的碰撞下,作为弱势群体之一的个人必然无法扭转时代发展的潮流。所以,“80后东北作家”在青春成长时期只能目睹国有企业改制给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动,默默地承受自身成长中内在的迷惘、无措与外部环境强加的伤痛。正如分析20世纪30年代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时无法脱离抗战背景,在分析这几位“80后东北作家”的作品时,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也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出现的带有创伤印记的青春少年形象和下岗工人形象也值得关注。
一、 青春创伤书写
叙述青春,言说成长,是每一位小说家的必修课[3]19。“80后东北作家”的作品也不乏青春主题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侧重对青春创伤经验的书写,其中林立着在各种创伤下选择出逃、自残、自杀的少年形象,这些创伤形象中又隐藏着作家对自身青春创伤的回望与宣泄。
1. 青春创伤
一个作家的早期作品,核心词一定和青春有关,因为青春是一个人精神燃烧的起点[4]222青春与成长是相互伴随、无法分割的,青春意味着成长,成长不可避免地遭遇心理的磨难或精神的创伤。创伤不能修复,磨难不能消除,于青春生命而言,就会引发悲剧[3]19。在青春成长中,因家庭剧变或缺乏家庭关爱等因素导致的带有创伤印记的少年形象,在双雪涛的《跛人》《安娜》《大路》,班宇的《盘锦豹子》《枪墓》,郑执的《生吞》《仙症》等作品中都有淋漓尽致地展现。创伤是引起持久病变的身体损伤,或能导致情绪异常的精神打击。它既包括生理创伤或身体创伤,又包括心理创伤或精神创伤[5]62。“80后东北作家”在作品中不约而同的侧重展示了少年的心理创伤,如在父母分开后借助恋爱转移情感,过早涉及性行为的刘一朵;目睹父亲下岗,随后走上犯罪道路的少年孙程;受尽治疗之苦,父母却不予理解和关爱的“我”;屡次妄想以“自杀”或“自残”行为结束自己生命的安娜;死亡的黄姝、秦理和“小女孩”……这些少年身上无不带着青春的创伤与成长的伤痛。家庭本应该是温馨和睦的殿堂,应该是充满爱与欢乐的庇护所。然而,“80后东北作家”笔下的少年们体会到的却是家庭带给他们的伤痛。“我四岁就开始学钢琴、书法、舞蹈,我妈老揍我……我妈好几次差点把我打死了。有一次她用电熨斗打我的头,我以为自己死了……”[6]119,“把钢琴搬走的那天,我抱着钢琴哭……我觉得如果它不见了,这个屋子真就剩我一个人了。”[6]120安娜遭受的来自至亲之人的痛打与冷落,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心灵上的创伤。一个人得有多孤独,才能把冷冰冰的钢琴当作亲人?《大路》中,“小女孩”的那句对亲人的描述,亲人“和你很熟,但是和你不相干。”[7]也是对心理孤独与创伤的揭示。《仙症》中的“我”因为口吃而被同学嘲笑,父母因而带“我”四处奔波、寻医问药,“在石景山的一间小诊所里,舌根被人用通电的钳子烫糊过,喝过用蝼蛄皮熬水的偏方,口腔含满碎石子读拼音表,一碗一碗地吐黑血。”[8]然而,在“我”已经坦然接受事实的时候,父母却“折磨我”成瘾,以至“我”被迫降级,并患上抑郁症。《生吞》中秦理父亲因是“8·3”大案犯罪团伙主犯,秦理因而被讥讽“犯罪也是种基因,能遗传”[9]。在这种家庭里成长,秦理纵然是天才,却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同学们的排斥、孤立与欺负。同样,黄姝也是因母亲的不法行为而被同学们孤立,她寄居在舅舅家,却被舅舅当作赚钱的工具,在小小年纪里遭受了性的凌辱……由此可见,“80后东北作家”笔下的这群性格孤僻、怪诞,甚至极端的少年,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青春伤痛。作为少年人,他们过早失掉了童年的单纯和天真,像成年人一样用充满怀疑、焦虑,甚至是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世界。但是,他们又无法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坦然地接受残酷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合适的自我拯救之路,因而又孩子气地抗拒着现状,损害着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具有创伤印记的少年有的选择了死亡,但死亡并不是他们最想要的选择,只是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的生命解脱方式。在面对青春创伤时,他们也曾在痛苦里挣扎,在绝望中呼救。如安娜对“我”讲述她童年的压抑与家庭的冰冷;“小女孩”向“我”诉说她的孤独与绝望;秦理和黄姝两人抱团取暖,在防空洞中寻找属于他们俩的星光;“我”对着“白仙家”的嚎啕反省;孙程借助书写来自我拯救,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们求生的努力与挣扎,只不过有的人挣扎成功了,有的人挣扎失败了。因为人的心理素质不同,抗打击能力各异,因而,面对几乎完全相同的创伤性经历,有人一击即倒,有人百折不挠[5]64。
2. 作家的创伤记忆
双雪涛在被问到借助青春记忆与成长写作,想表达什么的时候,回答“首先我觉得我并没有长大……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无声无息地长大了,而且很多人会非常轻易地遗忘自己的苦难,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跟上一代人比,我们的苦难是挺渺小的,甚至是挺可笑的。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我一直认为我们损坏过,有的人后来好了,有的人一直没好。”[10]因此“80后东北作家”的青春创作,不仅塑造了一群具有青春创伤印记的少年形象,还隐藏着对自身青春创伤的宣泄。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沦陷、家国危乱是东北流亡作家带有创伤印记的共同经历,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东北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浪潮与冲击下,以及在这种浪潮与冲击中无法从容应对的家庭与个人,都成为“80后东北作家”带有青春创伤印记的共同经历。那些早已习惯计划经济体制庇护的人群,在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中显得茫然无措。五六十年代聚集到这里工作的人们已经开始养老,接替父辈开始工作的人们此时已经进入壮年和中年,虽然还有劳动能力和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但是迅速调整的命令如又一次的“暴风骤雨”,使一个文化种群集体的生存和心理都被现实挤压到逼仄的境地,焦虑感弥漫全城,从而发展为无序的自我寻找中的集体迷茫[11]。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作家们,自然也受到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生活变动的影响。国家整改大历史情境,让他们心生恐惧。人和工作的联接断裂,带来生活极大的混乱,使他们的心理失衡,在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中,精神的纠结导致行为的滞后[11]。因此,“80后东北作家”在自己的少年时期目睹国有企业改制中父辈们的焦虑,也不得不像大人一样分担着父辈们在市场经济发展潮流中面对的生存压力。所以,他们的青春成长中也有着创伤的印记。他们作品中的对青春创伤的书写,便是对自我青春创伤的疗救。创伤叙事是人在遭遇现实困厄和精神磨难后的真诚的心灵告白。也只有通过真诚的心灵告白,心灵的创伤才能得到医治[5]65。双雪涛自述因住在铁西区,并且是工人子弟而与和平区学校的同学们格格不入,并引来老师的歧视,“我记得有一次开家长会,我妈穿着工厂的工作服去了学校,老师都不愿意跟她说话。”[12]52于是“家境的差别让我从那时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这个自卑感是不用具体的事情提醒你的。当时就清醒地认识到,你无法和这个世界对抗,根本打不赢。”[12]53这种从童年时期产生的自卑感与无力感,是在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的冲击下,由家庭生活境况波动产生的心灵创伤。同样生活在铁西区的班宇也有相似的经历,面对下岗,他说:“当时我就受不了了,那会儿我父母还没下岗,正濒临下岗,怎么‘下岗’突然就变成犯人一样了?我爸爸即将从一个工人变成一个‘犯人’,为什么会这样?”[13]61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当时所有人的困惑。从这时起,班宇的世界骤然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90年代末、2000年初中国东北冰冷的景象,父母下岗,城市凋敝,目之所及一片萧条。另一个是涅槃、枪炮与玫瑰,沈阳地下摇滚乐队疯狂与愤怒的演出现场”[13]60,班宇借助摇滚音乐的放纵与疯狂,将现实中的伤痛尽情地宣泄释放在无措的青春中爱上摇滚,并藉以慰藉、安抚自己深受创伤的心灵。青春无法逃离,也无法反击,只能忍受。但是,加在“80后东北作家”这一代人青春之上的还有沉重的时代伤痛,他们无力反击,只能目睹伤痛并默默承受。只能在伤痛沉淀后理性地回望,然后慢慢揭开已经结痂的伤疤,因为只有正视创伤、书写创伤,才能够治愈创伤。在这个意义上,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作品中的青春创伤书写,也是他们对自我创伤性经历的安抚与疗救。
二、 工人形象书写
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的东北经历着时代的阵痛,曾作为全国工业发展“领头羊”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区与“失业”“贫困”“破败”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变为被城市遗弃的区域[14]。东北在这一时期的经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为工人子弟的“80后东北作家”创作的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中下岗失业的工人父辈自然也成为这几位“80后东北作家”作品中主要的人物形象。但这几位“80后东北作家”对20世纪90年代下岗工人形象的书写并不是最早的,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在作品中对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问题早有反映。如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作品。但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写作多是着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领导层面对的艰难[15],在他们的作品中下岗工人形象更像是群体性的概念,而少了作为真实个人的鲜活形象。而且,他们是将“下岗工人”放置在“工厂内”,仅是侧重展示这群工人即将失业的苦难。而“80后东北作家”凭借自身的工人子弟身份成为20世纪90年代东北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亲历者,也成了无法很好地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潮流的工人父辈落魄、挣扎的见证者。所以,他们在作品中侧重表现工人个体下岗后,依然不能很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具体生活状况和真实的心理状态。这几位“80后东北作家”从子辈的视角出发,塑造了父辈作为家庭与社会多种角色的生动鲜活形象。一方面,他们在作品中还原下岗工人生活的艰难,以及建立在工厂制度之上的尊严感与荣誉感的坍塌;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无法及时地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潮流的下岗工人们谋求生活的努力,并给予这群被遗忘的、于困境中挣扎的工人父辈迟来的理解与关注。这几位“80后东北作家”笔下的下岗工人形象不再是群体性的苦难展示,而是具体鲜活的失落个人。除此之外,“80后东北作家”笔下的下岗工人并不像“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中的工人那样上访、罢工、静坐,反而是接受下岗的现实,响应国家号召,四处想办法、谋生活。如《聋哑时代》中,“我”的父母在下岗之后依靠卖煮苞米、茶叶蛋生活;《生吞》中,“我”的父母同样也选择了卖炸串这种小本生意维持生计;《肃杀》中的父亲下岗之后,拿着买断工龄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拉脚儿;《工人村》中的人们下岗之后也各谋生路:老孙在工人村的旧楼里租了两间房子开始经营不值钱的古董生意;下岗职工吕秀芬和丈夫刘建国也开起足疗店,并且疲倦地应付着姐夫接二连三的勒索;《光明堂》中,“我”的父亲也为谋生而离家远行,并把“我”寄托给许久不通音信的小姑,等等。前半生在工厂里被看作是“幸福的工人阶级”的父母一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大潮之下,曾经的荣誉与尊严消失殆尽。在“80后东北作家”的作品中,下岗工人们显然已经放下了自己光荣的工人阶级身份,安静地接受了冷酷的现实,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开始以最低的成本为基础,为个人生存辛酸挣扎,体现了东北人民特有的坚韧与担当。“80后东北作家”在作品中回溯20多年前父辈们切身经历的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经历时,既饱含真情,又富有理性。他们在作品中既没有掩盖工人父辈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无法从容应对的处境,也没有过分地夸大工人父辈突然间由高处跌落的失落与不堪一击。毕竟,导致工人们被城市‘抛弃’并且形成一种流浪状态的原因实则是双重的。这不仅仅来源于外部的刺激,更多的是这些父辈的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性格属性,那是质朴、老实,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懦弱的一代[16]。所以,“80后东北作家”也没有掩盖在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中工人父辈不能及时变通的性格缺点,没有掩盖工人父辈的麻木与自我堕落。如《光明堂》中“父亲失业之后,酒喝得勤,信也不怎么看了”[17]24,“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里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17]25还有日益消沉,靠着自己的“工龄买断金”与母亲的丧葬费来颓废地生活、赌博的工人,如《工人村》中的“我”,下岗半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处于坐吃山空状态,靠单位买断工龄给的钱过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提不起精神。我都想好了,要是哪天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这老房子一卖,还能混个几年吃喝。”[18]232而战伟却拿着母亲的丧葬费想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摩托变吉普”[18]235的发财捷径。还有被生活逼迫而违背人性与良知,不惜以他人生命为代价,来求取自己生活的工人形象,像《枪墓》里失业工人孙少军一家,在下岗之后的生活中挣扎无效,走上杀人抢劫之路;《生吞》中秦理的父亲也成为全国重要案件的犯罪同伙;黄姝的舅舅更是为了金钱,利用年幼的黄姝赚钱,等等。显而易见,这是一群别样的工人形象,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在道德的法码上失去了份量,失去了自己,迷失在不知的航向上[19]。他们迷恋他们的工厂时代,不想从过去走出来。而且经济失利和文化上的差异,下岗工人可以选择的路不多,再加上血缘和故乡的羁绊,基本上阻断了逃离铁西的路[20]。“80后东北作家”在作品中通过一个个以工人为主人公的故事,讲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影响下,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时代浪潮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冲击与波动。他们笔下的下岗工人形象常以苍凉感与无力感直戳人的心灵。但是,他们的作品并不仅仅展现父辈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艰难、挣扎,以及工人父辈的麻木、堕落,也展现了工人父辈对理想的坚持、对所热爱事物的执著追求。如《肃杀》中对足球有着近乎狂热般喜爱的肖树斌;《空中道路》中怀有建设空中道路设想的李承杰;《飞行家》中一生执著研究飞行器的二姑父李明奇;《大师》中棋艺精湛、钟爱下棋的父亲;《仙症》中有着航海幻想,努力追求人生顶点的姑父王战团,等等。除此之外,这几位“80后东北作家”对父辈饱有深刻的理解与尊重。如双雪涛说的那样:“我觉得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沉默的,比我们要有生命力,比我们笃定。”[10]又如郑执所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到这里喝酒,因为他们不想从过去出走,那个时候还有饭吃,有国家养,走出‘穷鬼乐园’这扇玻璃门,是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21]由此可见,“80后东北作家”笔下的下岗工人形象摆脱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中下岗工人形象群体化、概念化的特点,拥有了作为个人的鲜活形象。同时,这几位作家又以回溯式的写作避免了过度夸大生活苦难的问题,他们选取下岗工人的日常生活故事,注重展现下岗工人心理上的失落和努力生活的坚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东北工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三、 结 语
梁鸿说:“当一个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动,把一整拨人都挤压到外面的时候,这本身就是特别值得书写的一个东西。”[22]42这几位“80后东北作家”在自己的青春期见证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庇护下的工人们忽然变成下岗的、没有生活保障的普通人的生活变动,也见证了许多因此破产、破碎的家庭,同时也承受着这种变动的影响。所以一二十年过去之后,东北这样一种工业的状况,大量的破产、下岗所带来的后果,慢慢沉淀到了实际生活里边,败落、疼痛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又是这一代年轻作家所体会到的,他们就是后果的承担者[22]45。所以,这种沉淀到生活中的疼痛成为作家们创作的力量与源泉。当青春成长撞上国有企业改制浪潮,家庭经济变化、家庭破碎,以及大量工人下岗导致的社会暴力都会成为青春成长的创伤印记。所以,东北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影响下,经历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冲击,成为“80后东北作家”创作的主要背景,而在这种冲击中产生的创伤记忆和下岗工人形象也成为“80后东北作家”笔下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