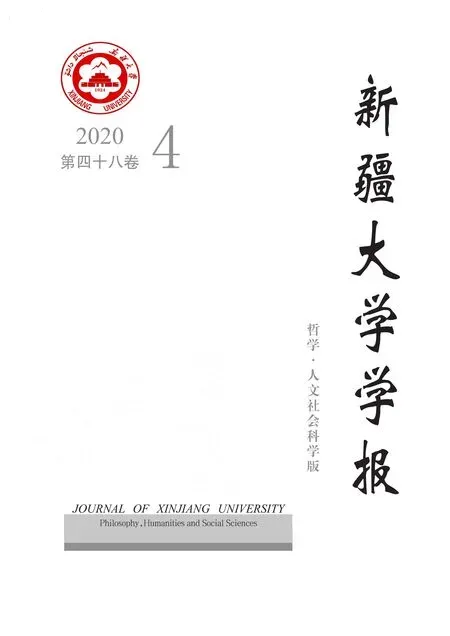值得学界关注和探讨的著述
——对妥建清教授《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的学术批评
2020-12-08郑惠生
郑惠生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广东汕头515041)
妥建清教授撰写的《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于201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该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其目标领域的价值,而且还具有学术研究、学术出版方面的启发意义,很值得学界同仁关注和探讨。在此,拟对其进行学术批评。
一、观点、材料、论证与结构
单从书名中的颓废、审美、晚明与现代性等这几个关键词来看,便可知该书视域非常之宽广,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著述。除晩明属于典型的历史分期概念外,颓废、审美和现代性等均可置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等多维视野中来加以考察。书的标题及目录显示其宗旨是从美学角度审察颓废,在阐明“颓废”的审美意含、审美价值以及揭示中国晩明“颓废审美”“规模”之大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起于晩明。可见,这是一部颇具学术雄心或者说是很有学术野心的著作。那么,妥建清教授的这一学术雄心实现了吗?实现了,至少是自圆其说地实现了。
首先,关于“颓废”审美意含、审美价值的阐释是较清晰的,也是可理解的。在日常话语中,“颓废”一词,意指“意志消沉,精神萎靡”[1]。在多个学科领域里,如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颓废”的意含基本上也是贬义的,像《应试教育只会量产颓废的大学生》等文章①参见余寒《应试教育只会量产颓废的大学生》,《呼伦贝尔日报》,2017年8月21日,第6版;李剑红《没资格颓废》,《金融博览》,2013年第2期,第80页;朱礼龙、陶新萍《文化颓废与企业危机》,《市场周刊》(管理探索),2004年第S1期,第40-41页;鲍尔吉·原野《贪官身体颓废论》,《廉政瞭望》,2005年第9期,第60页;叶筱编辑《越南展开反贪污和反颓废文化运动》,《文史博览》,2013年第9期,第43页;魏文彪《官场颓废文化是不良吏治的衍生物》,《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年第6期,第1页;丁大同《对现代颓废群体的道德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1期,第71-77页。,无须读正文,只看标题,就知道“颓废”是“负价值”的东西。然而,有个别领域却是例外的,如美学和文艺学。虽然这个别学科中的学者也有很多人视“颓废”为不是好东西,但仍有一些人从中看到了“正价值”,认为其在“美的创造”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如薛雯等人。②参见薛雯《颓废:人类身体与精神的文化症候》,《中国文化报》,2013年3月22日第3版;李雷《颓废:一种现代审美范畴》,《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82-87页;刘辉成《论颓废美的道德性——波德莱尔的文化道德观解读》,《攀登》,2008年第1期,第132-134页;程勇真《颓废主义美学及其审美价值分析》,《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56-160页。妥建清教授正是在此积极的意义上来立论的。
尽管全书并未有专门的章节而只是在“绪论”中讨论“颓废审美”概念问题,但妥建清教授在亦史亦论的基础上了提出自己的看法:“颓废作为一种去道德化的审美精神,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审美风格和文学审美风格。”[2]30并这样阐明“颓废审美风格”对于晩明的重要意含和价值:“晚明文士的颓废审美风格正是此种‘去道德化’的审美精神的表现,其通过躲避晚明生活世界所标举的升华意义上的崇高精神与人格,进而追求另类的精神与人格,并力求以此种消极的方式来消解社会的深度压抑,最大程度地追求个体的自由。因此,晚明文士的颓废审美风格已经具有个性解放的价值,并且表现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2]30这样的观点和认识,可以说是全书条分缕析的核心之所在。
其次,关于中国晩明“颓废审美”“规模”之大的揭示是较详细的,也是较充分的。从个体生命历程来看,“颓废”是一种无法完全避免的现象。区别只在于,某个生命阶段会多一些而在某个生命阶段则会少一些,某些个体身上表现得突出而在某些个体身上则表现得不明显。当“颓废”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成为主导的时候,这个个体就会被视为是“颓废者”或者“颓废”。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群、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和时代。不同的是,人群的“颓废”,由于高度的同质化,所以通常不用“普遍性”来指称。而社会和时代,由于存在着不同的人群,所以即便存在着大量的“颓废”现象,也不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因而其“颓废”与否,是以“普遍性”作为衡量标准的。当然,不同阶层或群体的“颓废”,在表明社会和时代的“颓废”程度上,意义是不一样的——跟非精英阶层的“颓废”相比,精英阶层的“颓废”更具“标示性”。如同一个长期处于严重“颓废”状态的人很快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一样,当一个社会处于“颓废”泛滥也即形成较大规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离崩散和重建不远了。在此意义上讲,中国晩明“颓废审美”的规模有多大,成了论证“晚明现代性”有多强的事实根据。
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奢华晚明与颓废的文化景观”里,妥建清教授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如何挑战、冲击程朱理学“天理压抑人欲”的主张入手,在勾勒“奢华之风”基础上探讨了晚明时期各阶层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并推导出其文化实质的“颓废”。
进入第三章和第四章,妥建清教授对晩明“颓废审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其中的“第三章形塑与表征:晚明文士颓废社会审美风格”,先对晚明文士的审美追求趋于“狂、怪、华、奇、痴、俗”进行分析,以之揭示那个时代广泛存在着“去正统化”“去崇高化”“去宰制化”“去道德化”的精神品格和审美旨趣,接着是对饮食(个性化、联觉化、本色化)、服饰(艳丽化、复古化、新奇化)、家居(玩好化、意境化、精致化)等若干不同的方面进行探讨,以之证明晩明文士的“颓废审美”追求不仅是在精神层面上,而且还落实到日常的物质生活里面。
其中的“第四章播散与演进:晚明文学颓废审美风格”,承接第三章的晚明“颓废社会审美”,进一步讨论晚明的“文学颓废审美”。这一章先从中国文学内部一直处于“宰制”地位的诗歌至晚明逐渐衰落论起,然后以戏曲、传奇、小说等文体和“戏仿”的流行乃至小品文的诸多变化为对象,深入地揭示了晚明文学“颓废审美”倾向的普遍存在。
最后,关于中国现代性起于晩明的论证是较完整的,也是较合理的。尽管该书涉及的话题众多,但其旨归无疑是“中国现代性起于何时”的这一关键性问题。而要讨论“中国现代性起于何时”,首先得在何谓“现代性”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而,作为长时段的一个学术热点,“现代性”的理解却是见仁见智,未曾形成共识。有社会学角度的,也有人学角度的;有政治学角度的,也有经济学角度的;有艺术学角度的,也有文艺学角度的。有近现代的,也有当代的;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单就当代中国而言,就有成千上万位学者参与讨论,其中还不乏各个领域中的重量级或次重量级人物,如李泽厚、钱中文等。①参见李泽厚《中国呼唤“情本体”的现代性》,《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0日,第5版;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5-19页;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24页;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第56-64页;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3-48页;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25-32页;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第20-33页;周宪《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45-54页;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第10-20页。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妥建清教授大胆立论,采用尤西林先生的“心性及其结构”概念,并在进一步阐释的基础上反驳那些与之相左的观点。这就是第一章的基本内容。
如果理解“现代性”概念止于“心性及其结构”层面,那么,“现代性”就仍近乎是一个“黑箱”。故而,在第二章里,妥建清教授在分梳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西方“现代性”观点的基础上,大胆地借鉴了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看法,提出了“现代性”的“标示物”为“颓废审美”,从而为整本书的阐发也即“中国现代性起于晚明”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在第三、四章介绍和分析晚明“颓废审美”盛况之后,第五章又通过“晚明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对比以及“晚明个性解放”的“个性”分析来进一步论证晚明“颓废审美”的特殊价值和现代意义。而第六章,则分梳晚明“颓废审美”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近现代以来“颓废”研究的进路及其各种思想,以之佐证将晚明“颓废审美”视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合理性。最后,也就是“结语”篇,妥建清教授在“夹引夹论”中再一次反驳“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外因论,重申晚明“颓废审美”的标志性意义,并指出这一探索及其结论“是一种从中国文化出发所表现出的人类文化可以高度会通的文化自信”[2]376。
综上所述,《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在总体上是一部比较严整的学术著作,它的观点鲜明、思路清晰、结构完整、材料丰富、论证深入、逻辑自洽,并且,还充满“文化自信”。
二、思想、创新与风格
如果该书只是达到上述所说的“比较严整”的水平,那么,就谈不上值得学界高度重视,而只能说跟时下许多目的远在学术之外的拼凑之作相比,它还不至于亏欠读者太多罢了。也就是说,在学术著作看似丰盈实则“贫困”的今天,该著述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并且还能给学术界和出版界带来启发。
首先要说的是,该书是一部“既有学问又有思想”的学术著作。十几年前,郭德茂教授就曾感慨地说,“文学研究界”,“常见没有思想的学问和没有学问的思想”[3]。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未有什么改观。但只要是认真地读了《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就知道该著确实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既不缺学问又不缺思想”的佳作。
有趣的是,王斑教授在为“汪晖涉嫌抄袭”辩护时曾有过这样不必要的担心:“注解喧宾夺主”,会让“独到思想完全被窒息”[4]。如果他现在读了有着大量注解的《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就知道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该书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在详注详解的背景下冒出来的。这里先列一例予以说明。
但是“历史”设若如黑格尔所言是想象叙述与事实本身的双重性,那么晚明现代性研究就非止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注脚。不惟是因作为明清史研究基础理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学说,概念含混而泛滥成灾,以至于合法性屡屡遭受质疑,被论者讥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资本主义萌芽死结”,甚而至于许多学者要求修正或拒绝使用资本主义萌芽,更是由于晚明毕竟是多元文化的时代,“晚明的中国展现的图景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以至于连错综复杂这个词在这一特定的时间框架外都失去其所特有的意义。在地域之间呈现出丰富差异的背景下,政治运动与学术思潮的多元性,以及人们对生活、朝廷所持的各种不同态度,产生出由多种异质所构成的现象。”因此,多元文化景观的晚明促逼着学术界必须检视晚明现代性研究的历史,寻绎新的研究视角给予其多维度的阐释。[2]2
上例正文343字,除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文字外,属于妥建清教授自己表述的约只有150 字,不足正文的一半,不足正文加上页下注的五分之一,是典型的详细注解。然而,正是这样一段包含着详细注解的文字,清晰地呈现出著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认可黑格尔关于“历史”的阐释并以之为据,支持李伯重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反思和检讨,宣称面对“多元文化景观的晚明”,“中国现代性起源”的研究应该也可以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思路。
至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但又常被视为是无须多加探究的问题:学术研究中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图省事的人可能会说,“学术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那么,是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来的吗?正确的答案是,有些可能不是,有些可能是。但即便“是”,也应该只是部分而非全部。为什么?因为“学术研究中的思想”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后者可以只是来源于生活实践或者说是对生活实践的一种“反应”;而前者则是“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思想”,尽管它并不排斥对于生活实践的思考,并且其成果最终还要返回生活实践中进行检验,但无论如何,仅靠对生活的“冥思苦想”是无法“成就”学术思想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就人类史而言,对于生活的“冥思苦想”,先哲时贤已经进行过千千万万次,这千千万万次的“冥思苦想”所沉淀下来的那一部分,就被称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谓“学术思想”,说到底就是能直接面对人类思想中的“结晶”也即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进行思考,并根据时代的变迁提出新的问题,寻找有别于先人的也是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总是表现为针对既有的也是具体的“学术思想”进行言说——或者反着说,或者接着说,或者补充性地说,或者修正性地说,但一定不会重复着说,一定不会自言自语地说,一定不会不知所云地说。①参见郑惠生《文艺学批评的功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第33页。
正是由于“学术思想”的匮乏,当前“天马行空”式的著述极为流行,甚至于连一些学术巨星和大师也无法幸免,其著述怎么看都像是报纸上的文字。也正是由于“学术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当前学术界才经常是鱼目混珠,把“大路货”当“珍宝”推崇。就此角度而言,妥建清教授撰写的《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堪称学术界和出版界努力“纠偏”的一个榜样。上列正文343字加页下注331字的例子,在该书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下面,再举一例予以说明。
纵使承认中国的现代性源于西方,可是此种“入侵”的现代性也只能在中国境内“众声喧哗”,很难指认它是卢梭的现代性,还是黑格尔抑或是尼采的现代性。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还是启蒙时期的现代性。因为纵观现代性的问题史,其在西方的言说也并非是统一的声音。卢梭是第一个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的法国哲学家。其以批判的方式回应当时工具理性宰制的现代社会,深刻地表达出他对人类知识等方面进步的质疑。有别于卢梭,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以乐观的方式迎接现代性的来临,其在“进步”“发展”的宏大叙事中礼赞现代性观念。尼采则是在“上帝死了”的呐喊声中否定理性宰制的现代性。尼采彻底颠覆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知识就是美德”的理性观念,提出以审美的酒神精神来拯救现代性的方案,“谁也别想摧毁我们对正在来临的希腊精神复活的信念,因为凭借这信念,我们才有希望用音乐的圣火更新和净化德国精神……现代萎靡不振的荒漠,一旦接触酒神的魔力,将如何突然变化”。由此可见,卢梭、黑格尔、尼采的现代性叙述业已迥然有别,我们接受的是谁的现代性呢?从现代性的起源而言,詹姆逊认为“现代性”一词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已使用该词,它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不含有现代优于过去的意思。路易·迪普雷(Louis Dupré)则将现代性上溯至14 世纪后期,认为人文主义摧毁了将宇宙、人和超验因素结合起来的传统综合。因此,就西方文化而言,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埋下了现代性的种子。吉登斯则认为现代性出现于17世纪,“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于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由此看来,詹姆逊、迪普雷、吉登斯所追溯的现代性起源已大不相同,我们接受的是何时的现代性呢?如是种种,都已说明现代性本身的多源性。因此,纵使中国接受西方的现代性,但是现代性也已“模糊不清”,殊难辨认。[2]367-368
在这八百多字,引用了7 个文献,涉及到6 位专家学者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与认识,表达了著者不同意把“中国现代性”归之于“西方挑战”的一个理由:连这些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见解都差别很大,我们凭什么来断定“中国现代性”是由“西方挑战”所造成的?
像这种在书中大量引用的情况,很有可能会被一些“天马行空”者视为是“掉书袋”。若真的如此,则可以断定,其说法如果不是在替自己的“空空如也”辩护,那就是他在学术认知上的误区所致。
“掉书袋”是一个贬义词,在生活中常被用以讥笑那些说话总是引经据典、卖弄学问的人。这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一般生活内容的理解与交流无须总是引经据典,所以常引经据典就会让人产生炫耀学识的感觉,这反而不利于沟通和交流。然而,在学术领域里,没有引证的思想便是一种“隔山打牛”的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缺乏学术继承、学术对话的思想。这里就不说你可能还存在着把别人的思想占为己有的情况了,只说没有引证,便意味着你的思想没有学术的基础和背景,也无法让人知道在学术上你是否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学术上也不是没有“掉书袋”的情形。那么,该如何判断呢?或者说,以何为标准呢?以量大量小来定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应该以著述者个人思想的有无来定。即便引用的量不大,如果没有个人的学术思想,或者个人的思想只停留于模棱两可的阶段,那也同样是一种“掉书袋”的表现,只是有时候这种“掉书袋”并非出于炫耀,而是由于未能透彻理解被引材料而无法作出有主见的判断所造成。
以上述角度观之,妥建清教授的《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有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整书的构架乃至遍布全书的言说细节均由“学术对话”组成,这既是该著述易于被察觉到的最大特点,也是其真正能够达到“创新质量”要求①参见郑惠生《“文艺学批评”建设:创新的视角》,《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第26页。的根由。因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再做长篇的引证,而只摘录几小段颇具豪情却是很有节制的文字。
“中华性”之论是20 世纪90 年代初一部分北京学人提出的。其核心观点认为现代性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中国的现代性是以中国的“他者化”为其特色的,这种现代性经历了五次重心转移,现已寿终正寝。在新的现实境遇里,有必要用“中华性”来代替“现代性”。此种“中华性”旨在建构一种“外不后于世界之新潮,内不失其固有之血脉”的新文化,从而与第一世界的文化形成对话。“中华性”论说的深意在于拒绝文化“他者化”的焦虑而重申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但值得质疑和反思的是此种二元对立意义上的否定“他者”是否就是“自我特性”(identity)的表征呢?此说是在申述民族文化的个性,进而解决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问题呢,抑或是一种裹挟着民族主义的冲动所制造出的情绪化说辞?[2]62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从普遍性的角度认为事物的质态取决于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还是文化回跃性的特殊规律,抑或是文化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异质文化的相遇与其仅仅是由于“挑战—回应”模式——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本位文化发生改变,不如说是本位文化自身内部因素重组的结果。[2]64-65
以“中华性”论者的后现代立场而言,他们追求碎片化,反对整体性,但其论述屡屡使用“现代性的终结”、“新时期”已经终结、“后新时期”已经到来等整体化的表述。其理论主张与语言表述之间包含着不可规避的矛盾。[2]71
学术自主性的追求难能可贵,但到底哪些是“中国本土语言”呢?为何“中国经验”必须用“民族语言”来解释呢?……实际上,民族语言、西方语言并非都是透明的概念,不需要反思可以直接使用。更重要的是,此种“语言民族主义”看似是反对西方霸权,实际上双方的逻辑相同,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我们之所以使用现代性,就是因为需要它。[2]71
赓续李欧梵被“五四”新文学所压抑的唯美-颓废文学研究,王德威揭橥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他以晚清小说的四重话语为轴线,重新撰写晚清文学的颓废景观……王德威对于晚清丰富的颓废文学景观的探寻,不仅旨在追寻被启蒙所压抑的中国文学欲望现代性传统,而且由晚清文学颓废与启蒙的辩证关系的诠释,揭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新论。但是王德威将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仅止于晚清小说,置晚明文学中所跃动的颓废因素于不顾,终至成为未完成的现代性。[2]361-362
上述几小段文字不仅在表达方式上非常个性化,而且还具有基于“实证和逻辑”②参见郑惠生《“文艺学批评”的理论构建》,《华文文学》,2017年第6期,第67页。之上的很浓烈的“对话-论辩”色彩。由于这种色彩在《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中随处可见,所以也可以说该著述具有典型的“对话-论辩”风格。那么,如何来评价这部“以立论为主”的书中所呈现出的“对话-论辩”风格呢?从波普尔的科学进步在于“猜想-反驳”[5]角度讲,答案肯定是:“典型且是最具魅力的学术进路”,而在当下则属于“难能可贵”。正是这种与先哲时贤不断的“对话-论辩”,让有学术价值的思想成分得以吸收,让缺乏学术价值的思想成分得以扬弃,从而确立有价值的或者是更有价值的新的学术思想。
至此,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凭什么“对话-论辩”?答案是凭“学术积累”,或者说凭“充足”的“知识储备”③参见郑惠生《论文艺学的越界——与陶东风教授商榷》,《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9页。。因为无“积累”便“无话可对”,更“无话可辩”。这种“无话”不仅仅是指由于自己没底气而表现出来的说了许多“无学术价值的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指由于自己的“无知”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对的对象的话”。这里,借鉴“镜像神经元”理论中的一个形象化说法:“我看见的你就是我自己”[6],可表述为“看不见别人学术思想的人其实就是自己没有什么学术思想”。
以此角度来看,《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就是一部真正有底气的“有话可对、有话可辩”的扎实之作。这一点,首先可从密密麻麻的页下注、书末列出的多达629 个的参考文献(含中文参考书籍284 个、翻译的外文参考书籍210 个、中文期刊109个、英文著作21个、英文文章5个)中看出来。其次,虽然此处无法在严格的“文本发生学”[7]的意义上来考证该出版物,但检索一下学术期刊上的文献,仍可知晓妥建清教授从“颓废审美”的角度探索“中国现代性”问题已有十几个年头的历史,并且在起始阶段就呈现出“对话-论辩”的鲜明个性。如《探寻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兼与陈平原先生商榷》等文①参见妥建清《探寻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兼与陈平原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60-64页;妥建清《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8-11页;妥建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体验——兼与李欧梵先生商榷》,《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5-10页;妥建清《多元的现代性——兼驳“文明的冲突”抑或“承认的政治”》,《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第84-88页;妥建清《颓废——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8-112页。,均依循“对话-论辩”的模式来建构其所要确立的理论思想,并终至汇成眼前这部四十万字且是首尾一贯的创新意义上的佳作。就此角度而言,《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的出版,不仅展现了妥建清教授个人独有的学术风采,而且还能够给当前“千人一面”的学术撰写和学术出版带来启示:“优秀的文艺学著作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符合学术规范,而且还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既展现了学术思想的深邃,又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
由上述可知,正是长期不懈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实践”,才使得妥建清教授能够如此娴熟地运用“对话-论辩”的手法,并将其贯穿于《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的始终,也才得以让该著的论述变得异常广博、充满生气,使之卓立于其目标领域。可以说,妥建清教授的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神,很值得目前尚处于虚浮阶段的学术界所学习和大力倡导。
三、问题与探讨
尽管笔者高度评价妥建清教授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以及在方法上的独特性,但对其著述中的一些思想和表述,仍觉得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当然,对于国内首部能够自圆其说地论证“中国现代性起源于晚明”的创新之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过于挑剔的印象,但从批评者的学术责任和良好的学术建设角度讲,这样的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似乎还是应该尽力而为。下面,分而述之。
1.关于“现代性理解”问题
著述承接尤西林先生的“心性及其结构”概念,将其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由于尤西林先生的“现代性”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也即“人学”意义上的概念,所以用之探讨“文学的现代性”就有其逻辑上的优势,非常契合“晚明现代性”发生的“内律论”。这种基于“文学即人学”理路上的“现代性”思想,既表现出妥建清教授的学术机智,也使得其著述逻辑自洽、水乳交融。
然而,著述也承接了尤西林先生“现代性”不属于“社会科学概念”的思想,并以之批判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认为他们“混用了二者,视人文科学基础用语的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用语的现代化”[2]74。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其说服力是不够强的。
首先,尽管“现代性”概念殊难厘定,尤西林先生把“现代性”当作只属于“人文科学”概念也不失为“一家之说”,但作为一个广泛流行的“用语”,它早已为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所使用,故而,我们没必要断定只有将其关进人文科学的“笼子”里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使用“现代性”概念的当否,不宜用“学科篱笆”的设置(广义语境)来衡量,而应根据其上下文也即指称的对象是否存在(狭义语境)来判断。
其次,既然尤西林先生意义上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是这样一种关系:“‘现代性’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现代化’的前提”[8],那么,就意味着两者无法“剪断”:“化”既可表征“性”,又能塑造“性”。从这个辩证的意义上讲,“现代性”和“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故而,无论是在“人”的层面上使用“现代性”和“现代化”,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使用“现代性”和“现代化”,都同样无可厚非,除非论者确实是不清楚两者的区别。由于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种类在广义的文化领域里偏重于人的精神生活层面,所以,用尤西林先生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来探讨,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也是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多用“现代性”来表述的一个重要原因。只不过,正像路易吉·卢卡·卡瓦里·斯福尔扎所提醒的那样:“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障碍”[9],我们不可因为“人学”领域里很适宜使用“现代性”一词,便认定该领域不能用“现代化”一词来指称“实存”的东西。限于本文的目的和篇幅,这一话题就不再展开。
2.关于“颓废审美认识”问题
“颓废”是一个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常会见到的“概念”,著述承接前人的部分学术思想,单从审美视角考察,挖掘其美好的一面,将其视为“心性”意义上的“现代性”表征,并在分梳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现代性起于晚明”的论证。就逻辑本身而言,可以说是相当完美。不过,如果从前提的设定角度看,仍有一些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在社会领域里,苏格拉底的“最美即最善”到今天仍然适用。而“至善至美”,无疑当属“最崇高”,如与邪恶的殊死斗争,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等。之所以说这些现象属于“崇高”的现象,同时也是“至善至美”的现象,那是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牺牲“小我”对于大多数人只能“仰望”。虽然艺术领域不甚相同,有形式美方面的要求,但在内容的美即善的要求方面,仍是不可或缺的。由此角度视之,“颓废审美”的价值或曰“颓废”的审美价值几何?应该说是一个很值得玩味也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其次,以李欧梵、王德威等先生为代表的“颓废审美”论,以反拨的方式“重现文学史”,“挽救”了一批被遮蔽了的作家,这对于传统上很注重“陌生性(strangeness)”[10]或曰个体“创造性”的文学艺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但由此而将其推为“现代性”的“曙光”乃至“表征”,这是否有“过分”之嫌?或者说,这样做是否与“颓废审美”在审美价值等级中所可能有的排序相称?
再次,就意含的“拒压抑”“去道德”“躲宰制”“抗大写”等阐释而言,“颓废审美”的确是一种与正统相背离的另类追求,也“具有个性解放的价值”。然而,借鉴彼得·J.卡赞斯坦在论述“世界文明”时的“多元多维”[11]说法,“颓废审美”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多维多元”的系统。在这驳杂的系统里,“各维各元”是很不一样的,其价值等级也是有别的。就此角度而言,是否有必要对“颓废审美”现象作进一步的梳理。比如,从审美主体角度讲,“颓废审美”的追求有些是高度自觉的,有些则不然。有些是“善于利用财富为自己增添荣光”[12],有些则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来表明同主流社会的距离或决裂。而在“价值等级”上,则存在着“是否可以将其等同”的问题。再如,从审美客体角度讲,“颓废审美”的对象有些偏于物质形态,有些偏于精神形态。而偏于精神形态的,又有偏于思想与偏于情感的差异。这不同的“颓废审美”,是否在价值方面是毫无差别的?又如,从审美范畴角度讲,“颓废审美”可分为相对的阳刚和相对的阴柔两种形态,若从“颓废审美”所可能具有的“抗大写”“拒宰制”方面予以考察,两者是否有“同样的力量”或者说“同等的价值”?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厘清了,对于李欧梵、王德威等先生把鲁迅的作品笼统地列入“颓废审美”范围的做法,我们是否还会完全认同?我们是否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只是出于“颓废审美”论的需要而在鲁迅身上看到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那一面”?对于王德威先生把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人的小说推举为“现代性”代表的这一做法,我们是否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无论进行何种批判性讨论,只有足够优秀的作品方能进入此范畴。然而,一旦某事被纳入讨论范围,其内容所蕴含的相对价值就变得不再重要?”[13]
3.关于“去道德化”问题
著述将“颓废审美”的内核概括为“去道德化”。从其阐释看,并没有大的问题,但这一用语,按通常的理解,有被误读的极大风险。
首先,自然美由于侧重形式而“在道德上中立”[14],但社会美由于侧重内容而刚好相反。对于艺术来说,正如舍勒肯斯所言:“情况总是或必然是这样: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都是一件作品的内在价值的组成部分。”[15]也正像阿诺德·柏林特所指出的:“忽略道德和艺术的关系不仅是愚蠢的,也是虚假的。”[16]甚至于在文学领域里,“对人生某个中心问题表现和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道德关注”还被看做是作品“具有第一流价值”[17]的条件。可是,著作中的“去道德化”表述,却很容易让人误读为“颓废审美者”要创造的是一种毫无“道德价值”的审美客体。
其次,在文明时代,没有道德立场的人是不存在的,关键是他有何种道德立场。无论是“颓废”还是“颓废审美”,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立场、道德境界,只是这种道德立场、道德境界与维持现存“社会秩序”的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要求相抵触罢了。可是,著作中的“去道德化”表述,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颓废审美者”是一群既“与社会道德秩序相左”又“可以毫无道德立场”的纯粹的“审美主义者”。
基于上述两点,笔者认为“去道德化”的表述应修改,使之更贴切、易懂。
4.关于“晚明颓废审美现象”问题
著述借助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晚明“颓废审美”文化景观进行了生动描绘和深入分析。从其框架来看,大致可分为“生活”和“文学”两大部分。由于这两大部分的阐述既比较详细又比较精辟,所以,从论证逻辑上讲,该著已经是很好地达到了研究的目的。不过,如果能够更多地注意一下晚明的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看看其跟晚明的文学相似度如何,进而决定是“梳爬”还是“予以必要的说明”,那么,或许会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5.关于“书名”问题
“颓废审美风格”中的“风格”一词,按正文所述,是承接了布封“风格即人”和钱钟书对“文如其人”[2]31发挥的思想,如果再从文艺学界的习惯用法来看,“风格”内涵当指个体的相对稳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个体的“创造性”,其无法复制使之区别于他人的“创造性”。简言之,风格的“独创性”内涵使其更适用于“文艺个体”而非“文艺群体”。当然,由于某些不同的个体在“创造性”表现上存在着相似的东西,所以,经“抽象概括”后,风格也可用以指称那些有相似之处的人及其创造物,此可称之为“风格类型”,如哥特式风格、巴洛克风格等等,只不过,即便如此,其内涵仍是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上讲,著述使用“颓废审美风格”是合理的,尤其是正文里面有对各种“颓废审美”个案的阐发,使其变得更加可以理解。
不过,当书名里把“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放在一起的时候,由于其过于简约而变得不易理解。实际上,无论是在哪一个文明时代,出现某一种风格或风格类型对于文学艺术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于在雅克·朗西埃的“文学的政治”[18]意义上讲,比“风格”类型覆盖范围更大的“纯文学”类型,也都是在建构异于特定“政治-社会”秩序的“自由自主”王国。概言之,仅仅风格或风格类型的出现并不能说明一个文明的时代有多大的变化。只有当某种风格类型是“普遍”地存在(统计学意义上)或者是“接二连三”地出现(动力学意义上)①参见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满涛、岳麟、杨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04页。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当其成为风尚或者是难以遏制的潮流时,它才可以用来说明这个时代变迁的情况或者是结构上的某些重要特点,也才有“资格”争取作为“现代性”的表征。由此角度看,把书名中“颓废审美风格”改为“颓废审美风尚”或“颓废审美风潮”,是不是更适宜一些?
另外,尽管“晚明现代性”概念在著述里是清晰的,但在书名里却是一个颇让人“猜想”的词组。它是指“晚明人的现代性”?还是指“晚明社会的现代性”?它是指“晚明文学现代性”?还是指“晚明艺术现代性”?抑或指“晚明审美现代性”?其实这些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探索的方法方式也不尽相同。故而,与其让读者去猜,不如明确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著述虽然不断地批判“起源”的“西方影响”论,也不断地批判经济、政治等在“现代性”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细读全书,可知其意图并非全盘否定,而主要在于它们都不属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内部因素”,因而也不能最有效地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就此而言,书名里的“晚明现代性”若改为“晚明文学现代性”,是否能更恰当地体现出著述的宗旨?
四、结 语
总之,妥建清教授撰写的《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以丰厚的积累为根基、以思想的创新为动力、以不止于“目的便是演示晚清作家之革新能力”[19]为目的、以“中国现代性”产生的自律论为立场、以“颓废审美”为焦点、以“对话-论辩”为主要方式,较充分地展现并深刻地阐释了文学乃至审美维度上晚明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在其目标领域里,难见有将如此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思辨、清晰的表达和鲜明的个性四者熔铸成浑然一体的著述。当然,无论是在优点方面,还是在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方面,上述的批评都远未穷尽。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可以看出,该著是一部饱含着思想和激情的学术力作,是一项由热血和汗水浸泡而成的学术成果。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个学术著述和学术出版总是跟各种实际利益挂钩而与学术热忱、学术积累、学术创新不大沾边的年代,对于妥建清教授这样的著述,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也无论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找到更多的瑕疵,或许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仅从“思想、继承、创新、规范、逻辑、风格”一样都不缺的这一点来讲,它就足以成为后学者的楷模,也可成为学术同行严格“自律”时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