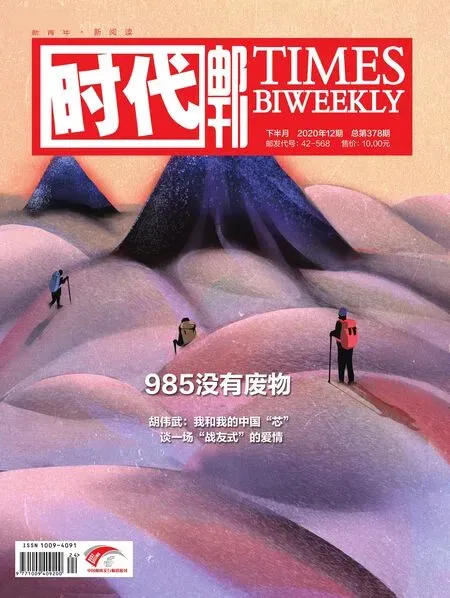迟子建:我就是个烟火气十足的人
2020-12-08
56年前那个元宵节的黄昏,迟子建出生在冰天雪地的漠河北极村。当时天将黑,窗外尚未挂灯,父亲给她起了乳名叫“迎灯”,这是爱她的读者们自称“灯谜”的由来。因为父亲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所以她有了“子建”的名字。显然,她没有辜负这个名字,从1983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600余万字,出版90余部单行本,曾获1次茅盾文学奖、3次鲁迅文学奖、1次冰心散文奖、1次庄重文文学奖、1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
37年来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继2015年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之后,她又推出了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新长篇《烟火漫卷》,这是她献给自己生活了30年的哈尔滨的一首长诗。哈尔滨对她来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可在她的笔下,那些曾经伤痛的眼泪最终化为了折射人间烟火的晶莹露珠。
生活积淀为写作安上翅膀
记者:从20年前的《伪满洲国》开始到现在的《烟火漫卷》,您的精神家园似乎逐渐从北极村转移到了哈尔滨?
迟子建:我的童年是在北极村长大的,关于那片故土的故事我已经写了很多。我17岁求学离开大兴安岭到了山外,1990年来到哈尔滨,至今已经生活30年了。初来哈尔滨,我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虽是它的居民,但更像个过客,还是倾情写我心心念念的故乡。直到上世纪末我打造《伪满洲国》,开始读哈尔滨城史,在作品中尝试建构它。但它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在我的作品中独立呈现过。我在哈尔滨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将笔伸向这座城,于是有了《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以及现在的《烟火漫卷》,我并不是特意选择30年这个节点来表达我对一座城市的感情和爱,而是我觉得哈尔滨这座城给了我动力,给我安上了一双翅膀,我就这样起飞。
记者:您是在作品中缔造着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吗?
迟子建: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现当代都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参与者。任何一个地理概念的区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所有文学写作者的共同资源。作家不能像某些低等动物那样,以野蛮的撒尿方式圈占文学领地,因为没有任何一块文学领地是私人的。无论是黑龙江还是哈尔滨,它的文学与它的经济一样,是所有乐于来此书写和开拓的人们的共同财富。
因为写作更关注生活细节
记者:您很喜欢城市里的烟火气吗?
迟子建:如果单纯从字面意义理解,我就是个烟火气十足的人。我喜欢吃,每天写完东西搞点好吃的,一荤一素,喝点红酒,我就觉得人生很美好了。我喜欢烟火人间的感觉,喜欢逛夜市,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比如在夜市里可以学习语言,一个卖鱼的,把半死不活的鱼形容为“半阴半阳的鱼”,这多文艺啊!我颈椎不好,去做理疗,路过一个卖香瓜的地方,我和其他人一样,在那挑挑选选。东北人买香瓜要先拿起来闻一闻香不香,我在那儿闻,卖瓜的人就说:“我这瓜都是千挑万选的,都是进入决赛的瓜。”“进入决赛的瓜”,这多生动啊!
记者:营造了诗意的文学世界,还能接受日常的庸常吗?
迟子建: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的情感,让你能尽情品咂。对于文学,我觉得应持有朴素的情感,因为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能使作家葆有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其实我的生活跟大家没什么两样,也得下厨,也得刷马桶,也得洗衣服。不同的是,因为爱好写作,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关注生活细节。
记者:您有没有灵感枯竭写不下去的时候?
迟子建:作家都是有局限的,没有感觉时不要硬写,没有哪个伟大作家是靠字数来奠定自己在文学史的地位的。遭遇写作的瓶颈怎么办?你把自己变小再变小,深吸一口气,这是需要眼界和底蕴的。冲出瓶颈,之后又是海阔天空,瓶颈就不会成为你创作的“紧箍咒”。
文学为虚无人生注入活力
记者:为什么您的作品总是有很苍凉的感觉?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迟子建:我热爱世俗生活,一锅好肉,一杯好茶,一碗浓汤,一瓶鲜花,都让我愉悦,在这点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骨子里,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如微尘,生命总有终点,不管多么伟大的艺术,总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没有完美的人,同样没有完美的人生。因为生长在极寒之地,我性格里有不屈的一面,这使我面对人生的磨难时,有一种坦然迎击暴风雪的感觉。可是作为女人,太坚强了说明你没有一副可以依靠的肩膀,又是多么不幸!
记者:写了这么多年写出自己最期待的作品了吗?还有什么人物是您特别想写的吗?
迟子建:我对期待的作品无法言说,因为艺术上的美好的期待,就是无法言说的。我从不刻意拎出一类人物,去为人物量身打造作品。而是酝酿成熟了一片“土地”,让人物自然地生长出来。一个作家不变是不可能的,但我属于渐变的那一类。突变,如果不是艺术上的顿醒,而是由于商业元素的侵入,那么它往往是以艺术趣味的降低为代价的。这样的变,不管多么热闹,都是功利的,失败的。对我来说,未来酝酿了什么样的“土地”,就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在等待着。
记者:对您来说,文学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您会怎么看文学无用论的说法?
迟子建:在有用的人眼里,文学是灯;在无用的人眼里,文学什么都不是。换个说法,如果一个盲人认定文学有用,那么他也许可以看到光;而一个视力很好的人认定文学无用,所有的书籍在他眼里都是黑暗的眼罩。文学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它为虚无的人生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