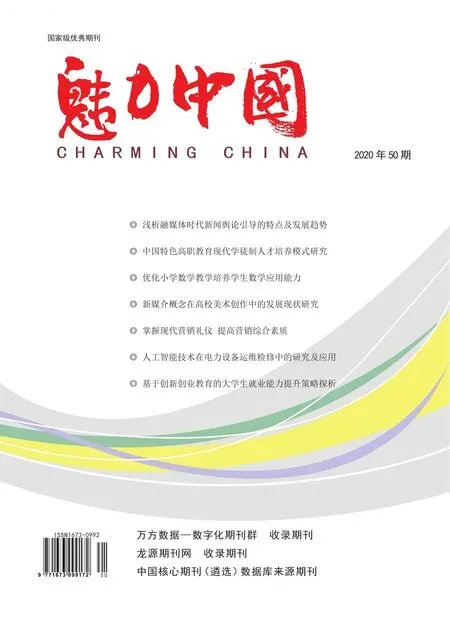追寻中记忆的复苏与生命的重生
——吉本芭娜娜小说创作浅析
2020-12-07王若雨
王若雨
(贵阳市城乡建设学校,贵州 贵阳 550001)
吉本芭娜娜原名吉本·真秀子,1964年7月生于东京,著名评论家、诗人、思想家吉本隆明的次女。一段在餐厅当服务员的打工经历,使得吉本与香蕉花结缘,“芭娜娜”由此而来。1987年,作为毕业论文尝试创作了短篇小说《月影》起,吉本先后出版了短片小说集《厨房》、中篇小说《哀愁的预感》、长篇小说《斑》、“睡眠三部曲”《白河夜船》、随笔集《菠萝布丁》、长篇小说《N·P》、短篇小说集《蜥蜴》、长篇小说《甘露》《蜜月旅行》等等,实际上她的创作囊括了除诗歌外的小说、散文、杂文、访谈录等多种体裁,但最擅长的是小说创作,由以短篇为主,广受欢迎,创造了总发行量高达470万本以上的惊人记录。以九十年代初创作的《甘露》为界,吉本将自己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她自己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偶然的话,我认为《甘露》这篇小说就标志着从《厨房》以来持续至今的第一期吉本芭娜娜的结束。”前后两期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主题上,第一期大都以单一主题为主,自《甘露》开始转向了多重主题的平行发展。第一期的作品给人有始有终的感觉,脉络清晰,但结尾处总会以主人公大段的内心独白收束全篇,这种感觉像是说教亦或总结的结尾,成了第一期普遍存在的弊端。第二期则开始淡化这一点,结尾比较开放,每一章都保持一种可以续写的状态。也有评论指出,第二期创作焦点不集中,显得凌乱松散,令人无从把握。总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吉本第二期的创作“更为立体地反映了复杂多变的世界,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结构都更加丰满和真实。”
一、独特的小说概念
吉本有着区别于传统立场的文学观,用其父吉本隆明的话来说,就是她持有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小说概念”。创作“容易接受、也容易理解”的作品,这种观念直接成就了她作品“通俗性”的一大特色,她希望即使是与书无缘的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也能够顺畅无阻。在创作中她常常将自己的身份置换为一个读者,想象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于是“渲染情绪”就成为吉本小说创作的主导。她认为:“世界各国的人能够共同理解的东西不是语言,而是类似于情绪的东西。”她总是着意去捕捉某个特定瞬间的极其微妙的心理感觉。这一特点,在《哀愁的预感》中贯穿始终。小说开头对雪野“阿姨”独自居住着的老式房子周围环境的描写就是主人公弥生的内心感觉。“一年四季都笼罩着粗犷的气息,譬如在雨停以后的时间里,房子所在的整个街区仿佛全变成了森林,弥漫着浓郁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周围的环境给弥生的感觉是粗犷的绿的,空气是浓郁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在描写弥生每次离家出走与阿姨的独处中,都会落笔阿姨的举手投足带给弥生的感觉。而在整体的叙述中,始终紧扣着一种淡淡的“哀愁”,行文风格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缓缓述说着一个故事。阿姨的生活非常古怪,“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对如此古怪的阿姨颇有好感”,“尽管阿姨沉默寡言,但只要凭他一个细小的动作,或视线的变化,或一个低头,我就能大概猜到她是高兴还是无聊,亦或生气……我总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大家都不了解她呢?为什么我这个小孩却能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呢?”这是小说开头弥生抛给自己的一个疑惑,更是抛给读者的疑惑,这种疑惑为之后的预感铺设下基础。小说前半部分的时空一直在不断地交错和转换着,不时地从一个回忆闪回到另一段回忆,在这过程中,弥生对阿姨的那种特殊的感觉指引着她的行动和思想,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像拼图一样,随着回忆与脑海中残留的幻影慢慢地开始朝着完整状态拼接,变得明晰起来,终于在阿姨那里得到了证实——阿姨是我的亲生姐姐。弥生的心理变化一直牵引着故事的发展,身份真相的迷雾随着弥生疑惑地解开层层散去。在叙述上,一直萦绕着一种哀伤的情感基调,当“我”将要回忆起什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哀伤的感觉,在弥生的身份揭晓后,回忆与哀伤的关联便浮出水面。阿姨讲述了那段弥生忘却的时光,一段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幸福时光,但因为一场意外戛然而止,造就了今天的弥生和雪野。
二、成长经历对创作的影响
人的成长过程是琐碎的,其中也许会出现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别的事件,这些或平凡琐碎或精彩特别的经历会进入大脑的记忆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各种行为,文学作品便能体现出这种微妙的影响。《哀愁的预感》中,在听到阿姨的男友正彦描述自己母亲之后弥生想:“人真是可悲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完全跳脱童年时代的咒语束缚。”莫言也曾说过:“对一个写作者来讲,少年时期是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即使一个成熟的作家,一辈子没用儿童视角写作过,但儿童时期的记忆和经验肯定在他的小说中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吉本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庭院、池塘的场景。如《哀愁的预感》里,弥生和家人曾经居住的地方的院子里就有一个池塘;《蜜月旅行》的开篇是主人公的一段独白:“我从小就喜欢我们家的庭院。”个中原因便是吉本小时候生活的庭院里有一个池塘,她常常坐在池塘边。就像《蜜月旅行》主人公说的“庭院是我感觉的出发点,是永远不会改变标准的空间”,幼时记忆中庭院和池塘或许也是吉本创作灵感的源泉,在作品中成为了某种隐喻和象征连接着故事发展的线索。从吉本幼年时期就立志当作家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写作道路的选择来看,和父亲的影响不无关系,父亲是知名作家这一点为吉本和姐姐创造了衣食无忧的家庭环境,同时父母的开明和宽容,使得吉本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拥有更多的自由。高中时期吉本开始了一段时长三年的恋爱,对方是邻家的男孩,他们的交往并没有令吉本为之兴奋,“他们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上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起”,这个男孩家境优越却常独自一人生活,这与吉本其乐融融总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成长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从他的身上吉本感触到了“孤独”。这一经历典型地反映在了《蜜月旅行》中,主人公的未婚夫与爷爷住在隔壁,家里透着阴暗与孤独,因为青梅竹马,两人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之间并没有炽热的感情。《厨房》中美影失去亲人空守厨房的身影中依稀也有当年那个独自在家的男孩的影子。同样大学时代的一段情感经历也对吉本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段恋情最终以分手告终,但却使她向心理的成熟迈出了一大步。“我们还年轻,这也许不是人生最后的恋爱。但是我看到了两人之间有生以来初次经历的丰富多彩的故事。”这是《月影》女主人公五月的感慨,又何尝不是发自吉本内心。赠送吉本盆栽香蕉的小学时代友人中的一个的突然故去,让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吉本对生与死产生了强烈的感受,送花人已逝去,而花仍静静地生长,这一体验在她众多作品对死亡主题的把握中无形地发挥着作用。
三、小说中的象征与隐喻
吉本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会设计许多事物或情景暗示某个事件某种心境。《哀愁的预感》中,弥生一家因为房子改建而不得不搬到一处破旧的平房应急,弥生在旧房洗澡时看见了一只全身红色的橡皮鸭子飘浮在浴池中。睡梦里浴池再次出现,而弥生脚边的小脸盆中又出现了那只玩具鸭。“在我第一次将在老房子的经历告诉母亲的那天,脑海中浮现的女孩站在深绿色的池塘边”。这些幻象、梦境和幻影中都出现了容器与水,这与什么有关?在回答弥生的问题时,雪野说“我们全家人住的房子,院子里有个池塘”,读者终于同弥生一起恍然大悟。阿姨与男孩正彦的关系,让弥生想起了关于插伞桶的事,一次离家出走住在阿姨家时,弥生将雨伞插进门边的插伞桶里,两三天后要用时,却发现整把伞都发霉了,告知阿姨,她却让弥生把它们都扔在房子背后,当它没有发生过。弥生“第一次观察了像废屋一样的房子背后”,那些阿姨所说的“当它没有发生过”的垃圾多得让人毛骨悚然。弥生不禁想到“阿姨对人是否也是说丢就丢”。雪野一直躲避正彦,但却不是因为不喜欢。正彦也有过不幸的童年,但他抛开了过去,因此“完全是一个幸福的王子”,而雪野却为了保留过去,而选择回避现实。正彦那“充满笑意的生活态度”使雪野感到不安,是她跨越不过的心理障碍。凡是“可怕的东西、讨厌的东西、可能伤害自己的东西就一律避开目光。”这是雪野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弱点。她因为害怕面对正彦,因而决绝分手,选择生活在幻想与回忆之中,独守在老宅之中就是最好的证明。对她来说时间是静止的,那些房后堆积的垃圾象征着被她埋葬的现实。正彦也被她“当作没有发生过”的东西扔掉了。文中两次提到婴儿,第一次是“我”在临时居住的旧屋的睡梦中,“我用双手将嚎啕不止的婴儿发了疯似的按进浴池的水里”。第二次是雪野放弃了自己与正彦的孩子。姐妹俩有了共同的“杀婴”体验,暗示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弥生忘记了过去,梦中杀婴象征了在现实生活中抹杀了过去。雪野死守过去,杀死腹中婴儿,象征着扼杀了自己在现实中的幸福。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颜色描写,具有很强的隐喻和象征作用。如出现在弥生幻觉中的红色玩具鸭,站在水池边的姐姐穿着红色的拖鞋,为什么是红色的?雪野讲述了那场车祸,在去青森的路上在转弯时与迎面开来的车相撞,两姐妹从车里爬出来,浑身都是血,血溅到眼睛里,整个世界看去都成了红色。红色成了潜意识里对这场改变命运的事故的记忆。这些手法,使得吉本以情绪变化为主线而少有情节的小说在朴素中意味深长。
吉本用细腻的女性笔触描写着生活中的故事,生动感性,萦绕着淡淡的哀伤,表达着无数女性无从述说的微妙情绪和敏感情怀,深受年轻女性和历经世事无常之伤痛的读者的喜爱。阅读她的作品,不需要一个理性的头脑,需要的是一颗感性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