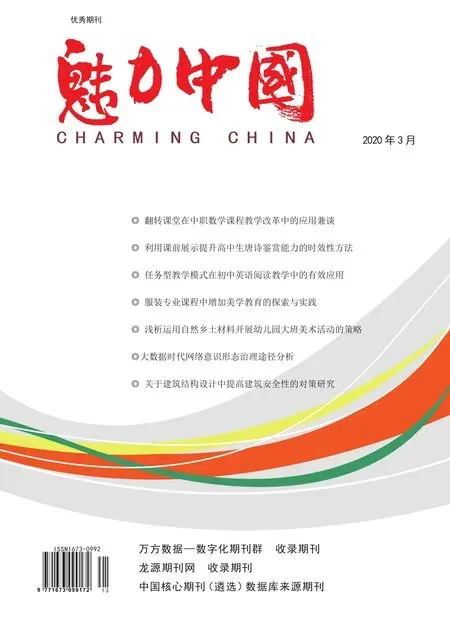是不是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浅析《呼兰河传》中的叙事视角
2020-12-07张丽芳
张丽芳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萧红是“明国四大才女”之一,又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呼兰河传》作为她广被赞誉的经典之作,读来直感叹她是少有的靠天才写作的作家。
优秀的作家,必要的有两点:人生奇观和独特的个人情感。萧红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唯一给了她爱意的长辈的离世,抗争包办婚姻执拗离家,流落异乡欠债难偿,未婚先孕,后又两度“抛”下生生骨肉,乱世中贫困潦倒,后只能向报社求助,因此结识萧军,萧红才算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从此靠写作为生,写字、恋爱、活着便是萧红最紧要的事,可她命运悲苦,数段恋爱皆以失败告终,便是野蛮生长,肆意潇洒,最终病死异乡,令人扼腕。
她的文字简却沉,她的出身和故乡带给她极特殊的情感体验,她的诚实和无畏,使她在运用那些长在她身体里的文字时得心应手,她仿佛只是将它们拿出来,进行了基础的编排,文章就成了。她的风格在中国女作家里独树一帜,文字时刻流散的的诗意,真实辽阔的童年回忆,对北方乡土文化传统和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刻揭露,流畅的叙事等,构成了独特的“萧红文风”。萧红的描写大都克制,她使用孩童视角,将所见所想写得亲切却客观,只因孩子常常是很多事都不明白,也无需明了的。读者却能从孩子的目光延伸,看到萧红真正展现的乡土中国的暗礁。在白话文刚刚兴起的年代,萧红的写作如此流畅,是难得的,她将日常写得像隆冬时下的大雪,天地万物即便是寒苦却显得静美,书中对北方农村的冬天的描写深深刻在了读者脑海中,多年以来,很多未见过东北风光的读者对于东北的印象便是萧红书中的模样。
萧红自己曾执拗地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象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虽然茅盾先生沉浸于《呼兰河传》多彩的“风土画”和“凄婉的歌谣”,但在为此书作序时仍说:“有人会觉得这不是一本小说”。其实不难看出,《呼兰河传》中不同章节、不同故事所展现出的批判效果是有所差异的,这种差异是源于《呼兰河传》中不同的叙事视角。萧红将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的转换运用得炉火纯青,其中全知视角主要运用于头两章,如第一章末尾“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萧红用第三人称叙事,观望着呼兰河,详细地描写呼兰河的自然风貌和民风民俗,正是这冷酷的客观,将生养她的呼兰河的封建和精神缺陷直接地呈现出来,越冷漠,批判的力度越大。
其后的叙事则多以孩童的视角“我”来展开,《呼兰河传》有自传性“嫌疑”也就是因为“我”几乎可以确定为“萧红”本人。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拟儿童视角。”《呼兰河传》运用儿童视角是很成功的,这部作品创作于萧红人生中最孤独、最凄凉的阶段,这位来自东北的文学洛神,一生颠沛流离,命途多舛。当时种种情感上的折磨与身体上的病痛一齐向她袭来,让萧红心力交瘁,几乎万念俱灰,但这反而使她内心产生了对童年生活的呼唤。
在第三、四章,讲述“我”的童年生活时,孩童视角运用得最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童年的萧红是孤独的,但也是快乐的。她被父母和祖母冷落,这也导致了她敏感、叛逆、忧郁的性格,从另一方面说,这就促成了后来面对包办婚姻她娜拉式的出走,也给了她文学上的敏锐和天赋。而祖父的疼爱和五彩缤纷的后花园又带给了她一生难再有的快乐和温暖,塑造了她热爱自然、热情活泼、大胆爱幻想的性格特征。无论萧红的童年快乐与否,故乡和祖父永远是她心里最柔软的一隅,是治疗她心伤的良药。第三章一开头,便是“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故事像是正式开始,儿童的客观,使得叙事既不流于煽情又不失于冷漠。孩童引领我们看到了真实、残酷却迷人的呼兰河,那是萧红的回忆,那是她来的地方,那是她的家。当她发问:“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谁知道,这是小迺莹在问祖父,还是飘零已久的萧红在向故乡发问?
后几章的孩童视角,不再说“我”与祖父,而是“看”“我”认识的人和事,即呼兰河这个地方的普罗大众。关于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悲剧发生却无力改变的孩子。、有读者说,以全知视角来讲这些故事,批判力度更大。但了解萧红才会明白,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萧红,从未曾忘记过她的呼兰河,从未忘却过在那片土地上蒙受苦难和正在蒙难的人民。她以一个孩子关心的视角、看上去碎片不讲规则的结构、散漫而诗意的语言,克制地表现着她的悲悯。她的文字细腻得近乎琐碎,以此回避着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些人物像最低级的生物,只是在活着,在一种原始性的顽强的生命力中,人是没有精神世界的。
一个作家,最好的文字常与故乡勾扯,文学上有“归乡”一概念,不得不说,苦痛的回忆是作家们的创作源泉,而一个作家的童年,往往决定了他们今后会写什么。《呼兰河传》的结尾,萧红写道:“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它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萧红以全知视角将呼兰河铺陈于世人面前,为读者呈现“生的艰难”。又以限知的孩童视角,把读者带回生养她的园与河,将自己呈给世界,这并不是孩子式的单纯怀念,而是参透人生的沉郁,萧红的内心,一定是饱含着对故乡的思痛和对人生的哀痛,才写出了《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