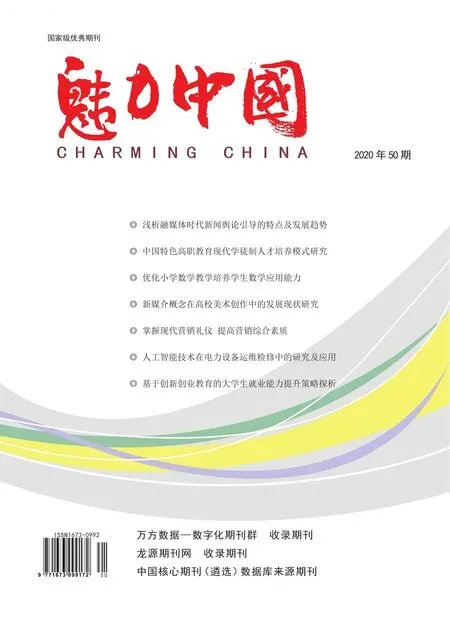论伏尔泰对《赵氏孤儿》中儒家观念的创造性接受
2020-12-07高子彦
高子彦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999078)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盛传已久,虽早在《春秋》中已有记载,但后人多以《史记》中的记录作为故事的可靠来源。因此,这段赵孤遇救的故事,自汉代以来,一直植根在中国民间。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脱胎于宋元王朝交替之时,而作为亡国之君的宋朝皇室姓赵。因此,在宋臣文天祥等人身上,再度上演了千年前晋国程婴等人一样的故事;而伏尔泰创作《中国孤儿》之时,资本社会的“礼崩乐坏”已经成为启蒙知识分子们的共识,而由传教士翻译出的《赵氏孤儿》带伏尔泰给了一个极好的契机,于是他便利用受普罗大众喜爱的戏剧以及为欧洲社会普遍接受的人文主义观念,来展示儒家观念的魅力,进而达到净化社会道德的目标。
目前,学界对于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进行创造性接受这一课题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本质上,只是对儒家观念照本宣科,是一部翻译作品;第二,伏尔泰是认同儒家观念的,但只是将作品改头换面,是一部套用儒家观念的欧洲故事;第三,《中国孤儿》并不能体现出伏尔泰是“欧洲儒者”,他与儒家观念存在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故而《中国孤儿》当中也未蕴含有儒家观念。
《赵氏孤儿》文中所提出的“儒家观念”和“人文主义”,前者是指由董仲舒概括、孔孟所提出的儒家“五常”概念,即“仁、义、礼、智、信、忠”所包含的一切观念及其衍生概念;后者则是指欧洲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主张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于维护人的人格尊严以及解放人性,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
同时,由于两者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改编目的下,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创造性接受了纪君祥在《赵氏孤儿》当中的儒家观念,使《中国孤儿》中的儒家观念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
因此,伏尔泰对《赵氏孤儿》中的儒家观念创造性接受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儒家观念中的“为忠善者”[7]90,同时以此为切入口,融入了君权民授的独特概念,将国家利益和君王利益捆绑在一起,即对于国家利益和君王利益等价至上的坚决肯定;其次是儒家观念中的传统礼教,同时又带有人文主义的色彩,通过富叶端美与丈夫张惕等人的慷慨赴死也是一个既不愿失去贞洁从而放弃自己的爱情,也不愿做不忠不义之人“不能为却定要为”的决定,这使得人物形象丰满的同时,又凸显了人性的光辉,从而使得《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中的儒家观念保持了高度的契合性,又带有了自身人文主义的色彩;最后是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家观念和人文主义的结合,即对于道德和礼教的肯定和对于野蛮的否定。在《赵氏孤儿》中,韩厥、程婴、公孙等正面人物甚至于屠岸贾等的反派,他们都围绕“德”这一字来行事,尊崇有德之人,而在《中国孤儿》中,“德”最大的化身就是成吉思汗,他最后的宽恕与大团圆结局正是对儒家观念中“德”最好的诠释。在“德”下用礼教来感化社会,是无论正派和反派的一种共识,这一点上相对于之前两点,《中国孤儿》则是将《赵氏孤儿》中的人物性格核心揉捏到一个角色的身上,使其成为“德”的化身,使得故事在带有儒家观念的同时,又蕴含有人文主义色彩,形成了自身的儒家观念。
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对儒家观念的改造以及独特认识提炼出来,将其与《赵氏孤儿》相比较,这不但能够给予目前中西方文化碰撞上一种独特的解释视角,更有助于文学上的横向借鉴,拓宽比较文学接受学上的研究方向,同时也能促进人们对于儒家观念整体规律的一种追求,最终能为现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比较文学上的共同渠道,实现两部作品中人物们共同追求的“天下大同”。
这两部作品中的儒家观念比较,在现在这个重提儒家文化以及全球化的时代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18世纪的欧洲广受欢迎,也意味着儒家观念在欧洲也是能够被得到肯定,儒家观念中的“仁、义、礼、智、信”也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也能为欧洲人所接受。这正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不断求索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