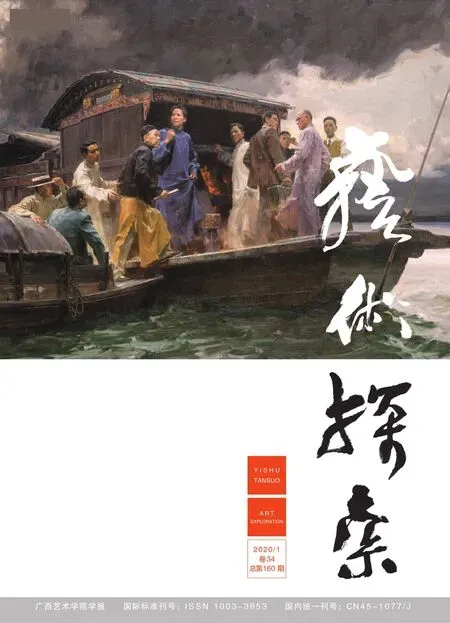“炫俗射利”的意图
——明代托伪之作《筠轩清秘录》研究
2020-12-07郭建平肖
郭建平肖 洁
(1,2.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一、总论
中国古代,尤其是到明清时期,江南一带并非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一地域拥有更多的文化积淀及历史记忆,曾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所独占”之说,江苏地域是明清时期著述的主要产生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江苏也是书画创作、收藏的中心,并产生了大量的画学著述,但针对画学著述的研究至今滞后。而且,明清时期江苏地区伪造古代及同时代名人书画的现象很严重(如苏州片等),书画作伪也促进了该地域书画著录中的伪作(这里主要指内容虚妄、错假之书)及托伪之作(这里主要指托名伪造的书籍)足劲发展,例如《宝绘录》,清梁章钜直言:“岂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耶?”[1]119四库馆臣亦对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有“疏于考证”的评价,此书所载的部分书画作品流传无序,真伪值得质疑。像《宝绘录》《六研斋笔记》(二者都出自于明代江苏地域)这类的艺术类著述还有很多,而有关研究成果至今鲜见。
早在清代中期考据学极盛之际,画学就应与其他学问一样,有机会到得到一次难得的整理、订正,但遗憾的是清代考据学家多重视天、算、历、术、数等领域,而鲜有人花精力疏释校刻画学古籍。以明清艺术类古籍善本中的伪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为线索揭示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及学术氛围,诸多有争议的艺术史考证研究也许能借此得以推进。
《筠轩清秘录》就是其中的一部托伪作品,但是目前来看,关于此书的深入研究鲜见,即使著作《中国伪书综考》《中国古籍编撰史》《明清论丛》等都用一段话提到了此书为托伪作品,但只是简单提及,并没有展开研究。论文《明代私家书目伪书考》《浅谈古籍伪书的编撰意图及其价值挖掘》笼统讨论了古籍伪书编撰的主要意图,认为《筠轩清秘录》为“牟财射利”之作,而且还谈到了此类意图流传的伪书大都较为粗糙,拼接痕迹明显,但只限于此,并没有专门对《筠轩清秘录》著书背景、文本内容及作者归属等问题进行学理层面的考证分析。可见,有关《筠轩清秘录》的深入研究为“硬骨头”式的研究“盲区”。对《筠轩清秘录》进行梳理、考辨源流,可以避免引用上的以讹传讹,也利于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挖掘工作。
二、“炫俗射利”——《清秘藏》变为“《筠轩清秘录》”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筠轩清秘录》:“旧本题董其昌撰,其昌有《学科考略》已著录,是书凡列目二十有九,皆论玉、石、铜、磁诸古器及法书名画之类。前有陈继儒序,谓可与项元汴《芗林清课》并称。今考其书,即张应文所撰《清秘藏》,但析二卷为三卷。盖应文之书,近日始有鲍氏知不足斋刊版,附其子丑《真迹日录》后。从前抄本,流传不甚显著。书贾以其昌名重,故伪造继儒之序以炫俗射利耳。”[2]
按:“盖应文之书,近日始有鲍氏知不足斋刊版”的意思是,在编四库总目的接近时间才有《清秘藏》的刊本,还是附在张应文儿子张丑的《真迹日录》之后,之前都是抄本形式,所以流传不畅,因此“书贾以其昌名重,故伪造继儒之序以炫俗射利耳”。书商把张应文所撰《清秘藏》抄本改为三卷,称为“《筠轩清秘录》”,著者托伪董其昌,又伪造陈继儒的序,以期获取重利。《筠轩清秘录》版本有:1.《筠轩清秘录》三卷,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2.《筠轩清秘录》三卷,清乌丝栏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清秘藏》:“应文,字茂实,昆山监生,屡试不第,乃一意以古器书画自娱。谦德即作《清河书画舫》及《真迹日录》之张丑,后改名也。是编杂论玩好赏鉴诸物,其曰《清秘藏》者,王穉登序谓取倪瓒清秘阁意也。上卷分二十门,下卷分十门,其体例略如《洞天清禄集》,其文则多采前人旧论,如铜剑一条本江淹《铜剑赞》之类,不一而足,而皆不著所出,盖犹沿明人剽剟之习。其中所列香名,多引佛经,所列奇宝,多引小说,颇参以子虚乌有之谈,亦不为典据。然于一切器玩,皆辨别真伪,品第甲乙,以及收藏装褙之类,一一言之甚详,亦颇有可采……此书成于应文临没之日,不得以续购为词,然则丑表所列,殆亦夸饰其富,不足尽信欤。此本为鲍士恭家知不足斋所刊,原附丑《真迹日录》后,盖《山谷集》末载《伐檀集》之例。今以各自为书,仍析出别著录焉。”[2]
按:“盖犹沿明人剽剟之习。其中所列香名,多引佛经,所列奇宝,多引小说,颇参以子虚乌有之谈,亦不为典据。然于一切器玩,皆辨别真伪,品第甲乙,以及收藏装褙之类,一一言之甚详,亦颇有可采,”这段话指明了明代著书环境的恶劣,抄袭成风,引用失范,粗疏错漏的著述到处可见。明清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反省之期,很多学者不免怀有“综述往古”的抱负,但也面临“后之人竭尽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范围”的焦虑。具体到明清艺术类著述研究来看,有关画法及画理的探讨,也许广度及深度方面可以并驰于前代,而记载书画作品收藏、鉴定情况的古籍虽数目可观,然一般都是继承前人观念及判断,欠缺严密考证及完善的研究体系建构。著书者往往没看到原作,在基本无法判断著述所提书画作品的真伪情况下,就埋头于书斋著书,资料多建立在前代著述上,若前人著书存疑,则可能导致后人著书的粗疏、错漏。此段提到此书还使用小说、佛经等文本内容,这类内容难以实证,尤其是小说内容多为子虚乌有之谈,不可信,不应成为被引用的典故。至于“然于一切器玩,皆辨别真伪,品第甲乙,以及收藏装褙之类,一一言之甚详,亦颇有可采”,说明四库馆臣对此著述中记载收藏装裱的内容基本上是持褒扬态度的。
“此本为鲍士恭家知不足斋所刊”表明《清秘藏》有知不足斋刊本,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筠轩清秘录》曾言“近日始有鲍氏知不足斋刊版”,看来知不足斋既刊刻了《清秘藏》,也刊刻了《筠轩清秘录》。
《筠轩清秘录》被后世认同的一个证据就是其被收录于曹溶(1613—1685年)及其门人陶越于康熙时所编辑的《学海类编》。此书为集成类的著述,收录书四百五十种,计八百一十卷,依据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学海类编》(无卷数,程晋芳家藏本),旧本题国朝曹溶编。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此编裒辑唐、宋以至国初诸书零篇散帙,统为正续二集,各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类,而集余之中又分行诣、事功、文词、纪述、考据、艺能、保摄、游览八子目,为书四百二十二种,而真本仅十之一,伪本乃十之九。或改头换面、别立书名,或移甲为乙、伪题作者,颠倒谬妄,不可殚述”。[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接下来还提到:“(《木笔杂钞》)其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今考其书,皆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之文,原书本八卷,此本摘抄二卷,别标新名,又伪撰小序弁于首,盖奸黠书贾所为,曹溶不辩而收之耳。”[2]由此可见,曹溶及门人陶越所辑《学海类编》虽收录的著述较多,但其中伪作也多,原因是“曹溶不辩而收之耳”,曹溶往往不去深究考证便辑录在册,有失严谨。
《学海类编》序《辑书大意》中提到:“开卷有益,然亦竟有无益者,弟观所不录书则所录者不可知矣。二氏之书专说元巫及成仙作佛之事不录,诬妄之书不录,志怪之书不录,因果报应之书不录,荒诞不经之书不录,秽裹谑詈及一切游戏之书不录(以上六条或全书中有一二段涉及者亦不复删),不全之书不录,诗不系事者不录,杂抄旧著成编、不出自己手笔者不录,《汉魏丛书》《津逮秘书》及《说海》谈丛等书所载者不录,部帙浩繁者不录,近日新刻之书及旧版流传尚多者不录,明末说部书不录,茶经酒谱诸书不录。”①曹溶《学海类编·辑书大意》,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民国九年(1920年)上海涵芬楼据清道光十一年(1836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的影印本。根据“近日新刻之书及旧版流传尚多者不录”可推测曹溶认为《筠轩清秘录》罕见,又认为此书作者为董其昌才收录的,同时赵仁甫(芝园居士)作序提到:“学海类编者,浙西曹秋岳先生之所辑,其门人陶子艾村之所增删也,所录古今书计有四百二十余种,皆海内士大夫家藏抄本,人世所稀见者”,由此可知,曹溶初见《筠轩清秘录》时,此书应为抄本,并且稀见。曹溶,字鉴躬,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定京师,仍原职。寻授顺天学政。疏荐明进士王崇简等五人,又请旌殉节明大学士苑景文、尚书倪元璐等二十八人,孝子徐基、义士王良翰等及节妇十余人……康熙初,裁缺归里。十八年,举鸿博,丁忧未赴,学士徐元文荐修明史。又数年,卒,有倦圃诗集”[3]。曹溶跨晚明到清代康熙年间,而康熙皇帝对董氏推崇至致,手摹其书,常列左右,晨夕欣赏。曹溶也是进士出身,虽身事二朝,但也是典型的时代文化精英,可惜也被《筠轩清秘录》所惑,没有意识到此书的出版本是书商为追求利益而伪托于董其昌,实际上是《清秘藏》内容,这点恰说明《清秘藏》流传不显。
但是需要一提的是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六言:“(明万历丙申刻本[1596年]《张应文藏书七种九卷附三卷》)此明张应文所著之书,凡《箪瓢乐》一卷、《老圃一得》二卷、《罗钟齐兰谱》一卷、《彝斋艺菊谱》一卷、《清秘藏》二卷、《山房四友谱》一卷、《清供品》一卷,七种。后附《茶经》一卷、《缾华谱》一卷、《朱砂鱼谱》一卷、《焚香略》一卷,则应文子谦德所撰。谦德后名丑,即撰《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两书者也。两书最为鉴赏书画家所引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著录。”可见,《清秘藏》也有明万历丙申(1596年)《张应文藏书七种九卷附三卷》刻本这一版本,知不足斋并不是最早的刻本,只遗憾可能因为张应文的影响力有限,这本书在这一时期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晚明时期印刷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成熟为书籍大规模出版和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科举制的发展,识字人数大量增加,对读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这一点在江南地域更为显著。这一带,据记载:考中进士的平均数从1388年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 名;1451年至1505年间,每三年约290 名;1508年至1643年间,每三年约330 名。[4]779这些源源不断产生的知识精英也有可能成为书画著录方面的作家主体和消费主体,龚自珍云:“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归养,望者风气渊雅,其故家谱系多闻人,或剞一书、或刻一帖,其小小异同,小小源流,动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骚然之士,闻其逸事而慕之,览其片楮而芳香恻悱”[5]155。明中后期以后,国库殷实,文人士大夫多以著书修谱为乐,大量私家书籍著述出版,不加以考证而多抄袭之作,书籍质量大大降低,《四库全书总目》云:“明人凡刻古书,多以私意窜乱之,万历以后尤甚”[2]。书贾为了提高书籍销量多伪托名人,精英文人一旦制造伪书或者伪书被归于其名下,流传会更广,影响会更大。而且明朝中晚期,市场上的图书商业化程度很高,因为利润可观,书贾不择手段想尽办法出售图书。《明代书籍价格考》曾言:“明万历年间当代刻本的平均售价为每卷1.8 钱银,与同时期每卷0.124 钱刻印成本比较,赢利率在12 倍以上。即使扣除其他种种支费或损耗,书商的利润仍应十分可观。”[6]64明代文坛名士田汝成曾说:“杭人做事苟简,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板之老嫩不均,一也;燥湿异性,二也;厚薄异体,三也;板不宿沤,而取办新材,易瓦易裂,四也; 刻手工拙淆杂,都料藉拙者以多克头家钱,五也。其他琐碎,料理不周,则奸伪百出,此杭刻所以不佳也。”[7]358可见,图书质量在明中后期整体商业化后堪忧,校勘缺乏谨慎的态度,伪作盗版书流行于市,卜正民在评价这一时期时曾指出:“张涛②张涛,万历时歙县知县。心目中的明朝历史是一部无情的衰落史。明朝从奠基者太祖(1368—1398年在位,亦称洪武皇帝)所强力推行的稳定的道德秩序最终滑向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在张涛眼中还是道德堕落的社会。张涛似乎敏锐地感觉到商业——被拟人化为钱神的罪恶面孔——才是将曾经安定有序的中国改变成一个无序骚动的世界的罪魁祸首。在这个世界中,商业使人们不断地奔波,欲求不断地升级,使社会禁忌彻底倾覆。通过放任消费去推动生产,商业瓦解了,张涛认为只有在纯粹的农业社会关系下才能实现的道德团结,竞争破坏了社会的共同准则”[8]9—10。虽然此段用词激烈,但却真实揭示了明中后期传统伦理道德观的下滑,商人甚至一些文人为求利益不择手段,托伪之作、假借名人之作大量出现在此时期。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曾阅览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此书有王国维手书题跋,更彰显珍贵,而且品相极好,但前页有“陈眉公先生重订”。据考,陈继儒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嘉靖帝崩不过八岁而已,不可能重订《孔子家语》,可见书商借陈继儒之名来促销。
还有内容基本全是错假的伪作在此时期也分外耀眼,例如明代张泰阶《宝绘录》③本文采用《宝绘录》的版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辨认不清的地方与饶玉成校本(清光绪刻本)相校。这些版本的《宝绘录》以及张泰阶另一著作《北征小草》均不乏手写体,辨认较有难度。本文所载所有《宝绘录》《北征小草》的内容,均为笔者等人辨认、断句,所以有错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内容基本错伪,《四库全书总目》所讥为后世文人所认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张泰阶的身份,他身世显赫,祖上三代均属精英士大夫阶层,张泰阶著《宝绘录》的意图值得深思。与其时间比较接近的重要文人,例如董其昌、陈继儒等,也有殊途同归的行为,《大观录》曾记载:“牧翁谓公画最矜慎,贵人巨公请乞,多倩人捉刀或点染。已就,童奴以赝笔相易,亦欣然题署,此殆是欤?”[9]817董其昌有代笔画,而陈继儒对赝托其名的书态度也是温和的,并没有采用手段制止,其在世时就有伪托其名的《宝颜堂秘笈》,他在《与戴悟轩》中陈言:“但书坊所刻《秘笈》之类,皆伪以弟名冒之”,又,《答费无学》言:“《秘笈》非弟书,书贾赝托以行,中无二三真者”。[11]148
三、《筠轩清秘录》与《清秘藏》重要内容考释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筠轩清秘录》:“旧本题董其昌撰,前有陈继儒序,谓可与项元汴《芗林清课》并称”[2]目前未见《芗林清课》这本书传世,应该是商人仿造陈继儒语气“假造”的一部书,但是四库馆臣对于《清秘藏》(也即《筠轩清秘录》)还是给与了不俗的评价:“然于一切器玩,皆辨别真伪,品第甲乙,以及收藏装褙之类,一一言之甚详,亦颇有可采”[2]。
由于目前未见有学者专门对《筠轩清秘录》与《清秘藏》重要内容进行考释,所以本文择其中有学术价值及独特见解之处进行释读,并略述管见,以俟公论。例如《清秘藏·叙临摹名手》中提到:“临摹名画宋老米第一,子昂次之,启南、伯虎、徵仲又次之,余俱未得其神”[11],作者认为书画临摹米芾第一,赵孟頫稍次,沈周、唐寅、文徵明又排在赵孟頫之后,其他画家则不能临出原作的神髓。关于临摹高下之分的内容董其昌的《画旨》也有涉及,云:“宋赵千里《设色桃源图卷》……及观此仇英临本,精工之极,真千里后身,虽文太史悉力为之,未必能胜”[12]90,提到文徵明临摹古画较之仇英仍有不足,显然《画旨》与《筠轩清秘录》的观点有矛盾之处,如果《画旨》与《筠轩清秘录》同为董其昌所作,不应出现这样的矛盾观点。
《筠轩清秘录·论法书》:“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即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论》《黄庭经》《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书,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昔钟尚书绍京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置真书一字。余可知矣,惟画价亦然,山水竹石可敌正书,人物小者及花鸟可敌行书,人物大者及神佛图像、宫室楼阁,可敌草书,走兽虫鱼又其下也。”[13]184-185此段内容可以作为明代中后期艺术市场书价与画价大致的对应标准,不同作者、书体、题材,价格不同,而其中画以山水为最,鸟兽虫鱼价格最低。与此类似的论点也见于文震亨④文震亨(1585—1645年)苏州府长洲人,字启美,崇祯元年(1628年)官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明亡,绝食死。谥节愍,其工诗善琴,长于书画,颇有家风。《长物志》:“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论》《黄庭》《画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计以字数。画价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贤象,可当正书;人物花鸟,可当行书,人物大者、及神佛图像、宫室楼阁,走兽虫鱼,可当草书”[14]174。略微不同的是文震亨认为“走兽虫鱼”的价格应大致等同于草书的价格,而《筠轩清秘录》则认为“走兽虫鱼”的价格应该更低。前文论述张应文《清秘藏》付梓于1596年,此时文震亨11 岁。王世贞在《张元配夫人王孺人墓志铭》中提到张“有二子,谦德聘郭,慎德聘徐。女三,一字文从简,余未字。诸孙,男八人,二焉厚德出,六为重德出。女十人,为厚德、重德者各五。葬在邑五保,姑邈字玕先垄之昭位”[15],又因张应文将女嫁于文震亨堂哥文从简,文震亨极有可能见到《清秘藏》,并受到影响。需要一提的是,《筠轩清秘录》对“吴派”的推崇贯穿全书,如“画学不以时代为限,各自成佛作祖,书法则不然,六朝不及晋魏,宋元愈不及六朝与唐。故蓄画,上自顾陆张吴,下及伯虎徵仲,皆为伟观,而蓄书必远求上古可也”[13]190,张应文对于绘画与书法古今优劣及位置升降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认为绘画上“自顾陆张吴,下及伯虎征仲,皆为伟观”,似乎每个时代都有标志性作品和人物,而书法则是追求魏晋风度为上。作者有意将文徵明、唐寅提升到与“顾陆张吴”一样的位置,推崇吴门画派的意图“昭然若揭”。
文章指出北宋“隐相”之一的梁师成“今人于宣和秘殿书画有瓢印题识,而二谱不载者,未可遽以为赝也,如大观初,禁天下不得传苏黄词翰,而宣和间以内侍梁师成,请捜访苏文忠墨迹,一纸定价万钱。幽人释子所藏悉归天府”[13]249,而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同样提及此问题:“今人于宣和秘殿书画有瓢印题识,而二谱不载者……以内侍梁师成,请捜访苏文忠墨迹,一纸定价万钱。幽人释子所藏悉归天,上见何远记甚详,岂亦可以无谱例之耶”[15]693。王世贞与作者相友善,文章观点相互影响实属正常,书中记载 “余向见元美家班、范二书乃真宗朝刻”,[13]227元美为王世贞的字,而同时在其书“叙鉴赏家”一节中将王世贞列为当朝收藏名家,张应文生前应该与王世贞交往甚密。
《筠轩清秘录》虽有抄袭借鉴之疑,但其中《论装裱收藏》不乏深刻的见解:“凡书画法帖不脱落不宜数装背,一装背则一损精神,此决然无疑者”,“凡法书、名画、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将收入窄小匣中锁闭,以纸四周糊口,勿令通气庶不至霉白”。[13]233,236作者认为收藏书画古物应注重收藏的时间、环境,梅雨天气之时应收入匣中,用纸包裹,防湿气进入导致纸张发霉,影响画面整体美感。此观点在其后的文震亨《长物志·装潢》与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七《书画》一章中均有所继承。
纵观此书,涉及玉石、铜器、琴剑、瓷器、名香、珠宝,以及法书、名画、书籍、墨纸砚的论述,并且以自己所见、所藏为例分析收藏技巧、判定标准,虽多为对前期、同期观点的整理,但其中仍不乏作者独特的见解,对后世尤其是《长物志》的成书理念有着一定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来看,有关《筠轩清秘录》或《清秘藏》深入研究至今鲜见,本文关注《筠轩清秘录》的托伪背景,是深感美术史研究若不能重视占据相当大比例的伪作及托伪作品的存在和影响,那么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就会产生一些以讹传讹的现象。在本文中,我们不仅关注《筠轩清秘录》或《清秘藏》文本内容本身,还对其所涉时代学术氛围、书人事理及书画类文献自身学理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展示厚重的中国古代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