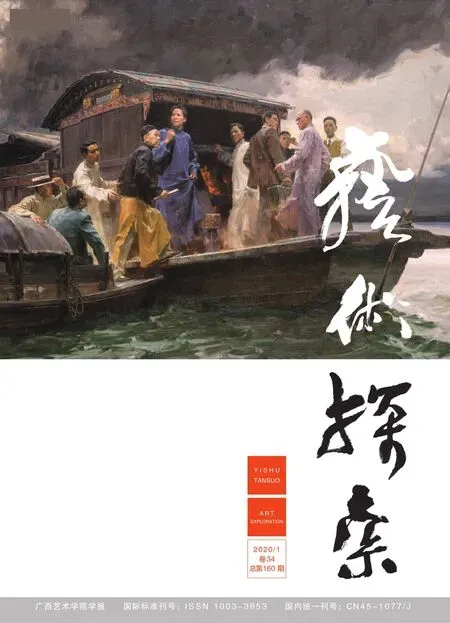南北宗论的史学转向
——西学东渐与问题虚构
2020-12-07韦宾
韦 宾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绘画理论:六法和南北宗论,但它们对于绘画实践的指导都是微弱的。南北宗论是董其昌首先提出的,但只是他的兴到之语,在他的画学体系中没有重要影响;董其昌的后学王时敏也不重视南北宗论。真正扛起南北宗论大旗的,是我们所说的南宗派,而这面旗帜是理论主张,它与王时敏等所主张的集大成论、性灵派主张的尊重性灵抒发的理论主张有明显区别。所以,虽然它有貌似的对画史的梳理,但本质是画学理论,而非画学历史——现当代学者也指出,若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南北宗论是站不住的。这个很正常,它本来就不是对绘画历史的梳理,而只是一种理论观点的表达。南北宗论问题,是清代画坛流派斗争的问题,是画学主张或画法问题,而不是一个对已往绘画历史梳理的史学问题。把画法问题曲解为史学问题,是现代“新”史学①本文所讲的“‘新’史学”指的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背景下,受西方史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史学,并不专指梁启超讲的“新史学”。相关研究可参考(日)手代木有儿《梁启超的史界革命与明治时期的历史学——关于晚清的进化论和历史观》(《近代中国》第十四辑)、孔令伟《近代历史科学对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史写作的影响》(《新美术》1999年第4 期)等。树起的一个无意义的学术命题。而围绕这一伪命题,学者们讨论了至少有一个世纪。
一、从画法到宗派:地理说的出现
康熙时《佩文斋书画谱》将“南北宗论”与郭若虚《论黄徐体异》《论曹吴体法》,《宣和画谱序》,郑侠《流民图》等均列入画论下之“画体”中。考“体”于此当指“准则”“法式”“样式”之类含义,《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讲品画之标准、绘画之材料及绘画之摹拓,则“画体”于此当指“品画之标准”。故《佩文斋书画谱》所讲的“画体”,则更应偏重于“准则”“法式”“样式”,而不是一种对绘画历史的总结。这种归类,不排除它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王原祁等人对南北宗论的基本判断:它不是一种历史的判断,只是一种理论认识。南北宗论是董其昌并不重视的画学理论,在清中期后,由于南宗派要排斥异己,南北宗论成为其理论支柱,但仍然限于画论的宗派论中,并不属于画史的论断。到了清中后期,因为宗派论的原因,它又渐被看成是一种史观,这种趋势到了晚清民初得到加强,大约是新史学兴起之后有意无意的假设而成的研究对象。其中,由于“科学”主义而引起的疑古派,是从史实上强烈反对南北宗论成立的。大体来讲,南北宗论从兴到之语演变成历史事实的判断,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宗派论;第二阶段,西学东渐;第三阶段,古史辨的推动。另外,近几年来,对这一问题也有反思,可视为第四阶段。
(一)地理与史实
自从南宗派将南北宗论竖立为扬南贬北的旗帜,南北宗论就暗含了从理论主张向历史事实转向的可能。在晚明,南宗派代表人物沈颢在《画麈·分宗》中说:
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气运复相敌也。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出韵幽澹,为文人开山。若荆、关、宏、璪、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之沈、文,慧灯无尽;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若赵幹、伯驹、伯骕、夏(马)远、夏珪,以至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辈,日就狐禅,衣钵尘土。[1]121
此即有以画史待南北宗论之意。到了王原祁的时代,宗派论更明显了。
宗派论是含糊的,由它出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理论上的,一是史实上的。我们推原南北宗论的初衷,它只是理论性的总结,不是史实的描述;但它被宗派论利用后,则容易将理论当成史实,这也是宗派论者乐于看到的。特别是清中期,出现以地理因素来解释南北宗论的说法,则明显有欲以地理之差别坐实南北分宗史实的倾向。如沈宗骞《芥舟学画编》第一篇《宗派》讲南北宗论:
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惟能学则咸归于正,不学则日流于偏。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
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禀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
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
故稽之前代,可入神品者,大率产之大江以南,若河朔雄杰气概,非不足怵人心目,若登诸幽人逸士,卷轴琴剑之旁,则微嫌粗暴。故佳者但可入能品耳。苟质虽禀此,而能浸润乎诗书,陶淑乎风雅,泽古而有得焉,则嶔崎磊落之中,饶有冲和纯粹之致,又安得以其北宗也而少之哉。[2]501
董其昌讲“南北宗论”时有一句话:“其人非南北耳”,但到了南宗派的沈宗骞,虽然也讲“其不可拘于南北者”,但不免有改成“其人亦南北耳”的嫌疑,其理由就是南北地域之别造成画家气质不同,因而决定其画风不同,即地理因素是决定南北差别的重要原因。这也就为将南北分宗作为历史事实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的童书业也讲地理,也将南北宗论作为历史事实来反对,是同一道理。
(二)地理与书法南北宗论
清代明确将绘画南北宗论当成一种历史事实的表述还不多见,但可以从间接的方面观察这种思想倾向。首先是从书法理论的角度观察。将书法的南北分派视为史实,则从嘉道间阮元论南北书派中见出一点线索。阮元《南北书派论》俨然是从史的考察来讲的:
元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今近年魏、齐、周、隋旧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迹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互相诟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3]188
阮元讲书法的南北分派,而不讲南北分“宗”,这种微妙的差别,反映了不同的观念。他在这里讲述的是历史现象,而不是理论问题,与画之南北宗论貌同实异。阮元以南北朝经学史学比附南北书派,或者也受到儒教南北分宗现象的影响。在这篇文字中,阮元说“南派乃江左风流”“北派则是中原古法”已涉及地理概念。晚清俞樾《陶心云稷山论书诗序》谈书法分南北两派时说:
自郑康成说《禹贡》,导山有阳列阴列之名,而后世遂分为南北二条,北条以河为主,南条以江为主。江河形势,千古不易,而风尚因之而异。微而至于艺事,画绘有南宗北宗,词曲有南曲北曲,又推而至于异教,佛家有南北二宗,道家亦有南北二宗,大率分南北而不分东西,乃江河大势使然也。凡南北分派者,实皆北胜于南,而人情则往往喜南而厌北,其端实始于唐。[4]591
这显然将阮元“南派乃江左风流”“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更明确为地理概念。
阮元作为《石渠宝笈续编》的参与者和《石渠随笔》的撰写者,从一般常理来讲,其《南北书派论》虽然没有讲是从绘画南北宗论来的,但他受绘画南北宗论的影响,也是不容否定的。明确将书法南北宗论与绘画南北宗论联系起来的,则是钱泳。而钱泳恰是从阮元的书法南北宗说展开的。钱泳《书法分南北宗》: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②(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书法分南北宗》,《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 册第167 页。又本卷《画学·总论》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轻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为皆非也。无论南北,只要有笔有墨,便是名家。”(《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 册第172 页)
这段文字对阮元之说概括得很好,从起首亦可知,书家南北派之说,确有自于画家南北宗说,而书家南北派说俨然以史论之,而“画家有南北宗”也暗含着它被看成历史事实的可能。这种书论暗中借鉴画论的情况,还有一例,即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九《欧颜柳论》:
然则右军之嫡嗣,当别欧与颜为二派,犹之禅家有南北宗也。虞虽统系之,然而虞与欧兄弟也,虞与颜则祖孙也,褚于欧则兄弟之子犹子也,颜柳于欧则亲尽而不属矣。世又有以欧柳并称者,故不可以不论。[5]431
这明显是借鉴绘画南北宗说的语气。在这种借鉴中,书法南北分宗是被当作史实的,也暗示他们将绘画南北宗看作史实。
(三)其他南北分宗说与地理
绘画南北宗论的影响不仅仅见于书法,且影响及于其他领域。比如诗分南北派、地理家之南北宗论等。这些领域出现的南北分宗说,也大多以史实待之,这也从侧面折射了绘画南北宗论被当成史实的可能。孔尚任《古铁斋诗序》:
画家分南北派,诗亦如之。北人诗隽而永,其失在夸。南人诗婉而风,其失在靡。虽有善学者,不能尽山川风土之气,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抵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为之而亦有不得者,乃不以已之意为诗,而假人之意以为诗。久假不归,虽山川风土亦不能效其功,所谓失在夸与靡者也。[6]708
此序虽然没有明确以史实看诗家南北分宗,但却明示这种分宗思想受了绘画南北宗论的影响。且如前所述,他也将南北相分归于地理原因,从地域差别上来强调这种相分的必然性。另如李元度《地理小补序》:
书画家及禅家皆有南北宗,二者殊途同归,特致力有不同耳。地理家亦然。王祎《青岩丛录》曰:葬书始于郭璞,后世传其术者分二宗,一主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法始于闽中,浙人传之,至宋王伋乃大行。一主形势,专求龙穴砂水之相配,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其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辿及赖大有辈,大江以南悉用之。二宗皆本于郭氏也。今按前法即所谓理气家,后法即所谓峦头家。据王氏之论,似杨曾专主形势矣。[7]429
这段俨然以史实待南北宗。所以此论的提出,容易惑人者在此。即南北宗天然有被误读为史实的倾向。特别要提的是,在这些论述中,地理因素是将南北分宗说归于历史事实的重要因素,而绘画南北宗论中,地理因素说的出现,显然也是将绘画南北宗论推向史实论的重要原因。
二、日本的误读及影响
如果说清代以来出现的这些倾向,将绘画南北宗论逐步推向史实论,那么,随着晚清的国际交流、语言翻译及观念隔阂等诸多因素,较早关注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日本将南北宗论直接理解为史实。
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向西方学习,他们对中国美术史的关心大约起于二十世纪初,其中,南北宗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受到关注的。二十世纪初③按陈彬和序,大村此书所涉内容在明治三十四年(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已刊布。大村西崖著,陈彬和译《中国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 页。,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将南北宗说的发明权归于莫是龙:“考南北二宗之说,盖自高齐之颜之推始,至唐之张爱宾,宋之郭若虚、邓公寿、赵希鹄,元之赵子昂等,则以为胸罗万卷之文人高士,当与仅挟技艺之职业画工有别,于是传至明代之莫云卿,遂成南北二宗之说。”[8]198他并未对南北宗说提出怀疑,只是略作补充说:
王摩诘为南宗元祖,其所作山水之轮廓,用钩斫皴法极少,此即文人画之特色。然未创渲淡之法,如明四大家之画,则全由北苑二米,元季四家而出也。此说在明末清初盛行,成为画坛之定论,是以浙派之澌灭,驯致文人之极盛也。[8]199
而且他俨然是接受这样的说法,并将其认定为史实的,谓:“清之绘画,仅南宗一派,有可述者”[8]217。1906年,泷精一发表《论中国山水画的南北二宗》说:
其实,画坛上的南北流派明显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才形成的。因除刚柔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区别。据我所知,中国画坛上的南北两派,并不是一开始就以笔致刚与柔的区别来区分,而是自唐至宋经历了一个历史阶段后,特别是产生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特性,如两派中大家除了用笔之外还创造出许多特殊的技法之后,才日益明显地区分出二大流派来。在唐代,李、王二氏画,除了用笔外,是否还有创作手法上的不同?我未能审知。即使如此,南宋时代北宗画家马、夏等人,不但发挥了笔墨的刚劲之趣,并且在布局上也创造出了单纯、清壮的风格,他们反对画院中过于讲究工细的另一派画家,力图在画中表现出幽逸的气韵,至此才形成所谓的北宗画特征,完善了北宗画的技艺,而成为后世所效法的北派。堪称南宗画派开山鼻祖的王维,善诗工画,人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后来的南宗画家皆以他为楷模……至宋以后,因时尚以及所遵奉的始祖的关系,引起两派的盛衰。[9]613
云云,显然是依据南北宗论并把它当成史实去讲的。
1916年内藤湖南《中国绘画史·清朝的绘画》:
中国画分南北派,这并不是根据地理划分的,这种分法主要是强调有两大派别,数百年来各自流传下来。有人说王翚将这两大流派的风格集于一身加以综合。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王翚并不是开山鼻祖,从明代开始,画坛上就已经出现了综合前人风格的气氛,唐寅等人最先学习北宗画派的手法,此人的北宗风格和宋元时期北宗大师的风格有所不同,他是那种比较接近南宗画派风格的北宗画家。从这时起,南北两派就有合并的倾向,到了清朝,王翚成功地将这两个画派综合在一起。以往各自独立的南北两派合二为一。[10]117
内藤湖南此文发表于1916年[10]217,他的这个论断,显然是以南北分宗为史实来看,并且对于清初王时敏推崇王石谷的说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1921年[10]217,内藤湖南《南画小论——论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仍然以南北宗的理论为史实:
南画开山鼻祖王维的作品出自盛唐,而与之相提并论的则是北宗始祖李思训父子的作品。因为到了宋代仍然有人继承王维的风格,描绘的作品都是现在所说的南画,因此认为王维开创了南画的观点并没有错误。[10]178
从日本早期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对南北宗的解读可以看到,他们基本将它看成历史事实。这些专家的误解不可能纯粹出于文字上的误读,因为有的学者与中国学者是有深入交流的。他们的看法,很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流行看法的影响。而这种观念通过日本人明确之后,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学界。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办大学教育,模仿西方模式,美术史也在其列。虽然中国有丰富的美术史遗产,但当时仍有美术史课“得暂缺之”的问题,于是教材的编撰首先依靠编译日本人的中国美术史教材,日本人对南北宗论的意见随之成为中国教材上流行的意见。
(一)陈师曾
陈师曾(1876—1923年)《中国绘画史》被认为是受日本著作影响极大的编译,也是以南北宗论为史实看的。他说:“唐朝山水可谓卓然成家,宗派别出。如李思训、王维、郑虔、卢鸿辈,以淡彩、水墨,各擅所长。而李思训父子细劲之皴法,金碧赋色又为特创。是后山水画南北分宗,盖始于此。时李思训为北宗,王维为南宗,历代相承,渊源可按。”[11]25“山水画至盛唐李氏父子乃集大成。后经安史之乱,入中唐,更有王维、郑虔辈出,别开一种水墨淡彩之山水画。其画传于韦偃、王洽、王宰、项容之徒,以至于五代之荆浩、关仝。中唐以后,以及北宋末之山水画家,大抵皆属南派。李思训一派,至南宋画院,睹再兴之运。”[11]26—27“清朝之山水,南宗独盛,北宗渐归澌灭。”[11]85“自清初至于乾、嘉之间,诸家虽各有特长,无不受南宗之化,惟金陵数子近于浙派者犹存北宗之风。”[11]88其第三编第一章《明朝之绘画》第三节《山水画之沿革》:
今就山水一科言之,自国初以至万历之际,属于南宋院体画之系统,可压倒南宋以降之画苑。其作品显著之征象于时代的色彩上见之,即可谓绍述南宋马远、夏珪之遗风。其南宋浑厚沈郁之趣,变而为建拔劲锐之风,遂树立浙派之新格。而周东邨、唐伯虎又属于南宋赵、李、刘之一派。周东邨乃介于南宗、北宗之间,而唐伯虎则偏重北派。盖山水画自唐始有南北之分,至明复有南北混合之势。明朝山水若南北分宗,难得显然之区画。其中有许多流派并行,皆各存其明朝时代之特相。今就其大致言之,可别为三种系统:即所谓属于马远、夏珪之一系统,李唐、刘松年之一系统,汲元季四大家之流者又别为一系统。此等流派之兴废,又可别为前后二时期:自国初以至万历,此等流派之中可谓属于前一系统者最盛行;万历末年以后,则后一系统者最占优胜。其势乃及于清之雍、乾之间,亦可谓由明末以贯于清朝也。明代正德、嘉靖之间,其属于后者之系统有沈周、文徵明,明末有董其昌、陈继儒辈接踵而起,其学识名望足压倒当时翰墨场中。文徵明本以文人画为标榜,董其昌等析笔墨之精微,究宋元之同异,以士大夫画之大成为己任,立南北两宗之区别俨然,有尚南贬北之论,倾倒一世。时代之风尚为之一变,而北宗渐衰矣。[11]70—71
可见,陈氏此书的主调即是史实论。需要注意的是,陈氏此书原稿成于1922年,1925年由俞剑华翰墨苑刊印,已有研究者指出,是受日本人所编中国美术史影响很大的,他将南北宗论直接作为史实对待,既有清代以来思想的影响,也有日本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潘天寿
同样,1926年潘天授(寿)(1897—1971年)编《中国绘画史》也主要从日本的著作中编译而来。④潘天授(寿)编《中国绘画史》1925年自叙:“本书大体以《佩文斋书画谱》,及中村不折、小鹿青云所著的《支那绘画史》为根柢,辅以《美术丛书》诸书;偏漏的地方,自是不免,还望读者有所指教。”(潘天授编《中国绘画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3 页。)此书中第二编《中世史》第三节《唐后期的绘画》说:
唐以后分山水为南北二大统系,以李思训为北宗的始祖,王维为南宗的始祖。明董其昌论南北二宗画说:“禅家有南北二宗(中略)”现在姑且不论他这样分派,是否妥当。只是后代常常从唐代寻山水画渊源,在此为最初着笔。原来山水画,从晋代汉人南下以后,蒸蒸焕发的风尚,到唐代完成格式而达于极点。至于唐人的喜好山水以及长于技术,可考寻当时的诸工艺品及诗文等,就可十分明瞭。[12]56
今查1937年正中书局出版,郭虚中所译的中村不折、小鹿青云著《中国绘画史》第二篇《中世期》第一章《唐代的绘画》第三节《唐代后期的绘画》相关内容如下:
后世分唐以降的历代山水画为南北二大系统,以李思训为北宗之祖,以王维为南宗的开山祖,像这样的南北画别之是否得当,我们暂置不问;至若后世求山水画的渊源于唐代者,实由于至唐始大成山水画的格式之故。⑤(日)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郭虚中译《中国绘画史》,正中书局,1937年,第43 页。按,原书出版于1913年。
如果对照前后文,可以看到,这种观点是潘氏直接移置日本人的说法过来的,只是加了一段董其昌的原文而已。
然而十年后,潘天寿的观点发生很大的转变。1936年,潘天寿在重新修订成的《中国绘画史》⑥见《弁言》所说。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 页。所新增之《绪论》中说:“吾国自有绘画以来……迄唐代李思训、王维出,更树为南北二大派。是后,递相祖述,作家如风云涌起,诚有不可胜数之概。”[13]1其第三编《中世史》第一章《唐代之绘画》:
至完成山水画之格法,代道释人物而为绘画之中心材题者,则赖有李思训父子与王维等,同时并起。于是山水画遂分南北二大宗,以李思训为北宗之始祖,王维为南宗之始祖。是说为明代莫云卿是龙所唱导,董其昌继而和之……盖吾国佛教,自初唐以来,禅宗顿盛,主直指顿悟,见性成佛;一时文人逸士,影响于禅家简静清妙,超远洒落之情趣,与寄兴写情之画风,恰相适合。于是王维之破墨,遂为当时之文士大夫所重,以成吾国文人画之祖。[13]62
中唐绘画,以主笔墨神趣之南宗山水,最有进展:作家亦最多。著名者,有韦偃、王宰、张璪、王洽诸人,以书法诗趣,各发展笔势墨韵之特长。[13]67
这种时隔十年的转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由最初怀疑南北分宗说而转向肯定南北分宗说是历史事实;二,将董其昌南北分宗说转让给莫是龙。
(三)傅抱石
陈师曾、潘天寿的编译又影响了傅抱石。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自序》说:“在六七年前,我曾费了七个月的时间,写《国画源流述概》十几万字,那时候国内尚无画史一类书籍出版……现在已出版的陈氏《中国绘画史》、潘氏《中国绘画史》、郑氏《中国画学全史》、朱氏《国画ABC》,不是都比我更丰富完善么?”[14]1“所以我重著这本书,是:A 提倡南宗。”[14]2可见他承认受陈师曾等人影响。
其中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郑氏《自序》谓我国自有画以来“迄乎唐代,李思训吴道玄王维辈出,遂赫然以画号大家,且树南北宗派焉。”[15]2第七章《唐之画学》:“安史乱后,入于中唐,则有王维者,创一种水墨淡彩之山水画法,谓之破墨山水,与李思训之青绿山水,绝然异途,而其势力之大,则或过之无不及,于是我国山水画,遂由此而分宗。李思训之青绿为北宗之祖;王维之破墨为南宗之祖。”[15]124即是从历史事实角度讲的。这种将南北宗论看作史实的认识,虽无证据为受日本人影响,但日本人明确了南北宗论是史实的这一观念。这种观念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晚清中日学界形成的一种共识。
在这种共识的影响下,傅抱石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发挥。他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唐代的朝野》一章总结说:
所谓文人画,所谓南宗,自是在野的。所谓北宗,自是在朝的。现在归纳一下:
在朝的绘画,即北宗。1.注重颜色骨法。2.完全客观的。3.制作繁难。4.缺少个性的显示。5.贵族的。
在野的绘画,即南宗,即文人画。1.注重水墨渲染。2.主观重于客观。3.挥洒容易。4.有自我的表现。5.平民的。[16]83
傅氏的这种历史总结,没有多少依据。此书承名世《导读》提到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说:“《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一书,是傅抱石尝试通过‘整个的系统’来认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实践。他以‘南北宗’的发生、发展为这一系统的基本结构,尽管未必能够全面反映传统绘画的演变历程,但就这一问题而言,他是竭尽了全力的。”[16]13
另外,傅抱石此书中出现的阶级论,也是西学影响南北宗论的表现之一。除傅抱石所述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用这种观点看南北宗论。如1937年李宝泉 《中国画南北宗作者及其地域性之研究》也将南北分宗当作历史事实,并认为外来西洋画将形成新的斗争势力:“由明末经清朝至于现代的中国画坛,南宗的力量是始终占着优势的。但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实生活,因有了外来西方另一种力量而起了变化;那西洋画在中国现代与未来的画坛上,也跟了政治社会经济而必然会引起那向来在中国南北宗之争以外的一种纠纷,以及变化与结果的。”[17]145而他也是以阶级论看南北之争:
中国画南北宗对峙问题的最大缘因,并非是为了南宗作者是识智份子,而北宗作者,却为非智识份子的画工,或画匠。那引起这南北宗对峙的最大缘因,乃是南宗的兴起是为了在朝或在野士大夫们的一种“享受”,而北宗的兴起,则为了皇亲国戚的贵族们的一种“享乐”。[17]135
1948年温肇炘《山水画的南北宗》认为南北宗论是莫是龙提出的:“分宗只不过是从内容发展到形式的一个运动过程罢了,并不是莫是龙一人所能设想出来的,他自有其历史的根据,并不唐突”[18]59; “我觉得在山水里与其说有南北二宗分立,到不如说是士大夫阶级和非士大夫阶级的对立来得妥当了”[18]60。当然,即便从阶级论角度讲南北宗论,也是以南北宗论为绘画的历史事实来看的。
三、古史辨与南北宗研究
在确认南北宗论是中国绘画历史的描述的前提下,出现了对这一结论的怀疑,认为南北宗论所描述的绘画史不合于历史事实。这集中表现在以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对南北宗论的研究。现在看来,这是现代受西学影响的新史学虚构的一个人为命题与一场无意义的争论。
(一)田中丰藏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古史辨学派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涉及南北宗论的研究。古史辨学派的形成,源于这样几个传统:中国传统的疑古思潮、日本的疑古史学、欧美的科学精神。这三个方面均有学者有相关论述,此不赘述。古史辨对于南北宗论的介入也体现了西学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童书业。而在此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日本的有关情况。现代学术界对于南北宗论提出疑问的,最早可见1912—1913年日本田中丰藏发表的《南画新论》: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南画的发展史,首先说了李思训派,其次说了王摩诘、董源、巨然、米氏父子。我认为这样在读者面前就渐渐阐明了南北二宗的意义,即李思训既非北宗始祖,王摩诘亦非南宗开山,原本仅是对自然界的态度不同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画法上才大相径庭。[19]629
但是,田中这段话并非对于南北分宗作为历史事实的否定,而只是细节上的调整。他说:“所谓南宗北宗,与其说是中国画史上独有的特殊现象,毋宁说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史都可发现的两种思想潮流。它们的分歧在中国表现得还不十分激烈。简要言之,北宗代表了那种立足于客观事实,喜爱典型,追求整齐,表现理想的倾向。与此相反,南宗的艺术风格则永远是放纵的、唯我的,任主观情愫尽情迸涌而不加制约的。”[19]638“在中国的南北两宗间,我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只能把两者都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而且两派都留下了具有同等价值的遗产。”[19]639田中丰藏虽然批判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存在的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南北宗论是历史事实⑦又如1942年青木正儿《南北画派论》:“回顾董其昌南北宗派说,被其归入南宗的王维、荆浩、关同、李成、范宽、郭忠恕、王诜实皆应列入北宗,故南画决非始于王维,北画亦非李思训一人为始祖。”(《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第652 页)云云,其所怀疑的只是细节上的问题,而对于画派南北相分的这样的史观,是没有改变的。。古原宏伸说:“田中三十二岁时发表在《国华》杂志上的连载《南画新论》是其以后发表的所有论文都未能超越的。文章富有新意和开创性。田中在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存在的矛盾。他的这种批判早于世界上的任何学者,比1935年青木(正儿)对“南北宗论”的批评更为彻底。”[20]268这当然也比童书业1936年将董其昌的分宗说断为伪画史早24年。从这种怀疑出发,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南北宗论的研究,基本一边倒地否定其为历史事实,其代表人物是滕固和童书业。
(二)滕固
1963年,俞剑华写《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对否定南北宗论的情况总结说:
在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以前,一部分研究画史的人,从文献记载上,从存世作品上,均可以发现南北分宗说没有充分根据,大胆地予以怀疑和否定。在滕固所著《唐宋绘画史》及《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中,就是这种态度。在我所写的《中国绘画史》中亦持同样见解。另有一部分研究画史的人,以考据的方法,来考证南北分宗说,把历史上许多证据摆列出来,证明分宗说的无稽,并进一步指出董其昌等创说的人别有用心。在这一方面首先发难的是童书业,他在1936年《考古社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继之启功在1939年在《辅仁大学学志》第七卷第一、二合期上发表了《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考》,对于童文有所商榷,同年童书业又在四月份的《大美晚报·文史周刊》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重论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兼答启功先生》,对于启文有所辨难,后来童书业又写了一篇四万字的长文《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发表在《齐鲁学报》第二期,是归纳了滕固、启功以及拙说,更加详细地考证了有关南北宗的各方面有关问题。他的主要之点是不承认董的南北分宗说,而就地理上、画法上另行说明了历史上的南方画派与北方画派;繁征博引,极尽考据家的能事。[21]470
文中所及滕固,是从日本学者那里,生发了对南北宗论作为史实的怀疑。
滕固留学日本的时候,田中丰藏的论文已经发表。滕固192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小史》说:“他(董其昌)将唐宋以来的画家,分为南北二宗,以南宗为文人之画,隐隐中绍述此派的正统以自居。其实他分南北二宗,没有多大的意义,不过拥护自己罢了。”[22]33又1933年出版的《唐宋绘画史》说:“南北宗之说,许多人都以为是董其昌所首唱的,实则董其昌同时代的或稍较前辈的莫是龙所唱导的”[22]41,并引董其昌:“云卿(莫的号)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来证明是莫是龙先提出,这当然不足为据。他说:
莫是龙、董其昌辈,把自唐以来的绘画,分为南北二宗,以李思训为北宗之祖,以王维为南宗之祖。这不但是李思训和王维死不肯承认的,且在当时事实上,绝无这种痕迹。盛唐之际,山水画取得独立的地位是一事实,而李思训和王维的作风之不同亦是一事实,但李思训和王维之间绝没有对立的关系。即到了宋代院体画成立了后,院体画也是士大夫画的一脉,不但不是对立的,且中间是相生相成的;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清楚楚地分成作为对峙的两支。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自有较详的说明。所以我说南北宗说是无意义是不合理,不是过分之词。[22]41
另外,他也指出,南北宗说是“南宗或文人画的运动,是近代绘画史上把元季四家定型化的一个运动”[22]42,并指出“有了南北宗说以后,一群人站在南宗的旗帜之下,一味不讲道理地抹杀院体画,无形中使人怠于找寻院体画之历史的价值”[22]42;“我们固然不必反常地把院体画提高,然亦不应当被南宗运动者所迷醉。我们只应站在客观的地位,把它们的生长、交流、对峙等情形,一一纳入历史的法则里而予以公平的估价”[22]42。从这一角度看,二十世纪上半叶南北宗论的批判运动,可以看作是院体画(北宗)逐渐取得一统地位后的斗争,但北宗一派的确没有在理论上有什么新的建树。滕固到过日本,他对南北宗论的怀疑晚于日本学者,因此,他一些关键性的论断,如论南北宗首倡于莫是龙,日本学者早已言之。⑧《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附录《滕固艺术活动系年》,滕氏《中国绘画小史》出版于1926年。《唐宋绘画史》出版于1933年。1957年,邓以蛰为滕氏《唐宋绘画史》写校后语谓:“最近有人对明末莫是龙、董其昌辈所倡导的画之南北宗说提出异议,不知本书作者二十余年前在这本著作中即已大张旗鼓地反对南北宗说,说它不符合于历史事实。”(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41 页)滕固力求“客观”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史观的影响,或者,二十世纪南北宗论批判运动也与西方史观有关。
(三)童书业
二十世纪对南北宗论的否定,主要基于南北分宗是历史事实而讲的。把“南北宗论”当成是画史,从而予以批判的,典型代表是古史辨学派的健将童书业。他在1936年《考古社刊》第四期上发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认为“南北宗论”是莫是龙首先提出来的,是伪画史。[23]248童书业并未留过学,但并不能说他没有受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童书业《画史》说:“从前人所说的‘南北宗’,固然不合历史真相,但真正的南北二体,也确是‘至石谷合而为一’。”[24]238又童书业《影响六百年中国画坛的大画家——黄子久》:
从前人把中国山水画家分成“南”、“北”两个宗派,根据考证的结果,知道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山水画的确可以按地区分做“南”、“北”两派。新的“南”、“北”派说法,是根据历史事实来分的,其理由我们另有专文叙述。大体上说:“北方画家用笔尚刚、尚方,所画多是北方的石山;南方画家用笔尚柔、尚圆,所画多是江南地区的土山。“北画”盛于南宋以前,“南画”盛于元以后(当然,也有北方人写“南”体山水和南方人写“北”体山水的)。“北”体山水画家,主要有:荆浩、关仝、李成、范宽、郭熙、李唐、马远、夏珪、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刘松年、仇英等;“南体”山水画家主要有董源、巨然、米芾、米友仁、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董其昌和所谓“四王、吴、恽”等(还有些人介乎两派之间的,如赵孟頫、沈周、文徵明、唐寅、石涛、龚贤等)。黄公望是“南派”中影响最大的画家;从他以后,六百年的中国山水画坛都受他的影响,直到最近的时候。[24]286
童书业这种按地理分布来划分南北画派的思路,延续了清代沈宗骞等人的做法,只是对自古以来行隶分野现象的一种归纳。童书业将“南北宗论”当作画史并予以批判,其原因大约如下。
原因之一,考据学和疑古思潮的影响。童书业《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说:“中国山水画分南北两宗之说,自明以后,只要是略懂绘画的人无不知道。宣之于口,笔之于书,大家都想不到这里面有绝大的问题。到了近年来,考据学大兴,历史上无论什么事物都要经过一番考据,才能继续存在。于是就渐有对这种说法怀疑的人。”[24]3他说,在中国怀疑山水画“南北宗”之说最早的人是王季欢。1925年,王季欢对童书业说:“山水画南北宗之说是不可信的,他们所谓南宗,多是北人;所谓北宗,多是南人”[24]3。1925年,陈师曾的书已刊印,日本学者的看法或者早已影响到中国,王季欢的观点未必不是来自日本人的看法。
原因之二,五四运动反封建思潮的影响。童书业《王麓台绘画的评价问题》谈到古今人对王原祁评价不同时说:
五四运动前后,民主革命思潮兴起,新派的绘画研究者,有反封建的要求,而麓台在绘画上的地位,正和桐城派大师方、姚等在文学上的地位差不多,甚至可以说,和孔子在思想界的地位差不多,所以绘画界的反封建锋芒,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到麓台身上去。不仅麓台,清代正统派绘画六大家“四王、吴、恽”都遭到批判。这种运动和“打倒孔家店”的运动是差不多的,在当时,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我个人受了先师王季欢先生和胡佩衡师、俞剑华先生等人的影响,也不自觉地成了反“四王”的一个积极者,并且曾对董其昌——“四王、吴、恽”画派的理论要害——“山水画南北宗说”进行了批判。[24]312
在这里,他承认也受了王季欢、胡佩衡、俞剑华的影响。另按下引《论胡佩衡先生的绘画》中也说:“我对于绘画史上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看法,主要是导源于俞剑华、王季欢两位先生的。”[24]333按前引俞剑华的回顾,俞剑华也应该受了滕固影响,或者说,其实童书业也是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的。
原因之三,北方画派的崛起。反对南北宗论,伴随着对院画或北派的重新认识,这在滕固的著作中即已表现出来。五四以来,绘画界出现了新情况,童书业《论胡佩衡先生的绘画》说:
本来五四以来,以北京为中心,早就形成了一个新北方画派,虽是有些南方人,到了北京,也创造了一些与江南派画不同的画格。这种画的特点,就是用笔比较刚劲,用墨比较湿厚、浓重,设色往往也比较浓,它和江南四王画派有显著的不同。而且新北方派的画家们还有新绘画理论,一般比较轻视董其昌以来的松江―太仓画派,有的推崇明人,有的推崇宋元,他们对于四王的余派,进行了一些批评。这种绘画上的“复古”,实际上是创新,以“复古”为号召,以创新为实质。胡佩衡先生就是这一派里的健将。胡先生除对王石谷尚有若干肯定外,对其它三王,特别是王麓台,压抑得很低。先是王季欢先生受他的影响,后来我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排斥董其昌以来的松江―太仓画派,高抬宋元,而主张创格。胡先生是还相信山水画分南北宗说的,王季欢先生和我则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这就是对于松江―太仓画派画论的怀疑。这种怀疑是导源于胡先生对于松江―太仓画派的轻视的。当然,我们又受到了俞剑华先生等人的影响,我对于绘画史上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看法,主要是导源于俞剑华、王季欢两位先生的。[24]332
其中他讲的胡佩衡受过西画影响,著有《冷庵画诣》,可窥其思想大概。而童书业则将其主要思想概括为“除对王石谷尚有若干肯定外,对其它三王,特别是王麓台,压抑得很低”。也可以想见,这种新北派画风的崛起,与湖社有关,或者也与西画的冲击有关。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对南北宗的反思,也可视作是西画东渐背景下必然出现的新情况。或者说,因为西画的冲击,也连带出现了对“北宗”画的重新认知。
另外,1947年钱夷斋《山水画非南北宗论》也认为绘画南北宗论虚妄无稽,毫无根据。他认为山水画要发展,须废弃南北宗论:
但事实到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被轻视的北宗画派,在遗迹上发掘到他们对绘画技巧贡献的伟大,并不亚于南宗诸家,甚至也有超越的地方。像不享大名的阎次平,他绘四乐图的山石皴法为大可惊人的,我们深叹继起无人,即就夏圭的长江万里图卷,也落落大方,真有磅礴的气象,决非吴仲圭的敌手。[25]7
1949年后约四五十年间,否定南北宗论成为学术界主流,只是近年来有关研究稍有变化,虽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南北宗论只是美学主张,但主流的认识仍然将其作为历史事实看待。
结语
总体来看,将南北宗论理解为历史事实,这种误解在日本学者那里得到加强,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学者。这件事走到极端,就是古史辨派的辨伪,其实这本身是一个假命题。南北宗论在美学或者绘画思想上是有价值的,但它绝非历史事实的陈述。二十世纪后半叶,逐渐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王原祁《麓台题画稿》之《题仿万壑松风》说:“此图以赵松雪题,董宗伯遂目为赵作,识者驳之,至今为疑。余以为此赏鉴家之言。若论画法,惟求宗旨,何论宋元”[26]217,对于南北宗论等,仍要从“宗旨”一边去看,而不能为“赏鉴家”的标准对待。虽然如此,南北宗论从未在实质上指导过艺术实践。它首先并未指导过董其昌的艺术实践,也未指导过王时敏的艺术实践。至于以南北宗论标榜的南宗派,他们真正的师法对象是黄公望,南北宗论只是他们排斥异己的幌子而已。到了二十世纪,南北宗论指导艺术实践更无从谈起。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它首先被误读为一种历史结论,进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最终沦于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假设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