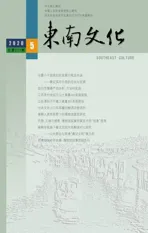在博物馆中讲故事:博物馆叙事的新方向
2020-12-07金姆赖斯王思怡
〔美〕金姆·赖斯(著)〔中〕王思怡(译)
(1.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美国华盛顿特区;2.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一个好的故事可以让人陷入其魅力中,并获得情感共鸣、心灵启迪甚至做出人生的某些转变。博物馆也致力于通过“讲故事”的手段来建构展览的意义和价值,而一个具有叙事潜力的展览并不意味着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诠释。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最重要的似乎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述故事的方法、如何在博物馆中“讲”故事以及如何将其“讲”成吸引、刺激观众的有趣故事。讲述数字故事、参观讲解中的故事、隐秘历史故事叙述等方面均为博物馆叙事的重要课题,其中,向观众提问、通过故事联结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反思这两种最为有效的叙述手段值得深入探索。通过提问吸引观众从展览找寻答案,同时通过阐述与观众经历相关的故事来帮助他们加深印象、抒发情感。
“讲故事”(storytelling)可以说在各行各业运用得十分广泛,甚至有些广告都打着“不是贩卖产品,而是贩卖故事”的宣传。一个好故事就像魔法一样让人深陷其中,使人感同身受,并进行沟通。从史前时代的口述到现代的数字化,人类讲故事的形式随着语言、文字、印刷、影像、媒体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从只依赖个人记忆的口述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书写时代,再到确立书写格式的印刷时代,再现多重感官的影像时代以及双向交互虚拟体验的数字时代,每个时代的故事都有着不同的传播媒介,博物馆见证着故事发展的历程。
博物馆叙事(museum narratives)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博物馆的重要支柱,讲故事的形式使所有人跨越文化与地域,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讲故事这种形式古已有之,在“文字”尚未被发明之前,人类通过“绘画”沟通,并编成故事流传,如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Grotte de Lascaux)就是典型的代表。我们经历了无法将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漫长时代,人类把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统统融入“故事”中,并通过口耳代代相传。神话、圣经故事、传说和民间故事,这些都是当时的典型故事形态,“故事”扮演了让人类认识世界的象征角色[1]。而如今在笔者看来,讲故事是博物馆工作的必要手段,通过故事我们分享兴趣,形成共同体。目前在西方社会,各行各业均十分关注讲故事这种形式。
讲故事可以将参观博物馆变成一种顿悟体验(aha experience)[2]。故事是我们最基本的学习方式,它有开始、结束和来龙去脉。讲故事的学习方式不是说教,而是鼓励个人思考和公共讨论。故事可以激发惊奇和赞叹,并能够让听故事的人想象不同的时空,可以从特别的案例而推之普遍,让人产生共鸣和共情[3]。故事可以保存个人和集体的记忆,同时向成人和儿童诉说。可以说,博物馆就是故事讲述者,因为自博物馆诞生以来,一些群体就认为博物馆中有值得被讲述的故事,其后便代代相传。
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只要通过网络搜索,任何信息都唾手可得。我们享受着丰富信息的便利性,每个人都可以从网上轻松获得并使用资讯。或许资讯本身有其价值,但如果只是单纯搜集而没有经过重组排列,这些信息只不过是成堆的毫无意义的原料。反之,如果能在众多原料当中挑选出可利用的信息并妥善组合,便能创造出带有新价值的内容。若要为爆炸的信息赋予价值,就必须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组合,并建立脉络将其串联起来。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使用信息并从中抽取出我们需要的信息。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博物馆的故事讲述具有特殊性。
人们被成千上万的信息围绕,而网络带给人们获得故事的便利渠道。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故事的一些属性。故事的讲述往往是从一个视角展开的,所以对于同一个故事便会有不同故事参与者的不同讲述。不仅如此,没有故事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接受故事的时代或人们立场的不同,故事也会被进行新的诠释和创作。因此,在数字时代,讲故事更应该考虑到故事的上述属性。讲故事是创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支配着我们如何体验故事,并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建立这个“框架”就像建立一个世界[4]。正如当我们阅读或玩电子游戏时,我们会在故事空间中填充角色、事件、背景等。这个框架可以受物理边界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受概念边界的限制,例如受文化规则约束。而数字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这种限制,数字的属性促使多元交流与互动。即使在数字时代,故事也非唾手可得。因为故事是在整合信息的过程中通过使用者的积极参与而产生的,所以在网络化的计算机环境中,通过数字媒体形成的数字故事创作从最初就是以“使用者的参与”为前提的[5]。
因此,博物馆展览的策划与观众之间的相互对话会在博物馆建构的所有内容里发挥作用,成为重要元素,而核心就在于能使双方相互沟通的叙事。在讲述博物馆数字故事中,最重要的是这种双向互动是可视的,文本不再是固定的、完结的,而是通过不断增减与变化来调整所呈现的内容。在数字时代,讲故事最直接的作用便是激发人们探索叙事的创造性潜力,丰富博物馆体验。而建构令人满意的叙事体验不仅仅需要对“讲述数字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的思考,更需要具体思考有关叙事的持久性问题,包括叙事的连贯性和差距以及探讨叙事的空间、互动和中间过渡方面的新机会。
在博物馆中讲故事最普遍的手段便是参观讲解(tour guide)。无论是馆内安排的讲解,还是其他机构和个人组织的参观讲解活动,都会用到讲故事的手段。在美国,有不少像Museum Hack之类的机构专门组织观众有趣地参观博物馆,他们会推出特定主题,面向特定群体开展讲解导览活动,甚至有些还提供道具和服饰让观众产生沉浸体验。笔者也曾经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们参加过这样的导览活动。这些学生既没有特定的专业,也没有受过博物馆学专业的训练。对于这些18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认为参观博物馆就像他们爷爷奶奶会做的事情。而这次有趣的导览使他们改变了之前对博物馆的刻板印象,发现参观博物馆也很有趣。这样的故事导览使博物馆参观更加有趣,同时也在人和物之间创造更加整体性或个性化的交互。但是这种机构进行的导览项目价格不菲,像美国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的导览活动需要49美元,而活动仅持续2小时。
当然,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博物馆都必须讲故事,而历史类的博物馆或历史建筑等在叙事方面更具吸引力。它们通过故事让观众切实地进行想象,从而增加代入感和参与兴趣,可以说讲故事是历史博物馆的核心形式。如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历史建筑福特剧院(Ford’s Theatre),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这里被行刺。起初,剧院地下一层有一个关于整个内战的展览,但很多学生团体却对此展览不感兴趣,也不了解到此处参观的目的。原本林肯刺杀案是一个十分具有戏剧性的故事,因为林肯的死成为内战彻底结束的预兆。而在此展览中却被弱化,使观众失去兴趣。博物馆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尝试改变,他们先把所有刺杀信息上传到手机,因为福特剧院是学生团体指定的参观地,而手机对于学生群体来说使用频繁。但剧院调查发现此下载量十分低,而其他类似的调查也发现在历史博物馆中只有不到10%的观众才下载附加信息和材料。因此,福特剧院改变了策略,他们制作了很多刺杀案当晚的人物模型,并将当事人对于枪击现场的叙述添加在各个人物模型上,同时还将各个人物的故事叙述做成了录音放在iPad里供观众收听。调查发现,这样的改进效果很好,观众很愿意听不同人物对事件的叙述,如坐在林肯旁边的妻子玛丽·托德(Mary Todd)的叙述:“血瞬间飞溅在裙子上,我的头和脸都被血覆盖……”这让很多观众感受到当晚的恐惧。同时,很多观众也从这样的叙述中联想到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被行刺和“9·11恐怖袭击事件”(September 11 attack),这就是讲故事的力量,将观众从过去带回现在。
与此同时,关于隐秘历史或苦难历史的故事叙述更能触动观众。以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的家——蒙蒂塞洛(Monticello)为例,该历史建筑及其展览尝试讲述一段隐秘的历史。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起草者,在美国历史和社会中享有极高声誉。但是在他提出平等主义思想的同时,家中却有二百多名奴隶,因此,在展览中如何诠释他的思想及其与奴隶的关系便变得十分敏感。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件使之变得愈发复杂的事情,那就是杰斐逊与家中黑奴萨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绯闻。传言萨莉所生的七个孩子全是杰斐逊的孩子,直到2000年,通过萨莉的后代与杰斐逊的DNA测试,结果显示亲生比例为95%,即杰斐逊便是当年孩子的父亲。但当观众参观蒙蒂塞洛时提出想要看到关于萨莉的描述,蒙蒂塞洛却以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为由而未展示萨莉的故事。之后,博物馆工作人员便开始了对萨莉的资料搜集,随后又开展了大型的口述历史项目,获得了很多在杰斐逊史料记录里没有的材料,这也许更能够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杰斐逊。很长一段时间,杰斐逊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如上帝般存在,但是因为有这样一段隐秘的故事才让人们意识到杰斐逊也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的缺点。2016年,考古人员发现了蒙蒂塞洛的浴室,通过相关考古证据可以推知该处便是萨莉的房间,而这个房间紧挨着杰斐逊的卧室。但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他们并没有萨莉的任何肖像,不知道她的相貌,这给展览的叙事造成了一些困难,后来他们用剪影和当时的服装做了较为艺术化的展示,给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这样适当留白的空间让观众自行发挥想象力作为填空或衔接,其实也是引导观众进行双向互动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在其他的媒介中也广泛应用,如在小说中被称为全景技巧(panoramic technique)[6],在电影中是蒙太奇(montage technique)[7],在漫画创作中则是封闭性联想(closure association)[8]。
而对于伤痛历史或苦难的叙述,使用受害者或幸存者的故事讲述十分具有说服力。如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不仅以展览的方式展示伤痛故事,同时还邀请幸存者到博物馆现场导览和讲述。这是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2012年,笔者带领来自伊朗的博物馆同仁参观大屠杀纪念馆。这里的背景是,中东地区是在政治、宗教上与以色列十分对立的区域,他们认为大屠杀不是真实的,是以色列人编出来的故事。当这25人参观时,他们表现得十分疑惑,所有人都认为展览是感人的但却并非真实发生的事。而正当他们要离开展厅时,其中一位博物馆志愿者开始向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他的家人在他12岁时全部遇难,而自己也被关进波兰集中营,之后他在战争结束前逃出集中营,并躲在树洞中靠吃树皮维生……而当这位志愿者在描述自己经历时,伊朗的博物馆同仁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过家人在战争中的不幸遇难,其中一位年轻的伊朗男士随后提到他母亲死于一场爆炸。这位年轻男士与志愿者分享着一种共同的情绪,他们之间产生了共情与共鸣,第一人称叙述的力量由此显现。
在博物馆空间中这些故事叙述如何传达给观众也需要进一步讨论。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曾举办过一个关于好莱坞服装(Hollywood Costume)的展览,馆方使用人物的全息投影技术(front-projected holographic display),根据演员参与影片的故事,讲述当时的拍摄轶事,同时结合电子触摸桌,观众可以自由地在电子触摸桌上观看图片、文档和视频等。
实际上,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讲故事,目的就是让故事更有趣、更吸引人。其中,直接向观众提问的方式屡试不爽,令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美国费城东州教养所博物馆(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 Museum),此处是19世纪美国最大的监狱,后来被停用而变成博物馆。在其“今日的监狱:大规模监禁时代的问题”(Prisons Today:Questions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展览中,馆方首先抛出“你有没有犯过法?”这一问题,观众的选择决定了其将看到的故事,大部分人会选“没有”,但实际上70%的美国人都曾有过“犯法”的时刻,比如超速等类似的“犯法”。但是为何大多数人都没有被捕或被送进监狱?这个展览便很快地吸引了观众,促使观众很想继续参观寻找答案。大约25年前,美国通过一项法律,如果你三次使用毒品被抓,你就会被直接送入监狱。这就导致了美国监狱的人数过量,每年监狱的花费竟然比大学的花费高出近三倍,这样的设计引发观众对于目前美国监禁问题和改革刑事审判系统的思考。
展览让观众产生共鸣和反思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它所传达情感的普通化和普遍化。与费城东州教养所博物馆相类似,瑞士伦茨堡施塔弗豪斯博物馆(Stapferhaus Lenzburg)的临时展览“关乎信仰”(A Matter of Faith)中有两道门(信或不信)供观众选择,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打开一扇门并进入展览,这就保证了展览接下来所要讲的故事是观众自主选择的结果,是他们所关心的内容,同时也与自身紧密相连。
如何才能将观众真正关心或观众自身的故事带入博物馆中?这是当下博物馆十分关注的话题。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城移民公寓博物馆(Manhattan Tenement Museum)便展开了在全国范围征集移民物件与故事的项目——“你的故事,我们的故事”(Your story,Our story)。移民公寓博物馆的展览也基于故事而展开。观众需预约参观,且参观时需跟随导览人员探索某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展览旨在呈现1863—1935年多个国家约七千名移民的家庭故事,虽然讲述的只是代表性家庭的故事,但也可成为当时这一群体的缩影。每个公寓都还原一户移民家庭生活并讲述他们的故事,如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便以戏剧性的开头展开:“一天早晨,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出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不知道他的去向,他是逃跑了还是意外死亡了?他有没有组成新的家庭?男主人的出走使女主人和四个孩子几乎没有生活来源。为了活下去,女主人在公寓里开起了裁缝店,终于能够养活一家人……”笔者的祖母一家也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当时也住在这个街区,这个故事引发了笔者对于祖母当年生活的联想。
英国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在联系观众方面的工作较为领先。他们早在2008年便开始在青少年观众中开展“说物”(Talking Objects)项目,通过物的故事来拉近与青少年观众的距离,同时也在不同背景的青少年间创造针对博物馆物的对话、思考和辩论的机会。与观众息息相关的“物的故事”(Object Stories)项目也在美国波特兰艺术博物馆(Portland Museum of Art)展开,此项目始于2010年,把更多的拥有不同背景的社群带入博物馆中,从而使波特兰艺术博物馆变成一个公众交流想法和相互沟通的平台。他们邀请流浪者、视障者、退伍军人、黑人、LGBT群体等分享自己的故事、物件或成为展览的策展人,目前这个项目的社会反响很好且一直延续至今。这样的方法不仅是博物馆与观众直接交流的重要手段,同时项目本身对观众来说也充满意义。
无论博物馆的叙事结构多么复杂,也不论讲故事的方式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只要其内部存在完整的逻辑链条,便会使展览有意义。因此,对于博物馆故事的叙述,比起“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说”。这并非意味着题材与主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说什么”已经是最基本的条件,而“如何诉说”“如何具体呈现”牵动着整个展览的内容,这一部分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说,讲述故事时,诉说相对不重要,呈现才是重要的。主题经常躲藏在“串联物”与“事件”的架构背后,然而观众实际上看到的是物与事件。所有展览的目的不在于用“说”的方式,而是用“呈现”的方式向观众传达背后的主题。博物馆通过故事与社群加强联系,正能体现当今博物馆需要明确的议题:其一,有关“谁在说话”(who says it)与“说了什么”(what is said)等叙事(narrative)与发声(voice)的议题;其二,有关“谁在听”(who is listening)以及诠释、理解与意义建构的议题[9]。
(本文主要基于Kym S.Rice于2019年12月31日在上海大学的讲座Museum Storytelling:New Direction in Museum Narratives拓展而来。)
[1]S.Cohan,L.M.Shires.Telling Stories: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London:Routledge,1988.
[2]L.Bedford.Storytelling:The Real Work of Museums.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2001,44(1):28.
[3]同[2],第30页。
[4]Amelia Wong.The Whole Story,and Then Some:“Digital Storytelling”in Evolving Museum Practice.[EB/OL][2015-01-31][2020-02-15] https://mw2015.museumsandtheweb.com/paper/the-whole-story-and-then-somedigital-storytelling-in-evolving-museum-practice/
[5]J.Hartley,K.McWilliam.“Computational Power Meets Human Contact.”In J.Hartley,K.McWilliam(eds.).Story Circle:Digital Storytelling Around the World.Chichester,UK:Wiley-Blackwell,2009:3-15.
[6]P.Lubbock.The Craft of Fiction.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3.
[7]L.Manovich.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The MIT Press,2002.
[8]S.McCloud.Understanding Comics:The Invisible Art.William Morrow Paperbacks,1994.
[9]E.H.Greenhill.Changing Value in the Art Museum: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In B.M.Carbonell(ed.).Museum Studies:An Anthology of Contexts.Blackwell,2004: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