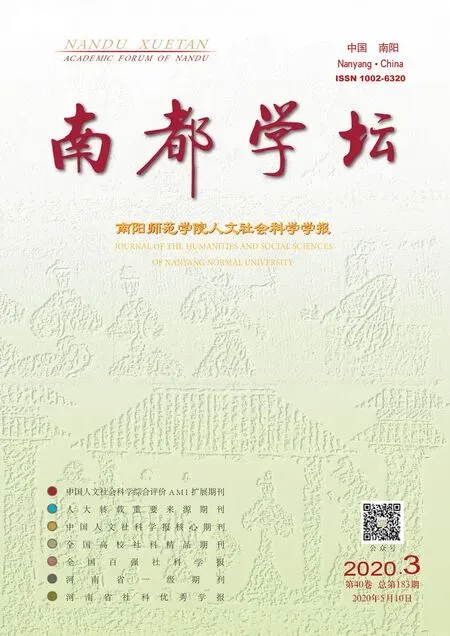延安时期中共祝寿活动的社会功能探析
2020-12-06焦金波
焦 金 波
(南阳师范学院 a.马克思主义学院;b.南水北调精神研究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祝寿活动,多为历史人物传记回忆录中所记载呈现。学术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对祝寿所作的总体性研究和对祝寿活动政治功能的专门性研究[1]。祝寿民俗活动是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定功能。这种功能包括它在社会生活与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所发挥的客观作用[2]27。祝寿作为国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图景和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关联,包含着众多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观念,具有重要社会功能。正因为如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祝寿为载体,通过举办大量祝寿活动,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从而改造社会习俗,建立社会新风尚。
一、弘扬敬老美德,诠释人生意义的教化功能
民俗在人类社会化文化过程中具有教育和模塑作用[2]27。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在根据地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教育和引领作用。
(一)承继优良传统,弘扬敬老美德
养老敬老,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优良文化传统。寿庆作为一种礼节形式,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实际作用[3]84,可以说突出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精神。因此,千百年来寿庆习俗广泛流传于我国民间,一直为人们所倡导和传承。
延安时期,作为局部执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祝寿活动,表达出自身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承继,同时更以执政党的身份在社会民众中倡导和弘扬这种传统,在根据地产生很好的影响。
(二)回望寿者阅历,诠释人生意义
寿庆仪式标识出人生岁月流逝的痕迹,社会变迁在生命历程中的映射,先辈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家族血脉谱系的繁衍,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4]160。人们在寿庆仪式中,回顾先辈人生足迹,回溯家族繁衍兴衰;追思生命之源,回首成长历程,激发生命动力,体悟个体生命价值,最终,在完成人生意义解读之后,将生命终极关怀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善待自身、感恩父母、回报社会,完成人生价值的书写与意义的升华。
回顾受贺者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其目的则在于解读受贺者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在祝贺朱德60岁寿辰时,中共中央在祝词中盛赞其忠诚人民, “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5],为民奋斗,不畏险阻,淡泊名利。周恩来在祝词中称颂其“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6]。东北民主联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称赞:“你一生爱民如子,疾恶如仇,为革命艰苦奋斗卅年。”[7]习仲勋撰文表示,要“学习您为了人民利益,不问个人得失”“百折不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钢铁般的原则立场”“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8]。而在此之前的朱德54岁寿辰时,陆定一发表《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回忆当年亲历的情景说:“他慈爱可亲”“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9]。中共中央祝贺徐特立70岁寿辰说:你对于民族人民,“抱有无限忠诚”;对敌人斗争,“不妥协不动摇”[10]。刘伯承50岁寿辰之际,朱德高度评价说:刘伯承“以其半生血汗,尽瘁于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仍不知疲倦,刻苦奋发,任重道远”[11]。由此可见,在对受贺者的高度评价中,为民服务、坚定信仰、不屈斗争、奋进担当成为重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受贺者人生意义的解读与褒奖。也就是说,受贺者的人生是追求民主进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革命人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奋斗,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受贺者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所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生意义的独特理解与阐释。这种理解与阐释,从民族国家高度,置于国家民族场域中去审视,超越传统意义上从家族延续发展来解读祝寿对象人生价值的特定维度,这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解读维度的升华。这种独特理解与阐释,借助祝寿这一特定宏大民间场景,通过持续不断举办的祝寿活动的反复持久的展示,灌输给根据地群众,从而使根据地群众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不断被引领并最终实现升华。
二、巩固同志情谊,密切政党合作的维系功能
“民俗是人们认同自己所属集团的标识。”它统一社会成员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使群体内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2]30。民俗具有维系功能。对于寿庆礼仪而言,它使祝贺者和受贺者之间获得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机会,是人们重温感情与加深情谊的重要契机,具有加深人际情感的交际功能,从而具有维系社会群体的功能。延安时期祝寿活动,更是将传统家族范围的祝寿活动变为公共性社会活动,将社会成员分散的心理体验与情感意识整合并升华为共同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发挥出加强社会成员间联系,凝聚社会群体,实现社会和谐的维系功能。
(一)巩固革命队伍中的个人友谊
延安时期祝寿活动具有重要的加深情谊的社会交际功能。徐特立60岁寿辰时,毛泽东致信徐特立,一代伟人对老师的尊敬热爱溢于言表: “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12]477朱德则写信表达出两人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亲密友谊:从南昌起义到长征直至现在,“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13]。吴玉章60岁寿辰之际,林伯渠饱含深情地写道:少小相知,而今白首,“缅怀我们这40年来共同经历的风浪”;“无论是你和我,难免有一种逾乎寻常的感情”;“为了值得珍贵的友谊,为了胜利的明天”;“祝福你健康地生活下去”;我们要看到我们“所要追求的新社会的”[14]150。祝寿成为根据地人际交往中加深情谊的重要载体,师生情、同学谊、战友缘等因此得以维系和强化。
(二)密切中共与其他民主进步力量的政治合作
延安时期,中共为延安五老祝寿,是团结和联合国内民主进步力量的重要契机。董必武60寿辰之际,率先寄送祝寿诗的黄炎培在诗后附语说:“吾人理想,大致相同”;“逐寇难,寇去而有以善其后,则尤难,兄教何以教我”[13]。邓初民称赞其“有品有学,至仁至义”“公忠自矢,爱国爱民”等诸种美德,郭沫若作诗《董老行》赞扬其高贵品质和不屈斗志,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等民主人士也都热情称赞高度评价[15]19。
中共多次为国统区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举办寿庆活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为马寅初60岁寿辰送贺联:“桃李增辉,坐帐无鹤;琴书做伴,支床有龟”,庆贺其健康长寿,赞扬其坚持真理、疾恶如仇、奋起抗争的斗争精神,揭露和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迫害。爱国将军冯玉祥60岁寿辰时,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祝寿诗,对其坚持抗日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15]18。郭沫若50岁诞辰时,董必武在《新华日报》出版的《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25周年特刊》上发表贺诗,称赞其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鼓励其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继续奋斗[16]43。此外,中共还向沈钧儒、鹿钟麟、洪深、梁希等庆寿,以此推动他们为抗日、民主、进步而奋斗。通过祝寿,中共极大地密切了与国内政治民主进步力量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使之与自己并肩作战,共同投身于民族解放大业中。
三、倡导文明贺寿,强化平等交往的规范功能
民俗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上升为成为群体标准模式,约束社会成员行为方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2]28。民俗中蕴含的各种规范是社会个体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在人们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潜意识,具有较为强大的威慑力量,制约着个体行为,对于规范人们行为、组织社会成员、维持社会秩序,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一般而言,民俗的规范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正相行为的倡导和对负相行为的规制。
(一)抵触庸俗风气,倡导文明、简朴贺寿
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祝寿是联络个人情感、密切私人关系的重要契机。在日常的民间祝寿中,往往存在庸俗不堪的比阔攀比,海喝山吃的奢侈浪费,人事之间的馈赠请托、拉关系走后门、拉帮结派,人际关系中的阿谀奉承、攀龙附凤、曲意逢迎等现象。更甚者借祝寿贺寿之机变相行贿受贿、大肆敛财。至此,祝寿已经严重变味走样,原本的养老敬老、注重孝道优良传统被严重地庸俗化低俗化,失去其初始的教化功能。
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以简朴、祥和、文明为主旨,在承继中国传统喜庆礼节的同时更带来了清新文明的空气。以徐特立66岁寿辰为例,先由主持人评价寿者生平,然后由贺者献旗献花、致贺词,最后由寿者致答谢词结束[17]。延安祝寿活动多是以文祝贺,健康向上,突出亲情友情,厉行节约,简摈繁文缛节,跳出传统吃喝的旧窠臼,抛弃庸俗的显摆比阔,杜绝海喝山吃的奢侈浪费,杜绝门生故吏及亲朋好友的馈赠请托,寿者摆脱迎送招待宾客之累,贺者免去购置寿礼的花费,不失为文雅之举。不仅如此,还有效遏止阿谀奉承、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的庸俗风气,防止借机敛财,有利于倡导和形成文明节俭新风尚,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功效。民间传统贺寿文化也因此得以规范,举办简朴、祥和、文明的贺寿活动在根据地蔚然成风。
(二)祝寿不论身份,彰显新型的人际关系
祝寿是对祝寿对象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确认和彰显。祝寿活动与祝寿对象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职权职务密切关联。祝寿活动举办的规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受贺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于普通者而言,祝寿往往是在家族范围,举办祝寿是为表达希望祝寿对象健康长寿、家族兴旺发达的美好祝福。只有在社会上拥有庞大和雄厚社会资源的人,在其祝寿这一特定人生礼仪活动中才会高朋满座、宾客如云,从而彰显祝寿对象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由此可见,就贺寿者与受贺者之间关系而言,以少尊老,以下贺上,以卑敬贵者居多,平行乃至逆向者较少,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贺寿者与受贺者在人际关系上的非对称。
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以民主平等友爱为目标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纠正传统民间寿庆中人际关系上的非对称现象,并逐渐成为普遍社会现象。从寿庆的举办方来讲,既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有祝寿对象所在机关(机构)。从祝寿对象来讲,成为祝寿对象的标准,是统一的、平等的,即为革命和人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祝寿对象之间,有的仅仅是年纪上的自然生理差别,而没有身份等级的区别,没有权力官职的不同。1944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举办的集体祝寿里,受贺者既包括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包括劳动英雄,还有普通的伙夫、马夫。对此,《解放日报》还于18日头版予以报道,而新闻结尾按照年龄(而非职务地位)大小顺序刊登受贺者名单及具体年龄[18],更是进一步彰显延安时期祝寿的标准。延安时期还出现党的领导者为普通群众祝寿的活动。林伯渠和谢觉哉亲自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为老炊事员举行的祝寿活动,受贺者则在主席位上入座[19]41。作为普通革命者,能和党的领导者一起成为祝寿对象,这已经明确向社会昭示,在边区的新社会里,无论职务高低,不管权力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而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格尊严没有尊卑之别,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团结友爱和谐的关系,理应相互尊重,相互关怀,互相帮助,一律平等,亲如手足。也就是说,延安时期中共的祝寿活动就是要在边区社会中建立一种民主平等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而祝寿本身也就是对这种新型人际关系的确认、体现和强化,从而改写传统民间寿庆中人际关系上的非对称现象,强化了人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理念。
四、活跃乡村文化,弥补物质匮乏的调剂功能
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可以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得到调剂[2]30-31。延安时期,根据地人民面临自然环境和敌对势力带来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战斗和生活,在严酷现实中生存与斗争。面对这种艰苦环境,心理慰藉和精神鼓舞所起到的调适有时比物质条件上的满足还要显著。延安时期,祝寿活动中的欢乐喜庆气氛和受人敬重的社会影响带来文化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丰满,极大地缓解了单调的乡村生活的乏味,消解了物质匮乏带来的苦涩。延安成为世人心目中激情澎湃、活力四射的精神圣地,祝寿这一民族活动的有效参与为之提供了积极的文化助益。
(一)欢乐喜庆的文体活动活跃乡村文化
农民群体文化水平比较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整年累月终日都在为生计而奔波。生产生活周而复始,单调繁忙劳累而乏味。单调乏味成为乡村生活的基调。延安时期,祝寿活动中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带来的欢乐喜庆气氛,有力地活跃了乡村文化生活。
延安时期,祝寿活动中,欢乐喜庆的氛围荡漾在民众中,乡村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朱德54岁寿辰当晚,八路军总部举行军民联欢文艺晚会,八路军总司令部的“火星剧团”、晋冀豫区党委的“太行山剧团”、一二九师的“先锋剧团”、三八六旅的“野火剧团”、前方鲁迅艺术学校的“鲁艺文工团”、太行三分区的“前哨剧团”和武乡的“光明剧团”、“盲人曲艺宣传队”、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怒吼剧社”等,都进行了节目表演。晚会结束后,还举行浩浩荡荡的灯火游行。朱德60岁寿辰,成为延安全体军民的节日,大街小巷插满红旗,社会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枣园举行盛大跳舞晚会,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举办秧歌晚会。寿辰当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大礼堂设立寿堂,商会暨各界市民则在民间吹鼓手欢奏声中前去祝寿,道路为之拥塞;寿堂前边保剧社演出秧歌[20]。晚上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演出评剧《捉放曹》《定军山》,并同时在舞厅举行盛大舞会。
在为中共领导人与普通百姓共同举办的集体祝寿中,亦是热闹非凡。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为杨家岭56位50岁以上的同志举办集体祝寿大会,会场四壁悬挂着中央负责同志、各部委、中央管理局赠送的寿灯、寿幛、寿联、寿诗、寿词,台上正中高悬着“万寿无疆”四个大字,主席台上点着两只大红寿烛。驻地附近老百姓组织民乐队,敲锣打鼓,伴送老同志入席。晚上民众剧团演出秦腔助兴并举行“盛大舞会”[19]190。
普通贺寿对象的祝寿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延安保育院,寿庆现场布置得花团锦簇,周围四壁挂满贺词,寿翁胸带红花,大家共同举杯为寿翁庆贺。延安中央医院为傅连障庆祝50岁寿辰之时,医院工作人员齐集会场祝寿,以互相拉唱的形式为傅连障献礼[21]196。
一场场祝寿活动中都充满欢笑、掌声、鲜花和歌舞,空气中则到处蔓延和洋溢着欢乐喜庆祥和的味道。祝寿活动中,剧团演出,歌唱跳舞,灯火游行,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单调的乡村生活被涂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人们在寿庆中尽情释放感情,昔日单调的乡村生活带来的沉闷、枯燥和烦恼随着寿庆的欢快一扫而空,民众心理得到调适,以愉悦欢快、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待生活和工作。
(二)崇尚劳者为尊,给民众以精神慰藉
延安时期,学习劳模、尊重劳模,成为中共领导的新型政权的新的社会风尚。为劳动者祝寿,是对延安时期中共倡导学习劳模、尊重劳模这一号召的扩大与补充,与后者一起构成尊重劳动、展示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重要载体。1945年元宵节毛泽东亲自为寿星祝酒并赠送日常生活用品作为礼物[22]。中共最高领导人为从未办过寿辰的普通农民举办寿辰,彰显和弘扬人民政权劳动光荣、尊重劳动的新价值理念。诚如当时林伯渠在为老炊事员祝寿之时所言:“不论职位高低,都没有贵贱之分,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做出重要贡献,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19]42对于成为受贺者的普通劳动者而言,老而为寿,寿而为尊,皆因劳动。受贺者劳而为尊,赢得受人敬重的社会地位,这使得社会民众在精神和心理上得到慰藉和安抚,幸福感和自豪感大大增强。社会地位的提升、精神生活的充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物质匮乏带来的苦涩,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民众战胜困难的勇气,增强了对革命事业和工作生活的信心。
总之,延安时期,中共以祝寿这一民俗活动为载体,通过举办大量的祝寿活动,充分发挥其教化、维系、规范、调节等社会功能,从而为改造社会习俗、建立社会新风尚、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向前发展提供积极的文化助益。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共不再举办祝寿活动,祝寿回归为正常的社会民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