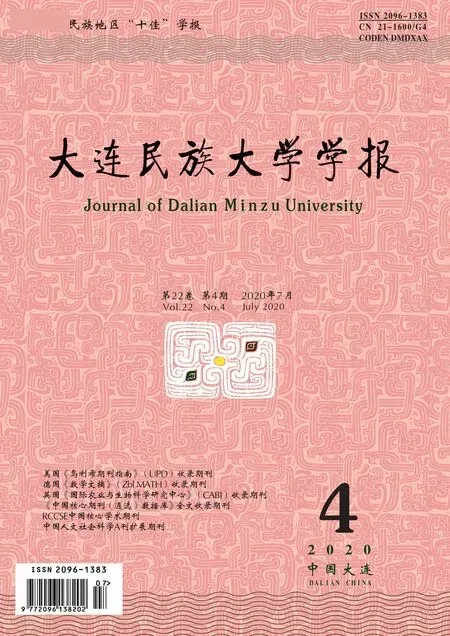解放区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以《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为中心
2020-12-04乔世华
乔世华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1949年4月24日,党中央决定把《解放日报》的报名交给上海,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上海《解放日报》于1949年5月28日创刊,现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1937年12月11日创刊(初为《抗敌报》,1940年11月7日改名),直到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改出《人民日报》(华北版)为止。《解放日报》“副刊”、《晋察冀日报》的“晋察冀艺术”专版会不定期刊登儿童文学的评介研究文章,通常都是选择在每年“四四”儿童节这样具有明显标志意义的时间节点前后发表。这些文章可谓应时之作,虽够不上洋洋大观,讨论问题并不深入也不够专业,但其中的总结和认识反映着当时解放区文艺家和理论家们对儿童文艺创作的理论思考,一些真知灼见值得重视。
一、关注儿童文艺创作
“没有受过教育的儿童,将是新社会的破坏者。”[1]当年解放区的有识之士从苏联儿童影片中获得了这个启发,解放区的领导人和文化教育工作者们对儿童教育以及儿童文艺的关注和重视是持之以恒的。当1938年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创办的解放区第一份儿童报纸《边区儿童》在延安创刊时,毛泽东就亲笔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42年《解放日报》的儿童节纪念专号上,毛泽东更有号召:“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所以,仅从儿童文艺的发展情形来看,虽然解放区条件艰苦、印刷出版有一定困难,但各类面向儿童开展的文艺活动仍然持续不断,儿童报刊方面先后有《边区儿童》《新少年》《少年之友》《西北儿童》《华北少年与儿童》《儿童生活》《儿童画报》等,还有由十几岁少年儿童编辑的文艺板报“少年高尔基”以及解放区开展的一些儿童演剧、绘画等活动,在丰富解放区儿童视听生活、教育儿童成长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区的文艺家们和理论工作者对此间儿童文学创作现象和活动往往及时予以总结和评介。
孙犁《儿童文艺的创作》肯定了解放区儿童文学已取得的成就,认为承继了叶圣陶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而且有所扩展:“边区的文艺工作是突击过来的。对于《稻草人》的道路,不只有充分追踪的勇气,而且有十足‘蜕变’和超越的可能,如边区的孩子普遍地参加了艺术活动(演剧跳舞),诗、歌谣的创作,如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少年高尔基’,对童话,儿童歌剧的注意等等。”同时也不回避当时中国儿童文学写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通病,比如有的作品并不真正懂得儿童而进行想当然的书写:“过去有许多运用上说句‘小了一个便’或是吸一下鼻涕便算是童话的特征的作品。其实儿童并不是老小一个什么什么或是老吸鼻涕的”,“其实儿童小便和吸鼻涕的遍数不见的比大人多到那里去”。在孙犁看来,一些童话作家之所以一写到孩子就把这些“厌作”[2]放到了第一位去,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儿童生活、儿童心理和童话特征。
邵子南《“少年高尔基”们》介绍了西战团儿童演剧队中出版文艺壁报“少年高尔基”的小鬼们的诗歌和散文写作,他们在十三到十六岁之间,其中两个是女性:“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并不是很高的,却能很好地感受诗。他们听着诗人的故事,学习着希腊古诗,学习彼得斐,休士,学习艾青……在这样的学习中,慢慢接近诗的本质,而发现他们自己创作里的毛病。他们从诗的本质上学习着诗”,“在创作上,他们有着一种新鲜的表现力,如前面曾引过的诗句,快活的勇敢气息,自由的格调。他们写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看见过的,有很大的关系的事物”,至于他们刚刚开始的散文尝试之作“有着故事的发展,有着人物的描写,文章长约两三千字”[3]。
夏石《略谈儿童戏剧》倡议晋察冀边区“有必要而且可能广泛地热烈地开展一个儿童戏剧运动”,他意识到现实中存在着一些制约儿童戏剧开展的因素,如“编制儿童剧团的困难”,创作者们对儿童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儿童趣味和儿童心理等有待克服[4]。
长怡《〈小故事集〉读后感》对文协主编、文救出版的《小故事集》进行评论,认为这本书中的十二篇故事“用这样锋利的精悍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这样丰富的、生动的战斗内容,这的确是我们边区文艺工作者极需要继续努力的一条道路”,还分别对其中几篇故事具体分析:《死也不向敌人屈服的》和《不投降的小姑娘》“突出的、有力的、描画出不屈的民族战士的雄姿”,“其他如《三个疯子的故事》、《孩子和大炮》等篇,也充分的做到:用朴素的简洁的言语,直爽的把边区人民对敌的仇恨和抗战胜利的信心明白的描画出来。这些风格是值得发扬的”。同时也不隐讳作品存在的一些缺点,如有的故事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一只羊和一挺机关枪》“故事本身写得欠完整”,《女人的头发》“损害”了主人公秀英“勇敢与冒险的气氛”,有的作品用词不妥当,“有些故事中的句子还嫌冗长”[5]等。
除了文学写作,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们也关注文艺演出,比如吴洛《孩子们的秧歌——抗小秧歌活动的一点经验》对抗属子弟学校组织的秧歌队在春节期间的演出进行介绍和评价。作者认识到像《夫妻识字》等一类秧歌戏于孩子们演出是很不适合的,而孩子们的秧歌剧兼有体育课、社会常识课和国语课等多种课业形式,对孩子们的健康和智慧发育、对孩子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丰富和语汇的充实以及思想情感的表达都有益。在肯定了儿童秧歌剧这一新的文艺形式的同时,文章期待儿童秧歌剧能续写新篇:“与过去旧的《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小小画家》等的儿童歌剧是完全不同的,新的儿童秧歌剧,是和社会相结合的建设新中国的新的儿童歌剧,这点是值得我们今后多注意的,我们应该多多的留意儿童们生活,收集他们的材料和他们自己的语汇,去创作更多的新儿童歌剧及儿童们的舞蹈。”[6]
二、重视发挥文学教育功能
解放区的文艺家们普遍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功用,把儿童文学视作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时事教育等的有效用的工具。
孙犁在《儿童文艺的创作》中认为:“孩子的一代,已经是参与了的战斗的一员。迫切的是需要政治的战斗的科学的教育。在今天用艺术来帮助儿童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感觉,达到更深刻更清楚,更敏快的习惯,使他们的知识扩张,使他们紧紧的接近到集团,和别人在一起获得进步,加速成长。这是民主的生活和战斗的前线。”因此,儿童读物写作被“当作边区儿童保育工作的一部分”[2]。夏石《略谈儿童戏剧》中开宗明义地提到儿童戏剧所具有的教育功效:“戏剧具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儿童戏剧对于儿童,它的作用更大,不仅因其通过舞台演出对人物形象的感应,而使他们由人,事,物,一切宇宙万象的无知得到一定的启发,由判别,认识的幼稚而获得一定的对真伪,善恶,美丑的判别力,和正确的观点;而且在其直接参加戏剧演出的实际工作中,更能逐渐的养成集团的组织的精神,和获得身心上康健优良的效果,因为戏剧是一种集团地创造的艺术,演员与健康的体格,优美的丰度又是不可分离的。”[4]罗东《四四感想》认为“艺术对孩子的教养也是大的,孩子们从艺术里可以陶冶出新的性情,革命的坚韧的敏锐的意志和高扬的天才”[7]。吴洛《孩子们的秧歌——抗小秧歌活动的一点经验》看到了儿童秧歌剧所发挥的教育效能:“孩子们的秧歌,不但在群众中得到它应有的收获,同时也教育了孩子们自己,这种教育不是书本上的死板的符号与概念,相反的,它是最实际的社会教育,正因为这样,它使孩子们的求知欲与兴趣提高,而孩子们的秧歌活动,便不仅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且是孩子们在上着自己的秧歌课。”[6]萧三主张提供给儿童“好的、精神的粮食”,应该被纳入到书写的内容是“八路军的小鬼在前方和后方作过、作着不少英勇的动人的抗战建国的事业”[8]。
可能正是因为看到当时解放区儿童教育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所进行的儿童教育却是畸形的,许多地区是以干部教育的一套内容与方式原封不动地灌输给天真纯洁的小脑子里。而制造了一批满口政治名词的‘小老头’”[1],基于“小小的娃娃,居然也能像大人一样,大谈其政治。这在我们那些比较好的小学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种情状,解放区的文化人士主张儿童本位的教育、书写和表达:“儿童教育必须要以儿童生活为中心。我们必须把儿童教育和儿童生活结合起来”,“希望优秀的群众工作者,文化人,教育家能拿出一部份时间来为儿童而工作,即使是只医治一两个小孩,只写作一两本儿童读物,只创办一所好的学校,对儿童,也就是对革命,那是贡献了应尽的力量。”[9]因此在对儿童文学更艺术、巧妙而贴心地发挥教育儿童功能方面有相应要求,如孙犁就设计过具体的建设路径,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在形式上应该“短小,浅白有韵,行动多于对白,民间形式,奔向民族形式”,在内容方面则要因应解放区的现实生活:“我们边区处在紧张的战斗,因此对于神话和幻想在儿童文艺中的运用,在分量上就不能像苏联在和平建设运动中的那样多。而内容和范围也应切合边区现实的要求。”[2]萧三则对儿童文学发展提出了两个希望:一是搜集整理民间百姓为儿童所讲述的故事;二是深入到儿童的现实生活中去:“活泼、天真、聪明、能干、耐苦、懂事如成年人”的小鬼们“直接在军队里、火线上,在敌后甚至在敌占区工作的”“在无数的剧团里演戏、唱歌、跳舞作宣传鼓动工作的,和工农兵大众真的打成一片”[8],采写解放区所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也就是说,时代赋予了解放区儿童以崭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家有责任为这个时代的儿童生活和精神世界立此存照。
三、呼吁新型儿童文学创作
因为意识到解放区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基于解放区儿童文学创作和发展中的薄弱情形,解放区文艺家们普遍发出倡导,呼吁文艺家同仁有更多更专业的儿童文学创作。
田间以他一向的诗意语言表达了为儿童创作的意愿,号召文艺家们“为新的一代而歌”:“我们要用勇敢的旋律、自由的旋律、新的旋律组织成新的一代底战歌,和生活歌;我们要用为花朵、为未来的手挖掘一条路使新的一代握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子成长起来”,“要把艺术的血液展开到孩子们底血液里去。”[10]孙犁提到“边区的儿童从六岁到十四岁的,以其全新的组织生活和战斗热力,要求着读物。无论是看的听的和唱的”,内中已经潜隐着对各个年龄段儿童多种多样的阅读需求加以重视的朦胧意识,他倡议“儿童文艺的作者,应该除去深入现实生活以外,更深入儿童的生活,研究其生活,心理,进步过程,不同的状态等等”[2]。在罗东看来,“孩子们富于幻想,没有成见,是真理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孩子的这种气质,是艺术的气质,孩子和艺术是有缘分的,他们接近艺术,爱艺术,是艺术的年轻底卫士”,所以文艺家们要给孩子“丰富的文化艺术生活”[7]。何其芳感慨成人对儿童生活和心理的隔膜,“我们恐怕并不大常常想着孩子们的事情”[11],因此期待同行们能切实为儿童做一些实际的文化工作。
萧三之写作《略谈儿童文学》,是有感于解放区所办的《街头小说》《给孩子们》专号的“内容、质量各方面都差一些”,也是为了赞助《西北儿童》这个唯一的边区儿童刊物的稿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实在太贫乏了,太不被重视了!中国千百万可爱的儿童就在这方面,也太可怜了!他们简直没有几本课外的读物可读”,而“他们非常需要营养”。还特别探讨儿童文学不发达的两个原因,汉字繁难和作家不重视:“首先当然要归罪于方块汉字之太艰深,使得十来岁的孩子无法认识许多字、无法读得懂一些仅有的读物。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诗人、作家实在也太少注意到这一个广大的年轻的读者层了。如不相信,请问每个作家、诗人:你一生为儿童写过多少作品?有没有写过关于儿童的许多诗、歌、小说、剧本?在中国全国,在大后方,在我们边区、延安,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数得出来几个儿童文学作家!?是不是中国不能产生儿童文学呢?还是我们的作家不屑于创作儿童文学呢?”遂一再吁求作家“写他们,为他们写吧!希望我们的作家、诗人们在下决心面向工农兵大众的时候,不忘掉这一年少的读者层。希望中国也有许多真正的儿童文学专家!”[8]
解放区的现实土壤已经决定了本来就具有浓厚现实关怀精神和强烈现实表达吁求的创作者们必然选取现实主义道路前行,就像孙犁、萧三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解放区儿童文学“对于神话和幻想在儿童文艺中的运用,在分量上就不能像苏联在和平建设运动中的那样多”,“内容和范围也应切合边区现实的要求”[2],作家要尽可能表现解放区儿童“英勇的动人的抗战建国的事业”[8]。解放区的接受环境以及文学受众的审美意愿也同样注定了此间乃至之后儿童文学的这一现实宿命。当时解放区“一百万以上的儿童和少年,能够在战争进度紧张的环境中”享受着小学教育,但实际效果并不容乐观[12],“一般社会人士或教育人士或中学毕业生,都认为现在的中学生程度太低,尤其是国文程度太低,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他们对国文的第一个要求,大部分是要求短小精干、生动具体、带故事性、对工作、思想、写作都有帮助,有实际教育意义的文章,其次是喜欢诗歌和浅近的文言文”[3]。如此接受情形当然就注定了解放区儿童文学创作的贫弱与粗粝形态,决定了解放区儿童文艺必然要走普及之路。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当时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走向。
四、介绍苏联儿童文学经验
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接近以及苏联儿童文学本身具有的强大势能,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们普遍重视同期苏联儿童文学创作经验,热衷于介绍和推广苏联儿童文学创作成就和理论建设,将之视为解放区儿童文学发展的标杆或圭臬。
这一方面反映在对苏联儿童文学发展情形的直接翻译介绍上,譬如葛一虹早先著有《苏联儿童戏剧》一书,解放区剧协1941年“四四”儿童节前夕曾有翻印此书的打算,不过因印刷困难而不得不延期,夏石《略谈儿童戏剧》中特意摘引了该书有关苏联儿童戏剧演剧情形的大量内容。《伊加尔卡的孩子们——苏联儿童集体创作》是苏联伊加尔卡这个新兴港口城市里一百多个十几岁孩子写作的诗歌、日记、短文所编辑成的书,该书部分内容为戈宝权节译在《晋察冀日报》上刊出,编者为此还加上按语表达对解放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艺作品的期待:“我们节登了几个断片,但从此我们也可看出来,儿童创作的新作风来,写到这里,要问一问晋察冀的孩子们,我们的《晋察冀的孩子们》呢?”[4]显见,苏联儿童文艺成为解放区儿童文学创作取镜的学习样板。再如庄路译自1943年12月《国际文学》英文版的一篇文章把战时苏联儿童文学出版局克服重重困难而在过去两年半中出版了三百部以上作家作品(每部印二万五千份到十万份)的情形进行了概括介绍,文章注意到苏联儿童读物的丰富和细致——从幼童、学童到少年都有适合其年龄特征的相对应的读物[5]。
另一方面,一些文章习惯于通过引用介绍苏联儿童文学成功发展经验或权威声音以壮大自身的理论探讨声威,如孙犁《儿童文艺的创作》就大篇幅介绍了苏联新儿童文艺创作因为借鉴神话、幻想和紧贴现实生活而繁荣发展的情形,还在文中引用了苏联儿童戏剧工作者奥林森“儿童是一种单独的实体,并不是一个成人的一种缩影”的言论以说明“儿童文艺创作之困难”,进而主张汲取国外尤其是苏联儿童文学的先进创作经验:“一切基础的切实的科学知识,应广泛的容纳到儿童读物里去。大家除去注意民间的童话,歌谣,儿童的绘画,木偶戏,儿童玩物等东西以外,要研究国外从伊索寓言到欧美特别是苏联的儿童读物的收获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形成边区特色的“新童话”:“在新童话里写入战斗,民主和科学。在表现上趋向儿童的喜好,太阳不妨可以弹琴,月亮可以表演,玉蜀黍可以成为炮弹,小花狗,空中飞的鹰,河水里的鱼,都可以开会,运输公粮,捉汉奸,打敌人了。”[2]萧三《略谈儿童文学》是从晒生活在苏联的一个孩童阿郎从七岁到十一岁之间的读书书单开始,详尽介绍了苏联儿童文学出版业态和丰富的儿童读物,借此来说明苏联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成就,同时还把自己书架上一本1940年的苏联儿童文学书的目录介绍给了解放区读者,该目录显示出苏联儿童文学书对学龄前儿童、年小儿童、中年儿童、大年儿童及少年等各年龄段儿童均区别对待。正是有了这种参照,他意识到“中国的儿童文学实在太贫乏了,太不被重视了”,“简直没有几本课外的读物可读”。该文章还引用了苏联《文学报》上的文章内容用以证明苏联儿童文学艺术成就的获得与苏联众多作家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关系密切[8]。解放区对苏联儿童文学及相关经验的重视,当然是因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但也的确与苏联儿童文学自身成就引人注目大有关系。所以,当1949年之后,这种偏重于从苏联儿童文学获取经验和理论资源的倾向自然随着解放区域的扩大而在更广大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决策和创作取镜的重要参照。
解放区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固然有些贫弱,但也留下了诸如孙犁《儿童文艺的创作》、萧三《略谈儿童文学》等值得后人珍视的理论文章,为诸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版)、《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希望出版社2015年版)和《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等专业研究书籍所收录或评骘;顺带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孙犁对《儿童文艺的创作》做过大幅度删改,这也意味着其在儿童文学基本问题认识上发生的变化[16]。总之,解放区的生活现实和儿童文学创作现实难说丰富,与创作相辅相成互为促动的理论也不可能凌虚蹈空地有更高远深入的发展,但上述理论文章有助于认识20世纪40年代以降解放区儿童文艺创作和相关理论研究的真实情形,也一定程度呈现了这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演进道路,解释了浪漫的、幻想的儿童文学写作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