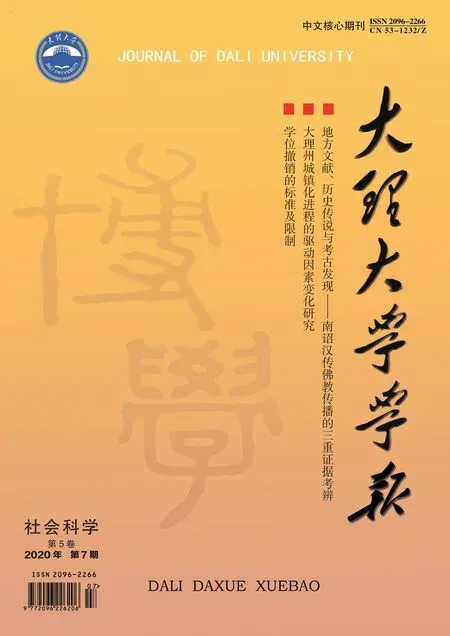地方文献、历史传说与考古发现
——南诏汉传佛教传播的三重证据考辨
2020-12-04孙浩然
孙浩然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昆明 650500)
一、问题的提出:南诏汉传佛教史的第三种类型史料
初唐诸帝经略云南,复置或新设南宁州、郎州、姚州诸都督府及众多羁縻州县,但各部落彼此不相统属,叛服无常。《资治通鉴》记载:“洱海河蛮以李、董等为名家大姓;勃弄之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相接,人众殷富,多于蜀川,无大酋长,好结仇怨。”〔1〕608至盛唐玄宗朝,僻居巍山一隅的蒙舍诏(南诏)在唐朝支持下统一洱海,随后并吞两爨,抗衡唐庭,统一云南,成为雄长东南亚的地方民族政权。此前,汉文典籍基本上没有关于南诏的记载,南诏其兴也勃焉,“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2〕471,一下子跳到历史舞台之上。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原本作为哀牢夷众多部落中一个的南诏王室,逐渐修改“九隆神话”。梵僧观音或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的故事,或许不是后世佛教徒、道教徒编造,而是南诏统治者论证合法性的一种策略。南诏统治者放弃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选择佛教、道教乃至儒教,既是一种信仰转变,也是一种政治策略。
《新唐书》说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3〕6267。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站在中央王朝立场上说:“逆贼蒙佥和舍等,浮竹遗种,沉木余苗……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4〕886唐懿宗时西川节度使牛丛《报坦绰书》也说南诏“出于六诏之微,非是西夷之长”〔4〕3862。南诏蒙氏属乌蛮,为了笼络分布甚广、部众甚多的哀牢夷诸部落,“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5〕68。唐玄宗册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史籍对沙壶州语焉不详,其辖境内当有不少以九隆后裔自居的“哀牢、昆明”部落,即使一些部落在血缘上不是一个祖先,但在文化上、信仰上追溯同一祖先,共祭九隆,在长期交往通婚中仍能产生强大的认同凝聚力。
但是,南诏的近邻“西洱河蛮”“西爨白蛮”“松外蛮”等部落,或“自云其先本汉人”〔6〕218,或“自言本皆华人”〔1〕600,或自认为“庄蹻之裔”〔3〕6321,汉文化水平较高,就不能以九隆崇拜凝聚认同了。南诏的远邻“东爨乌蛮”信奉“鬼教”,也不认同九隆神话。史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3〕6315;“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5〕31。有时军政领袖也要兼任大鬼主或都大鬼主,如唐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提到的“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书末还问“卿及百姓并平安好”〔4〕1287。南诏境内不仅生活着今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先民,也生活着一部分汉族先民乃至东南亚民族的先民。南诏早期的迅速崛起固然可以诉诸武力,却不能长期纯粹依赖武力威服“管内酋渠”。随着疆域拓展,所属部落增多,南诏迫切寻找能够适应自身扩张的意识形态,以增强境内各族人民的凝聚力。于是,在唐朝、吐蕃及东南亚各国广泛传播的佛教成为南诏统治者的信仰选择之一。南诏的佛教信仰既从汉地、藏地传入,也从印度或东南亚输入,同时糅合境内民族本土宗教的因素,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形态——阿吒力教。《南诏德化碑》有“阐三教,宾四门”〔4〕4590;“先灵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4〕4589;“潜军袭造船之师,伏尸遍毗舍之野”〔4〕4590等语。学者对此数句的解读莫衷一是,或言三教中有佛教,甚或说神炬、毗舍与婆罗门教有关。实际上,唐朝时“三教”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指儒释道三教,只是三教的排序时有不同而已。若换一个角度分析,上述不同阐释恰恰说明了南诏佛教信仰的多元性、融合性。
治宗教史者,经常面临史料甄别问题。宗教历史往往与神话传说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南诏佛教史尤其如此,且又苦于正史资料之不足。向达先生认为:“研究南诏的历史,显然有来源不同的两种史料。第一种是汉文史料,现存者有樊绰《蛮书》《新唐书·南蛮传》。第二种是从当地人民,特别是所谓白文,翻译出来的史料……可以杨慎《滇记》为代表……《滇记》乃是杨慎根据僰文《白古通》《元峰年运志》为之转写而成的。”〔7〕206向达特别强调“第二种类型的史料,大多根据云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传说,加以翻译和改编而成”〔7〕208,并将《南诏图传》也归入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中,认为《南诏图传》“上面有许多说明,可以作为南诏史史料看待”〔7〕208。《南诏图传》又题《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南诏末代王舜化贞中兴二年即公元899年,当唐昭宗光化二年。向达考证《南诏图传》“最多只能是大理时代的画,不能看得太早”,同时认为“从《南诏图传》起以至于《南诏野史》《白国因由》,一脉相传,井然不紊”〔7〕208。还指出“清康熙时的《白国因由》,亦出于《白古通》一类的书,其中充满了佛教传说和神话”〔7〕207,并力辩张氏白子国(又作白氏国、白国)乃属虚构。向达认为:“南诏同佛教的关系,并不如第二种史料所说之甚……南诏后来之信佛教,乃是事实。但在初期恐不如此。”〔7〕211研究南诏历史,必须考辨两种类型的史料,具体到南诏佛教史,尤其是汉传佛教史,第一种史料不过只言片语,第二种史料更需要审慎对待。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据第三种类型史料,即南诏历史遗迹的考古发现以及有关历史地名、人名、族名乃至官名封号等,与前两种史料互证,置于南诏与唐朝政治关系演变的政治史、社会史理论框架下展开分析,庶几可以勾勒南诏时期汉传佛教的历史概貌,加深我们对南诏佛教史乃至整个南诏史的认识。
二、历史传说的文本化及其辨析
一些明清时期的云南地方文献说佛教在汉代传入大理,可视作南诏以降佛教历史传说文本化的结果。明洪武年间主政云南的张紞所作《荡山寺记》引述地方传闻,说感通寺由唐南诏僧李成眉首建①参见〔明〕张紞《荡山寺记》。。然而明万历年间宦游云南的诸葛元声在《滇史》中则确定说:“大理感通寺,汉时摩腾、竺法兰由西天竺入中国时所建也。”〔8〕191至清康熙年间黄元治编纂《荡山志略》折中说:“感通寺,荡山主寺。世传汉时摩腾、竺法兰由西天竺入中国时建,唐李成眉重建。”②参见〔清〕黄元治《荡山志略·山水》。可见,南诏佛教历史传说不断以“或谓”“世传”的方式文本化,甚至言之凿凿地载入地方文献。李成眉贤者其人其事,成为解读南诏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传播情况的重要线索。
(一)李贤者传说事迹考辨
《南诏图传》所附文字卷说:“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9〕2399南诏在唐朝支持下统一洱海区域,自言“本唐风化”,尤其是异牟寻之前的南诏诸王推崇儒学,也受到唐朝道教、佛教的影响。权德舆《送袁中丞持节册回鹘序》说:“滇池昆明为西南雄部,尝乐声教。”〔4〕2220陈垣先生认为云南佛教最开始直接从印度经缅甸传来,然后从中原经四川传入,最后兼具显密诸宗:“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10〕4方国瑜先生认为:“中土、印度两路并存传播佛法于云南之说,似并可信,然主流则自中土来。”〔11〕218
大理国段智兴盛德五年(公元1180年)绘制的《张胜温画卷》有印度、中土及云南禅宗人物图像,神会和尚之后的“和尚张惟忠——贤者买顺嵯——纯陀大师——法光和尚”等人,可视为云南禅宗诸祖。明朝万历年间大理白族名宦李元阳修纂《云南通志》说:“张惟中,得达麽西来之旨,承菏泽之派,为云南五祖之宗。”〔12〕503清康熙年间僧人圆鼎所作《滇释记》说:“荆州惟忠禅师,大理张氏子,乃传六祖下荷泽之派,建法滇中,余行无考。”〔13〕10365又说:“买顺禅师,叶榆人也,从李成眉贤者薙染,屡有省发。贤者语师曰:‘佛法心宗传震旦数世矣,汝可往秉承。’于是走大方,见天皇悟和尚。”〔13〕10364-10365买顺得法后还参谒百丈、南泉等中原禅宗大德,“六祖之道传云南,自师为始”〔13〕10365。依据此说,买顺禅师与张惟忠没有师承关系,却曾师事李成眉。《滇释记》说:“圣师李成眉贤者中天竺人也,受般若多罗之后,长庆间游化至大理,大弘祖道。时南诏昭成王礼为师,乃建崇圣寺。”〔13〕10364强调李成眉嗣法中印度禅宗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法脉,乃是禅宗人物。但《滇释记》又说:“禅陀子,西域人也,天宝间随李贤者游化至大理。贤者建崇圣寺,命师诣西天画祇园精舍图,师朝去暮回……寺成,欲造大士像未就。师于城野遍募铜斤,随获随见沟井便投其中。后忽夜骤雨,旦起视之,遍寺皆流铜屑,遂用鼓铸立像高二十四尺……失传雨铜观音也。”〔13〕10364所记之事颇具密宗色彩,且唐玄宗天宝(公元742—756年)与唐穆宗长庆(公元821—824年)至少相距65年,其叙事依据不是史实而是传说。
一些地方文献将买顺与李贤者混为一人,进而又与李成眉混为一人,其身份也从禅宗和尚转为密宗和尚。万历《云南通志》说:“李贤者,姓李名买顺,道高德重,人呼李贤者。”〔12〕503《南诏野史淡生堂传钞本》说:“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砌人恭韬徽徐正。”〔13〕210《僰古通纪浅述》则说:“开元元年唐大匠恭韬徽义造三塔”〔13〕65,并在夹注中说恭韬徽义“即张鲁二班”。云南白族民间传说张班曾向鲁班学艺,也寓意在佛塔建造上,南诏获得唐朝帮助。从崇圣寺三塔的形制、建筑技术等分析,唐朝工匠参与崇圣寺及三塔的建筑并非妄言,也说明南诏佛教一度受到汉地佛教较大影响。
南诏早期从洱海地区到四川成都乃至中原参禅者不乏其人,法脉源流基本清晰,但中原禅宗在南诏传播可能五世而斩。相传唐元和八年、南诏劝龙盛龙兴四年(公元813年),云南禅宗九祖普济庆光禅师肇建水目山禅寺。云南地方文献因循转钞,将唐顺宗时亦即南诏王异牟寻当政晚期,作为南诏佛教传播的一个高峰,南诏王室开始推崇以密术相标榜的梵僧,注重讲经说法的汉传佛教逐渐式微。劝龙盛被权臣嵯巅所杀,其弟劝丰佑继位,以赞陀崛多为代表的梵僧迅速扩展势力,其后唐诏失和,梵僧在南诏朝野的影响很快超过禅师,以至南诏后期汉传佛教的传承沉寂无闻。恰恰说明密教晚于汉传佛教传入云南,其广为接受同样也经过一段曲折历史。
原本是禅宗传人的南诏僧人李贤者没有被民间遗忘,反而被不断神化并重新涂抹了密宗或阿吒力教色彩,言之凿凿载入地方文献。明万历《云南通志》说:“唐南诏重建崇圣寺之初,李贤者为寺厨侍者,一日殿成,诏讯于众曰:殿中三像以何为中尊?众未及时,贤者成声曰:中尊是我!诏怒其不逊,流之南甸,至彼坐化。”〔12〕503传说中的李贤者以“扫地僧”面目示人,因言获罪,折射出南诏王室后期优待梵僧、胡僧而排斥汉传佛教的史实。李贤者身后封神,其禅宗和尚的本来身份反而被深深隐藏了。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李贤者以念珠救治难产妇女的传说:“李贤者寓周城,主人其家妇所(产)难,贤者摘念珠一枚使吞之,珠在儿手中擎出,弃珠之地丛生珠树。”〔12〕251大理民间关于李贤者的神话由来已久,传播广泛,明末浙江绍兴文人张岱专记异闻的《夜船航》也有收录。
掀开李贤者传说文本的神秘面纱,我们看到南诏中期禅宗受到阿吒力教影响冲击而出现传承危机,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一些本来参修禅宗的南诏僧人,最后也很有可能改换门庭,后世民间传说也因此将南诏禅宗僧人密宗化了。
(二)《白国因由》叙事中的观音老僧与《方广经》
《白国因由》渲染了观音点化细奴逻的故事情节。观音最先来到罗刹国希老张敬家,张敬协助观音收服罗刹,但观音却为远在巍山的细奴逻授记,封张敬为宾居大王〔14〕587。神话传说背后的事实可能是佛教最初在倾向汉文化的洱海地区河蛮大姓中传播,从巍山崛起的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为笼络名家大姓,从部落图腾崇拜转向佛教信仰。
佛教在南诏国统治的中心洱海区域盛行之后,影响广泛而深远。白族人民普遍认为,大理三月街与佛教传播有关。《白国因由》说:“观音令婆罗部十七人以白音口授之,不久皆熟。自是转相传授,上村下营,善男信女,朔望会集,于三月十五日在榆城西搭蓬礼拜方广经……后人于此交易,传为祭观音街,即今之三月街也。”〔14〕590《白国因由》不像《南诏图传》那样,强调观音变化为“梵僧”,只说变化为“老僧”。观音老僧离开大理时让人们礼拜《方广经》,且用白语白音讲经说法,契合白族人民的心理。巍山县城北古城村的蒙舍城遗址出土一个有字瓦断片,依稀可辨“方广佛”字样〔15〕64。南诏在蒙舍城活动的时间要早于太和城。《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汉传佛教华严宗的主要经典,说明南诏早期佛教主要从汉地传播而来。《南诏图传》绘制的所谓“梵僧”形象,从其容貌、形态、服饰看,似乎并没有多少印度特色,而是带有典型的大唐服饰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梵僧的发型、冠饰等又有道教人物特征。这些都可说明,佛教最初从中原传入南诏并取得较大影响,是南诏与唐朝政治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后期,南诏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密切,才有大批梵僧入境,南诏佛教的密宗色彩开始凸显,但汉传佛教并没有完全从南诏消失。
三、地方文献的传说化及其辨析
唐初,云南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个别部族首领信仰佛教,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部族则没有人信仰佛教,也可证明佛教传入洱海地区,最初与汉地有密切关系。南诏崛起,加速了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历程。南诏朝中大臣与王畿百姓多是白蛮,大理国以来云南地方文献所载世代信仰佛教的白子国张氏让位于蒙氏细奴逻、南诏丞相张建成入唐朝觐并将佛教传入云南,应是白族先民历史传说文本化的结果。《南诏图传》所附文字卷说张建成是普苴诺苴大首领张宁健之子,又名化成,建构历史传说者将张建成当作张氏白子国的后裔。分析地方文献有关张建成的记载,可以找到汉传佛教在南诏早期传播的蛛丝马迹。种种迹象表明,在唐朝影响下南诏朝中部分汉文化水平较高的白蛮大臣率先信仰佛教,他们又推动南诏王室信仰佛教。白蛮中的河蛮、弄栋蛮、蜻蛉蛮极可能是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先民信仰佛教的主力军。
(一)张建成与南诏早期的汉传佛教
《僰古通纪浅述》说:“开元二十八年,遣张俭成赍白金百两、当归药材入贡”〔13〕59,又说:“天宝六年十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13〕61。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载:“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11〕120多种云南地方文献将张建成作为佛教自唐朝传入云南的第一人,惟其姓名、身份等信息众说纷纭,可证其本为历史传说。万历《云南通志》之《仙释·大理府》说喜州人张健成入唐朝觐在成都大慈寺撞钟求法〔12〕503-504,《仙释·蒙化府》又说:“张彦成蒙川人,南诏蒙晟罗遣彦成使于唐,礼待甚厚,赐以浮屠像而归,南中佛事自兹始”〔12〕503-504。无论张建成还是张健成、张俭成、张彦成,其人其事是解读南诏早期汉传佛教历史的又一关键线索。
大理喜州上洪坪村白族张氏奉张建成为始祖,张氏宗祠设在村南大慈寺,村中父老传说大慈寺是仿唐代成都大慈寺建造。景泰《云南图经志》也说张建成是大理喜州人,朝贡唐玄宗时路过成都大慈寺,恰逢寺内新钟铸就,老僧告诫说撞钟一声施舍黄金一两。张建成连连叩钟八十下,惊动寺内老僧。张建成以实相告,并施舍黄金八十两。老僧给张建成讲经说法,并改名化成,寓意南诏将接受佛法教化。《僰古通纪浅述》的记载大体相似,但情节略有不同,一是主角名为张俭成,二是入唐时间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三是扣钟地点在京城长安,四是扣钟二十八下,五是由玄宗赐名化成〔13〕59。
上述两个版本恰恰反映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两种路径。唐玄宗直接赐给佛书,代表国家立场,是上层路线;成都寺院老僧传授佛书,代表民间立场,是下层路线。两条路线在现实中各有可能,因此才有两个版本的历史传说。张建成撞钟明知故犯,说明佛教在云南民间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他想得到汉地佛教正传,因而不惜成本。《僰古通纪浅述》说唐朝不止一次赐给南诏佛经:“得唐宪宗六家经疏,国老杨白宽为僰人讲。又请张软义大师译经书于长寿寺。”〔13〕70康熙《蒙化府志》则说“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劝利晟请于唐,得六家经疏,命国老杨白宽为国人讲习”〔16〕39。这两则记载不仅失之简略,真伪亦需辨析,究竟是唐穆宗还是唐宪宗时期,六家经疏名目如何,注解何经,讲何内容,都不得而知。但从中至少可以索解两层含义:其一,佛教从汉地传入南诏后,白族先民是信仰主体,已经使用白语讲解佛经;其二,南诏时期可能已有白文,从唐朝传入的汉文佛经,还要专门翻译成白文,供知识分子阅读。白文最初或许因翻译佛经而创制,至少与翻译佛经有关。
张建成的历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南诏初期向唐朝学习佛教文化大体不差。《南诏野史》罗振常藏本说:“先是罗晟炎时,相国张建成欲于白崖建寺,卜之告吉。又云地下有三截观音,上截在西,中截在东,下截在东南。因盛炎旋卒,不果建。至是建寺,掘之果然。”〔17〕427《南诏野史》淡生堂钞本则说阁罗凤时“有张俭成算卜欲建寺白崖,卜告吉。又云地下有三截观音,上截在西,中截在东,下截在东南。掘之果然”〔13〕201。作为南诏王罗晟相国的张建成与作为阁罗凤时期卜师的张俭成,折射汉传佛教在南诏传播的上层路线与民间路线。南诏早期建寺供奉观音,还要打卦占卜,也说明佛教信仰中一定程度上交织着本土宗教的因素。地下掘出三截观音,若非事先有意为之,则说明南诏之前就有佛教流传云南,只是后来被废,所供观音像也遭到破坏。
(二)《宣师感通录》所说之多宝佛
唐代僧人道世所撰佛教类书《法苑珠林》卷十四收录《宣师感通录》,以佛教南山律宗开山祖师道宣与天人问答的形式,提到洱海地区佛教造像、建寺、造塔的情况。“昔迦叶佛时,有人于西耳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鹫山寺,有成都人往彼兴易,请像将还……其多宝佛旧在鹫头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河大阔,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经像尚存而无僧祝。经同此文,时闻钟声……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数极多。”〔18〕492-493
上述记载语近神话,但亦真亦幻,亦幻亦真,未必尽真,未必尽伪。道宣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卒于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主要活动于唐高祖、唐太宗、唐中宗时期。道世也是唐初高僧,《法苑珠林》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高宗时,已在洱海区域设置不少羁縻州县,东爨地区效忠唐庭,“西洱河天竺道”①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巂州都督刘伯英上疏:“松外诸蛮,率暂附亟叛,请击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语见《新唐书·南蛮传》。交通无阻,大唐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影响扩大,个别少数民族有进入云南贸易仕宦的机会极可能信仰佛教。《宣师感通录》提到当时四川成都与洱海地区的经贸往来、佛教文化交流非常密切,还详细说明从成都去洱海地区乃至天竺的道路旅途。“今向彼土,道由郎州,过大小不弄(勃弄)三千余里,方达西耳河……其地西北去巂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18〕492所说基本符合事实,并非完全杜撰。民国时期秦光玉编篡《续云南备征志》,从《太平广记》转述收录。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的提问:“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从地涌出?”〔18〕492所谓从地涌出,应是发掘出土古代多宝佛像。唐初云南有多宝佛造像,已经为历史实物所证明。唐武周时期所立的《王仁求碑》,在滇池之畔的安宁小石庄村葱蒙卧山,碑额所凿佛龛中雕有释迦牟尼佛、多宝佛说法像。可见,历史遗迹、考古发现亦能佐证历史传说与地方文献。
四、历史遗迹、考古发现与补充论证
有关南诏汉传佛教传播的历史传说不断文本化,同时文献资料也不断传说化,南诏汉传佛教的历史面貌究竟如何,还应借助第三种类型的史料,即历史遗迹、考古发现以及有关历史地名、人名、族名乃至官名、封号等辨别考证。第三种史料看似碎片化,但运用得当,与前两种资料互相印证,亦可收到以蠡测海、以管窥豹之功效。
(一)历史遗迹
《王仁求碑》由唐初著名文人四川成都闾丘均撰文,《全唐文》题为《唐朝故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上护军王府君碑铭并序》,清人王昶《金石萃编》题为《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碑文系其长子王善宝自书,从书法可见其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张柬之《请罢姚州屯戍表》称王善宝“蛮郎将”〔4〕886。正如很多白蛮大姓自言汉人之后,《王仁求碑》追溯其家族至太原,言其家族来到云南已历十余世。王仁求身在少数民族地区,但推崇中原文化,拥护唐王朝统治,在唐高宗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建议朝廷讨伐反叛的部落,并率部众征讨阳瓜州刺史蒙俭。王仁求之子王善宝袭父职,受到中央王朝信任。王善宝“宿卫京都”期间,有可能接触佛教文化,或者是一名佛教徒,才在其父墓碑上雕刻佛龛。佛龛内雕有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的释迦、多宝二尊佛像,是迄今发现云南年代最早的佛教石刻造像。释迦佛与多宝佛坐像并雕,流行于北朝汉地佛教造像中,其教理依据是《法华经·见宝塔品》。据此推断,王仁求乃至其父祖也有可能信仰佛教。唐初白蛮大姓家族中,也许不止一家信仰佛教。唐高祖时韦仁寿在西洱河设置八州十七县,部落子弟争相随韦仁寿入朝“贡方物”;武周长寿年间(公元692—694年)监察御史裴怀古对云南各部安抚有方,“姚巂蛮首相率诣阙”;云南一些部族首领子弟包括南诏王室子弟也曾“宿卫京师”,很可能因此接触并信仰佛教。
王仁求死于唐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年),至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正月十七日立碑,中间经过24年,推断很可能是举行特定佛教仪轨后重新立碑,也有可能重新安葬。《王仁求碑》载:“郁郁润泽,白虎之候可占;洪洪博平,雄龙之象终吉。故其土性淳质有如上代,安错仪轨弗践终经。”〔4〕1331王仁求死后时隔24年立碑或再葬,与《蛮书》所载白蛮、乌蛮速葬火葬风俗截然不同。后世云南密教火葬墓碑额造像多是尊胜佛母,《王仁求碑》碑额雕刻释迦佛与多宝佛,与初唐中原地区流行的碑额造像风格相似,其所信仰之佛教显然是汉传佛教。
南诏时期的历史古迹如崇圣寺三塔,其始建年代众说纷纭。胡蔚本《南诏野史》说大理崇圣寺三塔“塔顶旧有铁柱款识云:‘贞观六年尉迟敬德监造’”〔17〕193。学界普遍认为崇圣寺及三塔始建于公元九世纪初叶,当南诏丰劝佑时期。无论如何,将崇圣寺及三塔当作唐朝与南诏佛教文化交流的结晶大体不差。1976-1979年加固维修主塔千寻塔时,发现大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文物,一些佛像造型风格具有浓厚的汉传佛教色彩,可以判断是唐代造像。塔中藏有华严宗实际开创者法藏所译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剑川石宝山石窟开凿年代从南诏一直持续到大理国时期,造像题记的最早纪年是“天启十一年”,属南诏第十世王劝丰佑的年号,即公元850年。但石窟开凿应早于公元850年,早期的弥勒佛和阿弥陀佛造像在面相方圆和衣饰上带有汉传佛教的风格。
(二)考古发现
近年来考古发现一些南诏早期的寺庙遗址,出土石刻造像具有明显的汉传佛教特征。1990年,在巍山县庙街乡图山遗址东南半公里的石场岭,出土180余件佛教石刻造像,包括佛、菩萨、力士、罗汉头像或躯体断片,均为红砂石质。1991-1993年,云南省博物馆组织清理发掘,清理出一佛寺基址,一厅堂建筑基址和一方形佛塔塔基,同时还出土一批石刻佛像残片及有字瓦等。这批佛像没有密宗造像因素,具有非常明显的唐代造像风格。遗址出土的乳钉莲花纹瓦当、莲花及缠枝纹方砖等,似乎也与佛教有关。大理南诏阳苴咩城遗址中的葱园村古建筑遗址出土的一批有字瓦中有“田恕造寺”〔15〕6字样,苍山雪人峰寺庙遗址出土的南诏有字瓦模印“十五年买子酋造寺”“十五年造寺僧奴”“莫造寺”“田恕造”〔15〕10等字样,似与佛教寺院有关。买、顺、酋、莫、眉等可能是为建造寺院贡献砖瓦的供养人,而不是烧造砖瓦的匠人。《南诏德化碑》碑阴所附人名及史籍记载南诏人名中确有买、顺、酋、眉等字。人名中的这些字应与其所属部落乃至部落图腾有关。如“顺”可能与顺蛮有关,“莫”可能与徒莫祗蛮有关,“俭、望”可能与俭望蛮有关。南诏在统一云南各部落的过程中,吸纳部落首领进入政权。他们捐资建造寺院,也说明佛教在南诏进一步传播。
(三)历史地名
《蛮书》说:“河子镇至末栅馆五十里,至伽毗馆七十里。”〔5〕12方国瑜疑深利城在今永仁县苴却,伽毗馆在深利城附近之处〔19〕309。深利城之得名是否与舍利有关,伽毗馆之得名是否与迦毗罗卫有关?若其如此,可以推断在南诏与唐朝往来交通要道上的一些城镇,彼时已经传播佛教。
唐朝羁縻州之命名一般与其原部落名称或首领姓名有关,如《新唐书·南蛮传》说:“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3〕6351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在洱海地区设置舍利州,以施浪诏王世袭舍利州刺史。舍利专指佛骨舍利,有时也指高僧舍利,以舍利命名施浪诏故地,而不取部落首领姓名或部族名称,说明唐高宗时其地可能已传入佛教,且有高僧之舍利。《蛮书》说大釐城“东南十余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岛上,四面临水,夏月最清凉,南诏常于此城避暑”〔5〕118。此舍利或许为南诏王室供奉在洱海岛中,水城也因此而得名。
南诏时期,滇西有部族名僧耆,东方爨区有部族名弥勒、维摩。《丘北县志》说:“弥勒维摩,盖以地近天竺,人多信佛均以佛号名其部”①参见〔民国〕缪云章主编《丘北县志》,第九册维摩部考。,认为维摩、弥勒的地名从佛教名号而来。也有学者考证,弥勒、维摩系彝语,与佛教无关。
(四)历史人名
《新旧唐书》及《南诏野史》等文献都记载,唐韦皋部将杜毗罗与南诏异牟寻共破吐蕃。《太和喜洲杜氏家谱》载:“杜氏先祖乃唐时西川节度使韦皋部将杜毗罗……杜毗罗、杜罗盛、杜盛荣相继为南诏清平官。”〔20〕1051杜毗罗的名字可能与佛教有关。佛教释迦牟尼的父母之邦名迦毗罗卫,毗卢遮那佛是报身佛,俱毗罗财神守护人间的富贵福德;药师佛所属十二药叉神将中排名第一者为宫毗罗神,又名金毗罗神,统率七千神兵为佛教护法。北魏名臣杨机之子名杨毗罗,西安市曾出土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张毗罗墓志。无独有偶,杜毗罗之得名也应与佛教有关,说他本人或为他取名的父母应是佛教徒,大体不误。《僰古通纪浅述》说:“药师佛领十二神王,自西天来。主以兵陷巂州。”〔13〕21这条记载颇简但富于神秘色彩,是否暗示南诏特别信仰药师佛十二神王中的宫毗罗,并将之作为战神崇拜?尚需进一步考证。
五、结语
南诏在云南政治版图上的崛起,与佛教在云南宗教版图上的崛起,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某种内在关系。解读其中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南诏与唐朝的政治文化关系,分析聚讼纷纭的南诏汉传佛教历史,可以深化我们对南诏佛教的认识。只有辨清汉传佛教在南诏传播的历史脉络,才能揭开笼罩在南诏梵僧、胡僧、蕃僧或南诏密教、阿吒力教上的神秘面纱,还南诏佛教的本来面貌。笔者认为,在时间上,汉传佛教始终在南诏传播,或显现或潜伏,取决于南诏与唐朝关系紧密还是疏远。在空间上,汉传佛教先在个别拥护唐朝的白蛮部落传播,再传播至乌蛮部落中的一支蒙舍诏(南诏王室)。唐初经略云南设立的几座都督府如南宁州、郎州、姚州乃至川滇边境的戎州、巂州等,设有流官,驻有军队,城中若建有佛寺,则汉传佛教星落棋布于云南各部族之间。南诏王室信仰佛教,有政治策略的考量。唐时崛起的地方政权如吐蕃、回纥、渤海等,其王室都选择佛教信仰,南诏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统一境内民族尤其是影响较大的白蛮大姓,另一方面,是为了开展对外交往,加强同唐朝、吐蕃乃至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所以,南诏境内的佛教信仰融合了诸多部派,早期汉传佛教特征鲜明,后期则逐渐淡化,这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远近密切相关。
正史关于南诏汉传佛教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前辈向达对两种类型的南诏史料已经做了精辟论述,但仅仅依靠两种史料尚不能完成对南诏汉传佛教传播情况的研究。笔者提出第三种类型的南诏史料,历史遗迹、考古发现虽然不是文字记载,但可印证第一种南诏史料,也可说明第二种南诏史料未必皆妄。第一种史料的作者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难免大汉族主义倾向。第二种史料的作者不乏少数民族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其建构的神话或历史传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也能折射地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关南诏的文字记载,常见历史传说文本化与地方文献传说化两种倾向。神话传说在文本化之后,往往被“敬惜字纸”者当作正史,而汉文正史典籍中也未必没有神话传说。我们还应运用历史地名、历史人名、部落名乃至官名封号等信息,借助社会史的相关理论,对南诏汉传佛教历史展开综合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南诏社会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