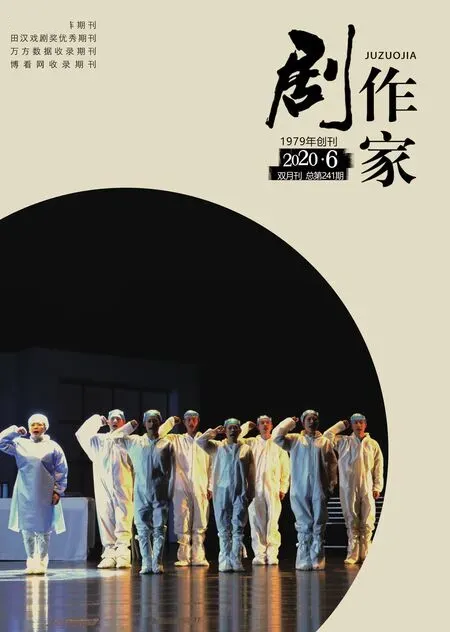《欲望号街车》:现代舞台下的经典再唤起
2020-12-03■京锐
■ 京 锐
田纳西·威廉斯的杰作《欲望号街车》在戏剧历史上是一场诗意的遐想和野蛮的力量之间的碰撞。自1947年在百老汇上映以来,它从未淡出人们的视线。2014年,英国的杨维克剧院(Young Vic Theatre)复排这部作品,使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戏剧再次获得新生。而当时间流转至2020年,当全球笼罩在疫情阴霾之下时,英国国家剧院将杨维克版本的《欲望号街车》以高清放映的方式免费上映,让它出现在全球观众的视野里。
《欲望号街车》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新奥兰多,由Ben Foster扮演的斯坦利和由Vanessa Kirby扮演的斯黛拉在出租房中过着平凡的生活,丈夫工作,妻子在家做家务。由Anderson扮演的斯黛拉的姐姐布兰奇家道中落,却不肯放弃以前的生活方式,脆弱的精神世界濒临崩溃,自南方的老家来到奥兰多投奔妹妹。因为她的生活环境迅速变坏,并与粗鲁残酷却宽容的妹夫处处不和,最后以致疯癫,被送进医院。脱离了老派而又脏乱的美国南部,杨维克剧院版本的《欲望号街车》换上崭新的现代皮囊,却仍然能够带领我们重温那一场激烈的碰撞。

无死角空间——“窒息感”的沉浸式舞美
这个版本的《欲望号街车》的舞台美术堪称大胆与激进。在如同古罗马圆形竞技台一般的舞台构造上,中心的圆盘空间是斯黛拉与斯坦利租住的公寓。仅有的钢柱勾勒出公寓空间的线条,散落着现代化的家具。钢铁的台阶指向楼上邻居的空间,并且两层两侧搭建伸入后台的走廊。主角布兰奇、斯坦利和斯黛拉的活动受限于公寓和其四周,被观众紧密围绕着,无法上下场,甚至连所有的换衣都是在灯光变暗的舞台上进行的。整个由钢铁骨架构成的空间犹如是公寓的X光片——骨感,穿透一切。自布兰奇上场,她就进入了这个透明空间,投奔到妹妹家中,而观众在离她不过两三米的地方开始,一圈圈围住她。自此,她好似陷入了一个类似偷窥狂的笼子。这种紧张乃至有点令人窒息的舞台给戏剧本身的矛盾施加了另一重张力。
这种框架感的舞台设计以及二楼的通道都让我想起1920年代俄罗斯建构主义舞台(Russian Constructivist stage),空间的组合极富几何抽象理念。然而在这个基础上,《欲望号街车》为了加强这种抽象空间的幽闭感,让其舞台上的所有功能性组件都是真实可用的,电灯开关可用,厨房水槽、卫生间里的洗手池、浴缸都是有自来水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带领观众进入这狼藉的生活。观众的目光自他们本身出发,从八角形剧场空间出发,聚集到居中的圆形空间和钢架结构的舞台,最终落在空间中生活化的家具物件上:厨房水槽堆积的餐具、未整理好的床及冰箱内部散落的食物。观众的视野由此完成了从平面和宏观到微观而立体的日常生活动作。如果说钢架的结构是冰冷和原始的,人类居住所留下的痕迹是柔软和有温度的,就如同人类固定的骨骼里容纳着血肉一般。这种对比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美学与时间。
显而易见,这个版本舞台空间的抽象性与以前《欲望号街车》表演版本力图复原1940年代的建筑与内部构造的想法大相径庭。在采访中,舞美设计师Magda Willi也表明自己的理念,他认为复刻过去的老房子对于舞台的影响微乎其微。不难理解,这种对于过去的极力模仿一旦被搬上舞台必然会引发此方面的批评——这种模仿是否真的是符合那个年代的?而抽象的现代钢架结构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一种本质的呈现,因为其从古至今都是房屋的基础架构和布局。这种设计从根本上杜绝了观众对于陈设和房屋的争议,将更多的视线投向剧本的核心本身。
除此之外,舞台是缓慢旋转的。透明而旋转的空间让舞台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无死角空间,每个主角每时每刻都必须被调度、是有事可做的,否则他就将与这个空间格格不入。例如,观众们被邀请观看斯坦利与同事们在客厅玩扑克牌的同时,布兰奇与她的倾慕对象也在门外窃窃私语,而斯黛拉则在洗手间刷牙。观众的视点被分散的同时,这种应接不暇的观看体验随着旋转的舞台反而更加多元。因为旋转的舞台不仅颠覆了传统舞台不同观众席位的固定观看视角,而且让舞台空间对于每一个观众所处的席位都是公平的和无死角的,更契合了剧中布兰奇的精神状态:自从家道中落,她通过酗酒来逃避现实,酒精给大脑带来的晕眩感与旋转的舞台是相似的,并且她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自拔,就如同没有出口的舞台空间一样。与旋转的舞台相伴的是极富现代性的灯光。当大幕拉起不久,斯坦利和他的同事玩扑克游戏时,绿色的灯光笼罩了舞台。绿色是嫉妒,是米奇出现时对于斯坦利男性气质的地位的倾慕。随着剧情展开,斯坦利和斯黛拉发生了肢体冲突。此时舞台上一片黑暗,没有任何灯光。随后当他们之间发生暧昧的亲密动作时,之前的男性气质变成了男女之间渐生的荷尔蒙,舞台上的灯光变成了彻底的红色,象征着在这部剧中暗示的性冲动与暴力。

游走于虚无之间的布兰奇——从现代外壳的舞台回归剧本
像原剧本一样,布兰奇被描绘成一位精致、优雅、极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精心爱护着自己受尊重且单纯的模样,她的性格变迁随着剧情展开,通过舞台上的色彩呈现。当她第一次出现时,她穿着白色的现代晚礼服,白色是纯洁,是天真。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她真实的样子却让白色成为了一种讽刺。而当她的真实作风被揭露时,她的颜色从柔和的、饱和度低的颜色变成了大胆的颜色。至最后一幕她迎来精神上的崩溃时,她穿着大红色的衣服,浓烈中又暗含似乎等待着毁灭般的悲切。这种色彩的运用象征着布兰奇的双重人格,她着意隐藏真实的自己是因为真实的她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纳。布兰奇的形象是具有很多阴暗面的,也因为她的谎话连篇而令人排斥。然而这一版本中的布兰奇的形象从剧本中的字里行间中升起,准确地唤起了观众的同情,每一个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某一部分。她被欲望所毁灭,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女人,活在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假面之后;然而她却又是那么纯粹地痛苦,让人无法不感同身受。
1947年,埃里亚·卡赞(Elia Kazan)首次制作的《欲望号街车》(以及四年后的电影版本)强调了斯坦利身上散发的原始的性吸引力,正如前些年的许多复排版本一样,这个版本的《欲望号街车》将布兰奇置于同情的焦点,将斯坦利设定为一个较为平庸而邋遢的男人,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评论认为这一版本表现出了女权主义的倾向。与剧本中较为隐晦的表达相比,《欲望号街车》更为赤裸地表达了当今女性对自己的刻板印象的认识——社会根据女性的年轻程度与吸引程度判断她们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之下,布兰奇对于自己年龄的始终不承认、对于自己外貌的不懈追求突然具有了情绪的重压,因为这几乎关系到她的生存立足。布兰奇也在剧中对斯黛拉说道:“男人们是看不见你的,也不会承认你的存在,除非你与他们做爱——而你必须要得到某人的承认,不然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在剧中,布兰奇的这一种生存法则被放大了,并同时被赋予了一种对自我保护的怀疑态度。她永远把自己定位为男性欲望的对象,所以斯坦利与布兰奇之间的性张力也就更加明显。比如斯坦利在客厅时,她在半透的分隔帘后更换衣物。另一方面,她将自己的性吸引力作为一种武器,比如在米奇试图亲吻她时回敬一巴掌。此外,布兰奇永远都在贬低斯坦利并说服妹妹离开他,与此同时却展现出与妹妹争夺斯坦利的注意力的行为。然而斯黛拉是毫无察觉的,因为怀孕的她对于自己的婚姻关系因新生命充满了期待和自信。
从舞台版本跳脱出来,回溯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本身。它出现于1950年代,这是美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过渡期,美国人民还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淡经历中完全恢复,家庭制度的日益瓦解也是明显的趋势。正如Hooti&Rashidy所描述的那样:每天,我们都在大街上彼此相遇,但彼此之间却不认识,甚至根本不愿意建立联系。我们似乎对于社交持恐惧的态度,因此似乎失去了公共生活的意识,最终这将导致一个孤立的世界。面对罢工、朝鲜战争等问题,1930年代和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美国民众感到幻灭和不安全感,因此战后的一代也是“幻灭”的一代。尽管在19世纪甚至更早以前,人们自我身份的追求问题就一直存在,但到了当代,自我的丧失和对自我的追求更是成为了当代美国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话题。从自我寻找的这一角度去看,此版本虽是现代的外壳,内核却没有改变。剧中,斯黛拉和布兰奇两姐妹在通过婚姻摆脱父权的过程中,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伴侣:斯黛拉选择斯坦利基于激情,而布兰奇对于丈夫艾伦的选择则基于对精致的偏爱。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后,布兰奇对于艾伦的侮辱性举止也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尽管布兰奇仍在为自己不切实际的生活观念苦苦追求与挣扎,但她为自己丈夫的自杀仍然负有额外的负罪感。舞台中,前后分别出现的枪声是布兰奇脑海中从未散去的、丈夫自杀的阴霾。
她的一生都在努力逃避人类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欲望是她预防死亡的解药。如果说死亡代表了时间的力量,那么布兰奇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试图隐瞒年龄,总是寻求更年轻的男人作为伴侣来抵消这种力量,这种渴望成为了抗击死亡的心理武器。当这些事情败露、她作为教师的道德尊严荡然无存时,她来到妹妹的家进行一场更加微妙的权力博弈。对于斯坦利来说,布兰奇是闯入夫妻舒适圈的不速之客,破坏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于是他通过揭露布兰奇的虚假过往来摧毁布兰奇与米奇结婚的可能,也摧毁了布兰奇想要开始新生活的美好愿景。这一行为部分是由报复而起,另一部分是用一次计划好的强奸来把布兰奇从自己的世界里唤醒。布兰奇的挑衅进一步唤起了斯坦利强奸行为的动机,最终导致自我和理智的双重毁灭。事实上,强奸的场景是布兰奇寻找自我身份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她彻底地崩溃、破碎,并被送往庇护所,而斯黛拉继续与丈夫住在一起,准备照顾新的生命,假装布兰奇从未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布兰奇是威廉斯笔下一种典型的女性形象,愿意始终活在过去的幻象里,不愿接受20世纪(另一种则是健康的、感性的拉丁裔女人,以一种救赎前者的形象出现)。南部世界在威廉斯的戏剧中是充满着挫败的人类愿望和失败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但威廉斯的戏剧也牢固地扎根于过去的世界,并拒绝与时俱进。当来自这个世界的角色被呈现在舞台上时,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都已经被诅咒了。正如布兰奇独自留在家中时所说:“我为之而战,为之流血,几乎为之而死!”她努力抵抗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瓦解,但无论怎样也抵挡不住其衰落速度和死亡的压力。随着家庭的瓦解,脆弱的个体发现自己处于敌对和恶劣的环境下无力承受命运,她们感到无根、孤独,也由此与家园、社会、旧的生活方式及自我疏远了。这种对自我的丧失在奢侈的男性世界中得以维持,让她无法将自己定义为女性代表,而是寻找男性中心——而这种寻找,无疑是失败的,不仅在她父亲身上,或是所嫁的人身上。因此,性不仅如前文所说成为了她停止时间、预防死亡的解药,更成为了她寻找自我的方式,寻找到“被认可的存在”。而她寻求自我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她自我寻找并不是参考她的现在,而是参考已经逝去的生活。《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一切戏剧动作都表明,一个人必须在多个个人和社会环境中寻找自我,而不是某个单个的框架。而当我们从现代的舞台回头看向剧本创作时的社会心理,布兰奇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戏剧展现她“在虚无的现实中寻找自我身份”这一本就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事件。
如何在不断被复排的经典剧作中平衡新意与旧内核,是当今的戏剧舞台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杨维克版本的《欲望号街车》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意义在于其在大胆粗犷的现代舞美外壳下,细腻地复刻剧中人物的熟悉灵魂,并唤起我们对于剧本本身的再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