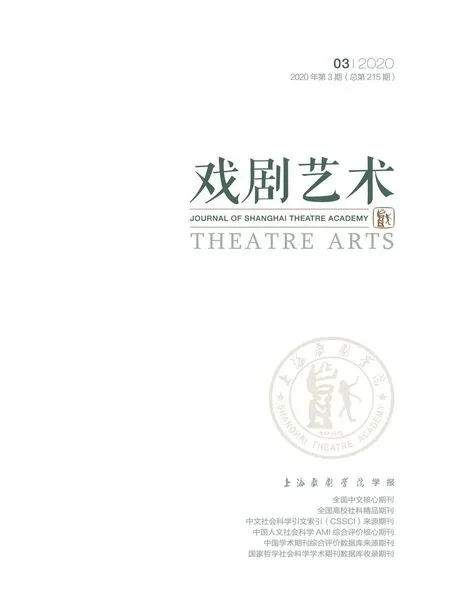从具身性理论重思环境戏剧的观众参与
2020-12-03邓菡彬
邓菡彬
1980年代以来,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理查·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等与传统戏剧观念大相径庭的思想席卷而来,震撼了几代戏剧人的戏剧本体观。但是观众参与的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身体理论,却仿佛最终只是在实验戏剧的小范围内产生影响,在不断呼唤“文学性”的声音中,总显得形迹可疑。
2016年底,《不眠之夜》的上海版成功上演,连续几年一票难求,复制了它在纽约的成功。大家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观众真的能够喜欢上参与式看戏,而谢克纳所说的“大部分未受话剧和京剧及其相关形式影响的中国传统戏剧完全是环境式的”(1)(美)理查·谢克纳 :《〈环境戏剧〉对中国戏剧有用吗?》,曹路生译,《戏剧艺术》,1997年第2期。《环境戏剧》中文版的序言提前四年单独发表。,难道并非虚言?当然,谢克纳本人并不喜欢这部打着“沉浸式戏剧”(immersive theater)新招牌问世的作品。(2)作者2014年至2015年在纽约大学访学期间与谢克纳进行了交流。国内学者也常对它的商业化进行抨击——虽然国内其他的跟风而上的沉浸式戏剧作品都难以达到如此的商业成功。文学性讨论的背后是思想性,而中国观众有可能接受什么样的具有思想性的观众参与呢?
一、第四堵墙的有无与被忽视的演员的具身性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是中国本土环境戏剧的“高光时刻”。在当时的上海人艺,谢克纳亲自导演并和他的副导演陈载澧、曹路生共同完成了《明日就要出山》,让不少以为自己不会紧张的观众心跳加速。谷亦安导演了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屋里的猫头鹰》,观众摸进“黑屋”,似乎成为了猫头鹰,偷窥人们烦躁、恐惧的生活。俞洛生在上海人艺由艺术沙龙改建成的酒吧间里导演了《留守女士》,演员的一颦一笑,都在观众的关注之中和影响之中。在北京,林兆华把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的所有空间变成一个大的环境戏剧,上演“’93戏剧卡拉OK之夜”。徐晓钟在中戏校园里导演了《樱桃园》。(3)叶志良 :《环境戏剧:与生活同构》,《戏剧文学》,1998年第7期。观众们对这些戏或喜欢或疑惑,但无论如何,往往觉得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新尝试。但是,为什么这股热潮又没能继续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批戏都是导演主导的,未能将环境戏剧的理念落实到演员的具身性(embodiment)上。“’93戏剧卡拉OK之夜”中林连昆、梁冠华等一众大佬,还是按照他们在镜框式舞台上的演法来演。《留守女士》热演一百多场,但主演吕凉和奚美娟演完这部戏后各自归位,他们的赫赫声名与环境戏剧的艺术手段,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在《明日就要出山》的录像中,作为演员,我能“共情”地感觉到剧中演员表情上的那种勉强:导演让我这么演,那我就这么演吧。中国演员所习惯的具身性是成为角色,用角色的身份来说话,这与环境戏剧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因而也就很难真正达成观众参与的目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第四堵墙”,隔绝了演员与观众直接交流的可能,这既是限制,也是保护。在更早的年代,当观众可更直接地与演员交流的时候,部分观众在其社会权力结构上的优势、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常常对演员的创作造成威胁。“第四堵墙”规范了观众和演员之间的关系,保护了演员在一定创作空间之内的自由,演员需要在排练中形成对一个人物或者戏剧进程的总体理解和表演贯穿线。演员有时会跟导演抱怨某一种演法“不舒服”,那导演就得找办法来改进或者妥协。观众的参与,则会破坏“第四堵墙”的保护,带来挥之不去的“不舒服”。
谢克纳等导演的做法,是对传统形态中观众参与的否定之否定,并非重新进入勾栏瓦肆、酒楼茶园的状态,但演员仍然常常会觉得被侵犯。所谓否定之否定,在于让这种感觉被侵犯的不稳定状态一直处于被讨论、被审视的状态之中。在《环境戏剧》这本书中,大量篇幅是在描述谢克纳导演的《酒神1969》《公社》等剧的排练和演出中,导演和演员之间的这种对峙性的工作,不仅有密集的思辨性讨论,更有随之而来的身体训练,这使演员即使没有第四堵墙的保护,仍可在冲突中抵近创作自由。
对《明日就要出山》进行知识考证,可发现两条很有意思的线索。这部戏的编剧孙惠柱,在为俞建村《跨文化视阈下的理查·谢克纳研究:以印度和中国为例》所作的《序》中,一方面说谢克纳“一贯的做派”,是对于“不同的声音”“得意洋洋”,另一方面也指出“有趣的是,中国大陆是谢克纳引起争论最少的地方”。(4)孙惠柱 :《序》,俞建村 :《跨文化视阈下的理查·谢克纳研究:以印度和中国为例》,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另一条线索是,谢克纳在《环境戏剧》中文版序言中谈到《明日就要出山》,仅是谈了“我面临中国戏剧界在80年代末期的好的方面和一些坏的方面”,好的方面是“大家渴望实验,尝试新的解决方法”,“从负面说存在着使一个剧院衰败的消极影响:雇了许多演员,只有其中一部分在工作;为了挣足够的钱生活,演员们不得不缺席排练去拍电视;一些人的态度是,把到剧院来看成是一种‘凑合对付’的工作,而不是一种生命的召唤,一种‘艺术中的生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5)(美)理查·谢克纳 :《〈环境戏剧〉对中国戏剧有用吗?》。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谢克纳在排练《明日就要出山》的时候,恰恰没有得到他最得意的“不同的声音”。一部分演员消极怠工,有可能是因为急着去挣钱,也有可能包含着对这种新的艺术手段的不认可,这种不认可是固化的,没有任何争论(但可能背后或者事后议论)。而另一部分渴望实验的演员,也会用崇拜和服从压制住内心的争论。这也是因为国内演员的语言文化习惯所致。这让大师在“引起争论最少”的中国反而陷入无物之阵,无法跟演员在辩论中推进。
由于当时的特殊原因,谢克纳提前回国,由两位副导演完成排练和最终的演出。所以也无法想象,如果工作时间更长,会不会找到办法打破演员的固有状态。我有幸在纽约连看两遍谢克纳近年唯一的作品《想象O》,对演员的状态印象深刻——他们不怕观众在身体状态上体现的任何质询。他们不怕思想线索被打搅,而是在格洛托夫斯基所说的从思想到身体的“真诚的,有训练的,准确的和全面的对赛”(6)(波兰)耶日·格洛托夫斯基 :《迈向质朴戏剧》,魏时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45页。中现场产生动态的连续性。这种演员的具身性,就可能直接带动观众的具身性,而非经过剧情和表意中介。相比而言,《明日就要出山》的演员,碰到观众突然的主动参与就“手足无措”(7)孙惠柱 :《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这其实还是在按照原来的表演模式,只是“捏”出了一条希望不被干扰的思想线索。
谢克纳抨击沉浸在角色中的表演,认为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不是让演员脱离感性状态,而是强调戏剧演员的双重任务,不是去演而是去“做出来”,这样才“需要他者相助”,才有机会停下来“用新鲜的眼光看事情”。(8)Richard Schechner, Environmental Theater(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Applause Books, 1994),pp.70-71.反观我们的演员,习惯舒舒服服地躲在跟他们的身份相异的角色里,或转移阵地、来到另外一个更为固定的角色里——“先锋戏剧的表演者”。他们并没有真正需要观众参与的动力,而只是甘愿或不甘愿地接受导演对观众参与的安排。这种没有解决观演具身性问题的“先锋戏剧”,难免沦为导演的独角戏。
时下一些称为“即兴戏剧”的戏,也力推观众参与,在坊间十分活跃,甚至被某些业内人士视为“先锋实验”,这是对“先锋实验”的庸俗化理解。这些戏往往利用观众的某种刻板期待,谋划出一种看似“参与式”的环境,但演员其实只能完成约定任务的表演,如果观众真的互动了,演员也不敢接招,只能假装没看见,继续往下演,连“手足无措”的底气都没有,“气场”顿破。这种“参与”,只是倒退回勾栏瓦肆中娱客的状态,是一种设计好的套路,还不如让演员躲在第四堵墙后。
在《不眠之夜》这样的沉浸式戏剧中,其实仍然有“第四堵墙”在保护演员,只是这堵墙由二维变成了三维,观众仿佛可以无限地贴近演员,但其实剧场礼仪和“黑衣人”(工作人员)的无处不在,仍然使得观众只能环绕观看而已,演员的身体存在仍然如旧:还是可以祭起斯氏体系里的“当众孤独”之法,沉浸在自己角色的世界里。
也是因为这种障眼法的广泛存在,本文没有采用在观众问题上语焉不详的雷曼(Hans-Thies Lehmann)的“后戏剧剧场”一词,而从另一位德国学者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的“具身性”语汇入手。
二、从“具身性认知”重新发现语言
在对《明日就要出山》的排练状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演员的语言文化习惯值得琢磨。语言学家赵元任从符号学的角度谈“中国语文”,他说:“在语言上有两个相反的势力在那儿对敌,一个就是说话的人或写字的人总喜欢偷懒,能够多方便多快就马马虎虎过去了,可是听的人或看字的人他要求清楚。”(9)赵元任 :《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2页。可能这样的关系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但是汉语在这方面确实很突出。剧场(包括排练厅)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公共性的地方,当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听得清楚的时候,语言就可能变得不够鲜活,好演员恰好又内心敏感,就可能变得不那么爱说话。
但是把表达和语言划等号是个误区。为了区别于传统的戏曲,把“drama”翻译成“话剧”,一定程度带偏了方向。时至今日,很多人分不清小品和短剧有什么区别。小品在各种晚会中被归入“语言类节目”,而话剧被很多人视为晚会小品的加长版。而实际上,剧场艺术是综合表达,空间造成的心理暗示、演员的身体状态引发的“共情”,都使得语言和非语言之间的半离合状态或中间状态,变得比日常生活之中的平均情形更为深广和生动。
在谢克纳写作《环境戏剧》的时代,只能通过仪式来类比:在环境戏剧中,观众实现了一种“仪式中的参与”,也就发生了离开日常生活状态的“转化”,“达到了(人的)存在的新秩序或新状态”。(10)Richard Schechner, Environmental Theater(expanded edition), p.101.但是借助现代科学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
1988年,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等神经科学家,在意大利用恒河猴进行实验,发现“镜像神经元”。在实验中,抓食物的猴子和看别的猴子或人抓食物的猴子,镜像神经元会产生相同的电生理反应。此项研究启发了在科学和人文交汇点进行思考的学者们用新的理论框架去解释过去实验方法未能触及的“共情”等人类身心活动。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V. S. Ramachandran)通过实验认定,正是因为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如果你要对他人的行动做出判断,那么你就必须在你大脑中运行相关运动的虚拟现实模拟”。(11)V.S. Ramachandran, The Tell-Tale Brain: A Neuroscientist's Quest for What Makes us Human(New York: Norton, 2011), p.123.他据此做了著名的解除截肢者的“幻肢”烦恼的著名的“镜盒”治疗实验。(12)See Ramachandran's TED talk, https://www.ted.com/talks/vs_ramachandran_3_clues_to_understanding_your_brain(Accessed April 4, 2020).这个实验所取得的“戏剧性的疗效”,被认为与人类学家拉图(Bruno Latour)提出的“演员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颇有相通,而与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相异。(13)Katja Guenther, “‘It's All Done With Mirrors’: V.S. Ramachandran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Phantom Limb Research.” Med Hist, 2016 Jul 60(3): 345-346.
在传统的心理学模式中,人的“感觉系统提供了经过转换的符号,中枢独立进行符号加工,运动系统再将加工结果转换为具体的状态和动作”,大脑中枢拥有符号加工的计算能力,高于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这实际上支持了西方哲学中长期流行的身心二元论。(14)叶浩生 :《镜像神经元:认知具身性的神经生物学证据》,《心理学探新》,2012年第1期。符号加工又比较依赖语言,哪怕是在潜意识领域,那就又支持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而镜像神经元不是通过感觉系统输入符号而发生计算反馈,而是通过内部模仿,从而根据所观察对象的动作行为的潜在意义进行主动的计算。比如在实验中,抓食物的猴子和看别的猴子或人抓食物的猴子,镜像神经元会产生相同的电生理反应。这就有可能使“共情”这种过去“使用实验方法还无法触及”的神秘的心理能力获得科学认知。
虽然暂时还缺少有效的办法向人类大脑植入电极来进行实验,但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仍然极大地推动了具身性这个概念成为科学与美学共享术语的可能性。
李希特分析过具身性这个词在戏剧领域的流变,他通过对格洛托夫斯基和哲学家梅洛-庞蒂的梳理,认为“具身性”最终脱离了戏剧文学对演员必须呈现剧本给定的符号意义的束缚,回归了可以被认知科学和人类学通用的身体的物质性。(15)Erika Fischer-Lichte,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Performance: A New 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Saskya Iris Jai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pp.77-83.这种理解打破了灵肉二元论,但仍有些过分强调个体的身体本身。谢克纳经过印度舞蹈表演的研究,就发现一种非西方式的表演中,情绪这种被西方式的演员更多地认为属于个人的东西,其实可以是“客观的、基于公共的和社会的氛围”。(16)Richard Schechner, “Rasaesthetics.” TDR: The Drama Review,Volume 45, Number 3 (T 171), Fall 2001,p.32.
割裂人的社会性而谈身体的物质性,使科学家在研究人类的问题上也容易绕弯路,比如巴瑞特的《情绪》一书描述了科学家们根据单体的人所设置的众多情绪研究模型,是如何得出各种似是而非而又保守的、有争议的局部结论。(17)参见(美)莉莎·费德曼·巴瑞特 :《情绪》,周芳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李希特的戏剧史建构,批判了使演员的身体受制于剧本的时代,但从历史辩证法而言,这其实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李希特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如梅耶荷德回归马戏等传统表演,也是传统的再创造。在经历了“文学的剧场”时代之后,戏剧表演进化出的,不是抽象的纯粹身体,而是“具身的思想”(embodied minds)。而这离不开人的社会性,也离不开语言。只是这个时候语言不再能由编剧来垄断。
哲学家陈嘉映是人类自然语言的捍卫者,他曾谈到,“自然语言充满了含混、不确定、情绪色彩、暗示、双关等等”,常给交流带来障碍,所以引得人工语言和逻辑语言的设计者们雄心勃勃,而人类虽然在数学、法律、计算机等领域取得“特定目的服务”的赫赫战功,但这些终归无法取代自然语言,因为后者是“依语言的实际用途生长出来的”,“词汇之间的勾连是多种多样的”。陈嘉映是非常“体贴”的文学阅读者,从他对人类语言的这个阐述来理解具身性认知中的戏剧语言,再合适不过了。
“猴子取食物”也反映了当前实验科学所发展到的程度,是用逻辑语言的无限小的方法(也就是陈嘉映介绍的罗素反复提倡的“奥康姆剃刀原则”)切分出来的一个切片。以语言为代表的人类高级行为活动,其重要特征就是在社会存在中的连续性和流动性。伟大的编剧所把握住的语言在这种连续性和流动性之中体现为台词,更体现为台词与台词之间的关系。
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里,医生在最后离场前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非洲这个时候应该是多么热呀”。对现场演出没有强烈体验的人可能意识不到,像这样的台词对编剧的高低是一道分水岭,对演员的好坏也是一块试金石。待在绝对化的文本意义所决定的角色中,或者待在孤立割裂的所谓“演员的身体”中,在这样的台词表达上都会“失色”。
2018年秋天,在莫斯科看到图米纳斯的《万尼亚舅舅》之前,我先在彼得堡看过另外一个剧院的《万尼亚舅舅》,觉得很不错。但是图米纳斯当艺术总监的瓦赫坦戈夫剧院不愧为当代俄罗斯最富声望的剧团,演员说出“非洲这个时候应该是多么热呀”这句看上去莫名其妙、无关痛痒的话时,我却泪流满面。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鼻子发酸。如果未来有足够的实验条件,也许能够证明是此刻演员的身体状态(包括留存在记忆中的此刻)触发了观众体内镜像神经元的模仿机制。镜框式舞台的布局和看似传统的第四堵墙的表演格局,也挡不住观众的身体感的强烈参与。
瓦赫坦戈夫剧院的版本和我在彼得堡看到的版本,时间相差一个小时,前者硬是把两小时的戏演足三个小时。多出来的这一个小时全部是演员的身体活动。俞建村曾经对谢克纳的代表作《酒神1969》做过精准的时间分析:非台词性的表演,占到了总时长的1/3以上。(18)俞建村 :《跨文化视阈下的理查·谢克纳研究:以印度和中国为例》,第24-25页。这些身体活动并非孤立,而是与台词难分彼此——语言不是处在狭窄的语言环境中,而是发自于整个的身体状态,发自于人和周围的人、事件之间的关系。
推崇演员身体性的“行动排练法”一度在国内引起很大兴趣,但是让演员“从自己的话慢慢地靠近剧本台词,即从自我感觉慢慢靠近人物感觉”却只适合排一些比较简单的戏,排不了《茶馆》,也排不了莎士比亚的戏剧。(19)刘国平 :《观察生活练习和行动分析法》,《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文库——论表演》,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540-541页。所以“文学的剧场”的阶段不应该被简单地“扬弃”,恰恰相反,格洛托夫斯基说“找出台词与演员的汇合”(20)格洛托夫斯基 :《迈向质朴戏剧》,第192页。,应该是在召唤契诃夫与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进行伟大的相遇。
三、环境戏剧的戏剧史意义和观众参与的具身性差异
环境戏剧推崇观众参与,但是即便谢克纳也有类似于镜框式舞台的作品,他也仍然将其归为环境戏剧。把环境戏剧理解为观众追着演员跑、观众被演员包围、四面的观众包围演区等,这些都是简单化的理解。环境戏剧来自于对上一个戏剧传统的反叛,也就是李希特所称的“文学的剧场”的传统。而这个反叛的文化根源,则是对欧洲殖民主义扩展所带来的所谓全球化的不满。俞建村生动地分析过谢克纳作品的东方文化来源:甚至在谢克纳还没有到过东方之前,经由格洛托夫斯基和阿尔托就已经受到了影响,在《酒神1969》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影响。看上去并不张扬的图米纳斯,其实也在这个反叛的源流里。
图米纳斯虽然在莫斯科执掌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衣钵传人瓦赫坦戈夫命名的剧院(由斯氏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三工作室演化而来),但他是立陶宛人。立陶宛是欧洲最后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保留着浓厚的多神教传统,而图米纳斯毫不讳言他受到这一传统的滋养。他的“幻想现实主义”当然来自对瓦赫坦戈夫的传承,但也是在重新召唤“戏剧作为酒神祭的‘通灵’意味”。(21)姜训禄 :《图米纳斯幻想现实主义戏剧的非写实形态与方法论启示——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例》,《戏剧艺术》,2019年第5期。图米纳斯所要求的“第三张脸”,正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不是传统体验派表演所理解的完全化身为角色。
姜训禄将图米纳斯的作品称为“氛围戏剧”,并且相当敏感地将图米纳斯的反叛与自己的观剧经验结合起来——“剧作家或导演再精巧的努力”,也会遭遇那些不同以往的观众的默然以对,“台下对台上的‘深度剖析’可能无动于衷”。(22)姜训禄 :《图米纳斯幻想现实主义戏剧的非写实形态与方法论启示——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例》。但与其说这是观众“审美意识的增强”以及“对剧本深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如说是观众的精神性、思想性诉求多样化了。编剧在剧本上、导演(伙同舞台美术)在形式上对先设性、思想性的把握能力也就随之瓦解。这带来的结果,是演员在舞台上所呈现的“具身的思想”才能通达观众的精神诉求。氛围好意味着这种通达的效果好。所以才有格洛托夫斯基振聋发聩的呼喊——剧场里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演员和观众。这不是说编剧、导演和舞台美术等都是无用的,而是说所有这些都需要服务于演员和观众之间“具身思想”的通达。
“具身思想”是这一阶段的剧场艺术与更早的酒神祭、萨满表演之类的核心区别,它天然就跨越单一文化,是多样性的、纵横交错的。很多学者关注谢克纳环境戏剧作品的跨文化问题,其实在当代,跨文化问题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文化跨到另一种,而是反复地“交叉感染”。谢克纳在纽约排德国戏剧作品《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把它带到印度时,原来设定的文化场景(比如典型的美式晚餐)就遇到困难,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通达性受阻。更要命的是在性、社会阶层意识方面,由于文化差异巨大,近两个月的巡演其实就成为一个不断在压力和冲击中对抗和调整的过程。(23)俞建村 :《跨文化视阈下的理查·谢克纳研究:以印度和中国为例》,第36-44页。在这部戏以及之后的《樱桃园》里,谢克纳越来越把印度当地的文化元素融进去,这对观众和演员之间“具身思想”的通道形式不断地造成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那个充斥着先声夺人的激进表达的艺术时代结束之后,环境戏剧所提出的问题,需要在中国语境中更“具身性”的解答。显然,其实是谢克纳未完成作品《明日就要出山》演出之后,某些专家妄下结论,说“中国观众没有参与心理”(24)俞建村 :《跨文化视阈下的理查·谢克纳研究:以印度和中国为例》,第66页。,是洪子诚所谓文学“一体化”冲动强烈的时代里(25)参见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创作者和裁决者的傲慢。《不眠之夜》起码向我们证明了中国观众不怕跟在后面跑三个小时所带来的不舒适。《奥涅金》虽是镜框式舞台作品,也证明了如此诗意而深刻的戏,也同样能够引发观众的激情,证明中国观众不是不需要思想,而是需要真正具身性的、有思想的作品。2019年底,我受重庆寅子剧场之邀,在重庆排演青年诗人三特的诗剧《银川之歌》。2019年我一共导演了5部环境戏剧手法的作品(包括复排),没有想到最后是这一部没有情节、语言相当晦涩的诗剧直指人心,观众的反馈和参与程度甚至超过之前刚刚完成的、已经饱受赞誉的《大海》(26)习霁鸿 :《闯海人的斑斓“浮世绘”:话剧〈大海〉首演赢满堂彩》,《海南日报》,2019年12月16日,B6版。,也超过老少咸宜的喜剧《水巷口来客》。有年仅几岁的小观众,整场不吵不闹,看完了《银川之歌》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哪怕我作为导演,也无法给出一个高高在上的回答。但某种具身性的通道显然是打开了,身体和诗人的语言一起,竟然超越了语言。
要了解这种具身性的微妙,还需要科学与艺术的持续交融。2019年,我与科技艺术策展人龙星如、人工智能工程师吴庭丞合作,根据谢克纳“味匣子”表演训练,采集数据模型,研发出一款人工智能情绪测谎仪“罗莎”。它可以识别人类8种基本情绪,已在北京、上海多处展览(27)胡珉琦 :《一场机器与情感的切磋》,《中国科学报》,2019年5月31日,第5版。,也赴奥地利参加了林茨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28)参见林茨电子艺术节网站中央美院“禅机”(Zen Machine)展览2020年2月15日相关信息:https://ars.electronica.art/outofthebox/en/zen-machine/.,接受了国内外不同文化、性别等属性的大量观众的参与互动。我们发现,基于一种中国演员(男性)的情绪样本训练的AI,在国内具有较好的跨性别识别率,而当跨越种族和国别之后,误差显著增加。那么,镜像神经元的工作模式,是否后天习得大于先天生成?那么,观众参与的“具身认知”也有可能更多是由文化决定的?我将继续与科学家开展协同研究,期待未来能够为我们对“具身思想”的认知增加更多的科学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