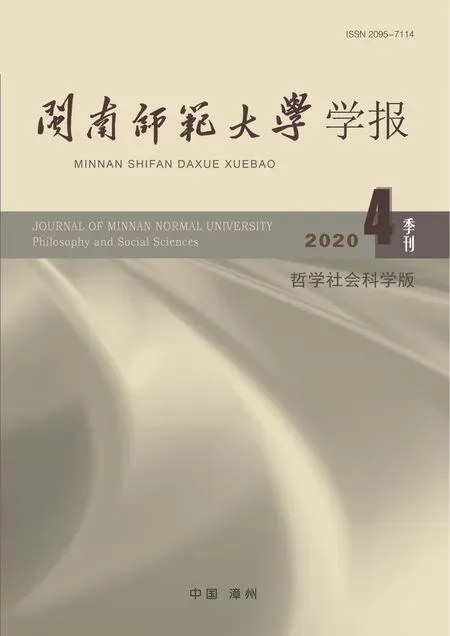试谈词义上下位化的相关问题
2020-12-03贾燕子
贾燕子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对上下义关系(Hyponymy)的研究是词汇语义学对于包括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以及部分-整体关系等词汇意义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上下义关系,早期学者也称之为语义包含(Inclusion)关系①语义学早期研究词义的包含关系时,只讨论上下义关系,故早期学者如Palmer(1976)、Lyons(1977)等,常把两个概念等同使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一般认为,上下义关系仅是包含关系中较为典型的一类,其它像整体-个体、整体-部分关系也属于语义包含关系。,指纵向两层类聚之中有两类词,其中意义较概括的、表示上位概念或类概念的词叫做上位词(Superordinate)或上义词(Hypernym),意义较具体的、表示下位概念或种概念的词叫做下位词(Subordinate)或下义词(Hyponym)。上下义关系是分层级的,常见的是两层,也有多层的[1](P66-67)。汉语史上,有一些词的词义古今发生了上下义位的变化。例如“江”“河”,先秦时期专指长江和黄河,汉魏以后成为“河流”的通称。“臭”春秋时期表气味义,东汉以来则主要指臭味。这种从下位词演变为上位词的现象可称为上位化,从上位词演变成下位词的现象可称为下位化,两种现象可合称为上下位化[2]。词义的上下位化是词义演变的类型之一,也是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目前学界对该现象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主要讨论词义上下位化的演化阶段、义位关系、机制、不平衡性及其原因等问题。
一、词义上下位演化的不同阶段
根据新义性质的不同,词义上下位的演化过程可以划分为指称义→泛指义/特指义→扩大/缩小三个不同的阶段,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一)第一阶段:指称义
表示上位义的词在具体语境中往往可以指称不同的下位义,这在语言使用中很常见。如“石”本义为石头、岩石。《说文·石部》:“石,山石也。”《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荀子·议兵》:“譬之若以卵投石。”在不同的语境中“石”可以指称不同种类的石头。可以指碑石。《墨子·兼爱下》:“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史记·秦始皇本纪》:“刻石颂秦德。”可以指礧石(即古代作战时从高处下投以打击敌人的石头)。《左传·襄公十年》:“荀偃、士匄帅卒攻偪阳,亲受矢石。”孔颖达疏:“兵法守城用礧石以击攻者。”可以指陨石。《公羊传·僖公十六年》:“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可以指药石(即中药里的矿物部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孔颖达疏:“治病药分用石,《本草》所云钟乳、礬、磁石之类多矣。”可以指砭石(古时治病用的石针)。《战国策·秦策二》:“扁鹊怒而投其石。”《韩诗外传》卷十:“扁鹊入,砥针砺石。”因此,本来表示上位义的词在不同的语境中用于指称不同的下位义,这样的例子极为常见。
本来表示下位义的词用于指称其上位义的例子相对较少。最为常见的情况,是人们在语言使用中用专名来指称类名或通名。例如在先秦典籍中,“江”“河”本是“长江”和“黄河”的专名,是表示“河流”义的下位词。《说文·水部》:“河,﹝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又:“江,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入海。”《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郑玄笺:“江也,汉也,南国之大水。”因为长江和黄河分别是南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在人们的认知中最具凸显性。故春秋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中就出现了“江河”“江海”“河海”等组合,泛指河流,这是一种临时性的以专名指代类名[3]。《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战国策·楚策四》:“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①王力(1982)指出,在上古典籍中,凡是“江”“河”似乎解作专名、通名都讲得通时,都应解作专名。此外,主要还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原本表示下位义的词,当其语义中所包涵的限定性成分在语言运用中呈现出来时②从隐含到呈现是汉语上古到中古期间词汇发展存在的“一条重要的规则”(胡敕瑞2005)。,该词往往指称其上位义。[4]例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陶渊明〈联句〉》:“高柯擢条干,远眺同天色。”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一“须阇提品第七”:“时儿回顾,见父拔刀欲杀其母。”上例中“眺”本义指向远处看,“顾”本义为回头看,由于其表示方向的语义要素“向远处”“回头”在句中已经作为修饰成分呈现了出现,因此两词都仅指称上位义“看”。
第二,在并列连用或对举结构中的下位词也多指称其上位义。例如《贤愚经》卷三“锯陀身施品第十五”:“剥皮去后,身肉赤裸,血出流离,难可看睹。”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北瞻芒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禅(神)皋显敞,实为胜地。”上例中的“睹”“瞻”“眺”“望”“顾”本都是表示“看视”概念的下位词,但它们在连用或对举使用时,本义的区别并不明显,主要指称上位义“看”[4]。
以上这些意义多数仅仅是各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指称义(Referential Meaning),还不是该词的词义(Sense)。只有当这种指称义经常使用,才成为该词的特指义或泛指义。
(二)第二阶段:泛指义/特指义
用一类事物中主要的个体来代表这一类事物用法的频繁出现就会导致表示该主要个体的词语产生“泛指”义,用某一类事物的通名或类名来称呼该类事物中某个个体的高频使用则导致表示该通名或类名的词语产生“特指”义③学界对“泛指”“特指”有不同的界定。如王力(1962:92)将泛指、特指等同于浑言、析言;杨琳(1996:209)认为一个词同时具有泛指义与特指义,二者是相对的。本文所谓的“泛指”是指一个词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用来表示其上位义,“特指”指一个词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用来表示其下位义。(参蒋绍愚2005:109-110)即一个词的原义与特指义、泛指义之间是上下位关系。。泛指/特指是一种共时的语言现象,一个词和它的泛指义/特指义出现在一个时代平面上[5](P111)。
例如现代汉语“皮”表示人或生物体的表层组织之义。先秦时期,“皮”专表动物的皮,且仅指从虎、豹、狐、鹿、鼠、羊、牛等兽类、畜类身上剥取的带毛的兽皮。《诗·墉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秦汉时期,偶见“皮”指称植物的表皮和人的皮肤的用例。《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树,赤皮支干,青叶,名曰朱木。”西汉刘向《新序·杂事》:“其为人也,臼头深目,长壮大节,昂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到东汉时期,《论衡》中“皮”单用15例,其中表示动物的皮9例,表示植物的皮4例,表示人的皮2例;《汉书》中“皮”共出现27例,其中仅3例表示植物的皮,其余用例都表示动物的皮。从使用频率来判断,“人或生物体的表层组织”义在东汉中土文献中可以看作是“皮”的泛指义。[6]
再如春秋时期“臭”本为气味义。《广雅》:“臭,凡气之总名。”《周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虞翻注:“臭,气也。”战国末年,“臭”开始由气味义向恶臭义转化[7](P541)。《山海经·大荒北经》:“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到西汉时期,“恶臭”义已经成为“臭”的特指义。因为从使用频率来看,“气味”义与“恶臭”义的用例数,在《淮南子》中分别为13例和3例,《说苑》中各2例,《史记》《盐铁论》中则都只出现了2例“恶臭”义[8]。
某词的泛指义或特指义还是该词在特定语境中表现出来的临时意义,它们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属于“隐涵义”(Implicature)。例如《汉书·天文志》:“至河平元年三月,旱,伤麦,民食榆皮。”例中“皮”与“榆”搭配,可推知其指植物的皮。《淮南子·说林》:“酤酒而酸,买肉而臭,然酤酒买肉不离屠沽之家。”例中“臭”与“酸”对文,故可推知指臭味。正因为有语境的限制,所以当这些词出现泛指/特指义时,才不会和它原来的意义混淆。
(三)第三阶段:扩大/缩小
一些词语的泛指义或特指义,得到社会的认可,使用范围广、频率高,脱离了对原语境的依赖性,可以发展成为固定义。当这些临时的泛指义或特指义被社会群体模仿而逐渐模式化、泛用化、规约化,进入语言系统成为该词的固定义时,就变成了扩大和缩小①学界关于词义扩大、缩小的说法,由于界定标准不同,所指的范围大小就有很大差别。范围最大的,把词义由具体到抽象、由特殊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的变化都称为词义的扩大,反之都称为词义的缩小(如赵克勤2005:125-131,符淮青2005:136-142,张志毅、张庆云2005:243-249);范围最小的,则仅把从下位义变为上位义的演变称为词义的扩大,反之称为词义的缩小。(如蒋绍愚2005:74-77,葛本仪2001:183-193)[9]。例如“皮”的词义扩大在东汉佛经中已经完成,《道地经》《修行本起经》《四谛经》中,表示人的皮肤、植物表皮的意义全部由“皮”承担,专指人皮肤的“肤”已不再使用。中土文献中“皮”词义的扩大则要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6]。“臭”在东汉词义的缩小已经完成,“恶臭”义已经成为其主导义位,本义“气味”义出现频次很低。如此期五部文献《论衡》《汉书》《风俗通义》《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中,仅出现了1例“气味”义,而表“臭味”义的用例则有32例[8]。可见,扩大/缩小是词义历史发展的结果。
综上可知,词在某些具体语境中往往可以指称其上下位义;特指义/泛指义是共时层面的上下义位变化,是上下位化必经的中间阶段;词义扩大/缩小是上下位化的结果。语言中大量的词语可以具有特指或泛指义②如王力等主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中以和的形式标注了词语的泛指义与特指义,在该书所收6400多个单音词中,产生泛指义的单音词有195个,产生特指义的单音词有171个,泛指义和特指义兼有的单音词有5个,共计371个。,但真正发生词义扩大、缩小演变的词语数量并不多。同时,泛指、扩大和特指、缩小又分别是一个连续统,其界限并不明确,划分的主要依据首先看该意义是否受语境的制约,其次是看其使用频率的高低。
二、上下位义与原义的义位关系
石安石曾指出:“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之间不能有一般与个别那样的包含关系。”[10](P54)一个词的上位义或下位义形成固定义后与本义并存,可能带来交际的不便。词义的扩大、缩小发生之后,原词义一般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而存在,因而一般不会增加新的义位。但是,从某意义可以脱离语境独立使用,到此意义成为该词的一个固定义,再到此固定义取代原义成为该词的主导义位,此过程是需要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的。所以从义位的角度来看,原义和上位义之间的关系表现为:
词的原义使用较长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泛指义。先是泛指义偶尔出现,之后逐渐用得多起来,最后泛指义成为该词的主导义位。例如“皮”由指动物的皮到表示人或生物体的表层组织之义。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上位化前后都只有一个义位。在只用原义和上位义偶尔或较少出现时,是以原义为主导义的一个义位;在上位义成为该词的常用义后,是以上位义为主导义的一个义位。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以原义为主导义的是一个义位,以上位义为主导义的是一个义位。
原义和下位义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情况类似而稍有不同:原义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了特指义用法,表现为较多地表示原义中某个方面的意义,而较少表示原义中其他方面的意义。例如“臭”由指各种气味,逐渐较多用于表示难闻的气味。在此阶段,原义是该词的主导义位,下位义是该词的特指义,特指义都要受到语境的制约。之后,下位义的用法越来越频繁,特指义的高频使用使得该意义可以脱离语境的制约而独立存在,下位义最终取代原义成为该词的主导义位,而原义则逐渐消失。
三、词义上下位演化的机制
历史语言学家近年来特别借重语用学的研究成果,用普遍适用的语用原则和语用推理来解释语言演变的动因和机制。[11]例如Grice提出了交谈“合作原则”的“适量原则”(Quantity),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足量原则”(Q-Principle),指(说话人为听话人省力着想)说的话要充足;一是“不过量原则”(R-Principle),指(说话人为自己省力着想)只说必要说的话[12]。Horn将“足量原则”称为“Q原则”(取Quantity的首字母),将“不过量原则”称为“R原则”(取Relevance的首字母)[13]。词义上下位演化的机制就是与转喻相关的基于R原则的语用推理。例如:当人们用“河{黄河}”来指河流、用“谷{谷物}”指稻谷时,话语的信息量显然都是不够的,但因为黄河在北方是河流中的典型成员、稻谷是谷物中的典型成员,所以听话人根据R原则,可以推知这是泛指或特指。这种由R原则引发的上位化与下位化,正好形成镜像[13]。
之所以说词义上下位演化的机制是与转喻相关的基于R原则的语用推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基于R原则的语用推理中,新义的信息量都要大于旧义。基于R原则的上位化涉及的信息量增大,是加合其他同类信息,即增加外延、减少内涵。比如“河”的新义“河流”相对于原义“黄河”,信息量增大,是因为“河流=黄河+淮河+漳河+……”。基于R原则的下位化涉及的信息量增大,是带上限定性,即增加内涵、减少外延。比如“谷”的新义“稻谷”可以理解为“某种常食用的谷物”[14]。
二是上位化是原义M1蕴涵(entail)新义M2,如“河”的“黄河”义M1蕴含“河流”义M2。下位化则是新义M2蕴涵原义M1,如“黄金”义M2蕴含“金属”义M1。凡是具有蕴涵关系的语义演变,新义与原义必定是相关的。
三是转喻引发的演变,新旧义有一个二义共存的阶段,原义和特指义/泛指义在共时层面往往共存。
四是因语用推理产生的意义,都是隐涵义,这个隐涵义可能转化为词汇义,也可能只是语境义[14]。尽管在特定的语境中词义上下位互为代替的情况较为常见,但词的泛指义或特指义能发展为固定义,并且该固定义又取代了原义的情况却极为有限。如“驹”泛指马或幼兽①“驹”本指二岁的马。《说文·马部》:“驹,马二岁曰驹。”《周礼·夏官·校人》:“春祭马祖,执驹。”郑玄注引郑司农曰:“二岁曰驹。”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指马。《周礼·夏官·校人》“则饰黄驹”孙诒让正义:“对文驹为小马,散文驹、马亦通称。”还可以指幼兽。《尸子》卷下:“虎豹之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石”特指碑石、礧石或药石,就始终没有发展成独立的词义。所以,就“驹”和“石”来说,就只是词的特指和泛指,而不是词义的扩大和缩小了。
四、上下位化的不平衡性及其原因
王力明确指出,词义缩小“这种情况在汉语中比较少见”[7]。王力的这一观察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如徐朝华说:“词义缩小的情况,在词义演变中不如词义的扩大那样常见。”[15](P241)贾彦德、高守纲等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16][17]。孙景涛(2010)则汇集了王力(1958)、洪成玉(1985)、蒋绍愚(1989)、贾彦德(1992)、赵克勤(1994)和徐朝华(2003)七部专书中提到的词义扩大和缩小的所有用例②孙文共收集到词义扩大37例,词义缩小26例。排除其中非上下位变化的词语之后,剩下词义扩大27例,缩小16例。,发现“扩大、缩小两种情况实际上并不平衡,具体情况是词义扩大多见而词义缩小却相当少见”[18]。正如孙文所说,虽然“这些专书并不是语料库性质的,但作者们取典型实例加以分析,况且是多家而不是一家,所以汇集在一起是可以反映客观语言状况的”[18]。
我们对专书词汇研究、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专著等已有研究中提到的上下位化现象做了较为全面的收集,共得到发生上位化演变的单音词42个,发生下位化演变的单音词18个,上位化比下位化现象更为常见。
发生上位化演变的单音词:江、河、氛、匠、柴、门、皮、肉、牙、墙、壁、鸭、泥、口、嘴、粮、响、血、雏、路、山、毛、坟、墓、园、圃、房、红、雌、雄、好、凝、卧、叫、睡、洗、看、醒、唱、咬、涉、济
发生下位化演变的单音词:金、宫、子、瓦、虫、谷、禽、寡、朕、妃、辇、玺、祥、臭、肥、恶、瘸、吃
为何上位化会比下位化更为常见呢?①张树清(2010)对王力等主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全面考察后发现,其中作为固定义的泛指义多于特指义,作为临时义的特指义多于泛指义。孙景涛认为,是因为“词义扩大容易形成固定义位,而词义缩小所形成的义位却不大容易固定下来”[18]。我们推测,这应该与名词的显著度或“可及性等级”有密切关系。如以上所列举的42个词义扩大的词语中,有28个名词,占总数的66.7%;18个词义缩小的词语中有名词14个,占77.8%。可见,发生上下位演变的词有相当一部分是名词。由于不同名词所代表的概念,人在认知过程中与其建立心理联系的难易度是不等的,故不同类型名词的固有显著度会存在差别,Dixon将之称为名词的“可及性等级”(Accessibility Hierarchy)[19](P85)。在语言使用中,人们经常用专名来泛指普通概念;反之,用普通名词来转指专门事物的情形就要少得多[20]。就是因为专有名词的可及性等级高于普通名词。当然,导致上下位化现象不平衡的原因应该不止这一个,该问题尚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