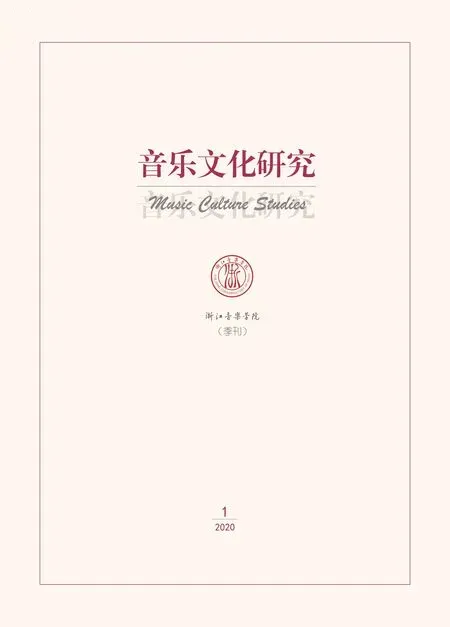古代琴论经典文本的分析与研究
——张岱琴学“生鲜之气”理论的现代阐释
2020-12-02王爱国
王爱国 翟 茜
内容提要:明清鼎革之际的文史家和艺术理论家张岱,在古琴演奏艺术的批评中,丰富和深化了“气”范畴的意义内涵,提出了“生鲜之气”说。“生鲜之气”说以“得手应心”为旨归,以“纯熟”“淘洗”“脱化”为路径,不仅阐明了音乐表演艺术的一般原理,且强调了生命与艺术高度的同一性。不仅于此,张岱还将“生鲜之气”作为涵盖整个传统艺术场域的审美范畴加以论述,试图藉此消解各艺术门类间审美认识上的暌离,从技术、艺术、学术三个向度,透射出其在当代艺术理论话语建构中的借鉴价值。
张岱(1597—1689?),明清鼎革之际的文史名家和艺术理论家,以《石匮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著述传世。张岱家学渊源,以散文见长,其文论高拔旷达,远法魏晋风度,近师阳明心学,透射出独异的文化气质与审美意蕴。不仅于此,张岱还是绍兴琴派杰出的代表人,他少年时便师从王侣鹅、王本吾学习古琴,善古琴曲数十首,对时年绍兴琴人、琴社、琴事多有记述,散见于《与何紫翔》《绍兴琴派》《丝社》《范与兰》等文述之中,为研究绍兴琴派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张岱善思多才,在琴学研究方面也造诣颇深,在《与何紫翔》文中,提出“生鲜之气”(生气)是琴乐修习中的至高原则,并对其在其他各门类艺术实践中的普适意义进行了缜密的阐述。笔者以为,“生鲜之气”(生气)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基本的审美范畴,不仅阐明了音乐表演艺术实践中的一般原理,且从技术、艺术、学术三个向度,对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拟对张岱“生鲜之气”说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探究其对当代艺术,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研究中的借鉴价值。
一、“生鲜之气”说的技术向度
张岱“生鲜之气”说的提出,缘起于古琴艺术实践中演奏技术问题的考量。《与何紫翔》文中,张岱对何鸣台、王本吾的古琴弹奏水平进行了评述:“何鸣台不能化板为活,其弊也实;王本吾不能练熟为生,其弊也油。二者皆是大病,而本吾为甚。”①据此,张岱将二人演奏中存在的弊病概括为“实”与“油”,并明确指出“油”是比“实”更加严重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张岱对古琴演奏理想境界的追索。
古人弹琴,吟揉绰注,得手应心,其间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应之灵,顿挫之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剔、一种生鲜之气,人不及知、已不及觉者。非十分纯熟,十分淘洗,十分脱化,必不能到此地步。②
张岱认为,“生鲜之气”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需以解决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为先导,尤其关注古琴演奏中手指力量、动作的掌控,以“得手应心”为旨归。古琴演奏讲求手指纵向运动中的运力之“巧”,横向运动中的变换之“奇”,前后旋律营构中的呼应之“灵”,节奏韵律变化顿挫之“妙”。藉此,“巧”“奇”“灵”“妙”成为古琴演奏技术层面需要达到的美学要求。
张岱还认为,古琴演奏若要实现从“得手”向“应心”的转化,还必须经过“纯熟”“淘洗”“脱化”三个渐次升华的修习阶段。他还特别强调:“非十分纯熟,十分陶洗,十分脱化,必不能到此地步。”藉此可见,古琴曲的修习实际上是一个勤勉练习,反复推敲,充分思考,逐步提升驾驭能力,使演奏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笔者以为,姑置“纯熟”“淘洗”“脱化”在琴学语境中的具体意义,从一般意义上,显见其在当代音乐表演艺术中的借鉴价值。
(一)纯熟
“纯熟”是通过音乐文本解析与技术技巧练习,熟练掌握作品的阶段。表演者从对作品各构成要素的解析入手,通过一定时期的强化练习,攻克技术难点,以达到音高、节奏、奏法准确,强弱对比合理,结构清晰完整、声部层次分明等技术要求,最终使作品演奏变得完整自如流畅。这与黑格尔秉持的艺术观相切合,黑格尔认为:“熟练的技巧不是从灵感来的,它完全要靠思索、勤勉和练习。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技巧,才可以驾驭外在的材料,不至因为它们不听命而受到妨碍。”③据此,“纯熟”阶段侧重于音高、节奏、指法、奏法、句法等技术元素的把握,使表演者能够轻松地驾驭作品中的材料,逐步实现音声构拟的准确、流畅与完整性相统一。
张岱还认为即便演奏达到了“纯熟”的境地,也仅是技术进阶的第一个阶段,尚需通过“淘洗”的过程来去粗取精以避免“照本宣科”式的音乐表演。
(二)淘洗
“淘洗”基本的释义为“革除;涤除”,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意。音乐表演中的“淘洗”,是通过反复推敲演练音乐细节,对音乐表演技巧进行进一步精细化处理的阶段。这一阶段侧重于解析音乐作品的构成元素,使音乐发展的逻辑更加严谨,音乐陈述的特色更加鲜明,音乐结构的对比明晰恰当,避免作品因局部细节处理粗糙而显得“语气”生硬,从而导致整体上的音乐诠释变得“言不由衷”。
“淘洗”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对音乐作品各细部环节十分精细的打磨。“淘洗”阶段通过“放大”音乐的局部,反复推敲音乐中的技术要点,寻求音乐陈述中最恰当合理的表现方式。音乐局部的精细化处理有多种方式,诸如放慢演奏速度的练习,节奏节拍的强化练习,技术难点的重点练习等。这一阶段,通过音乐细节精细打磨,使音乐作品在表演诠释中的乐句划分严谨,句法呼吸自然,音乐叙词流畅,音色模拟逼真,使音乐进行中速度、音色、力度所隐含的结构层次的表现更加合理,使音乐陈述中承接、呼应、递进、转折、衬托等逻辑关系的彰显更加鲜明。
(三)脱化
“脱化”的含义,从音乐表演层面来看,是表演者超越技术技巧的束缚,在音乐诠释中激活作品内在叙事性、抒情性、描写性、戏剧性等美学意涵的阶段。笔者以为,“脱化”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表演者音乐思维与技术技巧的成熟。有学者认为,艺术家个人表演风格的形成,“不仅可以表现在一些外在的肢体语言(姿势)和动作表情上,而且更能表现在艺术家将成熟的内在表现性意图和动机透射在音乐作品的细节中,从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乐句,甚至每一个音符的时值和力度等非常细微的方面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效果。”④表演者在具体的表演实践中,既能从微观的视角表现作品细部的特色,又能从宏观的视角把握作品的整体的结构脉络,使音乐表演变得成竹在胸,游刃有余,张弛有度。
二是音乐表演实现了重塑性与创造性的统一。表演者在深入研究音乐作品的基础上,将个人的审美理想融入作品,通过二度创作中的个性化诠释,反映出演奏者创造性的音乐思维。“音乐表演作为二度创造,是赋予音乐作品生命的创造行为,它不仅是忠实地再现原作,而且还有可能通过表演者的创造,对原作予以补充和丰富,甚至超出作曲家的预想,使音乐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这正是音乐表演作为二度创造的本质意义之所在。”⑤藉此可见,“脱化”是音乐表演者融通作品创作与个体诠释风格,实现音乐表演重塑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过程。
综上所述,“生鲜之气”是表演者融通生理与心理操作技能,贯通文本信息与音乐思维后,在音乐诠释中所呈现出的趣味生动且形象鲜活的审美意象。“生鲜之气”以技术层面的“得手”为发端,历经“纯熟”“淘洗”“脱化”三个阶段,超越技巧和谱本的束缚,追求“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⑥的境界,藉此表达艺术作品的生命感,赋予作品生动鲜活的精神力量。
二、“生鲜之气”说的艺术向度
张岱还将“生鲜之气”说从音乐引申至书画、戏剧、文学等域场加以说解,认为“生鲜之气”是多个艺术门类共通的美学原则。藉此,张岱创造性地将“生鲜之气”(生气)归结为中国传统艺术本原性的审美范畴,并对其在艺术创作与批评中的实践价值进行了阐述。
盖此练熟还生之法,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⑦
(一)音乐表演艺术
在音乐表演艺术中,张岱“生鲜之气”说的视域,既包含了琴、阮、箫等器乐演奏艺术,也包括了唱曲、戏曲等以演唱为主的声腔艺术。尽管各音乐品类在表演技巧方面的具体要求千差万别,但从表演美学的一般原则来看,都需讲求技术动作的精巧细致,表演状态的洒脱传神,语言表达的声情并茂,作品结构的合理彰显,节奏节拍的巧妙如理,使诠释者在音乐的音色、奏法、语言、腔词、形体等环节有精准的把握,从而使音乐表演变得生动鲜活且个性鲜明,藉此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据此,张岱就“生鲜之气”说在整个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域场中的本原性意义给予了肯定。
张岱的“生鲜之气”说作为主体精神在艺术上的投影,还被灌注到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其他领域。这与波兰著名音乐美学家卓菲娅·丽莎的音乐观念在语义的指向意义上有所契合。卓菲娅·丽莎认为:“音乐总是倾向于同其他种类的艺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艺术中没有达到像在音乐艺术中所达到的那样的高度。”⑧藉此可见,音乐艺术中所蕴含的美学观,始终保持着开放性的艺术品格。张岱藉此就“生鲜之气”在其他各门类艺术中所具有的普适意义加以说解。
(二)书法绘画艺术
在以书法、绘画为代表的视觉艺术中,张岱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的艺术观,将历代文人画家的所论的“生气”范畴加以融通,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
张岱在前人书画论述的基础上,强调了运笔中浓纤、轻重、肥瘦、缓急等精细化处理的意义,以求达到“练熟还生”的目的,概括性地指出笔法为“生鲜之气”之发端。有关“生气”范畴的解释,中国历代书画家皆认同书画外在形式语汇表征其生命化内容的观念。如梁武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中就认为笔法“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⑨唐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论执笔之法:“笔在指端则掌虚,运动适意,腾跃顿挫,生气在焉。”⑩古代画论中有关“生气”的论述也层见迭出,如东晋时期顾恺之就认为“小烈女,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画生气”是非常不自然的现象。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也曾批评丁光的画作:“虽擅名蝉雀,而笔迹轻赢,非不精谨,乏于生气。”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论画》中认为:“若形似无生气,神采至脱格,皆病也。”张岱与南宗山水著名画家陈继儒渊源颇深,又与时年松江画派陈洪绶、姚简叔等交往颇多,这对其艺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但在这里不是完全像绘画,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抽象的点、线、笔画,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意义。”有鉴于此,“生鲜之气”展现出艺术语言的形式化、技术化与生命形象的对应关系,藉此传达出古代书画家笔下所蕴含的浓烈的生命情感,表现出艺术与生命同一的认知。
(三)文学艺术
在对“诗歌”“作文”等文学作品创作的评述中,张岱吸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生气”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如钟嵘《诗品》载:“尝语徐太尉云:‘我诗歌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汤显祖就十分强调主体精神对文章生气的重要作用,他在《序丘毛伯稿》中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张岱将“生鲜之气”作为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观念,创造性地将其与他在文学领域提出的“冰雪之气”遥相对应,力求形成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发展中具有开创意义的美学观念。
有学者认为,张岱所论述的“生鲜之气”,“正是‘冰雪之气’从哲学层面、人格层面落实到艺术层面的面貌,它贯申于艺术创作过程之中,也就是张岱所说的‘思致文理’。在作品中,呈现为灵隽、淡远、生涩的韵致。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一种冰沁奇警如冷水浇背的艺术感受。”据此,“生鲜之气”是张岱从历代文人述论中拈出的,能够标志作品艺术品格的价值观念。“冰雪之气”说是张岱在文学领域与“生鲜之气”说可对应阐释的精神实体。无论是“生鲜之气”还是“冰雪之气”,其核心都是倡导艺术创作鲜活灵动的韵致,展现出艺术作品自由活泼的生机。据此,“生鲜之气”在文学领域的美学意义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生鲜之气”说在更为宽泛的艺术向度中展现了张岱思想自由的美学精神,“生鲜之气”总体上讲求从“技”到“艺”的转释过程,以“得手”为艺术创作的起步点,以“应心”反映出技术化的形式要素与生命化的艺术要素间的对应关系,在美学的联觉关系中展现出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酣畅纵恣的生命气质与艺术内涵。
三、“生鲜之气”说的学术向度
张岱的“生鲜之气”说,将古代的琴、书、画、戏曲中接续有致的理论相互融通,将其上升到覆盖艺术学全领域的学理学说。从现代的学术范式来看,“生鲜之气”说将“生”与“死”,“生”与“熟”,“生”与“鲜”归纳为三个相互对应的审美范畴,使其成为支撑该说的理论概念和术语,在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审美的认知中勾勒出其内在认识的脉络,发挥着现代学术观念上的引导作用。
(一)“生”与“死”
在张岱的艺术观念中,“生”与“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吾辈弹琴,亦惟取此一段生气矣。今苏下之人弹琴者,一字音绝,方出一声。停阁即久,脉络既断,生气全无。此是死法,吾辈不学之可也。
藉此可见,在张岱的观念中,如果在艺术的诠释中“生气全无”,便是“死法”,也就失去了其所讲求的美学价值。
“生”与“死”作为古代美学的范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美学历来关注审美对象内在生命意识的刻画。《老子·第四十二章》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在《管子·枢言》中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表明生命依靠气的有无而存在。“气即是‘生气远出’的生命。中国传统艺术以同样的观点来理解和表现对象,以同样的观点来理解艺术自身”,藉此,借助“气”和“韵”等哲学观念,中国传统艺术被赋予了生命性的特质,为中华传统艺术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
艺术中的“生”主要表现为“生气”“生动”“活法”等审美特征。唐司空图在《诗品二十四则·精神》中说:“生气远出,不着死灰。”明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也强调了“生”与“死”在古代美学意义上的对应关系,将“韵”的有无作为品评诗词品格的特质,强调“有韵则生,无韵则死”,认为有韵之诗具有活泼、灵动、清雅的美质,而无韵之诗则表现为僵死、沉抑、拘谨的病态之局。张岱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对“生气”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藉此可见,“生”与“死”的对应演化为艺术审美和创造中追求合规律的自由的基本命题,表明了艺术创造讲求的不墨守成规,突破既定的成式束缚所能达到的较为理想的境界。“生鲜之气”(生气)在“生”与“死”的对应阐释过程中产生,已然为现当代艺术审美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也是品鉴艺术创作美学价值的关键。
(二)“生”与“熟”
“生”与“熟”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范畴,较早的文论主要反映在诗文与绘画方面。早期有关“生”的阐释,主要侧重于表现技法方面,有“生硬”“生涩”之意,如宋人陈应行在诗词创作方面较早关注到了“生”与“熟”的对应关系,他在《吟窗杂录序》中说“一戒乎生硬,二戒乎烂熟”,认为“生硬”与“烂熟”都是诗词创作中需要戒除的弊病。后“生”的内涵又融入了“生机”“生意”“生气”的含义。
明清之际的文人画家,多借用“生熟”之说,来表述文人画所推崇的美学风格。如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需熟后生,画需生外熟。”认为书画的创作均需从技巧的熟练和工整的描绘入手,进而追求不拘泥于成法,追求生动质朴的艺术境界。而“熟”则是指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在技术技巧和形式结构方面严格严格遵守既有的规范所呈现的一种状态。据此,“熟”是艺术创作中的初级阶段,而“生”的含义因为融入了“生机”“生气”的意味,反而变成了艺术创作较为成熟的高级的阶段。
有关“练熟还生”对应关系的阐释,在明清之际的画论中日趋成熟。如明唐志契《绘事微言》中曾记录李仰怀论山水:“画山水不可太熟,熟则少文;不可太生,生则多戾;练熟还生,斯妙矣。”反映出明清之际文人画作提倡生拙古朴的美学风格。张岱以其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大胆的革新精神,把“生”与“熟”的对应关系引入到了琴学领域,借此追求琴学表演中生动鲜活的艺术境界。张岱将这种“练熟还生”的生命状态上升为涵盖多个艺术领域的审美范畴。有学者认为:“与‘生’‘熟’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张岱对‘无意得之’与‘有意得之’‘天工’与‘人力’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也是辨证的:他十分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强调全身心的投入,但又极力反对‘斧凿’,认为艺术的极境乃是建立在‘有意为之’基础上的‘无意得之’。”藉此可见,张岱论所论析的“生”与“熟”的对应关系,在现当代艺术创作中依然有着较高的借鉴价值。
(三)“生”与“鲜”
在张岱的美学观念中,“生”与“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关“生”的阐释,除却前述“生机”“生动”的意味之外,还包含着张岱自身对“生涩”之美的新的阐释和理解。张岱认为:“夫生,非涩勒离岐、遗忘断续之谓也。”而是指一种“人不极知、己不及觉”的“生鲜之气”(生气)。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阐述张岱对“生涩”一词的理解,认为:“‘生涩’是‘生鲜之气’灌注于语言中所呈现的面貌,语言经过‘练熟还生’的淘洗,必然达到‘生涩’的韵味。”可见,张岱有关“生涩”的阐释,包含着艺术创作中,凭借简练而有独特的技术语言,在艺术的创作中展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形成富有特色的表现风格的意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也认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可见诗词中所讲求的“生气”是为作者之真切感受和人格浸润所生发而出的,具有鲜活生动的表达的特质。
有关“鲜”的阐释,本具“鲜活”“鲜明”“新鲜”之意,其在艺术语境中的引申意义包含了返本开新,追求创造精神之意味,是艺术创作中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具体体现。“鲜”是艺术创作中美学意涵的外显,是艺术作品在展演中所显现出鲜活灵动,清新活泼,情韵别致,洗练传神的一种状态。据此,在“生”与“鲜”的对应关系中,其内涵即融入了艺术创作与批评主体对宇宙人生的真切理解,又兼具了出乎其外以求高致的美学意涵。
张岱的“生鲜之气”说,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的土壤,较早地关注到各艺术门类间的融通与阐释,因而具有前瞻性的意义。“中国古典美学和传统艺术既根源于自然,又超越了自然,真正做到了‘通天人之际’,而这实际上就是人类在审美王国中所追求的一种生命和精神的自由境界,一种人生与社会的最高境界,一种理想人格的崇高境界。”有鉴于此,张岱在融通了中国古代美学传统中有关“气”,“生气”,“生”与“死”,“生”与“熟”等多重观念之后,“生”在“鲜”的襄理下所呈现的“生鲜之气”,成为艺术审美中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审美范畴。据此,“生鲜之气”作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创作与批评话语中的审美范畴,其在中国当代艺术学中的本原性意义可见一斑。
结 语
张岱的“生鲜之气”说在继承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以古琴音乐的演奏艺术为范例,阐明了其所主张的音乐表演美学观念。张岱的“生鲜之气”说以音乐演奏艺术中的“得手应心”为旨归,以“纯熟”“淘洗”“脱化”渐次升华的三个阶段为路径,力求在音乐表演中达到生命与艺术的高度同构。在此基础上,张岱以其开阔的艺术视野,突破各艺术门类间的壁垒,将“生鲜之气”作为涵盖整个传统艺术理论阈场的美学范畴,试图消解各艺术门类间审美认识上的暌离,阐明了“生鲜之气”作为中国传统艺术核心观念的理论价值。
张岱的“生鲜之气”说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中国当代表演艺术理论话语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的意义。正如项阳先生所说:“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研究,就是要在文化的整体理念下接通音乐史和传统音乐两个既有学科,加强与大学术界的联系,借助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而对音乐文化的具体事项产生新的认知,将我们的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阐释是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向现代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不能简单机械地说解和阐释,尚需从中国传统的大文化的背景中加以审视,借助当代学术研究的多种方法,吸纳中西方美学中的思考与智慧,使其能够在当代的语境中重塑自身的传承品格,藉此成为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话语的思想源泉。
注释:
①[明]张岱:《与何紫翔》,载《嫏嬛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第170页。
②同①,第171页。
③[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5页。
④高佛晓:《音乐表演艺术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31-32页。
⑤张前:《音乐表演艺术论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⑥[清]魏源:《默觚上·学篇二》,载《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第5页。
⑦同①,第171页。
⑧[波兰]卓菲娅·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载于润洋译:《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译著新编》,中央音乐出版社,2003,第35页。
⑨[梁]萧衍:《答陶隐居论书》,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80页。
⑩[唐]张怀瓘:《六体书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