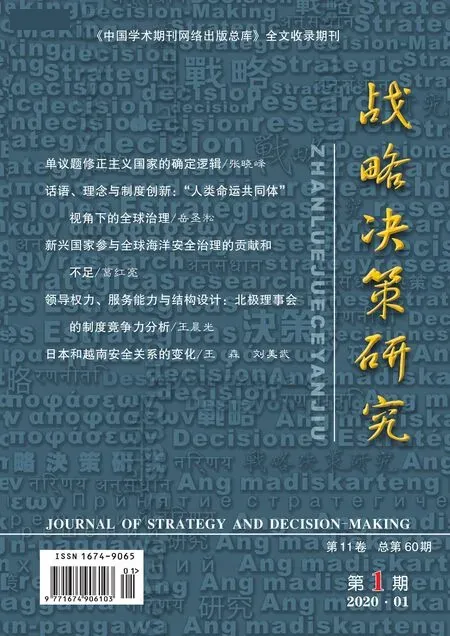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贡献和不足
2020-12-02葛红亮
葛红亮
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治理相似,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也偏向多元化,包括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传统海上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①在当代学术研究中,“新兴国家”并没有具体的界定范畴,因而也不存在一个严格的学术语境。实际上,这也为我们广泛定义新兴国家提供了可能。由于研究需要,笔者在文中对“新兴国家”的界定是相对于传统的海洋霸权国家而言,主要是指新兴海洋国家。因而主要选取了两个重要因素,一则在二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二则国家海洋意识的觉醒较晚。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新兴海洋公家日益增多,例如中国、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等。海洋安全治理是全球海洋治理最突出的内容。随着安全概念外延的不断拓展,海洋安全治理涉及的具体内容逐渐增多,既包括传统海上传统安全,也包括海上非传统安全挑战。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全球海洋安全问题与危机不断凸显,在原有海洋传统安全问题未获解决的情况下,海洋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多,海盗、海上武装抢劫、海上恐怖主义袭击及海洋生态危机等频现。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需要各国集体行动与加强合作相悖的是全球范围内治理主体的不均衡发展,而这则源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呈现出两个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现象:一方面,全球化催生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却也催生出传统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分野,它们的合作与分歧如今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关键,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可持续发展。②Thematic Think Piece,OHCHR,OHRLLS,UNDESA,UNEP,UNFPA,Global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commons in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beyond 2015,UDA,Jan.2013,pp.3-5.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也不可能例外。关于全球海洋安全的治理,传统国家与新兴国家的观念并不一致,因而它们在治理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面临的海洋安全环境及自身所处的地位有所差异,新兴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有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与路径依赖。在海洋意识不断觉醒的牵引下,它们对海洋治理领域的权力意识也不断加强,在日益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一条独特的制度性权力构建路径。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在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过程中,新兴国家的理念是什么?它们发挥了什么作用?做出了哪些贡献?
针对新兴国家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的参与和角色,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也给予了关注。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国别的角度来分析新兴国家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的参与及它们维护海上安全的努力。③龚晓辉:《马来西亚南海安全政策初探》,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59-66页;葛红亮:《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观念基础与方法论》,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4期,第56-65页;楼春豪:《战略认知转变与莫迪政府的海洋安全战略》,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98-131页;Tran Truong Thuy,Vietnam’s Maritim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in Security Outlook of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fense Sector,Tokyo: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2014,pp.85-100。同时,也有学者从国际组织层面,针对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探索这些由新兴国家构成的地区组织在海洋安全治理方面的参与。④刘若楠:《应对南海危机:东盟“自我修复”的措施及限度》,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4期,第25-53页;贺鉴:王璐:《海上安全: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新领域?》,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69-79页;David Michel&Russell Sticklor,Indian Ocean Rising:Maritime Security and Policy Challenges,Challenges ,stimson,2012,https://www.stimson.org/content/indian-ocean-rising-maritimesecurity-and-policy-challenges。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研究路径上展现出了差异。有些学者倾向于机制和规范的路径来分析印度尼西亚对南海安全治理的参与,⑤李峰、郑先武:《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第52-61页。有些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马来西亚、印尼等新兴国家在海上安全治理中的“大国平衡”战略。⑥苏莹莹:《马来西亚务实南海政策及其新变化》,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第89-104页;鞠海龙:《印度尼西亚海上安全政策及其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3期,第25-36页。由此来看,目前还少有研究者将视角聚焦于新兴国家这个群体及观察它们在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的共同表现。本文中尝试从整体层面探讨新兴国家对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参与及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共有特征。
一、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的环境与观念
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是史无前例的,而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面临的全球海洋政治环境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往,全球海洋国际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传统海上列强间围绕海洋要道控制、海上力量角逐与海洋霸权竞争及海外殖民地争夺。与以往不同,当今全球海洋国际政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广大新兴国家的兴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这恰恰构成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国际政治博弈与海洋安全治理的大环境。
“海洋世纪”最首要的特征便是海洋重要性的凸显。海洋重要性的凸显集中彰显在两个层面:一是海洋成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二是海洋是国家间往来与联系的纽带。受此影响,海洋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新高地。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步伐加快,海洋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关注的焦点。⑧张文木:《“海上丝绸之路”西太平洋航线的安全保障、关键环节与力量配置》,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88页。与此同时,随着陆地资源开发趋紧及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增多,对海洋的系统性研究与合作开发已经迫在眉睫且具有显著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无疑,这将加剧世界各国,特别是沿海国家,在海洋资源及其他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博弈与争夺。
中国等新兴国家越来越将海洋视为发展新高地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新兴国家海洋意识的普遍觉醒,而这也是当今海洋国际政治呈现出的第二个重要特点。与传统的发达国家不同,新兴国家的海洋意识觉醒较晚,对海洋的大规模利用或战略性运用普遍不足。然而,随着新兴国家融入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与世界关系的紧密程度不断增强,在这一过程中,海洋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而这促使新兴发展中国家重新认识海洋与重新审视海洋在其对外交往过程中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海洋意识普遍觉醒。随着新兴国家大规模的海上觉醒,现有国际海洋政治的秩序安排正面临着深刻挑战。在这一方面,由于新兴国家的数量与规模最为显著,亚太海域众多沿海国家海洋意识觉醒最为突出,而这正在深刻作用于地区现有的海上力量格局与秩序。对此,作为主要新兴国家之一的印度,有着深刻认识。在一份名为《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外交与战略》报告中,印度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在亚太海域的大规模军力部署、日本在海上力量发展方面的日渐活跃和强势、中国海上力量的后来居上及亚太地区其他沿海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海上力量建设的发展,亚太海域既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又成为众多中小国家在亚太事务中谋求地位与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力场。⑨Sunil Khilnani,Rajiv Kumar,Pratap Bhanu Mehta,Lt.Gen.Prakash Menon,etc,Non-Alignment 2.0: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Printed in India,2012,pp.12-13.不仅如此,海洋意识的普遍觉醒也构成了广泛存在的海洋领土争端与权益纠纷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前述因素的影响下,新兴国家在实现海洋安全与参与海洋安全治理方面面临着的任务既紧迫,又繁重多样。一方面,海洋安全日益成为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安全、边海疆安全与战略安全的重要构成因素。这就意味着重视海洋安全应该构成新兴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题中之义。而从内容上来看,海上安全包括海上传统安全与海上非传统安全两个部分。这使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时要承担的任务是多样的。它既包括保护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捍卫正当合理的海洋权益与展开海洋安全外交,还包括实现海洋生态安全与应对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同时,现今的全球海洋政治形势与海洋的“公域”性质也揭示了新兴国家实现海洋安全与开展海洋安全治理必须经由一条有别于以往海上争霸与海上强权博弈的道路,在“海上舞台”上保持良性竞争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在海洋安全治理方面展开合作。也就是说,如今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进程中倾向于持有综合的、共同的、合作的安全观。这一海洋安全治理观念在指导新兴国家进行海洋安全治理制度设计的同时,也影响着这些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
二、新兴国家参与海洋问题治理的制度偏好
在海洋安全治理层面,新兴国家由于海洋意识兴起不久,总体上来说还相对薄弱,总体上落后于传统的发达国家,而在内容上,新兴国家对海洋安全治理的关注比较晚、投入也相对比较少。因而,新兴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在关注海上安全力量建设的同时,对海洋安全治理的制度建设与规范塑造给予了很大关注。
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对制度与规范的偏好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主要新兴国家独立于二战以后,这些国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海洋权利意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觉醒的背景下,即通过制度与规范的路径来捍卫国家海洋权利与维护海洋安全。其中,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印度尼西亚是当今新兴国家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然而,它的群岛国家身份得到其他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认同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和印尼借由制度层面捍卫自身海洋权利与维护印尼海洋安全的努力是同步的。1957年12月,印度尼西亚处于朱安达·卡塔维查亚(Djuanda Kartawidjaja)内阁时期。以《朱安达宣言》(Djuanda Declaration)的公布为标志,印尼有了最早的涉及海洋的正式制度性文件,而这份宣言的核心即是向国际社会宣示印尼的群岛国家地位。印尼在此时公布这一宣言,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以印尼群岛国家身份的确立来维护印尼的海洋安全;其二,迎合全球海洋权利意识觉醒,在国际海洋秩序确立过程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声音。1958年,国际社会在日内瓦通过了包括《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与《大陆架》公约在内的奠定当时国际海洋制度基础的四个公约。尽管印尼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制度与观点,但由于这一时期国际海洋秩序依旧主要维护的是传统海洋大国的要求与利益,⑩高之国等主编:《国际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印尼依旧不得不为其群岛国家身份的确立及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继续努力。1960年第二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前夕,印尼通过并对外公布了《领水法第4号法令》(Act No.4 of 1960,Indonesian Territorial Waters,1960年2月18日)。明确了印尼12海里的领海宽度与印尼群岛间水域与资源完全的、排他的主权。尽管印尼此举遭到了美英等传统海洋国家的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所谓的“自由航行”,但在第二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印尼依旧坚持自身的观点和反对西方国家主张。不仅如此,印尼还以直线基线的方式确定了印尼的群岛基线及12海里的领海宽度,及在此后进一步要求外国船只通过印尼领海时须事先通报。印尼的制度努力最终在1982年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后实现了预期目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以下简称《公约》)对群岛国、群岛基线及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持有肯定态度。⑪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
根据“左侧变蓝色,一段时间后蓝色逐渐变浅”可判断,左侧铂电极是阳极,右侧电极为阴极。电解过程中阳极上先生成I2,当阴极上OH-迁移到左侧溶液中时,I2分子再跟OH-反应生成IO-3。要注意,由于中间是阴离子交换膜,且右侧溶液中生成大量OH-,所以电解过程中有大量的OH-由右侧定向迁移到左侧,也必定会有少量IO-3会从左侧迁移到右侧溶液中(因为左侧溶液中IO-3浓度大)。很明显,若是用阳离子交换膜代替阴离子交换膜,右侧溶液中OH-就不会大量向
海洋作为纽带将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与传统国家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是它们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博弈。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此时海洋安全治理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国家海洋权利及以此来实现海洋安全。而通过战后数次联合国海洋会议,新兴国家克服了海上安全力量的差距问题,积极参与到全球海洋问题治理中。通过制度性参与,新兴国家与传统国家在海洋方面的利益诉求总体上得到了平衡,而新兴国家在推动制度构建方面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当代国际海洋制度纲领性文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形成便是在新兴国家藉由制度来参与和积极推动的结果。⑫赵隆:《海洋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反向建构过程》,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40页。受此影响,新兴国家对持续参与全球海洋问题治理逐步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制度偏好。
三、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的制度设计
新兴国家能够藉由制度参与来维护自身的海洋权利,在根本上得益于全球海洋问题治理领域主权平等原则的确立。⑬沈雅梅:《当代海洋外交论析》,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4期,第42页。在这一原则下,新兴国家与传统海洋国家在全球海洋制度设计中拥有同等的地位,新兴国家不但同样获得了领海、毗连区和大陆架,而且还获得了持续参与全球海洋问题治理的平等权力。不仅如此,随着冷战后全球化与地区化的深入发展,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在这一背景下,新兴国家在海洋安全问题治理层面进行制度设计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过程中,集团外交就是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倚重的重要方式。而在冷战之后,在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过程中,地区内一系列多边机制则构成了这些国家进行制度设计的平台。
作为新兴国家参与的重要地区组织,东盟在海上安全治理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东南亚地区印尼等在内的新兴国家认为,“海上安全问题与关切”在性质上属跨境问题,因而在地区内寻求多边协商应对或在东盟框架下实现地区性方式来解决是比较理想的应对方式。⑭鲁道夫·塞维利诺著,王玉主等译:《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前任秘书长的洞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因而,在东盟的框架下,在地区内寻求多边协同应对地区的海上安全问题成为地区内海洋安全问题处理的重要规范,而海上安全问题也构成了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的重要一项内容,与东盟主导下的规范的重塑与分享密切相关。2003年,东盟以《巴厘第二协商一致宣言》为标志步入了构建“共同体”的新阶段,而这一宣言的第二个领域便是海上安全。在宣言中,东盟国家认为海上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和东盟国家在海上安全议题上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东盟国家就海洋安全议题展开合作应成为建设“东盟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量。⑮See ASEAN,2003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Adopted by the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at the 9thASEAN Summit in Bali,Indonesia,October 7,2003,https://asean.org/?static_post=declaration-of-asean-concord-ii-bali-concord-ii.此后,在东盟主导下的会议文件中,关于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地区海上和平与确保航行自由的规范一再出现。例如,针对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出现的海上争端及有可能带来的海上威胁,东盟的态度十分明确,即将这些议题作为“冲突预防”的重要内容,而建立冲突预防机制则成为东盟处理海上安全议题的重要规范与政策选择。⑯ASEAN,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Plan of Action,Vientiane,Laos,November 29,2004,https://asean.org/?static_post=asean-security-community-plan-of-action.
除了规范的塑造以外,东盟还十分强调海上安全问题规范的传播与分享。在成员国之间,东盟藉由东盟峰会、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实现这些规范的传播与内化。而在东盟与其他国家之间,例如中国、美国、印度等,东盟除了在双边渠道传播规范与制度,还通过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东盟+3”会议与“东盟+8”防长会议等多边场合,宣导东盟在处理海上安全议题层面的制度与规范。东盟是多边框架的“驾驶员”,其“中心性”地位的确立与维持有助于东盟在地区海上安全问题协商应对的相关规范得到其他大国尊重。因此,类似于东盟这样的新兴国家集团,它在参与海上安全治理过程中进行制度设计是基于规范的塑造及其传播、分享与学习达成的。
与传统海洋国家不同,新兴国家面对的海上安全问题要多一些,它们必须对海洋争端、纠纷及各种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予充分关注。因而,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它们在海上安全治理方面的制度设计在内容上既包括传统的海上争端、海上力量,又包括大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海上争端层面,东盟倡导的预防性机制在南海议题上得到了应用,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则是东盟国家和中国就海上争端解决和避免对地区局势产生紧张态势进行制度设计的结果。而在海上力量方面面,近年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海上安全力量的兴起,这些国家在海上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设计方面也开始有所建树。正是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2014年中国等新兴国家与美国等传统海洋国家一同达成了“海上以外相遇规则”。而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努力下,这一规则正在南海与东南亚海域得到落实。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海盗、海上跨国犯罪、海上环境污染、海上救助等则成为新兴国家进行制度设计的主要针对对象。《关于应对自然灾害的互相救助宣言》、《组织和控制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的东盟地区政策和战略》、《关于反海盗合作及其他海上安全协议的声明》与《东盟反恐公约》等规范与制度的确立表明,东盟国家在应对和参与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制度性成就。
在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激励下,新兴国家在海上安全治理层进行了积极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与规范的确立、重塑与分享构成了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制度化路径的主要步骤。新兴国家在海洋安全治理层面的制度设计,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了这些国家在参与海洋安全治理过程中获得制度性权力的根源。同时,这实际上也是新兴国家开展海洋安全治理实践的出发点。
四、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的实践及其不足
如今,新兴国家给予海洋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并由制度设计途径逐渐成为当前海洋安全治理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新兴国家还将海洋安全治理的制度参与和海上治理力量提升、海上安全合作密切结合起来。由此,新兴国家海洋安全治理在应对海上安全问题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
新兴国家海上安全治理的实践基于制度,但却实际上始自海上安全治理力量的重构与加强。新兴国家海上安全治理力量的发展与加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新兴国家在过往加强了对涉海部门的重构与统筹。同样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涉海部门的整合与统筹是新兴国家海上综合治理部门统筹协调的缩影。印尼曾在2005年就成立了海上安全协调委员会(Maritime Security Coordinating Board),重组海军、警察、交通与海关等涉海安全部门,加强海上执法和维护海上安全。在2014年佐科政府提出“海洋轴心”战略之后,海洋意识的再度加强促使佐科政府持续重构涉海部门。作为结果,海事统筹部设立。该部是佐科内阁的新设部门,统筹海事及渔业部、旅游部、交通部、能源及矿业部四个部门;主管兴建码头、建造船只、发展国内外海运、开发岛屿成为旅游区、加强海域边界的防御、开发海上油矿等与海洋有关的事务,并协助渔业发展,而与外交部、国防部也存在职能交叉。由此来看,由于涉海安全的综合性,改变涉海部门的多头管理是新兴国家加强涉海部门重构的方向,而相比印尼海上安全协调委员会,海事统筹部则承担着海洋经济发展与海上安全建设等多重职能,成为印尼实现海洋强国和加强海洋安全治理的最重要驱动力量。
同时,海上安全力量的建设与增强是新兴国家参与海上安全治理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与基础,而加强海空力量建设则构成了新兴国家推进海上安全力量增强的着力点。以东南亚地区的新兴国家为例,海空军力量建设与发展得到了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重视。然而,由于大多数新兴国家在技术层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海空力量发展方面受到了传统国家显著的战略牵引。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地区国家的军事援助,2015年美国投入了多达1.19亿美元帮助发展东南亚国家的海上能力,2016年则增加到1.4亿美元。而在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最具代表。⑰《外电: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调高至7900万美元》,载《参考消息》2015年11月26日。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海洋安全治理实践与海洋外交的开展是同步的。海洋外交在内容上主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缔结海洋条约与协定;其二是参与地区与国际海洋事务;其三是推进海洋军事外交;其四是和平解决海洋权益争端。⑱沈雅梅:《当代海洋外交论析》,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4期,第42页。实际上,这四个层面也构成了新兴国家直接参与海洋安全治理的主要方式。
针对海洋安全问题缔结海洋协定是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最为惯用的方式。印尼、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周边海域是当前东南亚海盗的重灾区,也是全球海盗袭击与抢劫事件最频发的海域。近些年,东南亚海域的海盗或武装抢劫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东南亚海域依旧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海盗多发区域。以2015年第一季度为例,全世界发生了54起海盗事件,而东南亚水域发生的海盗事件占比为55%,超过总数的一半。⑲《国际海事局:东南亚地区成为海盗事件新热点》,中新网,2015年4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4-22/7225187.shtml对此,印尼、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等新兴国家的有着相同的威胁感知。因而,印尼等四国早在2008年就在曼谷签署了《海上和空中巡逻合作协议》,而四个国家在海上安全治理方面的积极协调虽然并未彻底根除海盗等威胁,但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积极作用。
参与地区与国际海洋事务,特别是海洋安全事务,也有助于新兴国家参与海上安全治理。作为其中的典型,2004年印度洋海啸与2008年以来的亚丁湾巡航则一再体现了新兴国家在海洋安全治理层面的作用。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向受灾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在彼时被称为中国最大规模对外救援工作,而此次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印度洋海上安全治理的体现。针对索马里海盗的海洋安全治理迄今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参加海洋安全治理最重要的缩影。2008年以来,在索马里政府的请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在相继通过了1861、1838、1846、1851、1950号多个专项决议,授权有能力的国家、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⑳陈志瑞、吴文成:《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7页。随后,包括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内,多个国家向亚丁湾海域派遣了护航舰队,而中国在其中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构成了这一海域安全问题治理与形势好转的一支中坚力量。
通过双边、多边海上军事安全交流、演习与合作是新兴国家常见的对外军事外交活动,而这一过程对海洋安全治理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印尼作为新兴海洋国家,其“海洋轴心”战略的根源在于作为“两大洲和两大洋之间的国家”的定位。因而,将印尼在地理作为两大洲和两大洋中心、枢纽的战略位置转化为地缘上的“海洋轴心”成为印尼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强双边和多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事所难免。一方面,印尼相当重视加强海洋强国的地区与国际环境建设,在积极发展与中、美、日等国家海上合作关系中实现大国的“动态性平衡”。另外,印尼还十分注重东盟和环印度洋组织(IORA)等多边机制的作用。佐科政府不仅积极参与东盟主导下的地区多边海上军事交流,还积极借助2015年-2017年印尼担任环印度洋组织(IORA)主席国的机遇来推动印尼与印度洋国家之间全方位的海洋合作。
海洋争端长久未决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也是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亚太地区海洋争端及其在大国角逐中有着非常凸显的地位,例如南海议题,包括中国、印尼在内的新兴国家在就这些议题深入开展海洋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传统大国的挑战。而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兴国家在这一层面海洋安全治理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传统海洋国家惯于用“航行自由”与“公海治理”来介入地区国家海洋争端与地区海洋安全治理,进而对新兴国家在区域内开展海洋安全治理形成干扰。
综上来看,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既需要在自身治理力量方面着手,还需要处理好由于海洋权益争端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兴国家的海上安全治理力量建设与海洋安全治理实践进程始终面临传统海洋国家的战略牵制。不仅如此,由于传统海洋国家的干扰及新兴国家对海上安全威胁感知程度的不一致,新兴国家尽管在制度层面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尚不能完全达到地区、全球层面海上安全问题治理的需要,而它们需要在海上安全治理能力建设与协作方面多做努力。
五、结论
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新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的传统在当今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获得一部分制度性权力,另一方面也竭力在发展海上安全治理力量与开展治理实践层面作出努力及加强合作。虽然如此,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方面依旧受制于传统国家。虽然有西方学者在审视亚太海洋竞争时强调,中国、美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竞争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开展海洋合作。㉑Andrew S.Erickson,Can China Become a Maritime Power?,in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Holmes,edited,Asia Looks Seaward:Power and Maritime Strategy,London,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7,p.108.但地区海洋安全的形势现况却一再表明,传统海洋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依旧处于主导地位,而传统国家对新兴国家参与海上安全治理的战略牵引也是显著的。这无疑是新兴国家参与海洋安全治理进程中面临的最突出难题。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其已经明确就海洋安全问题的治理表达过看法。2014年6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希腊出席“中希海洋合作论坛”时发表了主题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强调了三点:其一是共同建设和平之海,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其二是共同建设合作之海,持续扩大国家海洋合作;其三是共同建设和谐之海,既强调国家之间的和谐与兼容并包,更强调人类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㉒李克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6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21/c_126651068.htm归结来看,中国针对海洋安全治理的主要原则包括:一是,海洋安全治理的目标在于实现和平海洋,其基础是公平海洋秩序的构建;二是,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三是,强调海洋安全治理的和谐内涵,海上安全治理主体之间要实现和谐及理顺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基于此,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在海洋安全治理过程中在制度、力量与关系建设方面还有不少需要克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