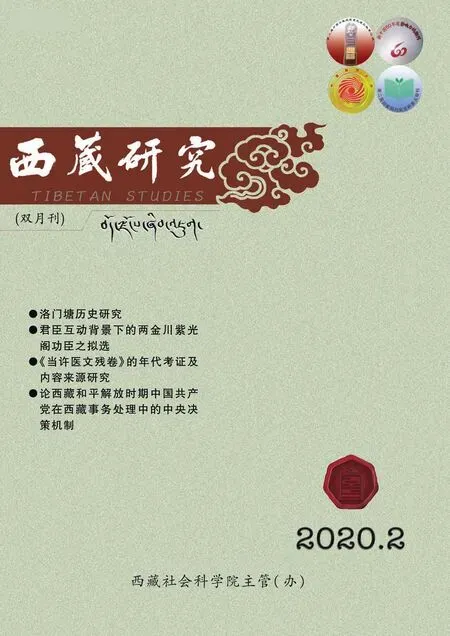《西藏图说》成书背景与文献价值考论
2020-12-02柳森
柳森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北京100081)
一、引言
《西藏图说》是驻藏大臣松筠在三次巡视西藏边防过程中实地绘制而成的西藏舆图集,亦是清代西藏方志中价值较高的一部图志。该书图文并茂,作者以中国古法绘制西藏舆图16幅,首为西藏总图1幅,后为以作者巡边行进路线所涉地域为限的15幅分图,每幅舆图之后均附以文字说明,简论图中所涉地域的山川形势、气候寒暖、经行要隘、管辖区域、道里路程等情况,其不仅是清代驻藏官兵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是清代边疆地理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现存版本中,嘉庆道光间《松筠丛书五种》本与嘉庆道光间《镇抚事宜》本均将《西藏图说》列为独立一种。不过,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刻本《西招图略》,其中,《西藏图说》却是《西招图略》的一部分。实际上,嘉庆三年(1797年)松筠在《西招图略》“序”中写道:“而图治者,宜防未然。因书二十有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其方舆,名之曰‘西招图略’。”①参见(清)松筠:《西招图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刻本。同时,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重刻西招图略序》曰:“湘圃相国特膺兹任,上体天子之恩,下悉卫藏之情,着有《西招图略》一书,分为二十八条,绘以‘图说’,于山川、形势、番汉、兵卡,令人开卷了然。”②参见(清)松筠:《西招图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刻本。另,松筠在《绥服纪略》篇末写道:“余自乾隆五十九年,蒙恩升授工部尚书、驻藏大臣,至嘉庆四年更换回京,在彼五载,所办事宜略见《纪行诗》《秋阅吟》暨《西招图略》。”③参见(清)松筠:《绥服纪略》,清嘉庆道光间刻《松筠丛书五种》本。可见其自述亦并未提及《西藏图说》。由此可知,松筠《西藏图说》应是其《西招图略》的一个原始组成部分,只是书贾等后人在刊印过程中拆分单刻成书而已。当然,因目前所见该书各版本图文内容相同,因此,并不影响深入探究《西藏图说》的成书背景与文献价值。
二、成书背景
松筠(1752—1835年),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乾隆十七年壬申二月二十六日亥时生,布勒噶齐太夫人出。”①(清)佚名:《松文清公升官录》,清朱格抄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翻译生员考补理藩院笔帖式,四十一年(1776年)充军机章京,四十八年(1783年)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五十年(1785年)任库伦办事大臣,由此开始其疆臣生涯。其累官户部银库员外郎、户部侍郎、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吉林将军、工部尚书兼都统、驻藏大臣、户部尚书、陕甘总督、湖广总督、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内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察哈尔都统、绥远城将军、正白旗汉军都统、礼部尚书、盛京将军、山海关副都统、左都御史、热河都统、兵部尚书、直隶总督、理藩院侍郎、正蓝旗蒙古都统等。晚年,因直言进谏而屡遭贬斥。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都统衔休致,逾年卒,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松筠虽为蒙古族,却好程朱理学,以汉文著《品节录》《西藏巡边记》《西招纪行诗》《西招图略》《丁巳秋阅吟》《绥服记略》《新疆识略》《伊犁总统事略》《松筠新疆奏稿》等,并参编《卫藏通志》。值得一提的是,松筠还以满文撰写了旨在规范旗人品行的《百二老人语录》,此世俗作品在现存清代满文古籍中弥足珍贵。
松筠任封疆大吏长达40余年,其中,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四年(1794—1799年)任驻藏大臣。松筠在藏期间,正值廓尔喀之役后西藏地方社会重建期,其认真执行清中央政府出台的《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留心藏政,豁免粮赋,捐银恤贫,重视边防,由此形成了个人“筹藏观”,同时,其躬身巡边,重视地理,留心记录,勤于著述,故而撰成《西藏图说》。松筠在《西藏图说》开篇“西藏总图”之后即明确指出:“绘为此图者,就巡阅之所经,识山川之阨要,特俾驻藏汉番官兵熟其形势。”可见,《西藏图说》即松筠三次巡阅边防的直接产物。因松筠三次巡边时间为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嘉庆二年(1797年)秋、嘉庆三年(1798年)春,因此,《西藏图说》资料收集整理应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1795—1798年)之间,而成书时间为嘉庆三年(1798年)。以此为时间节点,结合其时西藏地方社会形势,松筠的“筹藏观”与著述旨趣,笔者分析其成书背景如下:
(一)战后西藏地方社会重建是《西藏图说》成书的时代背景
松筠驻藏期间正值廓尔喀之役后西藏地方社会重建期。当时,适逢廓尔喀战祸戡平不久,西藏地方疮痍遍地,加之此前苛捐杂税较多,广大民众生活极端困苦,并出现土地荒芜、牲畜死亡、房屋坍塌等不利情况,由此,西藏地方的战后善后与社会重建刻不容缓。对此,乾隆帝认为:“此系极好机会,皆赖上天所赐,福康安等当趁此将藏中积习湔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方为妥善。”②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417,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辛亥条,清刻本。因此,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中央政府正式颁布了以《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计划,逐步开始在西藏地方实行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改革,内容涉及提高驻藏大臣地位,约束僧俗贵族,管控活佛转世,同时,体恤百姓生活,建立正规藏军,维护中国西南边防安全等,旨在达到既恢复西藏地方社会生产,又强化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管辖的治理目标。
松筠入藏的主要任务即推进落实《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以期尽快实现西藏地方的社会重建与政通人和。值得注意的是,善后章程明确规定在西藏地方建立驻藏大臣巡边检查制度。据《清实录》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驻藏大臣和琳等奏,前经奏准,每年春、秋二季,驻藏大臣分往各边界巡阅,第卫藏地方较冷,三、四月间播种,八、九月间收获,凡巡阅之期,正值番民农忙,需用乌拉人夫,殊多不便,请嗣后驻藏大臣每年五、六月农隙时,阅边看兵一次。得旨:是,知道了。”①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454,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庚午,清刻本。由此,既不耽误西藏地方农业生产,又保证驻藏大臣巡边检查制度的顺利施行。同时,驻藏大臣定期巡边的最终目的,正是为西藏地方社会重建在军事安全方面保驾护航。在此制度基础上,松筠在此次西藏地方社会重建期之内,不仅做好了驻藏大臣在经济、政治、行政方面的重要工作,而且切实履行了定期巡视西藏边防的重要任务,为保证西藏地方边防安全亲力亲为,而此巡边过程正是其《西藏图说》的资料收集与舆图初绘过程。
(二)松筠的“筹藏观”是《西藏图说》成书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与边疆发展史上,边臣疆吏是一个特殊群体,其个人政治素养与筹边观念往往对其所在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庄吉发先生认为:“处于同一个时代及社会关系中,边臣疆吏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边臣疆吏的个性倾向。有的边臣疆吏忧患意识浓厚,而献身于遐方绝域;有的边臣疆吏任性乖张,而纵酒于朔漠异域;有的边臣疆吏粉饰太平,而苟安于祟岭秘境。”[1]显然,松筠属于其中第一种,其在驻藏大臣任内不仅恪尽职守,而且锐意进取,为西藏地方社会重建献计献策,对西藏边防安全亦忧患有加。由此,松筠在治藏过程中形成了以社会民生建设与巩固边防安全并举为核心的“筹藏观”,而实地探察西藏地方边防并绘制详细舆图,正是其“筹藏观”的实践成果之一。松筠注重边防的筹藏观念,完整地体现在其《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巡边记》与《西招图略》中。对此,松筠自言:“是武备不可不修,操防不可不讲,爰绘散总之图,俾知舆地之险,固我疆隅,化彼觊觎,其率服即叙,莫不畏怀,而乐享升平矣。”②参见(清)松筠:《西招图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刻本。可见,松筠将巩固边防安全视为社会民生建设的重要外部保障。
一方面,松筠十分注重恢复西藏民生。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松筠针对当时西藏地方的差役与赋税制度等进行了必要调整,举措涉及减免赋税债务与差役负担,休养生息;赈济百姓,帮扶民众恢复生产;限制使用乌拉,有偿支付雇费;严禁霸占水渠农田和乘机敲诈勒索等。通过其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西藏地方民众负担得以减轻,生活逐步改善,同时,西藏地方社会秩序愈发安定,农牧业生产亦开始步入正轨。
另一方面,松筠重视守边,其《西招图略》开篇即《守边》,同时,其认为“图为备边而设”,即其非常重视舆图在西藏边防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这是《西藏图说》成书的直接原因。松筠第一次巡阅西藏边防,主要是为了抚恤西藏边远地区的民众以安定民生,第二次则是检查赈灾效果,第三次乃巡视后藏边防并操演兵丁。对此,松筠在《丁巳秋阅吟序》中写道:“乾隆乙卯岁,高宗纯皇帝发帑金四万两赈恤卫藏番民,恩至渥也。余照例巡阅,周览边城,敬布皇仁。凡所经行,既着篇什。洎丁巳之秋,又因稽核赈务,重阅招西,见民气之已苏,钦圣慈之广被。”③参见(清)松筠:《绥服纪略》,清嘉庆道光间刻《松筠丛书五种》本。由此,松筠在视察边地、检阅军队过程中,十分注意调查西藏边境地区的山川险胜,随时记录,最终绘成舆图。
在第一次巡边过程中,松筠即已认识到地理与舆图对西藏边防的重要性。据《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巡边记》载:“至协噶尔、定日左首之绒辖、喀达,定结西路之宗喀、琼噶尔、巩塘拉大山,皆为天然门户,曲水、巴则、江孜又为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哩、甘坝等处,界连藏曲大河,尤为前后藏第一险要,所有汉番官兵及噶布等,均宜熟悉。因于前后藏、江孜教场泐石,咸使对图讲求,人各胸中有主,方于汛防有益。”④参见(清)佚名纂修:《卫藏通志》卷4,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刻》本。可见,松筠下令将西藏地形图刻石为碑,以使江孜等地驻防官兵对西藏地形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利于巩固边防。在第二次巡边过程中,松筠作诗《过洋阿拉山》云:“惜未塞归路,网疏逸野豻(彼时,官兵初至,未谙舆图,如果预由甲错山阳分兵,经波绒巴游牧绕至羊阿拉及莽噶布堆登处,邀击之,可使片甲不归,并免辛亥之大役也)。巡边知扼要,特笔未容删。”①参见(清)松筠:《绥服纪略》,清嘉庆道光间刻《松筠丛书五种》本。可见,松筠十分重视舆图在边防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其认为廓尔喀商人到西藏边境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均比较熟悉西藏道里远近情况,而如果西藏官兵对西藏地理交通的基本情况不甚了解,则不免会重蹈廓尔喀之役覆辙。对此,其在《西招图略·审隘》中总结道:“守边之术,宜乎审隘绘图,使各汛官兵熟悉道里厄塞,方于缓急有益……此卫藏围圆大概,仅述要隘,绘图以示汛官,以重操防也。”②参见(清)松筠:《绥服纪略》,清嘉庆道光间刻《松筠丛书五种》本。
(三)松筠勤于著述是《西藏图说》成书的主观原因
由松筠生平可知,其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不仅注重修身存养,而且重视现世事功,因此,其不断强化自身文学修养,在所任之处尽量留存文史作品,其目的在于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松筠在《西招图略·述事》中写道:“夫处一方,宜悉一方故事,述而书之,便览焉……钦差善言,提撕警省也。”③参见(清)松筠:《西招图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刻本。可见,松筠将用心记录任内所处西藏地方情形,为继任者及相关人士提供参考和警示,视为驻藏大臣的重要职责。由此,《西藏图说》即松筠重视“述事”、勤于著述的重要成果。
据《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巡边记》载:“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边自前藏经曲水,过巴则、江孜,其十日行抵后藏,由札什伦布走冈坚寺、彭错岭、拉孜、罗罗胁噶尔,过定日、通拉大山,共计十一日,至聂拉木,又由达尔结岭西转,经过白孜草地、巩塘拉大山、琼噶尔寺南转,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济咙,仍旋宗喀,东北行十日,还至拉孜,入东山一日,至萨迦沟庙,自庙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冈坚,还至札什伦布,往复略地,随在绘图,知其概焉。”④参见(清)佚名纂修:《卫藏通志》卷4,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刻》本。此中“往复略地,随在绘图”即指明了松筠《西藏图说》的成书过程。此外,嘉庆三年(1798年)六月底,松筠将本年四月十九日起赴后藏西南边界巡边练兵情形奏报:“所有近年查看之所有关隘,奴才已分晰绘图,分发卫藏官兵,使之熟悉各地形式,悟其攻守之道,方可谓武备精强。并将此与相继遵旨办理事件一同列入交代事项,务使后任谨守勿怠。”[2]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图说》是驻藏大臣松筠亲身经历并独立撰写之作,这在清代西藏方志中并不多见。不同于《藏纪概》《西藏记述》《西域全书》《西藏志》《西域遗闻》《西藏见闻录》等之前成书的清代西藏方志,同时也有别于其后成书的《西藏图考》《西藏新志》等,以上作品多为作者参考官方档册、前人作品、间接转述而成,均属依靠二手材料纂修而成,即使在同为驻藏大臣和宁所作《西藏赋》中,源自亲身采访所得资料也不多,而松筠的《西藏图说》完全来源于其个人巡阅西藏边防的实践经历,对于一名封疆大吏来讲,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文献价值
《西藏图说》开篇为1幅西藏总图,标明西藏四至、主要程站及布鲁克巴、哲孟雄、噶哩噶达、阳布等相邻地区。15幅分图是:1.东起聂拉木西起济咙南抵阳布止;2.西藏极边之界(西南起济咙东北行由邦馨衮达宗喀至巩塘拉山琼噶尔寺);3.定日至喀达、窝朗卡桑木寺至绒辖、笃举山口至叠古芦;4.宗喀经萨喀至阿里;5.定日四至;6.喀达至阳布;7.拉孜至札什伦布;8.江孜以南边界;9.后藏至前藏;10.布达拉以北;11.前藏至拉里;12.拉里至昌都;13.察木多至巴塘;14.巴塘至理塘;15.理塘至打箭炉。
同时,在文字说明中,松筠提纲挈领地指出该书侧重点在于:西藏的西、南、北三个方位的舆图,即“驻藏汉番官兵熟其形势,故分图于西、南、北三面为稍详。至于东抵鱼通,此六千余里中,向化者百数十余年,与隶版图供赋役者,毫无以异,则但记其道里程站,而余悉在所略焉。”因此,15幅分图以西、南、北三面重点,而因东面川边藏区久已向化中原,内地官员尤其是川边藏区官员较为熟悉,因此,书中仅略述其道里、程站情况。最后,在分图之后附录两篇“程站”,分别是:自成都至后藏路程、前藏至西宁路程。详览该书,可知其文献价值如下:
(一)该书所载西藏舆图基本确定了清中央政府治下中国西藏的疆域,对于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廓尔喀之役之前,因对准噶尔势力的忌惮,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北部防务重视有加,却对西藏后藏及西南边界知之甚少。有学者指出:“因此,在清前期藏学文献中,记西藏北方各地关隘、边界,以及从拉萨到北方边界的路程,成为大多数文献的关注点,但对后藏的情况几乎很少涉及。”[3]但是,《西藏图说》则以舆图形式将西藏西南部及南部等边界情况如实记录。民国初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中国西藏的达旺地区划入英属印度势力范围,事实上,松筠在《西藏图说》“图九(后藏至前藏图)”中明确标明:达旺位于我国西藏与布鲁克巴界北部的西藏版图范围内,同时在文字说明部分明确指出:“由布达拉东渡江至东德庆,转而南至乃东,又分为二:一稍西行,有琼结、质谷、多宗等处,一稍东行,有雅堆、至结纶孜、错纳、达旺抵布鲁克巴界,皆藏中所谓山南处所也。”由松筠记载可知,达旺地区自古即属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著名学者冯明珠评价松筠著述《西招五种》的意义之一为:“勾勒出清朝的西藏范围,确定了西藏的版图,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力争藏域的依据。”[4]显然,这一评价是符合史实的。
(二)该书所载西藏舆图将其时清中央政府尤其是满蒙贵族与封疆大吏,对南亚次大陆国家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势力所辖区域的位置认知以图像形式固定下来。廓尔喀之役改变了喜马拉雅山地区诸国的政治格局,而中国西南边疆安全也由此暂时性地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其中,印度、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地理信息,开始在清中央政府的官方舆地认知中逐渐浮现。
松筠在《西藏图说》之“西藏总图”中西南部边界部分,清晰标注了“噶哩噶达”“东甲噶尔(即阿咱喇)”,并在图八(江孜以南边界)中亦明确标注了“噶哩噶达(西洋部落)”“东甲噶尔(即阿咱喇)”。其中,“噶哩噶达”即其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印度总督官邸所在地加尔各答,“甲噶尔”则系藏文髗Bb(印度)的汉语音译,而“东甲噶尔”即指东印度。实际上,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中央政府对于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的认知,主要来自福康安、和琳等涉藏及驻藏大臣的相关奏折,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不断变化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芜杂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曰,和琳奏接到拉特纳巴都尔禀称,遵奉来谕,各守境土,和睦邻封,并以噶哩噶达及拉卡纳窝各处部落听闻廓尔喀投顺天朝,俱差人至阳布贺喜,递送礼物……又据奏,噶哩噶达部长系第哩巴所属部落,巴尔底萨杂哩又系噶哩噶达所属小头人,其护送象马、蒙赏物件,已属从优,若更颁与勅旨,似觉稍为过分。”①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429,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丁巳条,清刻本。可见,此中所示“噶哩噶达”仅系一个与廓尔喀类似的位于印度次大陆的小部落,而“巴尔底萨杂哩”则是这个小部落的一名小头人。
同时,福康安在奏折中则称:“噶哩噶达即系披楞部落,为第哩巴察所属,该处自称为噶哩噶达,其别部落人称为披楞……廓尔喀闻知大兵已到前藏,于上年五月间预行差人赴该部落求救,那时我正在官寨值日,闻得该部长果尔那尔向廓尔喀来人告称,唐古忒服属天朝,就是天朝的地方,你们不知分量与唐古忒闹事,就是得罪天朝,我这里的人常在广东作买卖,大皇帝待的恩典很重,我再没有不帮天朝,转帮你们廓尔喀的道理……伏查第哩巴察在甲噶尔各部落中土宇较广,所属最多,噶哩噶达为第哩巴察属部中之大部落,与廓尔喀南界毗连,为边外极边之国。该处番民既在广东贸易,想来即系西洋相近地方。臣福康安、臣孙士毅在粤时未知有噶哩噶达,或系称名偶异,亦未可定。”②参见(清)佚名纂修:《卫藏通志》卷4,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刻》本。由此可知,当时福康安等权臣已向乾隆帝初步言明,噶哩噶达即披楞,而其似乎就是长期以来在广东地区与中国开展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但二者真实关系其又无法最终确认。
实际上,福康安所言“该部长果尔那尔”中的“果尔那尔”,即英文governer(总督)之汉语音译。同时,和琳所言“巴尔底萨杂哩”与福康安所言“第哩巴察(Delhi Pādishāh)”即指“德里的巴底沙”。在波斯语中“巴底沙(Pādishāh)”指代君主,由此,“德里的巴底沙”即指代印度莫卧儿帝国君主,亦可视为莫卧儿帝国之代称,对此,藏文作而驻藏或涉藏官员又将此藏文音译转为汉语音译,写作“第哩巴察”“第里巴叉”“巴尔底萨杂哩”等。可见,这些地理与名称信息均已指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但囿于时代局限与地理知识匮乏,受中华文化中心论影响,加之中西语言文化隔阂,使得曾任两广总督、经略中英广州贸易的福康安,仍对印度、西洋、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出现地理认知混乱。
颇为遗憾的是,与福康安相近,三次巡边的驻藏大臣松筠也对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等地理信息认知含混不清,仍将三者视为一个多重身份重叠的混合体。对于指代印度的“甲噶尔”,松筠认为:“甲噶尔,即大西天。”①参见(清)松筠:《丁巳秋阅吟》,清嘉庆道光间刻《松筠丛书五种》本。同时,松筠在《西招图略·守正》中写道:“闻甲噶尔、第里巴叉等部较比廓尔喀势大……昨岁丁巳,廓尔喀曾为甲噶尔贸易者不似从前常走阳布,而径行噶里噶达及布鲁克巴等部,以致伊部贸迁缺乏,肯乞饬令噶里噶达头人勿使甲噶尔商回经行彼部,仍走阳布,贸易方能有益。因谕以甲噶尔及噶里噶达等一如尔部,且尔与彼本各无辖,今为尔部有益,转饬伊等遵奉,则伊等必以于伊无益,而禀肯转饬尔部遵奉,是则反与尔等不便,莫若尔部与伊等讲和。总之,经过商贩果能薄收其税,则来者必多,可望恒与尔部有益。该使闻之,唯唯而去,旋即奏蒙圣鉴,有案。”②参见(清)松筠:《西招图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刻本。由此可知,松筠与福康安等认知基本相同并与乾隆帝保持一致,仍将“甲噶尔”“噶里噶达”视为与廓尔喀类似的极边部落。不过,松筠将“噶哩噶达”标注为“西洋部落”,这是在对英国、南亚次大陆国家地区认知方面的一大进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松筠将当时清中央政府满蒙高层对印度、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国家与特殊机构的认知情况,以舆图形式如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世了解其时清廷统治者与满蒙权臣的天下观、英国观、朝贡体系观念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该书绘图较为精细,对研究西藏历史地理沿革和其时西藏交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图中均用双框突出标注了当时西藏的塘汛即关卡所在地。在15幅分图中共标注了:定日汛、江达汛、拉甲汛、拉里汛、察木多汛、昂地汛、乍丫汛、江卡汛、巴塘汛、理塘汛、中渡汛、打箭炉等12个塘汛所在地,这是此前涉藏史志中并未提及的,具有显著的创新性,由此,后世可直观了解其时西藏交通的重要节点及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布防情况。其次,附录的“前藏至西宁路程”与其它清代西藏方志所载程途不尽相同,对于后世开展汉藏交通路线问题等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此,黄沛翘将这一程途记载全部转载至其《西藏图考》中并注释为:“以上前藏至西宁路程,惟《西招图略》卷后附录,与《西域志》《卫藏图识》《西藏志》诸书不同,录此参考。”③参见(清)黄沛翘纂修:《西藏图考》卷4,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滇南李培荣刻本。
(四)该书中“说”即文字说明内容均突出边防的重要性,对后世了解和研究西藏地方边防发展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松筠在“图五(定日四达图)”的文字说明中写道:“而萨迦之西南,踰中乌拉山,西至玛布嘉,以合于春堆,为巴勒布等贸易经行之路,而其险要,外则罗哩、果琼拉岩峡联络之屏障,内则甲错大山、拉固隆固阻隘天成,甲错大山多瘴气,孰非重关叠塞耶。”由此可见,松筠经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萨迦至春堆一带边防地位突出,是防范相邻地方势力入侵的天然屏障。同时,在“图六(喀达至阳布)”中,松筠直接在图中“霞乌拉山”上方注明“辛亥年(笔者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遁向经此,冻毙千数百人”“外通廓尔喀界”,并在文字说明中阐明:“路在喀达东南,绕出走三日乃至鄂博界所,稍西有霞乌拉山及两海子,并非正路,仲秋则雪,寒气切肤,而山最险厄。辛亥之役,廓番避正路而经此遁回,冻毙几尽,其不轨之报欤。”这不仅直接说明霞乌拉山及周边湖泊在边境防御中的重要屏障作用,而且也指出廓尔喀之役中廓尔喀军兵败逃的方向与大致路线。此外,这也体现了松筠对这场战争的严正立场,即廓尔喀之役完全是廓尔喀蓄意发动的,而其入侵西藏地方的行为不仅是非法的,更有悖于正义公理,因此,对于廓尔喀军兵遁逃遇难,松筠认为乃“其不轨之报欤”。这对后世还原廓尔喀之役全过程亦具有借鉴意义。
(五)该书的文字说明内容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史料价值,对后世了解和研究其时西藏地方盐业生产及贸易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在“图四(宗喀经萨喀至阿里)”文字说明部分,松筠指出:“由宗喀而北,经达朗拉山、贾贾渡、苏布拉,爰至萨喀。西北行者为盐池,产盐最多,不第为卫藏沿边所资。而南踰济咙边外一带以及廓尔喀以外等部落无不仰赖,唐古忒贩运贸迁为食也。”这一记载不仅明确了当时西藏地方最大盐产地的地理位置,而且也指明了食盐为当时西藏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而廓尔喀侵藏的借口之一便是“西藏运往之食盐掺土”,这表明西藏地方所产食盐对廓尔喀等周边地区十分重要,因此,这也佐证了廓尔喀在食盐进口方面对西藏的依赖,有利于后世进一步探究廓尔喀之役的起因。值得一提的是,对此,松筠在《桑萨》一诗中亦提及:“纾力能余力(能纾民力乃得其力),防微谨细微(萨喀南界落敏汤,外通廓尔喀,其西北界连阿哩境,有盐池,是为边外一带希冀者,此虽细微,不可不谨慎)。”①参见(清)松筠:《丁巳秋阅吟》,清嘉庆道光间刻《松筠丛书五种》本。由此,这两处记载恰好相互印证。
四、结语
在清代历任驻藏大臣中,惟有松筠重视舆图在西藏边防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只有松筠绘制了如此详细的西藏舆图,这些舆图对强化西藏地方边防,保障当时中国西南地区军事安全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原地区官员与民众更加直观地了解西藏地方地理与交通提供了直观参考。该书对后世影响较大,刊刻成书后即在驻藏官员及川边藏区官员中广为流传。《四川通志·西域》(嘉庆)即参考了松筠《西藏图说》,参编者汪仲洋在其诗《以所撰西域志六卷呈松相国得长句一首》中写道:“继于成都书肆中购得相国所著《西招图略》,一图一说,虽万里之外,番程蛮徼无不了如指掌,然后稍知藏卫门径,参涉他说,遂咸卷帙。”②(清)汪仲洋撰:《心知堂诗稿》卷17,清道光七年(1827年)刻本。同时,如前文所言,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任四川成绵道王师道亦觉松筠作品可供公事所参,其在《重刻西招图略跋》中言及:“道光二十有七年,岁在丁未,予时摄成绵道篆,公余之暇,因检《西招图略》旧本,命工重刻。”③参见(清)松筠:《西招图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师道刻本。
清末之际,英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西藏地方步步紧逼,导致西藏地方危机日益加剧,驻藏大臣必须处理十分棘手的涉英问题,同时也引起中原地区广大爱国知识菁英对西藏地方的严切关注。光绪十三年(1887年),总理衙门转奏四川总督刘秉璋、驻藏大臣文硕会奏议办藏印边界通商问事宜,“查该大臣所据《西招图略》绘述藏边情形,系故大学士松筠所著。”[5]可见,松筠所绘西藏舆图已成为其时驻藏大臣的重要参考资料。由此,以黄沛翘《西藏图考》为代表的一系列涉藏方志作品相继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图考》所载十二幅《西招原图》,均转摹自《西藏图说》。黄沛翘对松筠《西藏图说》评价为:“自来西藏专图,无有逾此者。”④参见(清)黄沛翘纂修:《西藏图考》卷首,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滇南李培荣刻本。如今通过纵向比较可知,黄沛翘如此评价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切合实际的。
尽管松筠于公暇完成的《西藏图说》是清代地缘政治学的重要著作,但其毕竟不是专业舆图测绘人士,因此,该书亦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囿于时代局限,乾嘉时期清政府治下中国闭关锁国日趋严重,并未推广康熙时期已引入清廷的西方地理测绘方法和舆图绘制技术,因此,松筠在《西藏图说》中所绘舆图不仅均未使用经纬度线与比例尺,而且并未采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绘法,而仍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写意式绘图方法,这与《卫藏图识》具有相似之处,从而导致书中所载地理位置均失精准。另一方面,该书中所有舆图均方向倒置,即左东右西、上南下北,这导致舆图实用性与观赏性下降。对此问题,较早注意并明确指出的是黄沛翘,其认为“松图最明确,而方向倒置。”①参见(清)黄沛翘纂修:《西藏图考》卷首,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滇南李培荣刻本。对于绘图方向倒置的原因,松筠在《西藏图说》中明言:“图为备边而设,故分图从边疆起,由远至近,亦怀柔内向,而图皆绘以北向,缘取拱极之义也。”黄沛翘也对此加以解释,即“文清公取怀柔之义,左东右西,取拱极之义,上南下北方向与古法异,人颇惜之。然其形势之熟悉,险要之详明,棋布星罗,灿然大备。”②参见(清)黄沛翘纂修:《西藏图考》卷首,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滇南李培荣刻本。如其所言,虽然松筠在绘制西藏舆图过程中秉承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观,并展现了其赞誉当时专制帝王丰功伟业的个人政治情结,但在客观上看,《西藏图说》所载西藏舆图的全面性与详细性是有目共睹的。应该说,《西藏图说》是致力筹藏的封疆大吏松筠对中国传统舆地学、清代边疆学和清代方志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