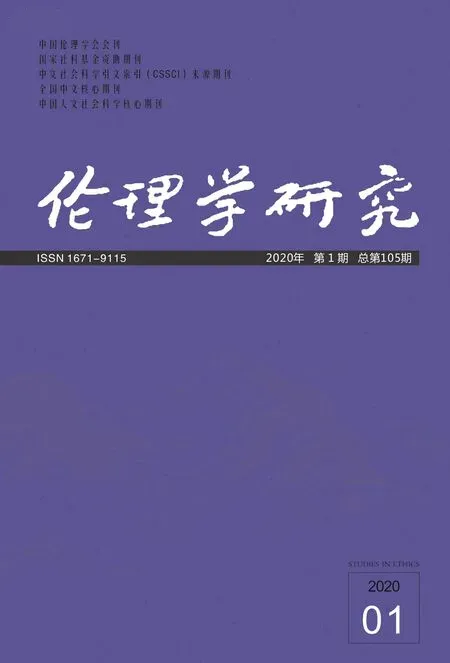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2020-12-02吴之声
李 萍,吴之声
“礼”与“教化”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先秦儒家以礼来教化人,范导人伦关系,从而构建社会的和谐伦理秩序。孔子以仁释礼,孟子摄礼入心,重视礼对于人的德性教化功用,通过人的道德修为与德性涵养,由内向外、由己及人地达致人伦关系与社会秩序的谐和。但进入战国末期,礼制衰落与仁义价值危机使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走向崩溃边缘。面对“礼义不行,教化不成”(《荀子·尧问》)的社会现实,荀子在批判继承孔孟的礼与教化理念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礼”教为战国末期的分乱转向秦汉时代的大一统提供了伦理秩序支撑,对儒家思想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具有重要而突出的作用。因此,重新审视与把握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内在的逻辑理路,为当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教育与秩序建设提供借鉴,具有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人之生也不能无群”:荀子“礼”教的逻辑起缘
“人”是先秦儒家教化的对象,对“人”及“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同思考与理解形成了先秦儒家教化的不同范式。孟子以人心之善推证人性之善,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以四心言人的仁义礼智之性,并将之提升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高度,故言人无四心非人也。孟子还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能以仁礼存心,“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爱人敬人,将心性之善发用到人伦日常中,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从而形成良善的人道秩序。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礼”内化于心,人存其心、养其性便能获得人之为人的本质和道德主体性。在这里,主体的道德形塑相对于主体与他者的伦理关系结构具有优先性。与孟子不同,荀子从具体的历史文化与社群结构及人在其中的社会文化角色[1](P18、26)来理解和回答“人”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并以此阐释礼教的起缘与必要性。
荀子关于“人之所以为人”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在《非相》篇有明了阐述:“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人道何以异于禽兽,荀子进一步回答:“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由此可以看出,荀子对“人”的理解确实与孟子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理路,荀子是从“群”与“人道”来揭释和把握人的本质的,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能群,群道(人道)秩序之所以形成乃在于人的“辨”与“分”,“辨”与“分”之所以可能乃在于“礼”和“义”。在荀子看来,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物,人在“群”的礼义中获得文化身份和道德义务,人之“群”也由礼义而形成具有秩序的社会整体,故牟宗三先生说荀子“从未孤离其所牵连之群与夫其所依以立之礼(理)”[2](P210)来空谈人。“礼”是人成其为人、获得社会文化角色与自我主体性的道德资源,也是群成其为群、群中个体与他者的人伦秩序之形成的客观理据。
荀子认为孟子以人的四心言人之本质,并由仁之亲、义之敬的推己及人过程来型构社会秩序,没有关涉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礼义世界及其具有的群之整体性,仅有仁义之心而无礼不足以成就人的德性与人伦之秩序。故荀子言:“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虚之,非礼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荀子·大略》)杨倞解释:“虽有仁义,无礼以节之,亦不成”,“里与门,皆谓礼也”[3](P476)。因此,人不能脱离礼而徒存仁义之心,仁义之心的发用及其推恩亦不能脱离礼所涵有的客观规定性。依乎此,荀子以礼言人之高义乃在于为人的仁义之心和人道秩序的落实寻觅客观的文化历史境域。荀子言人之“义”“辨”与人之“群”“分”都离不开“礼”,“礼”是联结个体之人与整体之群的客观基础和成群之道,此即“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故“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荀子·王制》)。人要成其为人、群要成其为群就离不开礼的涵化与形塑,荀子由此从人之所以为人和人道秩序落成的维度证成儒家礼教的必要性。
荀子不仅看到了人具有“群”的社会属性,还看到了人性中好恶喜怒之情与欲的自然属性,并分析了情与欲对群之秩序的影响。荀子认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荀子·性恶》),“寒而欲暖,劳而欲息”(《荀子·荣辱》),是人生而有之、自然而然的情性,具有“材朴”的性质,也即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的状态。但在现实生活中,“中”之性的发用往往受惑于外物与利欲而离其“材朴”之资质,趋向与人争斗、乱理犯分之“恶”。荀子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论释礼的起源时指出,人生而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向外强求,这种欲求若没有度量与价值的规约,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争斗的漩涡,人伦秩序就会走向混乱与崩溃。荀子进一步点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人之情与欲所具有的恶之趋向对人的群性和群之秩序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如何矫治人的情欲以维护群的稳定性和人伦秩序的谐和成为荀子需要直面的问题。荀子的回答是以“礼”来理化人之性、涵养人之礼义精神,也即“化性”与“起伪”。
面对人之趋恶的情欲,荀子认为以“礼”来化性与起伪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在荀子看来,人如若顺从自然情欲的任性发展而不受礼之约限,就会唯物利是图、偏险悖乱而不正,故荀子强调“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性恶》),以使人之情性合乎人道而归于治。荀子在《礼论》篇中亦有云:“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可见,“礼”既节制人的情欲,又滋养人之情欲,使人的欲求在外物世界中得到合理满足。人之趋恶的情性也正是在“礼”之节与养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被迁化而向善,进而使人伦关系由争乱穷困之态归于皆有所称、各得其宜之态。同时,荀子还重视通过“心虑而能为之动”(《荀子·正名》)的思虑与习伪之过程来使礼义规范内化而成为人的德性,以此成性伪之合而达乎天下之治境。由此处可知,荀子言人亦重“心”,但荀子之“心”不同于孟子的道德本心,而是以义辨为基础指向人伦秩序的“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荀子·性恶》),故荀子云:“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在荀子那里,“心之知”和“心之伪”为礼之教的内化,为人徙恶向善、由自然情性走向社会群性提供了通途。
统而言之,荀子重视与高扬儒家的“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在荀子看来,人要摆脱自然情性状态下的逐利纷争而走向有“义”有“分”、人伦秩序谐和的“群居”状态,就要接受“礼”的教化。这里的“礼”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契合于孔子之仁的生活方式与秩序[4](P235),也为《中庸》所言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之“和”提供了可能。
二、“群居和一”:荀子“礼”教的伦理归旨
构建谐和良善的人伦与社会秩序是儒家推崇仁礼及其教化的目的所在,体现了儒家对人类理想社会与生存状态的追求。孔子从“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出发,以忠恕之道与中庸之则来推己及人,从而构建“个人—家庭—社会”仁爱和谐的秩序图景。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由仁礼之心向外“推恩”,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天下谐和之境。可以说,“贵和”是儒家社会秩序图景的特征,也是儒家使仁礼之价值在社会群体生活中得到落实的保证。“和”为“礼”所内涵,是“礼”谐和人际、安伦经国的内生性功能,故《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荀子从“人生不能无群”出发,在“贵和”的基础上进一步描绘出儒家以礼义教化人所要达致的“群居和一”之社会理想。
荀子认为人生而有不能离群之社会性,但群的凝聚不是不待而然的,因为在社会性之外,人还有趋利嫉恶好声色的自然情性,顺任情性的自然发展就会使群分崩离析,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需要“礼”之涵化和调节,才能使个体与他者在有序平衡的互动中成就“分”明“伦”定之群。荀子云:“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荀子的“群”不是个体简单粗俗集合而成之群体,而是个体经由礼的教化与涵养,不断扬弃自身自然情欲后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群”是个体在礼的化分下获得现实而具体的伦理角色与道德自觉的共同场域。“和”与“一”是荀子之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在荀子看来,群之和谐与稳定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齐一无异,因为“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荀子·王制》),故要以礼定分,以分安伦,使人在群之分位层级结构中获得情欲的满足,从而促成人际之和,并在和中达致群之一统。在礼的范导与涵化下,群的“和”亦即群的“一”之状态,是人的争夺分裂之状经由礼之教化而进达谐和统一之态,“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王制》),由此人之为人与成群才能优异于群外之物。
综而言之,“群居和一”的人伦与社会秩序理想是荀子“礼”教的归旨。
第一,荀子以礼之“普遍化”使内禀自然情性的个体向群之伦理实体复归。面对具有趋恶之自然情欲的个体,荀子认为要化其性不能仅“顺诗书而已”(《荀子·劝学》),而须“待乎礼之条贯以通之”[2](P196),也即使内具自然情欲的个体在礼的教化中获得其明确的社会文化身份与伦理道德义务,从而使自然情欲的个别性经由礼的教化与提点之普遍化而获得其在社会伦理实体中的客观规定性。此时之人,已不再是自然的、孤立的、趋恶的个体,而是内化社会规范、践履道德义务、维护伦理实体的群中之人。由此处言,则荀子之“礼”为儒家仁义精神与价值的发用和落实提供了客观的框架与情境。在荀子之“群”中,为人君者“以礼分施”,为人臣者“以礼侍君”,为人父者“宽惠而有礼”,为人子者“敬爱而致文”,为人兄者“慈爱而见友”,为人弟者“敬诎而不苟”[3](P228)。个体之人由礼而获得其在群中之分位权利及其责任义务,个体在认同权利和义务的过程中化性而起伪、修礼而成德,进而自觉维护与归复于群之伦理实体,成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荀子·王制》)的和谐秩序。
第二,荀子以礼之涵融实现社会层级分明与人伦谐和的统一。荀子身处战国末期,人之情欲膨胀与社会秩序破坏的现实使荀子意识到须要以礼来重新确立社会分位层级和重整人伦秩序。荀子在《富国》篇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君王到庶人皆要由礼之分而定其位,在各自的分位上各守其职、各尽其能。农人“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与大夫“分职而听”[3](P210),以礼定分、以分定职才能使“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可见礼对社会职分秩序结构的化造之功。值得重视的是,荀子以礼化定的社会分位层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对礼的践履与成德情形而动态流动。在荀子看来,人可为尧禹,可为农贾,在于人之习礼积伪;“无恤亲疏,无偏贵贱”(《荀子·王霸》),虽出身贵族,如若不修礼成德,则归之于庶人。荀子经由礼构建了一个尚贤使能、无德不贵的公道社会,“于不平之中暗寓平等”[5](P112),从而实现社会分位与人伦关系的有序和谐。
第三,荀子以礼之范导使人的情欲满足与约制趋向“和一”。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情欲,需要向外寻求满足,但外物资源是有限的,若不能使人的情欲追求得到“度量分界”,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争夺敌斗的无序无群状态。故荀子以礼来安排和落定人们在社会中的分位,依据分位赋予人们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使人们的欲求得到满足但又不逾越其必要限度。如此,人与人之间就不会因为欲求受到资源限制而落入争乱穷困之境,资源亦不会因人的无限欲求而被消耗殆尽,“欲”与“物”得以相持而长。由乎此,荀子在《王制》篇中所言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便可得见其深层蕴意。事实上,战国末期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较孔孟时期更为复杂与多元,人的欲求亦随之而日益多样,荀子察悉于此,明乎人伦与社会秩序之谐和不能仅依仁心的发用,更要依靠具有客观性的礼来范导人之情欲,发挥情欲之积极功用。荀子以礼来定分和化导人的欲求,使人在礼的涵养中各载其事、各得其宜,“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从而使整体之社会进达“群居和一”之境。
三、礼道合一与秩序合理性:荀子“礼”教的价值皈依
儒家教化的意旨在于构建谐和的人伦与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其本质上是合客观性与主观性于一体的实存伦理秩序关系,其“首要问题是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6]。孔子以仁释礼与成礼,孟子则摄礼入心,尽“四心”而知人性与天命,从而使孔孟的以礼化人获得仁义的价值基础,以仁义为基础经教化而形成的人伦与社会秩序便具有其合理性。此外,孔孟的仁义还因其联通了天命与人性,人通过道德修养可达天人合一之境界,从而使儒家的教化获得超越性的价值,这在《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可见其逻辑意涵。与孔孟不同,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使荀子重新思索人与天的关系,荀子认为天对人的德性涵成不具有主宰性的价值意义,人类社会伦理秩序重构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亦不源于天道,而是源于人道的觉醒和有为。“礼”是人道觉醒与有为而累积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制度,为人的仁义之心的发用和人伦秩序的落成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框架,而不致使仁义之心因天之神秘而脱离人道实际。同时,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不仅具有外在的规范,亦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和合理性。
荀子认为万物的存在与运行皆有其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道并不主宰人道,人之德性与社会有序运行的价值本原并不来自于天,故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的主张。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人道更为可贵与重要,荀子在《儒效》篇说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而“在人者莫明于礼义”(《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礼”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道”,是成人之道、成事之理、安国之命,人不接受礼的教化涵养,不遵循礼的规范原则,便不能化性而起伪,就会成为“无方之民”(《荀子·礼论》),如此人和社会便会失“道”而陷入争斗纷乱的无序状态,故荀子曰:“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作为人道之极的礼并非生成于天,而是圣王用心思虑、后天习伪,也即人道有为的结果。礼生于人道之伪,是人道之伪的结晶,但其一旦形成便具有“道”的独立性与本体性,从而为个人的成德和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提供本原价值与合理性依据。荀子还把事天地、尊先祖与隆君师作为礼之三本[3](P340),礼是联结人与天地、先祖、君师的价值纽带,人循礼化性、修礼成德便能达致与天地参之境界,人类社会接受君师的礼教而谨守践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荀子·天论》),便能进达秩序谐和的治平之境。可见,作为人道之极的礼为人伦与社会秩序提供了其所以然之理据,而谐和的人伦与社会秩序又体现了礼之价值。
作为人道之极的礼与人的内在情感和心理结构相契合,礼因缘于人的内在情理变化,又协调人之自然情感的向外发用,满足着人对情感的价值诉求,从而为礼之化人及社会秩序落实提供价值合理性。“情”是荀子伦理与教化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情欲与情感的两个基本义涵。荀子以礼教化人既是要矫治人之性情中的趋恶之欲望,又是要范导人的自然情感表达、形塑人的内在情理结构。荀子在《礼论》篇以儒家重视的丧礼与祭礼为例,揭释人之情感与礼的内在联系。《礼论》有载:“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又载:“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丧祭之礼根据人的情感需求而设立,蕴含着人对逝者的哀伤之情与对先祖的念思之情,同时,丧祭之礼的规范又约限着人的悲哀与思慕之情的表达程度,使人的情感得到合理表露,使情与文(礼)谐和俱尽,故荀子云:“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荀子·礼论》)。因此,以丧祭之礼对人进行道德教化,可以涵养人的情性操行、调节社会的人伦秩序,这与《论语·学而》所云之“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相呼应。丧祭之礼与哀思之情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延展为具有普遍性的礼与情的关系,即礼出于人的内在自然情感需求,又约制与化导人的自然情感,“是人的冲动的文明表达”[7](P6),从而使人在礼的教化下“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荀子·修身》)。礼既因出于人之情理而获得其合理性,又因其使人的情理表达有序、无过不及而蕴涵着中庸之道与价值。
作为人道之极的礼还是人类社会规范与制度背后的“理”,为规范与制度的存在、运行提供客观依据和价值正当性。在荀子的礼论思想中,“礼”既是具体而详的规范准则和制度系统,又是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理和道。礼之为理与道,表现出了礼所内具的浑厚、广大、隆高与诚明之本质,故荀子曰:“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荀子·礼论》)也正因为礼具有这样的本质特性,荀子把礼喻为“直之至”的“绳墨”“平之至”的“衡”“方圆之至”的“规矩”,故人学习礼和效法礼方能克服虚伪诈利之情欲而成为“有方之士”,群体社会以礼为规范制度之法式方能成为有序谐和之整体。明乎此,荀子何以谓礼为人道之极便可得其要旨。礼内蕴着理和道,为其成为人之行为规范原则与社会制度框架提供合理性根据与基础,人接受礼之理与道的滋养而化性成德,人之群体接受礼之理与道的分疏涵养而化成秩序公正合理之治平社会,故荀子亦曰:“礼者,治辨之极也”(《荀子·议兵》)。
四、“礼乐之统”与秩序极成:荀子“礼”教的落实途路
荀子之“礼”教起缘于“人生不能无群”的人之社会性与“人之性恶”(《荀子·性恶》)的自然情欲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基于此,荀子根据人的自然情性结构,通过礼的定分和养欲,对人进行礼义教化和德性涵塑,使人从自然性的存在走向社会性的存在,使人的情感与欲望得到合理恰当的表达和实现,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礼的协调涵化下走向有序谐和,从而使礼义教化的意旨和价值诉求在现实实践中得到落实。荀子根据人生来有欲求的人性现实和“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荀子·荣辱》)的人伦实际,以礼义为价值基础,赋予人们不同的社会定位和伦理角色,以“分”来约限和范导人们的情欲追求,使人的自然生命在礼的涵养中与礼义精神交融互通,从而提升人之德性和避免人在自然状态中的犯分乱理,故荀子曰:“群而无分则争……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
荀子的“礼以分养和”主要从人伦关系和社会职事之分际进言,在礼的涵养协调下使人的情欲实现和社会的秩序建构趋向合理与公道。从人伦关系言,荀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是人与人之间的重要伦理关系,这些伦理关系建基于人性之实与自然情感,又内涵着礼对人之角色与义务的规定,如“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荀子·非十二子》),故荀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贵贱有差、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对人伦和社会秩序的极成具有重要功用,并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荀子·天论》)。从社会职事言,荀子认为“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国》),个人的道德修为和技艺能力有限且与他人相异,社会要实现整体之有序谐和发展就要依礼分职分工而事,故有君王、诸侯、士大夫、庶人之分,又有农人、贾人、百工之别,此即荀子所谓“谪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荀子·儒效》)。从事不同职位之人修己安正,守礼尽责,发挥自身的内在潜能,使个人的情欲与价值追求得到合理且充分实现,社会由此达致职分而民有德、次定而序有齐的“群居和一”景象,荀子云:“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荀子以礼定分与安伦,使礼对人的范导和人伦秩序的形成在客观实践中落实,但如何使规范之礼内化于人心而植根于人的精神生命中,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了以乐致和、礼乐相统的化人进途,使人在乐的陶冶熏化中心悦诚服地顺和于礼。人如果只是机械地接受礼而没有乐的陶养,则会失去性情之感性与生命之柔性;社会秩序如果只是单维地接受礼的安排而没有乐的疏导,则“人与人之间,会导致精神上的离隔”[4](P235),社会徒有秩序之规范而无人心之谐和。因此,儒家重视乐在人的情理结构与道德人格之培养中的功用,使人之性情丰圆和人伦秩序和融在乐的化育中得以成就。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有曰:“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和《论语》常将礼、乐连用,礼与乐相统而成,乐是人的仁礼之心得以生成发用、社会礼制规范得以入化人心的保证。孟子以仁义释乐,丰富了乐的道德意蕴。荀子承继了孔子和儒家以乐治心、养情与成德的传统,并在“礼”的系统中重新阐释了“乐”,发挥“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之特点,礼乐相兼并施,使儒家之教化真正落入人心。
与礼之源起一样,荀子亦从人的自然性情来阐释乐的起源,认为乐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乐起于人的内在性情需要,同时又陶治人之性情而使之和顺合善。在荀子看来,人生而有好恶喜怒哀乐之自然情感,这些自然情感的表达显露若不合于礼义之道则会流于邪恶,从而使人情不化、人与人之间陷入偏险争乱之境地。圣人先王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悖乱,故制礼乐来修正人之行为,陶冶涵养人之性情,使乐之“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荀子·乐论》),天下便能因人之情感与行为表现合乎礼乐而归于顺和,荀子故云:“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荀子之所以以乐陶养人之性情而使之合于礼,是因为乐能以其鼓钟、音律、节奏来恢弘人之志意、肃庄人之容貌、齐正人之行为;乐之清明广大及其旋律还内蕴着顺合天地与时变的礼道,以乐化人即是以道制欲,使人的趋恶之自然性情在乐之潜移默化的陶冶涵养中扬弃其恶而内植与他人谐和有爱之德。明乎荀子此意,孔子之“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和《礼记·乐记》之“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便可深明其旨。
荀子以礼定分、以分区别人之社会角色而形成人伦秩序,同时又以乐致和、以乐和顺人之心性与情感,使礼和秩序之规范内化为人心之自觉自律而终得落实。在荀子的教化理论中,“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礼之经在于显发人之真诚敬意而教人践履秩序之规范,乐之情在于直达人心而化外在规范为人之清明心志和德性,礼乐相统使得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故荀子云:“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荀子·乐论》),乐蕴涵着中庸之道,君臣听之则和敬,父子兄弟听之则和亲,长少贵贱听之则和顺,乐“审一以定和”(《荀子·乐论》),导引人在礼之分异中寻思和体认礼之一道,并在此中感化人心、变化风俗,使天下和睦治平。可见,“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礼为天地之序,乐为天地之和,有礼而无乐或有乐而无礼皆不能安伦与化物,只有礼乐相统方能极成人伦有序之架构与社会谐和之秩序。综而言之,荀子以礼统乐、以乐通礼,在礼乐之教化中转变人之自然质性,陶冶人之心性情感,使人情理融洽、志意清明,“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8](P109),并由人之成德而使整体之社会进达“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的“群居和一”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