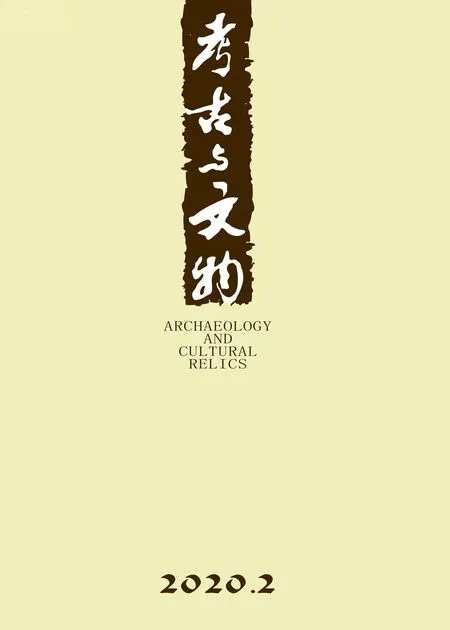东周铜箪铜考
——兼论“樽”与“觯”
2020-12-01樊波成
樊波成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一
战国秦汉饮器以“卮”为主,即当时的“单环耳筒形杯”。宋代《博古图》误将“耳杯”定为“卮”;又以造型相似之故,将一种双环耳、深腹的器类称之为“卮”[1]。近代以来,学者们认识到这种双环耳深腹容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而非汉代[2]。1966年洛阳春秋墓所出同类器物,器底有铭曰“哀成叔之”。刘翔据自名“”改称“卮”为“”[3]。2003年,李学勤将伯游父器自名“”隶定为“”,读作“卮”[4]。本世纪以来,朱凤瀚、齐耐心和路国权等排列铜类型,厘清了铜的演变序列[5],却仍未能确定器名。此外,铜的性质学界也是聚讼已久:宋人将铜视为饮酒器(卮、双耳杯),《西清古鉴》则称为“承盘之舟”[6],近来还有“酒器椭杯”“调食之盉”“代匜之注水器”“饮器兼盛酒器”“古之肥皂盒”等说[7]。至于上海博物馆所藏自名为“左关之”的战国齐地铜器,则为量器无疑。
《仪礼·士虞礼》:“匜水错于盘中,南流,在西阶之南,箪巾在其东。”《少牢馈食礼》曰:“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盘东。一宗人奉箪巾,南面于盘北。”郝敬云:“箪以盛巾,在庙门右。内以西为右,尸入于此盥手。”[21]黄以周曰:“门之设盘箪,犹庭之设洗。”[22]春秋至战国初年,“箪”与“盘”“匜”等器相配以沃盥,箪之深腹正适用于用于盛放巾、栉等盥洗小件。《周礼·春官·司巫》《说文》中还有“宗庙盛主器”之“匰”。在《孟子》等战国文献中,又常见“箪食壶浆”“箪食豆羹”等内容,显然是将箪用于盛放饭食。
箪也是量器,松江本《急就章》“蠡斗参升半巵箪”[23],正以“箪”为“半量”。《论语·雍也》颜渊“一箪食”犹《汉书·项籍传》“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孟康注:“半,五升器名也。”[24]“箪”即“半”,值晚周秦汉之五升,可供古人半饥半饱支撑一天,《庄子·天下篇》:“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又:《说文》引《汉律令》曰:“箪,小筐也。……匡(筐),饭器也,筥也。……筥,䈰也。……䈰,一曰饭器,容五升。”《说文》中筐、箪、筥、筲(䈰)等饭器浑言不别,皆容五升。《仪礼·聘礼》曰:“筥半斛。”《仪礼·聘礼·记》曰:“凡饩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汉魏《旧图》云:“大筐受五斛,小筐受五斗”,或作“小筐受五升”[25]。是筐、箪、筥、筲诸器,小者为五升(半斗),中者为半斛,大者为五斛(半钟),正与前述“左关之”以“”为“半量”相应。
二
楚地战国墓葬曾出土过一批“镂孔杯”形器。有的为三矮足,如包山M2:172/195[26]、长台关M1:242[27];有的为十字镂孔杯底,如望山WM1:T81[28]、江陵雨台山M264:31[29];有的无底,如曾侯乙墓E.3[30]。这类器形口径大底径小(曾侯乙墓E.3图版可能是倒置),壁斜直,通体镂孔勾连。在考古报告中,他们有镂孔杯、奁、熏杯、筒形器等不同称呼。程平山认为它们是熏香器,与传世文献中“篝”关系密切[31];也有学者认为镂孔杯与酒器“卮”相关[32]。
“镂孔杯”出土位置各有不同:包山M2:172出于东室第六层,四周都是放置丝织品的方形彩绘竹笥(如159、160号),包山M2:195出于东室第七层,附近有“会欢之觞”和人字纹竹笥,竹笥内部大多残有枣核或动物骨骼。长台关M1:242出于墓室北侧,附近可能是铜镜。望山WM1:T81出于头箱西侧,附近为陶簋、陶匕与陶匜,出土时由丝帛包裹、杯内有圆木和其他植物残片。曾侯乙墓E.3出于东室第二层,附近金盏及其漏勺。从器物组合上看,“镂孔杯”似乎与饮食器、容器、衣妆、熏香各有关联。
《诗经·召南·采苹》“维筐及筥”毛传曰:“方曰筐,圆曰筥。”[45]是筥为圆口器。此外,《方言》谓“筥”为楚地之“篝”,而《类篇》又谓“篝”为“上大下小”,“白之”和“”都是上大下小圜口形,正与之相符。
明确“筥”的器型有助于确证春秋时代饮器“觯”的具体所指。宋人曾将商周之际的鼓腹束颈容器“祼雚”称为“觯”,又把三足器“祼彝”称为“爵”,并无可靠依据[46]。现在我们知道,《仪礼》中的“爵”指的是“伯公父爵”一类的圈足圆口“斗形爵”,这正与北宋《新定三礼图》的描述基本相符[47],《新定三礼图》的价值也因此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新定三礼图》透视技法古怪,但仍保留了器形的关键特征。以筒形容器为例,“铏”和“新莽嘉量”的实物上下等宽,《新订三礼图》的“铏”和“斛”也是两壁平行[48];实物“上大下小”的“筥”,对应在《新定三礼图》中也是两侧线条向下收缩。有意思的是,与“筥”同形的正是饮器“觯”。就实物而言,西周中期至战国早期确有一类与“白之”外形极为相似的筒形杯;这类筒形杯的轮廓也经常出现在“东周铜器刻纹”的射礼燕饮场景中。属于这一器类的“万杯”(《集成》06515)自名曰“()”,为“觯”字之异体[49]。在1961张家坡西周窖藏、安丘柘山镇春秋墓、曾侯乙墓中,这类“筒形杯”还与当时饮酒器“爵”同出一处且一一配对[50]。《仪礼·乡饮酒礼》曰:“献用爵,其他用觯。”《仪礼》饮酒器的基本组合也正是“爵”与“觯”。此外,“筒形觯”与今日用于饮水饮酒的“品脱杯”(容积500~600ml)造型相似,也十分符合人们饮酒饮水的习惯。因此,西周晚期至战国初年的饮酒器当为“筒形杯(觯)”和“斗形爵”的组合,而非过去学者所说的“卮”(、箪)。
[1]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M].扬州:广陵书社,2010:322-324.
[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台北:大通书局影印,1941:454.
[4]李学勤.释东周器名卮及有关文字[C]//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30-332.
[5]a.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62.b.齐耐心.东周青铜卮的整理与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c.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98-201.
[6]梁诗正.西清古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88.
[7]同[5]c:199-203.
[8]裘锡圭.齐量制补说[J].中国史研究,2019(1).
[9]a.同[5].b.同[7]:200.
[10]a.同[3].b.同[7]:201.
[11] 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1(4).其中M4:6 登记为Ⅱ式壶(Ⅰ式为“醴壶”),Ⅱ式壶造型与同时期自名曰“盥壶”的君壶相似。
[12]同[3].
[1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墓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插页.
[14] 原释为“二椹钱”。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M].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287.
[15] 盏属食器,参见程欣人,刘彬徽.古盏小议[J].江汉考古,1983(1).
[16] 陈剑.青铜器自名代称连称研究[C]//中国文字研究(第1 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
[17]上海博物馆编.齐量[M].上海:上海博物馆,1959:31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124.
[20]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4:327-329.
[21]郝敬.仪礼节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63.
[22]黄以州.礼书通故[M].北京:中华书局,2007:895.
[23] 颜师古本改“斗”作“升”,改“箪”为“觛”,参见张传官.急就篇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2017:216.
[2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03.
[25] a.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374.b.聂崇义.新定三礼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41.
[26]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89.
[2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51.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78.
[29] 湖北省荆州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89.
[30]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49.
[31]程平山.镂孔杯浅议[J].华夏考古,1995(4).
[32]同[14]:255.
[33]同[26]:515.
[34]同[14].
[35] 郭若愚.长沙仰天湖战国竹简文字的摹写和考释[J].上海博物馆刊,1986(3):21-34.
[36]a.同[26].b.同[14].
[3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50.
[38]同[26].
[39]同[14].
[40]同[37]:1273.
[41]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150-151.
[42]同[24]:420.
[43]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6:879.
[44]同[43]:670.
[4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80.
[46] 谢明文.谈谈金文中宋人所谓“觯”的自名[J].中国文字,2016(新42):135-144.
[47] 李春桃.从斗形爵的称谓谈到三足爵的命名[C]//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8(89.2):47-118.
[48] a.同[15]:393.b.裘锡圭.鋞与桱桯[C]//裘锡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7-11.
[49]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7.
[50]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5:22图版三二.b.同[30]:370-371图229、图版一三五.c.安丘市博物馆.山东安丘柘山镇东古庙村春秋墓[J].文物,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