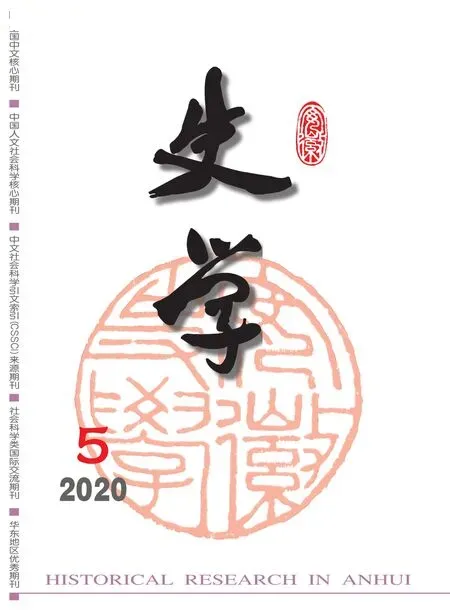从“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
——1949年前后晋西北农村妇女分工变化之考察
2020-12-01
(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丁玲在1942年“三八节”感言中称:虽然“妇女”两字将会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地被提出,还是一个未知的答题。但“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1)郜元宝、孙洁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那么,如何才能“强己”呢?在劳动中获取经济报酬、争取独立人格无疑是其基本路径之一。晋西北作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进入华北的第一站,这里的农村社会经历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1949—1956年间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革命与建设始终贯穿其中。当妇女劳动与中共革命动员、妇女解放策略及社会经济政策相互交织,晋西北农村妇女分工则开始发生质的转变。近年来学界关于农村妇女分工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妇女分工本身及宏观层面考述,而对于1949年前后农村妇女分工实况则缺乏实证研究。(2)如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李斌:《农村性别分工的嬗变——合作化时期的湘北塘村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郑晔、王昕:《论农村妇女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等。鉴于此,笔者以馆藏档案及《抗战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资料为依托,系统阐释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晋西北农村妇女分工的嬗变历程及其意义。
一、走出家庭:农村妇女分工的第一步
晋西北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可耕地有限,农作物主要有莜麦、山药蛋、大黄、羊皮等。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使得该地区发展模式落后、文化生活保守。在家庭关系中,妇女成为“养儿抱蛋、缝新补烂”(3)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的替补角色,活动范围始终囿于一“家”之中。这种传统的“男外女内”性别分工使妇女几乎与家庭经济权力隔离,尽管妇女在操持家务之余从事纺织劳动,但家庭经济支配权依然与之无缘。如临南县妇女刘能林从不知道自己织的布能卖多少钱,更不敢开口要钱花。(4)《妇女纺织变工的组织者——刘能林》,《抗战日报》1944年1月29日。
是何种因素导致传统家庭关系中妇女地位低下呢?究其因果,一是女性劳动收入相较男性微乎其微,不足以负担家庭开支,以致在家庭经济中不得不依赖男性,而这种经济依赖反过来为传统的“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做了“合理”解释。二是传统社会妇女既无资格参与国家政事,又无财产继承权、转让权、选举权。在晋西北百姓观念中,女孩长大是要嫁人的,所谓嫁汉嫁汉即为穿衣吃饭。至于上学读书、婚姻自由,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20世纪40年代晋西北包办、买卖婚姻等现象属于农村社会常态。如兴县赵家川口刘姓人家一个9岁玩童娶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一早要替丈夫晾尿湿的垫褥,晚上要给婆母捣背捶腿,婆母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家境不好娶不起婆姨者,不是养童养媳就是租妻,以图传宗接代。(5)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100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战争打破了乡村往日平静。1940年中共力量进入晋西北,根据地政府认识到民众动员必须与“解放妇女”工作联系起来。那么,“解放妇女”为何要被看成根据地民众动员不可或缺的因素?毛泽东在1940年2月《给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写道:“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地政府鼓励妇女首先从经济独立入手,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来改变自己命运,进而实现“妇女解放”。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经历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而身处革命洪流中的农村妇女在这一革命年代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其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劳动对于妇女的意义是否与以前有所不同?
从1941年3月开始,日军在华北各地实行“强化治安”,不断“蚕食”中共抗日根据地。到1942年秋,晋西北根据地比1940年前半年缩小1/3,人口由300万减少到100万,劳力和耕地的减少使得军民生活十分困难。同年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中共晋西区委书记林枫:晋西北只有人口70—100万,望检查缩小的原因,必须振奋军心民心。(7)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为应对时艰,晋西北根据地发起大生产运动,而此时农村地区深受日军侵袭和参军热潮双重影响,男性劳力锐减,女性的地位则日益凸显。1943年,岢岚县妇女全体动员抢割,担负了整个收割任务的7/10。(8)《岢岚群众秋收忙》,《抗战日报》1943年10月14日。同年,临县白全英组织妇女变工互助参加劳动生产,夏收时动员40个妇女按住地远近编为5个变工小组,“谁家麦子先熟,就先给谁家割,给谁家割,在谁家吃饭,长下工给工钱”,仅用10天时间全村麦子就收割完成;根据这次经验,秋收时妇女开了一个会,还是照常变工互助,妇女刨山药、割谷子、糜子、高粱,男子挽黑豆,吃饭与前一样,妇女做工如有剩余按半个男工给工资,13天工夫就把农作物收回场里。白全英兴奋地说:“我在家时是女人,上地是男人。”(9)《妇女特等劳动英雄——白全英》,《抗战日报》1944年2月1日。
不过,由于受生理条件限制,妇女在农田劳动中多从事收割等较具技术性的工作,而对一些用力较大且影响收成的农活如耕地、播种等,男人还是愿意亲力亲为。体现在工资待遇上,女工工资一般相当于男工一半。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待遇对于妇女而言,解放程度远远不够,但相对于传统意义中的女性角色可谓迈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关键一步。女性分工不再限于“内”而逐渐向“外”扩延,且在劳动生产过程中选取了适于自己的组织形式——变工互助,其中既有妇女间的变工互助,亦有妇女与男人间的变工互助。如临县在1943年秋收中某村向全县各村发出挑战,条件之一是发动50%的妇女参加变工。在这一挑战动员中,妇女段家作领导的小组4人第一天就收糜子3亩;某村妇女36人编成7组,每天打场上地;李福荣领导的小组4男3女一天割高粱11亩,女的剪穗子,男的挖根子,分工合作。(10)《临县展开秋收竞赛》,《抗战日报》1943年10月21日。变工互助的意义不再仅仅限于解决某时某事之困难,而在补齐短板之时提升劳动效率;更重要者是在互助中妇女被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以平等的位置与男性建立合作。妇女开始对自身有了全面了解,而男人则通过互助合作看到了妇女的作用,有利于妇女劳动报酬的提高和地位的改变。
20世纪40年代初,晋西北根据地因日军扫荡、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及连年自然灾害,军民生活极度窘迫,不少妇女衣不蔽体甚至不敢出门。如岚县某村有242口人,虽尽可能节省穿布,但每年仍得拿370多石莜麦换布,以致很多人因换布做衣而影响吃饭问题。(11)《岚县劳动英雄王七月后组织纺妇解决穿衣问题》,《抗战日报》1944年5月30日。因此,大力发展纺织以解决军民穿衣问题成为根据地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然随着妇女被广泛地动员到农田劳动中,“男外女内”“男耕女织”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已被打破。既然女性分工开始向“外”延伸,那么,原先属于女性“内”的分工是否发生变化?“男耕”发展为男女同耕,而“女织”依然还是女织吗?
事实证明,在实现“脱下破皮袄换上新布衣”的大生产运动中,妇女依然是纺织运动的主力军。晋西北各地如兴县、保德、岢岚、神府等都开办了纺织训练班,妇纺运动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神府仅一、三、六区即有纺妇2000人、纺车千架,既有年过六旬的老太婆又有10岁左右的小女孩,甚至一部分男人已热心学习纺线。(12)《神府纺织业飞跃发展》,《抗战日报》1944年5月11日。河曲仅城关、巡镇就有纺妇780人,每人有纺车1辆,另有织布机7架。(13)《河曲城关巡镇妇纺飞跃发展》,《抗战日报》1944年7月15日。临南一、二、三区连七八岁女孩都学会纺线,许多村的男人帮忙拐线、缠穗子,如劳动英雄刘文锦村就有20多个男人学会纺线。(14)《临南完成第一期标准布》,《抗战日报》1944年5月18日。由此可见,纺织运动已成为以女性为主体,涵盖各年龄阶段的全民参与的生产运动。尽管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是女性,但男人的学习和参与无疑是对传统性别分工中“女织”印象的破冰,甚至成为根据地性别分工开始转型的风向标。
那么,20世纪40年代晋西北妇纺运动中妇女的角色与传统性别分工中妇女的纺织角色有何不同?
第一,劳动价值不同。晋西北妇纺运动开始突破家庭向社会化过渡。妇女通过纺织劳动可以获得社会荣誉、物质奖励、工资报酬等。如1943年10月2日三区专署召开的奖励妇纺大会上,刘能林、刘秋香、高如兰3人被选为全区纺织劳动英雄,奖励刘能林农币500元、手巾2条、织布锯1口,刘秋香农币440元、手巾1条、锯1口,高如兰农币330元、手巾1条、锯1口。(15)《临南三区奖励纺妇》,《抗战日报》1943年10月21日。此外,三专署还针对精纺制定标准,工资累增,从10支纱起,5天内能纺10支者工资50元,7天内能纺12支者77元,10天内能纺14支者115元,如能在12天内纺至16支纱则增至150元。(16)《三专属订精纺标准》,《抗战日报》1943年9月2日。
第二,劳动意义不同。晋西北妇纺运动不再仅仅是满足家庭穿衣用布,而更多的是要保证根据地抗日部队穿衣需求。如1943年6月至9月间二区妇女纺织量较前增加2000多匹,她们说“这是咱们军队穿的,织的要比咱们穿的还好。”为此,她们尽可能买最好的棉花,政府规定每匹布重3斤,而其织的普遍都在3斤半左右,有的甚至达4斤重,织的布可以说又漂亮又结实。(17)《临南妇女加工精织标准布》,《抗战日报》1943年10月16日。同时,一区妇女不到半月即完成军鞋1900双,准备在10天内再完成1800双。有的妇女还托人把自己名字写在鞋底上。五区各村妇女展开做军鞋竞赛,某村妇女做出的军鞋一般都是鞋帮4层新布、鞋底填布10层,每双缝7000针以上,大家都连夜赶做。(18)《临县妇女热烈拥军》,《抗战日报》1943年9月14日。由此可见,纺织劳动对于根据地妇女而言,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小家”范围而向根据地这个“大家”延伸,妇女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其社会性的一面。
不过,农村妇女角色的社会化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如何将“解放妇女”这一抽象概念落实到具体的“妇女解放”,根据地政府把着力点集中于“吃”“穿”两方面。因为,这既与农民生活以至生存密切相关,亦与家庭成员经济地位紧密相连。通过改变传统家庭关系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动员妇女参与农田劳动、男性配合纺织劳动,并给予妇女适当的社会荣誉、经济报酬、政治权利,从细节处入手,逐渐改变妇女思想,促其经济独立。1940年刘能林被选为妇救会秘书,她在参加行政村会议时讲到:“真是!一个农村妇女的解放,可不容易了!别说参加领导工作,自己的男人首先不高兴,设法阻挠、反对,自己也有许多困难:胆怯、不惯……认识慢慢的提高,想:参加抗日工作革命工作为什么不坚决些呐!于是克服着自己的弱点,说服着自己的男人,照顾公事,也照顾家事,一边忙着工作,一边自己还是辛勤的纺织。”(19)《妇女纺织变工的组织者——刘能林》,《抗战日报》1944年1月29日。
由此可见,20世纪40年代妇女分工的重心不在于妇女工种的变动,而在于其劳动价值是否得到社会认同。传统意义上的妇女劳动既没有得到家庭重视,更没有得到社会认同,以致其劳动既不能获得必要的报酬,更不能获得平等独立的身份。相反,根据地倡导妇女分工,使妇女劳动得到政权保证、群众认同。经济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鼓励,促使妇女开始追求平等独立的人格和身份。
二、追求平等:农村妇女分工的质变
新中国之初,经济疲敝,百废待兴。如何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主要议题,而1950年代初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内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初,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妇女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被发动起来。根据各地经验,凡发动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有成绩者,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力缺乏问题,亦增加了农民收入,进而推动了农业生产。(20)《河北山西两省百分之七十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1月10日。与此同时,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以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要求各地妇联配合当地政府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妇女参加春耕、夏锄、夏收,当年老解放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人数一般达50%—70%,有些半老区达40%。195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妇联指示各级妇联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文章,将组织教育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作为各级妇联中心任务。(21)《全国妇联指示各级妇联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
据调查,1950年山西各地妇女参加生产者已超过全国妇代会要求“动员50%以上妇女参加生产”的目标,不仅有50%以上的整、半劳力参加了春耕,在三秋阶段甚至高达70%左右。(22)《河北山西两省百分之七十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1月10日。1951年妇女参加生产的在山西老区约占妇女劳力(除孕、产、疾病、老弱妇女外)的90%左右,其中基础好的县占总劳力的60%左右,一般的县亦达15%左右。(23)《山西省怎样发动农村妇女走上生产战线》,《人民日报》1952年3月7日。
不过,晋西北妇女广泛参与农田劳动并非始于1950年代,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中共革命动员中积极地参加了田野劳动。如前所述,50年代延续开来的妇女参与农田劳动是否仅仅出于劳力不足,还是基于40年代已基本形成的男女共同劳动的惯性?若是基于劳力缺乏,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时期劳力缺乏?以上问题可以从50年代国家粮食生产政策在晋西北的落实情况中窥见一斑。
时至1952年国家农业经济逐步回暖、粮食产量持续增加,虽然1953年粮食增产率开始有所下降,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仍推动着粮食总产量的上升势头。不过,在农业经济稳步增长时,如何利用农业积累来支援工业化建设则成为国家领导人面临的又一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政府决定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以兴县为例,1953年政府开始宣传和普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乡村代表在这一政策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如东坡乡代表刘赶当按计划应卖收购粮500斤却自动卖粮1800斤,并动员3户亲戚卖粮5700斤,带头发动全村卖粮1.5万斤(按计划收购7700斤),超过任务近一倍。在这些人带头下,1953年国家统购完成数为900万斤,超过任务量50%。(24)《兴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关于五年来的工作总结》(1955年3月),兴县档案馆档案,档号:A13-1-21。以下凡引该档案者仅标注档号。再看1954年,据1954年统购摸产计算,当年粮食作物实播种面积1237274亩,每亩平均实产49.8斤,是1953年亩产51.75斤的96.23%,达计划亩产59.6斤的83.5%。尽管粮食作物亩产没有达到计划产量,但1954年兴县依然超额完成国家给予的1120万斤购粮任务。(25)《兴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四年的几项主要工作总结和五五年农业生产计划草案报告》,档号:A7-1-56。
是什么因素促使村民普遍支持统购统销粮食政策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出自于村民对国家政策的积极配合,另一方面表现出村民已累积有一定数量余粮。如兴县六区14乡有3107户售粮户,积极售粮争取超额者1248户,占总售粮户40%。另据52村调查,党员929人、团员664人中超额完成任务的有党员556人、团员398人,占总人数59.9%。同时,为发动村民出售余粮,白家沟乡召开烈军属座谈会,再次声明残烈军属卖了余粮照样能享受代耕优耕政策,烈属王引留当场卖粮1000斤,军属王茂招亦超额完成统购任务1500斤,并带动全村4天内摸实产量。蔡家崖乡干部李芝荣检讨自己上年没有卖足余粮而自报卖新旧粮4000斤。白家沟村妇弓焕兰自报卖粮150斤,并带动该村6个妇女卖粮900斤。(26)《兴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四年的几项主要工作总结和五五年农业生产计划草案报告》,档号:A7-1-56。由此可见,兴县能超额完成1953—1954年统购任务的很大原因在于农民有较多余粮出售,而余粮累积必需投入大量劳力,妇女的参与无疑又是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般来说,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春耕较少,秋收居多。这一情形在50年代发生改变。如1950年兴县妇女在春耕生产中,7区151村有女性劳力55519人,参加生产人数21321人,占总人数38.4%。将近2/5的妇女参加春耕生产,说明妇女开始作为重要劳力逐步走进农田生产核心圈。同时,妇女从事农田劳动类别更广泛,开荒、积肥、送肥、点种、锄麦、打圪拉、植树等劳动都有参与。据相关统计,在1950年妇女参与各项劳动中,保德2区229名妇女开荒864亩,每人平均3.8亩;神池3区1572名妇女开荒635.5亩,每人平均0.4亩;岚县1区妇女600人送肥4365担,每人平均7.3担;神池3区妇女485人送肥7093担,每人平均14.6担;岢岚2个村妇女130人植树406株,每人平均3.6株。(27)山西省民主妇联筹委会编:《1950年妇女参加春耕生产总结》,1950年7月印,第20、22、23、25页。
农村妇女有机会有条件从事主要的农业劳动,是体现“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只有通过农田劳动,农村妇女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才能改变人们习惯中认为的“妇女不顶事”的传统观念。1950年山西省妇联计划发动30%的妇女参加经常性农业劳动,并使之学习和掌握生产技术。(28)《华北各省妇联订出计划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5月6日。在工作好的地区,妇女绝大部分参加锄地、收割、打场等劳动,还有少数参加浸种、选种、耕耩等技术劳动,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已占妇女全、半劳力的50%以上,个别地方甚至高达80%左右,最低亦在20%—40%左右。(29)《全国妇联发布指示组织妇女参加春耕》,《人民日报》1950年4月6日。在此基础上,妇联还动员她们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农业劳动,如做好农忙准备工作,保证全年农业生产不违农时,特别是浸种、拌种、选种、抓虫等防治病虫害等工作。(30)《全国妇联指示各级妇联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
由上可知,在农田生产中无论参加生产人数的广度,还是从事具体农田劳动的深度,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在1950年代都比之前更进一步。她们除切草、喂牲口、担水、送饭外,一般都直接参加了春耕、夏锄、秋收等主要劳动。可以说,妇女在政治上的解放必须与经济上的解放密切结合,妇女自己编了解放歌:“土地改革翻了身,合作互助栽富根,婚姻自主结了婚,妇女们活的像了人。”许多男人亦说:“现在妇女可和从前不一样啦,再不敢小看啦!”(31)《山西省怎样发动农村妇女走上生产战线》,《人民日报》1952年3月7日。不可否认,正是有了经济上的解放,妇女政治上的解放才具“底气”。
三、走向社会:农村妇女分工的社会化
新中国初期,为了应对粮食压力和满足劳力需求,妇女被广泛地发动参加农田劳动,而两性共同参与赋予农田劳动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别蕴意。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开辟了道路,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妇女逐年增加,许多较好的农业社妇女劳动日数一般都占劳动日总数的20%—30%左右。当然,妇女劳动不能是无偿的,在报酬方面虽和男人一样挣劳动工分,但在劳动工分计量上却显得如此“廉价”。一些互助组、合作社不仅在妇女评分计酬中压低分数压低分值,或只记分不算账,甚至不把参加劳动的妇女当作社员而是看作短工。在一些互助组中普遍存在“男互助女单干”现象,许多互助组员和合作社员存在“重男轻女”观念,不愿吸收妇女参加或同工不同酬。(32)《积极领导农村妇女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人民日报》1954年3月8日。还有一些互助合作组织,妻子劳动,丈夫挣分。(33)《全国妇联发布指示组织妇女参加春耕》,《人民日报》1950年4月6日。此种现象不仅影响妇女生产及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且影响到农田生产效率及互助合作组织的巩固发展。
为解决上述问题,195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男女劳动力应该按照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实行同样的报酬。”(34)《积极领导农村妇女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人民日报》1954年3月8日。这一决议的颁布,无论从生产角度出发还是从妇女解放角度考虑,都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同工同酬”亦被看作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衡量男女是否平等的一个重要尺度。
1950年妇联发现互助组、合作社在评分计酬中存在男女不对等现象后,提出“男女同劳同分”“一家男女分别记分”主张,对于男女劳力计算应根据“同工同酬”原则,按劳取酬,以刺激妇女劳动积极性,纠正把妇女劳力一律当作半劳力的看法。(35)《全国妇联发布指示组织妇女参加春耕》,《人民日报》1950年4月6日。不过,虽然政府和妇联极力推进男女同工同酬,但晋西北至1951年各地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仍屡见不鲜,各地政府对“同工同酬”原则贯彻不够彻底。(36)《山西省怎样发动农村妇女走上生产战线》,《人民日报》1952年3月7日。
晋西北男女“同工同酬”问题与19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不同,关中地区男性逐渐退出棉田管理而转由女性接管,并由此导致棉花田间劳作工分下降,即不是男女“同工”,所以不能“同酬”。(37)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晋西北男性并未退出种植棉花、小麦、莜麦、麻等任何一种农田劳动,男性要求在生产中和妇女有一定分工,但不愿妇女完全代替自己。亦与湘北塘村不同,塘村田间生产中存在分别适合男女劳力特征的农活,男女从事不同的农活,故不能“同工”,也就不能“同酬”。(38)李斌:《农村性别分工的嬗变——合作化时期的湘北塘村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晋西北各地生产劳动基本上都需妇女同男性一起参加农业生产,特别是农忙季节,如锄苗、下种、抢种等,或者是细致繁琐的农活,如浸种、选种、锄草、经营棉田等。可以说,晋西北男女分工是在整个家庭计划下分工合作、各尽所能,其更多考虑的是田间需求及人员配合。至于报酬方面,因分工没有明确界限,故各地多采取死分活评评分方式或一定农活上按件计工制。如1955年兴县刘家庄等72社将妇女劳力按劳动能力确定底分,在此基础上按完成情况评分。(39)《关于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总结报告》,档号:A13-1-30。
上述记工办法确实提高了妇女劳动积极性。很多先进妇女在参加一般的田间劳作外还积极参加了全省农业技术改良运动,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广新式农具、浸拌选种、拔除病株、捕杀害虫等。岢岚县宋木沟村先进妇女提出“技术送上门”口号,亲自做发芽试验,挨家挨户宣传。先进妇女李改枝、陈俊英等帮助群众进行温汤浸种。据神池等7县所属198村调查,为了减少来年虫害,1951年妇女共刨、烧谷茬1738亩。(40)《山西省怎样发动农村妇女走上生产战线》,《人民日报》1952年3月7日。同时,妇女在劳动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较多的农业技术。妇女深度参与农业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们轻视妇女劳动的看法,亦减少了互助组有意压低妇女工分甚至不评底分的现象。不过,记工评分办法不能完全肯定是“同工同酬”,因为妇女单独确定的劳动底分一般都没有男性高,通常女性劳作一天能获4—6分,同时规定女性出勤天数为24—25天,而男性为28—30天。(41)被采访人白牛,男,兴县黑峪口人,采访时间2017年8月13日。在1956年9月兴县麻子塔村四联社制定的《秋收预算分配方案》中,预算劳动日方面男劳力劳动底分138.7个,女劳力底分79.7个,当年四联社总劳力259人,其中男劳力147人、女劳力112人(42)《麻子塔四联社秋收预算分配方案》,档号:A116-2-95。,可得平均每男劳力底分0.94个工、女劳力底分0.71个工,由此可见,单个女劳力的底分普遍不及男性。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妇女技术高低不一、劳动强度不同、劳动时间不稳定等,这均要被克扣工分。所以,在农田劳动记工中实际实行两种记工办法,即同一性别条件下的按劳取酬和按性别不同分别取酬。1953年兴县妇联工作计划中要求能劳动的妇女“全部参加农副业生产”,并“争取男女同工同酬”;(43)《兴县县妇联关于冬前的几项具体工作计划》,档号:A13-1-3。其中“争取”二字间接说明男女同工同酬不易实现,及诉求和现实之间存在不一致性。
事实上,即使妇女获得参与农田劳动的平等机会,亦并不意味着其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因为在中国家庭关系中,女性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那么,如何处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各地出现各不相同的问题。山西省妇联在总结1950年发动农村妇女参加春耕生产报告时指出:一些干部简单地认为“把妇女弄到地里就是‘发动’,参加了生产就能‘解放’,而不照顾家庭利益,不解决妇女特殊问题,因此不但妇女生产情绪不高,连男农民也反对。”(44)《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进一步联系与教育广大妇女》,《人民日报》1951年2月15日。为此,全国妇联指示要注意尽可能地解决妇女参加生产中的困难,满足妇女合理而又可能实现的要求。(45)《全国妇联指示各级妇联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
在妇女走向农田劳动过程中,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合理解决农忙时间妇女上地与做家务带孩子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难题,经互助组变通后由老人变工看孩子,妇女按时奶小孩及提前回家。(46)《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进一步联系与教育广大妇女》,《人民日报》1951年2月15日。一些互助组、合作社还组织农忙托儿所,如兴县1953—1957年建设计划中就多次提到要建立多所托儿所。(47)《兴县五三至五七年建设计划》,档号:A7-1-42。据1956年统计,兴县在266个社中建立81个幼儿园、1247个托儿组,共教养男女儿童6216个。家务、带孩子、农田劳动不仅把妇女时间碎片化,亦使妇女为应付不同工作精疲力竭,故这些组织得到妇女支持和拥护。妇女劳动时间的延长和稳定,对于其走出家庭和分工的社会化转型具有一定意义。如王家峁技丰社幼儿园成立后有6个小孩的妇女高兰英在6月份前已做61个劳动日,以往每日日常生活就使之焦头烂额。(48)《关于春耕生产总结和第二次整社工作的检查总结报告》,档号:A116-1-7。
20世纪50年代晋西北妇女对于农田劳动的广泛参与是在国家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背景下逐步深化的,妇女经济权益和政治地位开始得到重视,家庭地位随之改变。妇女性别分工的社会化,在促使妇女生产情绪日渐高涨、加速农业生产的同时,亦反哺于“男女平等”的主流话语。可以说,制度安排与农村社会妇女关系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
结 语
综前所述,晋西北农村的性别分工由传统意义的“男耕女织”“男外女内”,到20世纪40年代女性开始参与农田劳动,再到20世纪50年代普遍参与农田劳动且与男性“同工同酬”,其间的嬗变与农村现实需要和中共农业政策密不可分。事实上,对于男女分工这一具有复杂而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不仅中国学者给予关注,西方学者也予以多方探讨。一位西方学者甚至如此评述两性关系:“女人如果不是男人的奴隶,至少始终是他的附庸,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4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那么,男女真的无法平等吗?女性如何从男性附庸“物”的角色转变为与男性对等的“人”,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为两性关系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历史借鉴。
1940年代晋西北根据地生存堪忧,粮食、穿衣严重短缺,边区政府为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实现自给,广大妇女首次成为动员的重要人群;新中国初期,粮食问题依然突出,广大妇女仍被作为主要劳力投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20世纪50年代粮食增产作出积极贡献。女性大规模参与农业劳动,并同男性获得同样的劳动“报酬”,使得妇女开始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人身权利得到社会尊重,为新中国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契机。事实上,中共政权下妇女分工重心不在于妇女工种的变动,而在于其劳动价值已获“官方”保证和社会认同。正是因妇女劳动价值的质性变动,妇女政治、经济和家庭地位随之提升。妇女分工的社会化转型,对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并开始追求独立平等的人权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