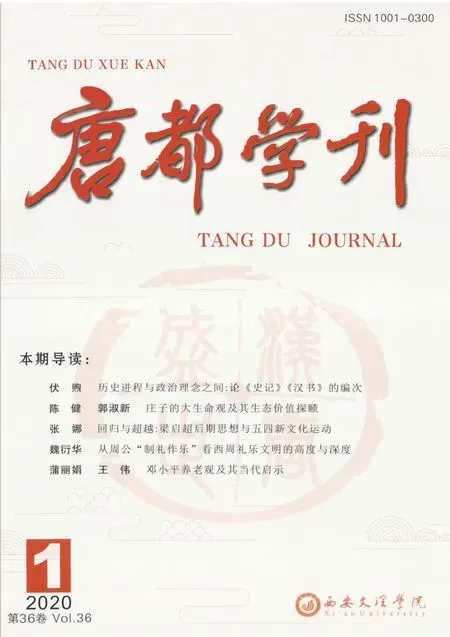《蜀道难》源流与“诗史”演变
2020-12-01蒲向明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与传媒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一、《蜀道难》溯源晋末而今见最早作品出于南朝
唐初文学文献《艺文类聚》卷42收录的南朝梁简文帝萧纲《蜀道难》曲,是我们现知最早的《蜀道难》乐府作品。或许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创作了类似乐府,但因未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知道其具体情况。诗体流变是一个逐渐演进的历史过程,具有源远流长的特点。
《蜀道难》旧题乐府的源头,至迟可追溯到晋末,从文献搜检可发现其蛛丝马迹。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0在萧纲《蜀道难二首》之下题注说:“《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蜀道难行》,今不歌。”《隋书·经籍志》称:“《古今乐录》十二卷,陈沙门智匠撰。”新旧《唐书》《宋史》著录13卷。王僧虔,南朝刘宋、南齐时人,其《技录》列《蜀道难行》于“瑟调曲”类,属于当时可传之曲,不传之曲另有标明。《古今乐录》云不歌者,系魏晋南北朝流行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蜀道难行》,已与萧纲《蜀道难》不属一个辞曲体系,其间并未有明确的继承关系。
所以,《艺文类聚》录“乐府”歌辞,发轫汉魏,先采自曹操《短歌行》,后面录有魏明帝(曹叡)、晋陆机作品,继之有六朝至隋代诗家如卢思道的作品数十首。而《蜀道难》曲则源自萧纲的两首作品:
建平督邮道,鱼复永安宫。若奏巴渝曲,时当君思中。(其一)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其二)[1]
很显然,第一首《蜀道难》曲并未吟咏到具体的蜀道。建平,郡名,在楚地巫山县。《舆地广记》卷33说:“中卞巫山县,故楚之巫都。秦昭王伐楚,取之以为县,属南郡,二汉因之,晋立建平郡,宋、齐、梁、西魏、后周皆因之。又《艺文类聚》卷六引《幽冥录》: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对,俗谓二郡督邮争界此。又《水经注·江水》:江水自建平至东界峡,盛宏之渭之空泠峡。峡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间远望,势交岭表,有五六峰参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像,攘袂相对,俗传两郡督邮争界于此。”[2]萧纲写巫山县的督邮道,重在突出一个人文地理的典故,很有文学色彩,但纪实性较模糊,反映蜀道就很有些游离表象。“二郡督邮争于界”的民间传说,最先收于《幽冥录》,《水经注》对此也是陈陈相因罢了。不同的是,《水经注》对督邮道的记述,却颇有生动之处,但让人从字里行间能悟出经三峡水路到达蜀地,真正不易。“鱼复永安宫”,显然是作者展开的想象。《汉书·地理志上》:“巴郡十一属县有鱼复。”《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迳南乡峡,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经对历史的追忆和回顾,渲染出一个大的人文场景,为后两句诗“写心”做好了足够的铺垫。全诗语句清丽而笔力雄健,一反其以往“轻艳”风格。巴渝曲,古代川东地区民歌,曲调凄婉。早在刘邦定三秦之前,巴地已有“巴渝曲”在民间传唱,汉初被釆编成宫廷乐曲传世。最后两句诗,声入情境,风格雅致而别有韵味,很好地体现了萧纲《蜀道难》乐府诗之作“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的特点。从萧纲第一首《蜀道难》可以看出,此作系他在都督荆、雍、梁、南秦、北秦、益、宁七州诸军事之际所写。因为他在较大的一个人文场景之中展开诗意,由所见所闻情思绵延,不禁浸入怀古幽思之中,故清人王夫之惊叹道:“小诗得如许高深,岂非绝唱!”[3]比较而言,萧纲的第二首《蜀道难》曲,前两句歌咏蜀道之难在于巫山、巴水的曲回和凄凉,对应于当时长江下游南朝政治中心入蜀的水道。所写场景阔大,用“巫山”和“巴水”二词描画整个长江三峡,利于营造诗歌意境。巫山,位于今重庆、湖北两省市交界,北与大巴山相连,长江穿流其中,形成三峡。巴水,《水经注·江水》说:“巴水出晋昌郡宣汉县巴岭山。”又《太平寰宇记》卷110:“巴水源出巴山,沿流合宝塘水。”此两句并非实指巴岭山或巴山所出巴水,而是代指三峡之水。所谓“三回曲”,言其迂回曲折。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说:“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水经注》所言三峡全长700里,为估测之数,1949年后实测仅193千米。后两句写船行在巴水之上,不断有阵阵悠扬的笛声传来,声调时高时低,两岸的猿啼不住,声断还续[4]。《太平御览》卷53引《荆州记》:“唯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峦叠嶂,隐天蔽日……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老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两句诗,在前面描画的场景之中,更是注入了声、情。江岸笛声传来,时低时高,悠扬婉转;而猿声凄清,时断时续,山谷传响,长鸣不绝。特别是最后一句,点化古《渔者歌》,意在抒写心中幽情,景、声、情三者融为一体,音律和谐,营造出一片清丽忧伤的新境界,令人回味无穷。
总起来看,萧纲《蜀道难》两首写巫山一带的险峻地势及蜀道水路之难,是汉魏以来历代文人有关蜀道诗歌创作持续层累的结果。作品虽短小,但不失凝练与旨远;用语直白,却不乏描写与渲染。从情感表达方式看,萧纲以当时最为兴盛的五言四句为体,浅易写实、直白单纯,触境寄情,言虽短却多巧思,具体展现了由楚入蜀的道路之艰险难行。
二、萧纲文学集团成员对《蜀道难》创作的继承和发展
差不多与萧纲同时,属于南朝梁简文帝文学集团成员的刘孝威,在萧纲《蜀道难》乐府诗创作上又有继承和发展。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42乐部二“乐府”载录如下:
玉垒高无极,铜梁不可攀。双流迸巇道,九坂涩阳关。
邓侯束马去,王生敛辔还。惧身充叱驭,奉玉若犹悭。(其一)
嵎山金碧有光辉,迁亭车马正轻肥。弥思王褒拥节去,复忆相如乘传归。君平子云寂不嗣,江汉英灵已信稀。(其二)[1]756
台静农《两汉乐舞考》最早注意到了这种继承关系,他指出:“《蜀道难》:古辞亡;《乐府解题》曰:‘《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阻,与《蜀国弦》颇同(唐吴竞《乐府古题要解》作又有《蜀国篇》与此颇同(1)鉴于本文引文较多,为行文方便且减少累赘,所引常见文献只用夹注标出篇名,不再列入参考文献或另外出注。)。’按刘孝威拟作云:‘玉垒高无极,铜梁不可攀’与古辞意同,是古辞六朝时犹存也。”[5]这里的“与古辞意同”,当然不是指与王僧虔《技录》所收《蜀道难行》相同,肯定是指《艺文类聚》之前所收萧纲《蜀道难》二首,但言蜀道“铜梁、玉垒险阻”是在陆路,就在川西经松潘、茂州、阴平、武都、祁山、天水、关山、凤翔、关中的陇蜀道上。这个《蜀道难》题意的开掘,刘孝威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至于《蜀国弦》《蜀国篇》等类似作品,而今不见有传,最大的可能是,它们属于六朝后期或隋唐时期的模拟之作,且思想艺术成就稍逊以致不传,似可解颐。
“玉垒高无极”,作者显然是用了夸张手法。玉垒,即玉垒山,在今四川省理县东南,汉晋六朝多作成都代称。西晋左思《蜀都赋》:“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刘逵注曰:“玉垒,山名也,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此注翔实精核,为后世所称许。宋代杨万里《送邱宗卿帅蜀》:“玉垒顿清开宿雾,雪山增重起秋风”;明代陆采《明珠记·江会》:“金城围日月,玉垒压函秦”;清代张素《拟李义山〈 井络〉》诗:“玉垒山前花黯黯,锦官城外鼓逢逢”等等均化用其意。“铜梁不可攀”,则比喻铜梁山之高。唐代李善注左思《蜀都赋》说“铜梁山在巴东”,《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山有石梁横亘,色如铜,连互二十余里,故曰铜梁,山岭平整,环合诸峰,此为独秀。”作者以此两句说明持节前往都督蜀地及周边军事,可谓使命重大。诗言虽简,蕴涵颇丰。第一首诗提及秦国李冰治水、汉朝王阳、王尊入蜀、三国邓艾偷袭阴平等历史故事,重在写蜀都西南道路的艰险难行。刘孝威《蜀道难》其二,在思绪上承接其一的内容,通过汉代王褒金马碧鸡的典故、司马相如通西南夷轶事,深化蜀道通西南在历史上的不易。《汉书·郊祀志》:“宣帝时,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故李商隐《为荥阳公上西川李相公状》称王褒为“碧鸡使者”[6]。最后两句,引西汉严君平和其学生扬雄事,他们虽学问、诗赋成就巨大,但因陇蜀道阻隔而莫名于时世、后继乏人,由蜀道艰难而生发出作者对蜀地人文衰落的无限感慨与悲哀。
刘孝威的这两首《蜀道难》,较之于萧纲之作,在题旨的开拓上已经现出眼界扩展、意境深化、人文历史丰富等显著进步和创新。在艺术上,葛晓音先生对其诗歌体式的继承与超越,有独到而深刻阐述:该作“一半五言一半七言”,“杂言句法伸缩,其换韵自有御风出虚之妙,七言则句法啴缓,转韵处必用促节醒拍,而后脉络紧遒,音调圆转”[7]。指明刘孝威《蜀道难》不仅避免了全篇五言的节奏单调,而且有助于表现思维的跳跃性,一改魏晋诗歌句式过于繁复、意脉不连贯的弊病,显然是艺术方面最独到的开拓。这两首作品前后照应,形散神聚,有对眼前景物的抒写,也有贯通古今的倾情联想,在内心感触不断蓄积的过程中,适配情绪的明、暗掩映和喜、愁交织,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稍晚,梁陈诗人阴铿作《蜀道难》乐府,以古人不畏蜀道之难的典故抒写眼前道路艰难,现实意义凸显,给人身临其境之感。阴铿系南朝大诗人,字子坚,生卒年不详,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梁时曾任湘东法曹参军,入陈后以文才为文帝赞赏,官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约卒于陈文帝天嘉末年。阴铿举止不同众人,又非世族,仕梁并不得意,早期的《蜀道难》乐府诗正是他借咏蜀道之难慨叹功名不易获得。在主旨的提炼上,一跃而升华为慨叹求取功名的危险。全诗如下:
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
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8]
这首诗表现陇蜀道之难的主要意象,是“高山积雪”“阴栈屡烧”“轮摧九折”“骑阻星桥”,但落脚点在蜀道难的含义上。诗以洗练的笔墨勾勒了自然形势的高险,缘景生情,不免使人感到自然的蜀道如此艰难,人生的履途何其坎坷,功名怎能轻易得到?这里不免融入了作者的身世之悲。起笔两句先从歌咏前人赴陇入蜀之事入手,赞扬汉代王尊不惧险阻、忠诚事国的行为。借对王尊的称颂,通过他赴蜀做益州刺史一事,引出对蜀地山川险阻的描写。中间四句,写蜀道险要难行,从大处写意着笔。高岷有雪,即岷山高耸、终年积雪。写陇蜀道艰难,自然会写到阴平郡的栈道(阴栈),一种于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而成的道路。《战国策·秦策》有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可见在早秦时期,它是古代川北、陕南、陇南一带重要的入蜀通道。栈道连桓、万丈深谷、悬崖峭壁——阴铿所见蜀道之艰难,亦满目矣。就连那坚固的车轮,也会摧折在九曲迂回的山路上;就是那骁勇的骑兵,也会受阻于七星桥前。最末二句,通过对蜀中山川险阻的具体描绘,发出“功名讵可要”的感慨。这正是生当乱世、屡历仕艰诗人内心矛盾的自然流露[9]。
阴铿此诗,虽是歌咏蜀中山川险阻这一传统内容,但它同时还赞扬了王尊,并流露出“功名讵可要”的思索,在思想意义上是有突破和丰富的。孙绍振先生《〈蜀道难〉:三个层次之“难”》一文认为,此“蜀道难成为功名难的隐喻”[10],观点较之前人有所突破。但他依然认为阴铿所写之“难”就是道路之难,自然条件和人作对之“难”,价值是负面的,虽有形容渲染,但毕竟在抒写心灵的层次上缺乏热情和想象。
三、梁陈初唐《蜀道难》:助推李白创作该题达至巅峰
南朝文学题材较窄,尤其诗歌创作如此。其时大多数诗人的作品不是刻画景物,就是描写艳情,究其竟,那时的诗人普遍还没有把写诗看成是表现时局政治、倾吐胸襟心思的手段,而只作为写景遣兴、迎送奉和的交际工具。然而,阴铿《蜀道难》有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特质,他以“体语具排”的方式来表现蜀道之难,发出功名利禄可贵,若为生命故,险途皆可抛的感叹。
从诗歌史的演进发展看,阴铿《蜀道难》为代表的创作,深刻影响到了后来唐宋诗乐府的创作。“阴铿《蜀道难》诗在句法、对仗、炼字、炼句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他和同时代的优秀诗人对山水风光的描写,对表现自然美的探求,都影响了后世特别是唐代的诗人。”[11]如杜甫铸就兼收并蓄气度的渊源,特别是乐府诗那些句式和传神的字眼,不免使人想到阴铿,当然杜甫也诚恳地说自己是下功夫学阴铿、何逊的。由此看来,阴铿的诗是由汉魏过渡到唐体的桥梁,他本人也是由古诗过渡到律诗的功臣[12]。在乐府旧题《蜀道难》的演变中尤其如此。
唐初张文琮《蜀道难》,就从阴铿的创作中得到了启迪。他在刘孝威、阴铿诗作已有夸张用词的基础上加以拓展。郭茂倩《乐府诗集》录该诗云:
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
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
张文琮(生卒年不详),唐贝州(今河北清和县)人,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三迁亳州刺史,永徽中拜户部侍郎,神龙中累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后出为绛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他今存诗不多,《全唐诗》录其诗仅六首。《蜀中名胜记》称此《蜀道难》作者为梁张悰,未云何据,后人多不取[13]。梁山,一名大剑山,在今四川剑阁县。此诗第一二句近似白描,写蜀道之难在“高险”。三四句写蜀道之难在“低险”。寥廓,空旷深远貌。郁盘,曲折阻滞。南朝梁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此江称豁险,兹山复郁盘。”李善注:“《子虚赋》曰:‘其山则盘纡岪郁’”。五、六两句使用了纪实又不乏夸张的手法,平视前眺,绝岭、危峦之间,时隐时现的飞桥和栈道伸向远方。飞梁,本指凌空架的桥,如郦道元《水经注·晋水》有句:“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在这里指悬空飞架于悬崖峭壁上的桥形栈道。从写作心理上看,作者仰视梁山天险,巉岩接天,俯瞰山谷深不见底,山路盘环,前眺栈道横架天堑。末两句揽辔长叹,是感慨路途艰难超出想象,也是对人生不易、生命存续的深刻抒发。诗人丰富的情感,因面对蜀道而得以深刻、全面地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大剑送别刘右史》诗:“金碧禺山远,关梁蜀道难。相逢属晚岁,相送动征鞍。地咽绵州冷,云凝剑阁寒。倘遇忠孝所,为道忆长安。”此写蜀道难,几乎涵盖了自刘孝威、阴铿、张文琮以来诸多《蜀道难》乐府旧题作品的借鉴与吸收:金马碧鸡典故、禺山遥远阻隔、关口梁山之险、忠孝所之九折阪等等,都进入了作者的抒写视野,表现道路开辟之难、跋涉攀登以及居留不易,归于对题旨含义的趋同性提炼,又做了不同角度的意蕴延展。从唐初张文琮、卢照邻的“蜀道难”作品主题看:或引用历史典故,或直叙蜀道沿途峻岭崔嵬,水流湍急;或两相结合,以实景抒胸臆,以情真景实写蜀道;语言平实简练,仍不失汉魏遗风;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又从中可窥见夸张、追忆、联想的写作意图,表现方式愈加纯熟,已较为明确地显现出太白笔法。有学者认为,卢照邻之作,或关涉“钟会入蜀通行的阴平道,曾经也实现了便捷的川陕(甘)交通”[14], 就是把初唐诗人写蜀道难,看作一个秦蜀道、陇蜀道的一个路网系统来对待,实现了不同视角的文学观照。
李白《蜀道难》,是整个乐府旧题《蜀道难》源流发展到盛唐的集大成者。就题旨而言,他表现的“难”,是一种立体化的展开。第一“难”,沿历史时间的纵向维度表达:古老而悲壮,对自然条件之“恶”仅作陪衬;第二“难”,重在写环境与“人事”之险,难到极端,令人听之色变;第三“难”,在于“咨嗟”,在于无言的感叹。全诗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回环感叹之中,形成一种节奏和韵味的微妙关系,激发读者的吟诵热情和多重想象。就篇幅和容量而言,李白《蜀道难》远超其前面诸作,这方面论者众多,各有解说,我们无意展开深论。但就乐府古体源流的突破性贡献方面,总体是一改空间上单纯铺排夸张,而是多重意象的复合排列,并且伴随着情感的起伏和跳跃。在时间上,通贯古今,把写蜀道之难与武公太白、五丁开山等远古神话传说维系在一起,以夸张笔墨写历史上不可逾越的蜀道险阻,拉开了乐府之章咏叹的前奏,妙在引人入胜。在空间上,着力刻画蜀道高危难行:岭绝胜于峨眉、高标接天、挡住六龙回日;回川险危见于冲波激浪、曲折回旋、水势令人心惊胆寒。在意象上,黄鹤难飞、猿猱愁攀、畏途巉岩、悲鸟号木、子规啼夜、飞瀑喧豗、崖石壑雷……形成多种美学蕴含交织。尤其写青泥岭(在今甘肃徽县境),并不立足于“悬崖万仞,山多云雨”的传统抒写,而是着意就其峰路的萦回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惧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在青泥岭上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即便未至该唐代入蜀要地,读之困危之状如在目前。在情绪上,生动描摹惊惧、感叹、惊悚、感慨、愤慨、称颂等方面,整体看惊与叹、赞与颂,水乳交融在全诗的字里行间。该作句式上的骈散交织,节奏上的缓急交替,色彩上的斑斓缤纷,点染着重重审美意象,这是以前所有《蜀道难》乐府难以达到的艺术高度。
表面上看,李白《蜀道难》是在奇、异、怪、险四个方面下功夫,其实不然,作品更深一层地揭示了社会人事之“险”。作者深切地意识到,蜀道险阻不免包括着军阀割据的政治隐忧。诗的最后,意象转折引起节奏上一连串的转化。散文式的议论句法,从慨叹地理位置的“险”,转变为忧虑潜沉独立王国可能的存在,已不仅仅是情绪的表达,而且出现了思想的转折,“可以引起我们对祖国河山和祖国的文学艺术的热爱的”[15]。面对思想意义与艺术形象之间的不平衡,作者采用了回避的办法放下,早还其家、侧身西望、长声感叹。但后续众多学者并不满足于此,用社会政治含义诠释诗的落脚点,于是有了忧戚杜甫、房琯犯剑南节度使严武,或讽刺唐王朝另一节度使章仇兼琼,或为安史乱后玄宗逃蜀而作等等揣度之说。在我们看来,明人胡震亨和顾炎武所论李白《蜀道难》“自为蜀咏”“别无寓意”颇为贴切。
四、《蜀道难》唐后余续与杜甫流离陇蜀之“诗史”
在李白《蜀道难》之后,乐府《蜀道难》题意的开拓与创作渐渐式微。唐代岑参《早上五盘岭》、罗隐《谩天岭》、韦庄《焦崖阁》、姚合《送李馀及第归蜀》、齐己《送人入蜀》等作品在题材上都写到了“蜀道难”,但无一直接用乐府旧题《蜀道难》创作,或许李白因《蜀道难》获“谪仙”的称誉和《蜀道难》的“光赫”,使他们心有畏葸,故用其他诗题写蜀道难之实,浅尝辄止而已。宋后政治中心变易,“西部时代让位于东部时代,蜀道文化衰落,运河文化崛起,梦回汉唐就成为元明清蜀道文学的主题”[16]。“蜀道难”成为历代墨客笔下道路难行、仕途险仄、人生不易的代名词。宋代梅尧臣《送杨浩秘丞入蜀》、石介《蜀道自勉》、欧阳修《送左殿丞入蜀》、汪元量《蜀道》、金代赵秉文《题王摩诘画明皇剑阁图》、元代魏初《毕舜举兰亭图》、明代王恭《拟唐韩君平送长沙李少府入蜀》、清代曾燠《蜀道难》等诗作可为代表。
在唐后,诗人创作《蜀道难》,不再师法魏晋六朝写意,而是直接模拟谪仙之笔。如南宋汪元量《蜀道》诗:“蜀道难行高接天,秦关勒马望西川。峨眉崒嵂知何处,剑阁崔巍若箇边。”[17]写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吟咏降香途中经历。作者从凤州至两当,南行经青泥岭到剑阁,阅尽关山险境,而峨眉亦已在指望之中。遍观全诗,创作之法模拟李白一看便知。明“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东里集》收《蜀道难》一首,也是以规范旧题的形式出现,先以山水视角直叙道路险峻,再写人马觳觫之状,兼用历史典故依托,而用岩崖鸟道意象承继李白笔法。他还有一首《度鸡鸣山马上口号与同行者》: “蜀道天下险, 王尊叱其御。何况鸡鸣道, 今随六龙度。”反衬、烘托之法与前作颇同。明代吴国伦《甔甀洞稿》收《蜀道难》二首,从不同角度切入主题,不离神话传说引申行旅之状,历史典故衬托蜀道之险。明代江源《桂轩续稿》录杂言《蜀道难》五言先闻其声,其后十句七言间用五言穿插,体语具排,从不同方位写蜀道险峻,又黏连着抒情感慨,在继承李白笔法上自筑格致,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清代曾燠《赏雨茅屋诗集》有《蜀道难》诗,开篇模拟李白,以从历史典故与自然奇险写行路之难,推想成分很多,但想象力却贫瘠匮乏。清人汤鹏《海秋诗集》录七言绝句《蜀道难》“石栈天梯蜀道难,长蛇猛虎怯追攀。可怜太白逍遥客,西顾蚕丛劝早还”化用李白诗句,多少体现了对太白《蜀道难》内涵的理解[18]。这些作品的意蕴主旨和蜀道内涵在《蜀道难》源流与李白诗作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更多地体现出社会大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对蜀道山水诗的影响,因而能触及人心,体现了很好的接受价值。
综观乐府旧题《蜀道难》源流的历史演进,创作手法上出现了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变,写景抒情实现了由景情分咏到情景交融的突破。特别是在诗式构思方面,李白《蜀道难》实现了以前诸作由感慨个人寄寓向社会性、现实性的忧生之叹的跃升,成为从自然山水与历史典故结合到极写山水化用典故与神话传说的分水岭。《蜀道难》源流以山水抒写行旅陇蜀、秦蜀的独具为特色,运用高山险途的诗歌意象冲击着历代读者的内心,极大地丰富了山水诗的内涵和意蕴,从中可以看到蜀道地域为中心的山水题材诗歌,展示了各个时代士大夫文人审观蜀道文化的多种心态和情致,具有深厚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最早记载李白《蜀道难》为旷世奇作并赞誉其为“谪仙”,是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9]
这段记载取录“触事兴咏”之“本事”,在写李白诗“本事”时捎带插叙了杜甫及其创作。贺知章在蜀道逆旅(客舍)慕名访见李白,地点应在青泥岭至京师之间,或在近于京师的客栈更为合理一些。贺初次见面对李白相貌的第一印象就是“奇其姿”,而后李白出示《蜀道难》,贺未读完就以不禁引起惊叹,誉为“谪仙”,以致金龟换酒、把盏尽醉。这个本事未记载贺知章的具体评语和惊叹言辞,但从赞誉为谪仙人的话语间,赞赏之情已溢于言表,以致以诗交友、似酒逢知己。或许,贺知章见李白《蜀道难》的惊叹,在“奇之又奇”,在于该作将蜀道的艰险铺陈得淋漓尽致,形象更为丰满,情感更为跳荡。特别是引入蜀国神话,将山川的险峻空间与历史的神秘时间结合在一起,越显示其艰难荒远,“惊风雨”“泣鬼神”盖出于此矣。相比刘孝威《蜀道难》写艰险山道中的历史人物,李白诗的长处在于将这些人物泛化,并非实指更能折射出多层含义,既可指友人,又可指自已以至古往今来一切在人生道路上奔波攀援的人。詹锳先生揣测《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均为同时之作,其中或有什么寓意[20],不免深受历史上比兴说诗传统的深刻影响,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
实际上,乐府旧题《蜀道难》源流发展至李白时期,已经形成了《蜀道难》题材的浪漫主义“诗史”现象。钱钟书指出:
盖“诗史”陈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辨者所敢附和也。[21]
李白沿用乐府旧题,在照应、铺排旧题的基础上,采取拟代方式结构意象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传统同类诗文的影响,但他又力求独创,在西晋张载《剑阁铭》的启发下引用历代防策议论衬托蜀道惊险,形成一个贯串全篇的完整蜀道意象。这个蜀道意象展示的艰难险恶内涵,既有自然性的一面,又有社会性的一面。就其自然性一面来说, 蜀道意象不仅是阴森险峻,又是宏伟壮观的;就其社会性一面来说,蜀道意象不仅是令人恐惧,令人哀叹,同时也表现着对于艰难时世的积极进取。李白创新就在于将如许复杂多端的感受、情绪、直觉、意志熔铸在蜀道意象中,因而使得意境奇崛,具有雄健奔放的情调。这种“诗史”现象,遵循浪漫主义为主的情感逻辑,运用想象、夸张,将神话与现实、自然与人生、古久与现今有机地、完满地结合在一起,达成“为情而造文”的高妙境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五、《蜀道难》源流与“诗史”内涵解颐演变
如果说乐府旧题《蜀道难》源流发展到李白及其以后,创作上出现了一种浪漫主义“诗史”现象,那么孟棨《本事诗》则捎带插叙杜甫及其流离陇蜀的创作时,真正揭开了现实主义特质的“诗史”之发端。《本事诗》先提到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诗成泣鬼神”,而后认为杜诗不仅写李白之人生经历,而且还记述他本人流离陇蜀的人生遭际,用“时人”之语评价“诗史”,以揭示杜甫诗歌尤其是其中陇蜀诗的性质及特点[22]。在孟棨看来,“诗史”的创作者杜甫对他本人日常生活的“诗化”抒写,虽突出特点在于叙事性和写实性,但题材范围不应扩展到杜诗全部,应该只限于其“流离陇蜀”的题材范畴。
杜甫“流离陇蜀”时,备尝艰苦,行道艰难,有“陇道难”之称[23]。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近半百的杜子美,从关中出发向北翻越陇坂到达陇右,再从陇右经成州同谷县入蜀而“一岁四行役”。具体行程是:年初自洛阳西行华州;七月,又从华州去秦州;十月,从秦州到同谷;十二月,从同谷县到成都(自陇右赴剑南)。他遭遇到了生活困顿和陇蜀道艰难:《秦州杂诗》其一“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发秦州》“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同谷七歌》其二:“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秦州杂诗》其四:“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空囊》:“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这里的“吾道”,就是他历经千辛万苦的陇蜀道。冯至先生说:这一年确是杜甫一生中“最艰苦的一年”[24]。苦难出诗人,杜甫“流离陇蜀”之行创作颇丰,达一百二十多首诗作,即便连章组诗也竟有10 组52 首(包括其中的五言律组诗)。这些作品载述了杜甫流离陇蜀的艰难,同时也叙写了秦州的风俗民情,并且描摹了从秦陇到蜀途中、陇蜀道上山川独有的奇险和壮丽,其中有关陇蜀道的两组24 首纪行诗后人多有评赞。苏东坡《风月堂诗话》卷上有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说:“(杜甫)两纪行诗,《发秦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无复差外。昔韩子苍尝论此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0指出:“(杜甫)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清初学者李因笃《杜诗镜铨》卷7不无由衷地盛赞:“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从诸多评语中可以看出,杜甫“流离陇蜀”道中创作的组诗重在纪实,以便对陇蜀道途风土人情、山川胜景和黎民生活予以生动呈现。与以往纪行诗偏重抒情不同,他这类“流离陇蜀”道中的系列作品,更好地突出了“有诗若史”的特点。
杜甫的“诗史”,因为陇蜀道而创作风格急遽变化。晚明诗论家江盈科《杜诗详注》卷8对此诠释云:“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以至写陇蜀山水成为“真手笔”。 康熙朝学人蒋金式《杜诗镜铨》卷7则从另一角度批注说:“少陵入蜀诗,与柳州柳子厚诸记,剔险搜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成此奇地奇文,令读者应接不暇。”当今学者莫砺锋指出:“就山水而言,只有秦陇、夔巫之地那样雄奇伟丽的高山巨川才能真正拨动杜甫的心弦,从而发出最和谐的共鸣。”[25]这种风格变化与《蜀道难》乐府有异有同,值得研究。
杜甫“流离陇蜀”的“陇道难”作品除了风格上与李白《蜀道难》有相近之处外,在写作地点上以青泥岭为交叉点,从不同视角反映了蜀道的险阻和人文色彩、自然景色的深厚与瑰丽。杜甫《发秦州》是流离陇蜀之“诗史”纪行组诗的首篇,有统领全组诗的作用,其中惆怅、郁闷的心情被融入对陇右山水的描绘之中,因而奠定了“陇道难”组诗也即“诗史”的基调(2)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蜀道难》诗在写作心理背景、表现手法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作品风格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杜诗沉郁质实而李诗雄壮豪放。这一点与本部分的论述关系较为密切,但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做展开。。而以李白《蜀道难》为代表的乐府旧题系列,以宽阔的胸怀去容纳蜀道上壮美的山川,以开朗的性格抒发别情,浑厚豪迈之情淡化了离愁别绪,同时开朗狂放之情又点染并强化了旷达舒怀氛围。同是写蜀道难,李白“谪仙”之笔表现出用虚的浪漫气息,而杜甫“诗史”之笔则显露着沉郁的写实痕迹。比较而言,“写实”比“用虚”难度更大,杜甫“流离陇蜀”的“诗史”实际是“戴着镣铐的跳舞”,能天马行空般自由、随意,可不受时空限制地去任意想象、夸张、虚构,像《蜀道难》那样,张扬出显著的个人色彩。
杜甫“流离陇蜀”的“诗史”,不乏优秀的乐府作品。杜甫的乐府取法阴铿、何逊,但表现力主要是在“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也有少数借用旧题来写新事的[26]。北宋《乐府诗集》收录杜诗古题乐府有《前出塞》(9 首)、《后出塞》(5 首)、《丽人行》《少年行》(3 首)、《前后苦寒行》(各2 首),总计22 首。葛晓音先生对此有所质疑,她提出判定新乐府的三大标准[27], 依此标准判定杜诗新题乐府共31 首:《兵车行》《苦战行》《大麦行》《贫交行》《去秋行》《光禄坂行》《负薪行》《折槛行》《最能行》《沙苑行》《锦树行》《蚕谷行》《岁宴行》《虎牙行》、“三吏”“三别”、《洗兵马》《哀王孙》《哀江头》《冬狩行》《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留花门》《客从》《自平》《白马》。赵海菱先生赞同这种分法,但指出如此之分对杜甫“诗史”乐府作品或有遗漏,如《凤凰台》。而且,她主张杜甫新题乐府有两个方面内容的作品应包含其中:第一是安史乱后自述漂泊陇蜀陷于困顿的诗,如《发秦州》《石龛》《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水会渡》等“流离陇蜀”的作品,具有哀时伤世的意义;第二是包含着特殊象征意义的一些咏物诗,如《杜鹃》《桃竹杖引赠章留后》《石笋行》《杜鹃行》等。赵海菱还认为,杜甫新题乐府(包括其陇蜀诗)应在五六十首左右[28],其中包括杜甫原始意义“诗史”的大部分作品,说明杜甫“诗史”所受汉乐府影响之深。就杜甫“诗史”内容与手法原初状态看,这些分析和研究相对于乐府《蜀道难》源流是有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的。
综上所述,孟棨以后,对“诗史”意义的解读发生了历史性的演变,正如冯至所言:“杜甫的诗一向称为诗史。我们现在也常沿用这个名称标志杜诗的特点,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29]。“诗史”不仅与“集大成”“诗圣”一起,成为杜甫的专享誉称,而且成为杜诗经典的主要条件或标志,即人所称道不已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认为,杜甫新题乐府中的陇蜀纪行诗(陇道难诗)具备的叙事性、纪实性特点,更接近“诗史”本义,带有更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些反映蜀道难的作品,并未停留于对史实本身的描述,而是尽可能以时事为背景映衬,将场景片断典型化,从而包含陇、蜀道难最大的历史容量,这种在陇蜀道上对生存境遇的强烈感受用他的新乐府表现出来,就更接近自六朝以来的旧题乐府《蜀道难》系列以史实为背景观照人生的创作意旨。而今众多后继者主动学习杜甫陇蜀“诗史”以诗记事、反映现实的艺术特点,由于创作意识的自觉,在有意之间逐渐形成了特有的“诗史”精神[30]。尤其是在陇蜀道和秦蜀道交叉点的青泥岭这个文学地理的位置上,李白和杜甫都发出蜀道难的喟叹,就如同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蜀道难》系“谪仙”奇文,并杜甫“流离陇蜀”之诗史于一道,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研究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学事象,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