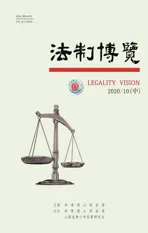论当代中国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和平衡
2020-11-30何献棉
何献棉
大新县发展和改革局,广西 崇左 532300
在司法实践中,公众评判案件结果的好坏往往基于当地的民风民俗、人情世故,即从情理角度出发。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因此,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当代中国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和平衡,让法律变得生活化、大众化,使法律为更多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纳。
一、法理与情理的辩证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当法理与情理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抉择?是应该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坚持法理,还是应该以为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坚持情理?抑或兼而有之?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基本的落脚点应是准确把握法理与情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情理是人类在长久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对事物的普遍认知,是被广泛接受的公序良俗、民间习惯等的统称,是普通大众可以接纳的对伦理是非进行评判的标准,它是基于一般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来衡量人的行为,不具有确定性,依靠人民的自觉遵循来体现。而法理不是大众的情感,它是对社会规范最高、最权威、最核心的归纳和总结,是创造法律规则的逻辑基础,具有确定性,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障。但情理和法理又是相通的,情理和法理都是对事物规律的归纳和总结,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所以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生相伴,密不可分。
二、法理和情理的冲突实例
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折射出了电影背后法理与情理的真实博弈。电影的原型陆勇2002年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随后由于国产药及骨髓配型不成功一直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陆勇在自己尝试吃印度仿制的“格列卫”后发现该药对治疗白血病效果不错,而且价格(500元一瓶)比瑞士生产的正版“格列卫”(40000元一瓶)便宜很多后,向广大吃不起进口药的病友推荐,越来越多的病友请陆勇帮忙到印度购买在国内没有卖的仿制药来维持生命,最终案发,陆勇被冠以贩卖“假药”罪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数百名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法外开恩,免予刑事处罚。
而何为“假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正)》第四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假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一)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三)变质的;(四)被污染的;(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六)所标明的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3]
从法理上来说,陆勇帮助病友购买的仿制药就符合假药的规定,其实施的行为侵害了国家的医药监管秩序和瑞士正版“格列卫”的商业利益,陆勇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司法机关从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角度出发,打击制售“假药”的行为是其职责所在。但从情理角度来说,陆勇所贩卖的“假药”因为价格低廉,使得许多因病致贫的病人能够买得起药,病情得以缓解,生命得以延续,让大部分患病家庭看到了生的希望。这就清晰地凸显出情理与法理之间的冲突。
常言道,“法律不外乎人情”,是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在制定法律或者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可接受度。尤其在执法过程中,既要考虑处罚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也要考虑社会大众的价值判断,符合朴素的伦理道德观。陆勇案能够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触碰了公众的“法感情”,以至于绝大部分人在看到此案时可能会推己及人地把自己放在嫌疑人的位置上来考虑、分析问题,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权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权利,理应高于国家的医药监管秩序和瑞士正版“格列卫”的商业利益。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深层次的因素,即任何医药公司斥巨资研制出来的最新药物,都可以被其他冠以治病救人的理由公开仿制,那就没有公司愿意研发新药物来抗击疾病,这对未来人类应对新疾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面对这样两难的情形,就需要我们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在法理与情理之间进行平衡。最终,2015年2月27日,湖南省检察院对陆勇做出不起诉决定,不起诉的理由之一是“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4]而陆勇案也引起了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关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关规定,为减轻广大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药费负担并有更多用药选择,自2018年5月1日起,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5]同时,明确大病医保能够覆盖更多的病症和更多的药品,扩大了医保体系覆盖范围,加大了医疗保障力度。
三、法理与情理冲突的解决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7]五大法治体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背后有情有义。要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词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让当事人胜败皆明、心服口服。”
(一)制定符合情理的法律,奠定法治建设基石
美国法学家霍姆斯说过:“法律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情关注,法律深植于人类的心性之中,法律的最大正当性,在于其与人类最深沉天性之契合无间。”[8]一部法律的制定,必然离不开基本的常理、情理的支撑。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当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伦理、亲情、道德等情理因素,使制定的法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和认可。而公众在法律制定、施行的过程中也牢固树立了法律信仰,奠定了法治建设基石。
(二)裁判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法官在裁判具体个案时,不应仅仅是简单地把法律规定套用到案件中,还要充分运用权责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在情理和法理之间反复考量、推敲,从中找出定分止争的最佳方法,用既不违反法律精神,又符合案件事实及情理的方式,[9]妥善裁决案件,以法理情理服人。
(三)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法治意识
通过持续不断地普法宣传教育,积极拓展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覆盖面,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营造浓厚的法律氛围,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让广大人民群众做到胸中有法律,自觉用法律指导自己的行为活动。
四、结语
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难题,是情理与法理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相互冲突的具体体现。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不论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或是普通大众都应当各尽其责,勇于担当,真正实现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与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