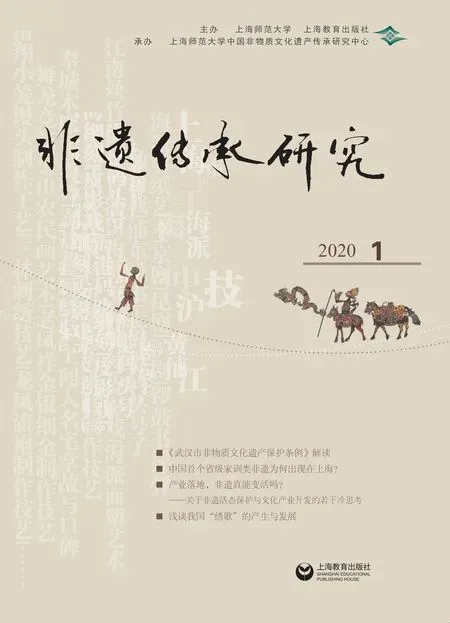产业落地,非遗真能变活吗?
——关于非遗活态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的若干冷思考
2020-11-30胡迟
胡迟
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这几年一直颇受热议。在众多的呼声中,文化产业开发成为非遗保护最好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也因此,媒体报道中出现这样的标题:产业落地,让非遗变活。
这个标题让我“细思极恐”。所以,今天我想追问一句:产业落地,非遗真能变活吗?
首先,我想回到原点,先来梳理一下非遗与文化产业的概念。我给自己提了四个问题:非遗是什么?非遗要保护的是什么?文化产业是什么?文化产业要开发的是什么?
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形成、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简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其特点是活态流变。
那么,非遗要保护的是什么?非遗要保护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而这些信息的载体,是传承人。传承人上承下传,将人创造出来的核心文化通过人进行完整的传递、传播、传承。
文化产业是什么?“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20 世纪初,最初出现在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or W.Adorno)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它的英语是culture industry,可以译为“文化工业”,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文化产业要开发的是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可以由工业化生产并符合四个特征(即系列化、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工精细化和消费的大众化)的产品(如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有声制品、视听制品等)及其相关服务。由此可知,文化产业要开发的是可供工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供大众消费的系列文化产品。
这么一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非遗要守护的是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是千变万化的活态流变性,是老祖宗薪火传万代的绝活绝技,是机械生产无法取代的技艺部分。由个人创造性始,最终的指向更是无限的属于个体的创造性。
而文化产业打造的则是一种程式化、标准化的产品制造体系,是一种将创意固化,以批量生产和高强度的市场营销进入大众消费的研发与生产。它要开发的,是能由机械进行标准化生产的项目。
其实,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可以交叉的部分极小,而它们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可以说是基本相悖的。
那么,为什么会想到用文化产业开发来拯救非遗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这是从终极目标倒推出来的。众所周知,非遗保护的三个阶段是:(1)挖掘、记录整理、存档;(2)传承、传播、发展;(3)让非遗有机融入现代生活。非遗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非遗有机融入现代生活。而文化产业的目的是什么?是生产出满足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产品。于是,顺理成章,一个创造性的想法就产生了:以非遗元素来生产满足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产品,让非遗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无缝对接。这个想法对吗?站在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说,完全对。因为对于一直忽略民族文化资源的文化产业来说,传统文化元素的注入是一次创造性的革新,是一次天才的激活,这一领域也会因为这样的一种思维转向,变得生机蓬勃。但站在非遗保护的角度来说,这种结合是喜忧参半的。
2005年至今,我们建构了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基本完成了非遗保护的第一阶段任务:挖掘、记录整理、存档。目前,我们已进入非遗保护的第二阶段:传承、传播、发展。正是此时,文化产业加盟了。注入非遗元素的文化产业以强大的生产能力与销售渠道让很多居于穷乡僻壤的非遗项目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就非遗的传播与普及来说,无疑是助火添柴。酒香也怕巷子深,混个脸熟总是好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结合充满忧患的另一面。因为,对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来说,以产业为主导,无疑是进入了舍本求末的误区。为什么呢?
一是就生产性质来说,非遗生产性保护需要的时间成本,文化产业付不起。
很多非遗项目是现代工业生产无法取代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项目正是因为包含着现代工业生产无法取代的核心技艺才,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录。比如宣纸的纸寿千年,在于它108 道工序环环相扣,其中自然漂白这一工序决定了宣纸能不能达到纸寿千年的品质。但自然漂白这一工序要经历四季风霜雨露,这样的时间成本与市场需求是不配套的。而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来说,这一程序不能减,因为这是宣纸传统生产的精髓。但对于很多文化产业来说,这样的时间成本,它们付不起。类似的例子还有云南的扎染工艺,因为市场需求陡增,为了节省时间成本,许多生产者以化学染剂代替植物(板蓝根)染料,破坏了云南扎染的材料要素。
产业化包含以下关键要素:市场化的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所以产业化会用各种工业化手法缩略程序,节省时间成本,以达到大批量、规模化的生产,满足市场需求。这种思维模式和生产模式在文化产业领域无可厚非,但对应非遗保护,就犯了大忌。
所以,产业化的宣纸和扎染生产,已经不属于非遗保护的范畴。不但如此,产业化的产品由于量多价低,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非遗产品的市场。如果以非遗保护名义进行产业化生产,更是失去了非遗保护的应有之义。
二是就生产者来说,传承人所秉持的工匠精神,容易被文化产业的商业运作消耗。
非遗保护项目朝着大的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许多传承人都去做生意,都去做企业家,家庭作坊变成规模企业,小型公司变成大公司,在当地成为纳税大户,成为榜样,成为明星企业,这是不少地方政府热切希望看到的事情。相当多的传承人都被当地政府绑架到这一个轨道上,给他们钱,给他们地,要求他们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但很多非遗项目,尤其是一些个体化的手工技艺,从构思到制作,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而它的价值也就在于不可复制的原创性与精工制造的精细与独特。如甘而可的徽州漆器制作技艺项目,徽州漆器做起来工序多,时间长,制作一件漆器长的要一两年,短的也要八九个月时间。制作量很少,甘而可工作室七八个人一年只能做十几、二十件漆器。不少人告诉他趁着现在信誉好、市场大,不要亲自做了,搞产业化,做大做强。但甘而可认为,徽州的传统漆器工艺种类很多,他现在更重要的事是静下心来把它们恢复出来,让人们看到徽州传统漆器的精品。他目前只收了6 名徒弟,他认为传承不能看规模,要看效果。他用心把这6 名徒弟带出来,徒弟们日后再去收徒,这样,徽州漆器的传承人就自然能呈几何倍数增加。这样的传承,不违反客观规律,也更有效。同样的例子还有吴水森家族的万安罗盘制作技艺项目。吴水森的儿子拒绝了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因为对于东南亚和日本市场,万安罗盘并不是一件单纯的工艺品,它是风水师的工具。吴水森家族制作的罗盘之所以工艺精良,功能精准,就在于每一个工艺环节的打磨,稍有失误,就要从头再来,因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且大多数制作环节是无法用机械取代的。
如果这些项目的传承人被绑架到产业化轨道上,成为集团老总,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商业运作消耗,自己为品牌代言,批量加工似是而非的产品。那么结果可能正如甘而可所说,30年磨出来的个人品牌,不出几年就会砸在自己手里。
这些能抗拒利益诱惑的传承人是有文化自觉的人。如果一味提倡产业化,并实行政策倾斜,很多传承人会被这种利益引诱冲昏头脑,走上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
三是就文化价值来说,非遗的多重文化内涵,容易被文化产业提取的符号元素消解。
任何一个非遗项目,都有支撑这个项目的诸多因素,如材料的因素、工艺的因素、工艺伦理的因素等,其中总有两三个要素是支撑这个项目人文价值的核心要素。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包含非遗元素的文化产品,号称“制以时变”,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拼贴。一个典型传统图案,贴在服装上,贴在钱包上,贴在手包上,贴在电脑包上……一个有多重文化内涵的非遗项目,在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渐渐变成了几个容易辨识的符号元素。这种所谓的创新与发展,是时代和商业的急就章。而非遗真正的价值,会被这些符号元素消解。另外,也正如冯骥才先生所担忧的,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经济潜力较大的、能成为卖点的便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那一部分则被搁置一旁,由此造成非遗被割裂与分化。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就是消失得最快的非遗。
四是就利益分配与文化自信来说,传承人的潜在利益被侵犯,文化自信被损伤。
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非遗具有群体性的特征,不是个人的独有产物,如何界定权利主体,目前尚无定论。但传承人作为非遗保护的主体,他们记忆里与技艺里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信息元素,应该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与利益的保障。但由于文化产业开发的介入,一些传承人的利益无形中被损害、削减乃至被剥夺。比如,目前正在兴起的产学研结合的开发模式就有不少有待探讨的地方。一般来说,项目开发首先要组建一支由顾问、研发、生产、销售四个部分组成的工作团队,顾问团队主要由文化行政管理机构人员组成;研发团队主要由公司设计团队、学院及相关非遗传承人组成;生产团队主要由公司、学院教师和民间工艺从业者组成,销售团队主要由公司相关销售人员组成。然后通过前期采风、企划方向、设计初稿、样品制作、产品整合、产品包装、产品推广、上市销售、调研总结的研发模式,研发出系列主题产品,并初步建立产供销供应链。
这种产学研模式几乎是很多非遗项目产业开发的基本模式。而且,从经济效益来看,确实在短期内实现了多方共赢。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呢?比如:这个团队里,非遗传承人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在研发生产中,传承人的话语权是否得到充分保障与尊重?公司和传承人如何进行利润分配?他们的知识产权是否得到保障?
这些问题,在具体运作中都会备受争议。通过调研发现,传承人对这种开发也是颇有疑虑的。虽然在开发原则中强调了尊重当地文化和传承人,保护个性,向民间学习等,但在具体运作中,传承人无形中成了弱势群体和帮扶对象。不论是在设计团队还是在生产团队,传承人都不处于主导地位。非遗保护十几年来帮他们塑造的文化自信,在产业化开发中又被吞噬,从审美趣味到传统技艺,他们都要被改造,以期适应市场。而且,这种开发以及培育出来的品牌,虽然让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最大的获益者(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肯定不是当地的传承人。当地传承人感觉自己的地方资源被外人主导垄断了,而他们——非遗文化的承载者、非遗保护的主体人群,成了文化产业的打工仔。这种隐性身份的落差,让传承人无法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情形,也是和非遗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非遗保护首先是护根、护本,而不是一味地对老树上残留的枝叶镶金镀银,招摇于世,谋取短期热闹和商业利益。非遗的创新发展是老树发新花,前提是我们要先护养这棵老树,让它自己焕发生机,而不是急着给它枝头缀满假花。
非遗元素能激活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开发有利于非遗的传播,但文化产业开发绝不能涵盖或替代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将文化产业开发作为非遗保护的正途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其实是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