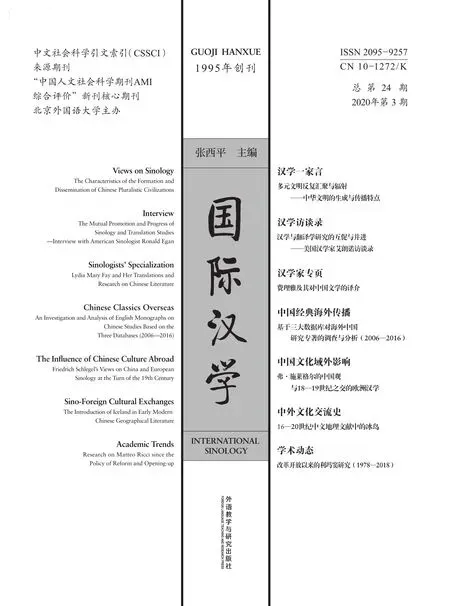《燕行录》中的商业演剧与“故国”记忆
2020-11-30任婷婷
□ 任婷婷
中国戏曲研究既应以本国文献为史料,梳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又须借助异域材料和不同的文化立场,补充本国材料之不足。葛兆光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命题中,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便是用周边文献资料来解释中国:“通过‘别国’来定位‘我国’,就像找镜子来反照自身,同时,对于‘我国’文化的定位如何,也决定对‘别国’即对于异国文化的评价”①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153 页。。
明清时期,朝鲜来华使团成员将其燕京(北京)之行及在华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朝鲜历史上将此资料统称为“燕行录”或“燕行文献”。通过《燕行录》中有关戏园和戏曲演剧的记录,以“从周边看中国”为视角,一方面可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247 页。,补充康熙至光绪年间有关戏园生态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观周边,考察中国戏曲在亚洲传播过程中,朝鲜王朝的接受意识以及受众的文化心态。
一、商业戏台及其经营
田仲一成(Tanaka Issei)认为“中国不存在清代初期北京戏园的详细记载”③田仲一成著,岸田利辉(Tosiki Kisida)译:《清初朝鲜使节燕行路程上所见的商业演剧之形成》,《曲学》2013 年第1 卷,第348 页。。的确,清代本土梨园文献多为对演员、剧本的品评与整理:以乾隆年间《燕兰小谱》为代表的“花谱”一类文体,多为对男旦演员的品评、排名、传记以及他们与文人诗词唱和、交往的记录;清代刊印的戏曲剧本《缀白裘》,收录当时剧场经常演出的昆曲和花部乱弹的折子戏,是具有演出脚本特点的剧本整理。而《燕行录》中的相关戏曲文献,虽偶有对演员的记录,却较为零散,并非撰者关注之重点,往往在叙述剧情时一笔带过,正如金昌业在观看《姜女望夫》时写演员的出场:“其女人,即前扮作秦桧妻者,其实男子也。其声音容态,酷似女人”④程芸:《〈燕行录全集〉演剧史料辑录》,《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1 页。。洪大容在观看《正德皇帝翡翠园故迹》后用同样方式提及演员:“有男子略施脂粉,扮作艳妓,泰色极其美,往往为愁怨状。”⑤《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26 页。除此之外,《燕行录》中更无对剧本的记录整理,仅仅是在叙述中提到剧名而已。
虽鲜有对演员与剧本的关注,但《燕行录》却补充了本土文献之不足。朝鲜使者聚焦戏台,尤其关注带有商业性质的“剧场”——不仅记录茶园和流动戏台的建筑,还关注其创建和经营管理,无论是京城奢华的戏园演剧还是村舍的流浪艺人,都是他们的关注对象。这些记录使我们看到清代戏园生态之全貌,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史料。正如程芸所撰《“燕行录”戏曲史料的学术价值初探》一文中指出:“古代朝鲜使行的‘燕行录’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戏曲史料,有关城市商业演剧和宫廷承应演剧的记载尤其值得重视,可以弥补我国本土史料的某些不足。”①程芸:《“燕行录”戏曲史料的学术价值初探》,《戏曲艺术》2013 年第2 期,第65 页。
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的《场戏》一文是较有代表性的观戏笔记,此后燕行使臣或其弟子多模仿此种记录方式。②比如金晶善于道光十三年所撰《燕辕直指》中的《场戏记》一文,在写作模式、行文风格、观察视角等方面明显模仿了《场戏》。参见《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41—243 页。此文用大量笔墨描绘所观茶园戏台的建筑:
其屋上为十三梁,倚北壁筑数尺之态,围以雕栏,即戏台也。方十数步,北隔锦帐,帐外有板阶一层,上有六七人,皆执乐器,笙簧、弦子、壶(胡)琴、短笛、大鼓、大钲、牙拍等诸器备焉。锦帐之内,戏子所隐身换装也。左右为门,垂绣帘,戏子所出入也。门有柱联一对,句语妍丽,上有扁,曰“玉色金声”,曰“润色太平”。周悬羊角、花梨、绡画、玻璃,诸灯皆彩线流苏、珠贝璎珞。台之三面环以为阶,以坐观者。其上为板楼一层,亦三面,周置高桌,桌上西瓜子一楪(碟),茶碗七,糊胶一钟,其香丝一机,终日不绝火,为吸烟具也。桌之三面,俱置凳子,恰坐七人,以向戏台。后列之凳桌更高一层,令俯观无碍。③《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25 页。
这段文字非常详细地还原了清朝戏园的样貌,从戏台的材质、规模到上场门、下场门,甚至演员化妆间,记录周详。从戏台规制到门柱的装饰上可见此戏园的高贵奢华,观众台三面面向戏台,分两层,每桌能坐七位观众,桌上摆有茶、瓜子、糊胶、烟具,一应俱全。其实,早在洪大容之前,金昌业就已非常关注戏台的样式:
戏屋之制,长仅三丈,广二丈许,上皆覆簟,去地六七尺,铺板为棚,分其前为轩,后为室。室三面围簟为壁,室轩之间隔以帷。凡戏子共十余人,而惟登场者在轩,余皆在室中。每扮戏,自室中出来,其换服色,又还入室中,盖戏具皆藏室中也。④同上,第221 页。
朝鲜使者早期对戏园的观察笔记奠定了此后《燕行录》中戏曲演剧的记录基调,这种基调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他们每每观看戏曲演出,总会留意茶园戏楼或村社戏台的构建,且以金昌业和洪大容的记录模式为参照。
从《燕行录》的记录来看,清代戏园、茶园中的戏台都属于比较高档的观戏场所,戏台建筑华丽,观众台亦很壮观。比如金晶善看到的广德堂:
戏台之制,筑砖为广厦,高可六七丈,四角均齐,广可五六十,间间皆长梁。就北壁下截九分一设间架,隔以锦帐。帐左右有门,门垂帘子,盖藏戏具而换服之所也。帐前向南筑方坛,周可七八间,此则演戏之所也。⑤同上,第241 页。
广和戏楼与广德堂一样,皆属于规制宏敞的豪华戏楼,道光三年(1823)对此记录如下:
四面设层楼,雕窗朱栏,金币新鲜。中央起一屋,隔半为室,戏徒与戏具皆在其内。室外有厅,宽广,布龙文大毡,为设戏之所。⑥同上,第251 页。
到了道光十年(1830),广和戏楼比之前更为华丽:
楼制极宏敞,栏槛四围如口字。中设戏场,可以倚栏而临视。梁椽之间,下垂铁索,悬以羊角绣灯,几为数百颗,所以备夜燕也。楼上间间障隔,而每设床桌椅子,所以处观戏之人,而每间贳银四两,饮食之需亦入其中云。①《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45 页。
从《燕行录》中对各个戏楼的记录来看,高级戏楼的规制大同小异,②再如据金昌业《赴燕日记》中记录:“至其处,则有十二梁大楼,方正层阁,内为八十余间,中央作堂,倡辈游戏于此。铺以氍毹,高床椅桌左右排置,帷幔幡幢旗帜剑枪备在。楼前金额及柱联金字,照耀有光。乐夫主壁各踞而坐,隔间后面若室,倡夫易服于此,金鼓吹锣之具皆在其中。东西设门,垂以锦幄,戏西出而东入。楼四面作层轩浮栏,层层坐人观望。四均楼上积千百坐桌,周置庭中井,井作间逐行定坐,各主一床,而坐后者架两叠床,正对戏楼,无枳蔽妨碍之患。”参见《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54 页。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传统戏台相似,可见清朝的戏园建筑已经非常成熟。
在《燕行录》中,不仅可以看到诸如“广和楼”这种奢华戏台,乡舍间的戏屋也给朝鲜来华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小村坊无庙堂处,则必趁上元、中元设此簟台,以演诸戏。尝于古家铺道中,车乘联络不绝,女子共载一车,不下七八,皆凝妆盛饰,阅数百车,皆村妇之观小黑山场戏,日暮罢归者。③《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31 页。
虽临时搭建戏台,用绣帐隔出演员的化妆场所,不如戏园宏制,但基本设施齐全,亦能吸引乘车前来观看的观众,且“容止极其都雅”,观众质量与戏园茶园中并无太大差别:
见最巨架屋之上设高棚,以红碧绣帐中分而障之。帐内即是诸戏汉妆着戏具、换面改头、做出戏本之地,而帐外即是戏基,设长桌,有吹笳弄笛之人踞桌而坐。左右栏边设交椅,使观光者踞之。与上使设交椅于棚下而坐。且有男女之来观者,皆妆盛饰乘车而来,驻车于棚下,仍乘车观玩,容止极其都雅。④同上,第246 页。
这些“冲州撞府”的流动艺人,并没有足够资本搭建戏屋,只能临时搭建簟屋设戏,停留日期多则十余日,少则数日,再辗转到其他地方。虽戏台简陋,数两银子便可观看他们的演出,但演出非常精彩,令朝鲜使臣“大欢乐而忘归”。
东归至玉田县,见街上设簟屋张戏,乃与数两银,拈戏目中《快活林》以试之,乃《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事也,比本传小异,或谓戏场之用,别有寅(演)本也……令人大欢乐而忘归,然后知一世之狂惑有以也。⑤同上,第226 页。
当然,朝鲜使者的目光并未只停留于这种带有“剧场”性质的戏台,还深谙其商业化的经营模式,对商业化演出表现出了格外的敏感。乾隆三十一年(1766),洪大容《场戏》一文最先观注戏庄的成本与经营:“正阳门外有十数戏庄,自官征税,有差。其大者,创立之费银已八九万两,修改之功不与焉。则其收息之繁富,亦可想也。”⑥同上,第225 页。道光十三年(1833),金晶善记录更为详细:
无论中外,凡演戏之处必有戏台。其出财营建者,谓之戏主。其创立之费银已七八万两,又逐岁修改,招戏子,设戏收息,上纳官税,下稠戏雇,其余则自取之。其收钱之多,可知也……南西东三壁别作层楼,每一间各有定贳,南壁正中最上楼贳为白银十两云。南壁西隅只设一门,一人守之。⑦同上,第241 页。
又曰:“观者到门,先收钱乃许入。观者之众寡,债为之低仰。”⑧同上。戏台的创立成本大概在七万到九万两银子之间,戏园中可坐数千观众,但观众的位置不同,所花费用亦不相同:“人各出钱,有差,无钱者坐之阶下,上下可坐数千人,男左女右,不相杂乱。”⑨同上,第249 页。在商业化程度如此高的戏园中,若满座的情况下,除去纳官税、招戏子、雇员工的成本,利润相当可观。
观众秩序维持得有条不紊,更能体现清代戏院经营管理的正规化。戏园中观众从入场到观看的流程清晰:
观者到门,先收钱乃许入。观者之众寡,债为之低仰。戏事方始,戏主为设茶酒果羞及溺器于各人之前,观到剧处齐笑齐止,无或喧聒。虽淫亵嬉慢之中,节制之整严,有如师律之不可犯,亦足见大地规抚之一端。①《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41 页。
足见管理者的严谨,而观众“其终日观者,无少喧哗,但闻笑声。他人所坐之凳,不得杂坐,坐者不复立,盖防于瞻视故也”②同上,第238 页。,如同今天的剧院,非常讲究秩序,不能乱坐,更不能到处走动。观众之间亦可相互监督,作者还讲述了最初进入戏院时,由于不懂剧院的规矩而造成的窘状:
盖余自初强聒,既大违其俗,乘虚攘座,真东国之恧习,而苟悦目下,不俟明日,又东人之躁性。其戏主及帮子之许之,若不欲拘以礼俗然也。同坐者皆相避身,亦有厌苦色。③同上,第226 页。
观众自身对于约定俗成的规矩也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正如洪大容所见:
凡楼台上下,可坐累百千人,凡欲观戏者,必先得戏主标纸粘于桌上,乃许其座。一粘之后,虽终日空座,他人不敢侵。标座既满,虽光棍恧少,不欲强观,习俗之不苟也。④同上,第225 页。
《燕行录》中对戏台和商业演剧的关注与中国文人对演员和剧本的青睐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其中原因何在?事实上,朝鲜时代的戏剧还未成熟,多为歌舞戏等百戏性质的戏剧,正如田耕旭所撰《韩国的传统戏剧》中记载:
朝鲜时代,戏剧主要演于乡傩(傩礼)、中国使臣接送、闻喜宴、水陆斋、盂兰盆斋、官办活动、邑祭、洞察与士大夫家宴上,而至朝鲜后期,流浪艺人集团辗转民间,作形式多样的演出。此外,还在举办各种国家庆典与地方官府活动时也进行演出。其戏一般被称为傩戏、傩礼、傩、山台傩礼、彩棚傩礼、杂戏、百戏、歌舞百戏、与山台戏,归根结底皆属于散乐百戏之类。⑤田耕旭著,文盛哉译:《韩国的传统戏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30—131 页。
按照王国维对戏曲的定义,“以歌舞演故事”⑥王国维:《王国维论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年,第126 页。,朝鲜时代的戏剧只见“歌舞”而未有“演故事”,故仍处于“前戏剧时代”。受本国戏剧生态的局限,朝鲜使者对戏剧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即使在北京观看到如此成熟的戏曲演出时,仍然难以聚焦充满戏剧性的舞台表演和故事情节。此外,语言的隔阂和对中国戏曲表演手法的不熟悉也造成了欣赏障碍,“但既不识事实,真是痴人前说梦,满座欢笑,只从人裒如而已”⑦《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26 页。。
二、舞台上的“故国”文化记忆
《燕行录》中的戏曲史料,既补充了清代戏台资料,又阐释了朝鲜王朝在叙述中国戏曲过程中所彰显的文化心态:由于深受儒家文艺观念的影响,“厌清思明”的文化心理浸透在字里行间,故笔记中不免有对戏曲演剧过度解读的现象。
朝鲜使者认为文艺能反映社会盛衰、政治得失,这种将文艺与政治联系起来的观念显然受到中国儒家文艺观的影响。正如他们所言:
每设一本,呈戏之人无虑数百,皆服锦绣之衣,逐本易衣,而皆汉官袍帽。……自黄帝尧舜,莫不像其衣冠,随题演之。王阳明曰:“《韶》是舜一本戏,《武》是武王一本戏,则桀纣幽厉亦当有一本戏。”今之所演,乃夷狄一本戏耶!既无季札之知,则未可遽论其德政,而大抵乐律高孤亢极,上不下交矣。歌清而激,下无所隐矣。中原先王之乐,吾其已矣夫!⑧同上,第232—233 页。
对儒家文化十分推崇的朝鲜使者将清朝视为“夷狄”,认为清朝没有“季札之知”,更不懂得通过音乐来观察德政。文中不仅引用明代王阳明的话作为立论根据,且大发议论,断言“高孤亢极”的音乐风格是上层统治阶级和底层老百姓不能交流的表现,“歌清而激”之音则是底层百姓没有隐忍痛苦的证据。儒家思想要求文艺作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讲究中和之美;当朝鲜使者看到“高孤亢极”的花部盛行时,痛心感慨中原先王之乐已逝,足见他们对儒家文化之推崇。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使者格外重视戏曲劝善惩戒的功能。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观得民间演剧时记载:“然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劝惩”①《九州学林》2010 年春夏季,第222 页。,又有“究其本,则似出于劝善惩戒之意,而状多骇异”②同上,第234 页。,并将戏曲的道德教化提高到与《诗经》相同的地位:
且以忠孝义烈,如《五伦全备》等事,扮寅(演)逼其真。词曲以激扬之、笙箫以涤荡之,使观者揪然如见其人,有以日迁善而不自知。此其惩劝之功,或不异于《雅》、《南》之教,则亦不可少也。③同上,第225 页。
中国儒家文艺观中,无论是诗文的“兴观群怨”说、“怨刺上政”说、“文以载道”说,还是戏曲中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都以教化为文学艺术之根本,重视作品对人格塑造的熏陶作用。正是因为将儒家文艺观作为戏曲鉴赏的注解,朝鲜使者在观看戏曲演出时,出现了对戏曲服饰过度解读的现象。中国戏曲的服装以明代服饰为基础,虽有汉、唐、宋代服装的痕迹,亦吸收清代服装的造型和图案,但主要风格仍是明代服装特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而在朝鲜使臣的眼中,戏曲的服装却有了另外一层深意。洪大容观《游龙戏凤》时描述演员服装:“其官人皆着网巾、纱帽、团领,宛有华制。耸肩大步,顾眄有度,所谓汉官威仪者,其在斯矣。”④同上,第226 页。对戏曲服饰并无深入研究的朝鲜使臣,看到舞台上着明代风格戏服的演员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其“汉官威仪”,认为这是汉文化的遗风,并借此追忆大明王朝。洪大容又写道:“惟陆沉以来,汉官威仪,历代章服,遗民所耸瞻,后王所取法,则非细故也。”⑤同上,第225 页。可见,汉文化的威严在他们心中已然根深蒂固,戏曲衣冠乃保存汉文化的方式,并非“细故”。朝鲜使者不谋而合地对戏曲服饰采取了这种接受态度,戏曲服饰唤起了他们对汉文化的追忆之情:“《扮戏》:清音阁起五云端,粉墨丛中见汉官。最是天家回首处,居然黄发换朱颜”⑥同上,第234 页。,并为只能在舞台上看到汉族衣冠而悲痛感叹:“嗟乎,中州衣冠扫地而尽,乃因倡戏而见,岂不痛哉!”⑦同上,第238 页。又有“而前代冠服制度,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尤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⑧同上,第222 页。他们在严禁穿戴明朝服饰的高压政策下,借戏曲舞台来追忆先朝汉文化,并赞美戏曲演员的这种文化传承。徐长辅在《蓟山纪程》中有记载:
有百十红衣军,手奉一队黄布帐,自西而前,瞬息间遮其庭,设为三门,而场戏之具皆从门入,各藏假面,其阔袖、圆领、幞头、大带,一应先王法服,或绝类东制,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也。⑨同上,第237 页。
约定俗成的戏曲服装在朝鲜使臣眼中变成“礼失而求诸野”,这种解读在今天看来言过其实,实际上蕴含了朝鲜王国对“故国”明王朝和汉文化的怀念以及对礼乐制度的敬畏:“清箪楼台绛帐垂,城南大路迎胡儿。王风委地求诸野,礼乐衣冠尽在斯”⑩同上,第238 页。,“其戏都是倡优之技,不足为奇,惟其服饰之华丽、器物之精备,非数万金不能办”⑪同上,第251 页。。
事实上,《燕行录》中所体现出的朝鲜使者对中国戏曲的接受,实乃其个人视野和历史视野的结合。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提出的,人的理解活动受其“前理解”的制约:“我们之所以将某事解释为某事,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先见与先概念之上,解释决不是一种对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觉因素的领悟。”①姚斯、R. 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21 页。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认为,接受者的社会历史是构成“前理解”的要素之一,因此接受者受到历史因素所造成对接受对象的“偏见”,不仅是历史现实本身,并且是接受者理解的条件:
如果我们愿意正确对待人类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至关紧要的就是实实在在地为偏颇的概念恢复地位,从而认识到有些偏见是合理的这一事实。②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第7 页。
朝鲜使者对清代戏曲接受的“前理解”即是几百年来朝鲜王朝与明清两代的政治纠葛。
历史上,朝鲜王朝一直与明朝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政治交往。李成桂自1392 成立王朝以来,多次派往朝鲜使节往返中朝两国,向明朝皇帝进贡。《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悉赉便番,殆不胜书。”③张廷玉等:《明史》,卷320,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468 页。1592年,日本攻打朝鲜,明朝出兵救援,与朝鲜共同抗日七年之久,明朝在朝鲜人心中早已有再造之恩:“其兴灭扶颠之德,与天无极,此古今属国之未始有德于天朝也”④吴晗:《朝鲜李朝史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3991 页。,而朝鲜王朝与清朝之间是皇太极分别于1627 年和1632 年分别攻打朝鲜所建立起来的宗藩关系,因此朝鲜王朝心理上更认同明朝,对清朝则是不得不臣服,表现出厌恶鄙夷之感,甚至流露出反清复明的想法。从朝鲜使者出使中国所撰见闻的名称便可以管窥此心理差异:明朝时称为《朝天录》,而到了清朝则称《燕行录》。可见,他们将明朝皇帝视为天子,而清朝只是北京之行的所见所闻。
这种政治立场使朝鲜王朝在文化观念和认识体系上更认同明朝的文化,并以“后明朝”和“小中华”⑤有关朝鲜王朝的这种文化心理,葛兆光在《宅兹中国》的“明以后无中华:朝鲜人的观感”一节中有详细论述。参见《宅兹中国》,第153—157 页。自居。王政尧在讨论这这一问题时也持此观点:
对于朝鲜李朝历届使臣和学者而言,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在每一出戏中都能看到的以明代为主、几乎占领舞台的各种戏服!更何况中国传统戏曲的服饰还具有不受朝代、地域和季节限制等特点,从而,使朝鲜李朝历届使团成员们交口称赞!他们存在心灵深处的那种“厌清思明”的心结在清代戏剧舞台上得到了满足和释放,他们享受了这种精神慰藉,并看到了希望。⑥王政尧:《朝鲜〈燕行录〉著者爱戏辨析》,《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5 辑,第166 页。
一方面,清代戏曲演出的兴盛给他们带来耳目一新之感,他们的文字中流露出对繁华演剧的热衷;另一方面,由于“厌清思明”的文化心理,使其面对如此兴盛的戏曲演出时仍无法投入纯粹的艺术欣赏中。带着这种矛盾的心理,朝鲜使臣才表现出如此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接受心理。
结 语
通过对《燕行录》中有关中国戏曲的文本解读,一方面摆脱长期以来的西方视角,在亚洲视野内反观中国,正如葛兆光所言:
我觉得,不能不改变长期以来习惯地以 “西方”(尤其是欧洲)为尺度和背景来观察中国,以及用现代的政治国家来讨论历史的文化中国的方法,可能需要通过“周边”(或者像日本人说的那样叫“周缘”),来重新审视中国这个特别的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历史存在和现实意义。⑦葛兆光:《想象异域》,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6 页。
另一方面可借此来考察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心态,进一步研究中国戏曲在亚洲各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