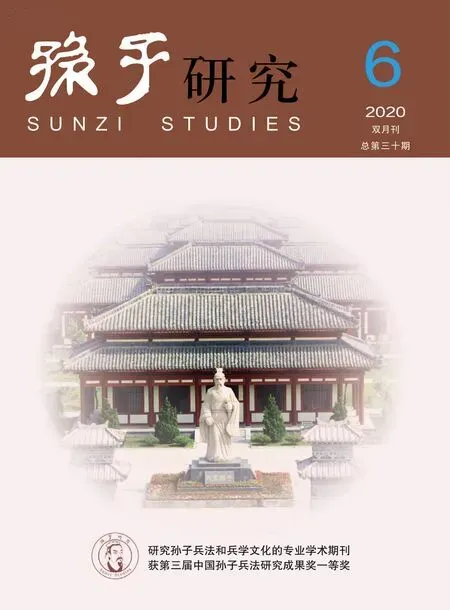邢玠与《经略御倭奏议》
2020-11-30罗琳
罗 琳
邢玠(1540—1612),字搢伯,号崑田,明代益都(今属山东青州)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曾任密云县令、陕西按察使、大同巡抚、云贵总督等官职,在边二十余年,颇有威名。万历二十五年朝鲜战争再度爆发后,邢玠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粮道经略,全面负责援朝御倭战争的事宜。本文拟对邢玠援朝御倭战争前的军事实践、《经略御倭奏议》的军事思想以及其在援朝御倭中发挥的作用略作探讨。
一、援朝御倭战争前邢玠的军事实践
援朝御倭战争前邢玠的军事实践主要是治兵西北和戡播之役。邢玠进士及第后,任密云县令。任职期间,鼓励民众修筑长城,对于防御蒙古族铁骑起到了重要作用。万历三年(1575),邢玠擢升为浙江道御史,巡按甘肃;万历六年(1578)担任河南按察使司佥事,“主管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1]。万历十年(1582)转任山西行太仆寺卿,在宁武驻防,自此开始了他的文官治兵之路。邢玠在治兵宁武初期,宁武军纪松散,军队混乱,宁武守将王大纲提出以军饷抵顶采青费,并暗地安排军士300 余人逼挟粮饷,鼓噪作乱。邢玠沉着应对并果断采取措施,逮捕作乱之人,“责以大义,咸蒲伏请罪。遂按法诛王大纲等八人,余无敢动。嗣后二十年无脱巾之呼”[2]。从而稳定了宁武驻军,加强了军事防御。
万历十二年(1584),刑玠晋升为山西粮储参政,不久又升为陕西按察使,治兵甘州。甘州地处偏远,地势险要,时常遭受蒙古族骑兵劫掠,百姓们苦不堪言。邢玠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专门安排部下深入牧区了解骑兵动向,以便做好防御敌人的准备。“公精设间谍,每先知番夷动息,以扼其吭。夷犯土窑,则出精骑击之,擒斩数十。邀其归路,几歼矣。夷下马乞哀,许之。罚牛马千余。”[3]同时,水塘一地,因为水源充足,牧草茂盛,当地百姓和士兵每年都会在此地储备大量的牧草,饲养牲畜,而蒙古庄秃赖部则经常对水塘一带进行劫掠。对此,邢玠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公令多以畜饵之。虏益深入,焚燎四合,先于水口设三伏以待。虏见火惊走,炮弩齐发,击杀数百人,所遗失无算”[4]。慑于邢玠的威严,别部皆胁息,曰:“邢公真天威!不敢再窥边矣。”[5]
万历十八年(1590),邢玠被起用为山西布政使,随即晋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当时明朝的北部边防形势十分严峻,邢玠果断行事,对大同军务进行了严格整治。调整将帅,以李东阳代替麻贵为大同总兵官;整顿武备,整饬军纪,更新兵器,开展屯垦,并报请皇上批准,拨款增收粮草,储备日丰。即使在宁夏发生兵变时,邢玠也没有放松对北部边境的防御。果然,蒙古史车部乘宁夏发生兵变之机,派遣2000 多骑兵侵略大同属地火焰堡,邢玠设伏将其全部擒获。最终,史车部为其折服,不敢犯边。
万历二十二年(1594),邢玠担任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川贵,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因为邢玠在驻边时经常与少数民族打交道,深谙恩威并施之效。所以,邢玠一入蜀,便“一面宣谕朝廷恩威,一面牌催两省刻期整饬兵粮,如其负固,自当议剿”[6]。邢玠到达四川后,一方面镇压、剪除与杨应龙结党之人,同时对杨应龙进行招降,以免他殊死反抗,造成明军更大的伤亡和损失;另一方面,他令云、川、贵三省军队随时准备剿杀杨应龙。杨应龙在得知朝廷决定大开杀戒时,心中大为害怕。当他得知可以伏罪时,便立即决定俯首称臣,上报朝廷,表示愿意把罪人及罚金献于朝廷以求减罪。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邢玠根据朝廷旨意下令有关官员处理此事,最后的处理结果为:杨应龙穿着囚服在松坎匍匐郊迎,并且上交十二名罪人及四万两赎银,以此来抵消他的死罪,朝廷将杨应龙革职,并由其长子暂代,将其次子杨可栋押做人质。同时朝廷在松坎设立了同知治理,以重庆知府王士琦为川东兵备使,压制杨氏势力。
邢玠在西北治边,彰显了其优秀的治兵才能。在平定播州土司之乱时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略,不但为朝廷免去后顾之忧,也间接地为最终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邢玠在边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为以后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经略御倭奏议》的军事思想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月,明朝与日本的和谈破裂,邢玠意识到事态严重,特意向朝廷建议,应尽快向朝鲜境内运送粮草和其他物资,随时做好应战的准备。朝廷接受了邢玠的建议,先后调整了兵部以及负责援朝御倭事务的官员,并于三月二十九日“升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7]。于是,邢玠随即亲赴朝鲜指挥作战。在战争期间,邢玠就有关战争事宜的建言,及时上奏明廷,并且得到万历皇帝的回复和支持,有关邢玠在东征过程中的上疏被称为《经略御倭奏议》。今存《经略御倭奏议》五卷,是邢玠援朝御倭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主要包括三方面:
其一,水陆结合,输送粮草。粮草问题一直是影响战局的关键因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亘古不变。邢玠在《经略御倭奏议》里就有关粮草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言与策略。他汲取了战争初期因粮草匮乏影响军事行动的教训,重视后勤保障,上奏明廷令“山东巡抚将原发官银买籴米豆及应解临、德两仓二万石折色银两,趁此秋收,分投籴买,装船发运”(《经略御倭奏议》卷二)。针对朝鲜境内战乱频发、筹粮困难的情况,主张以国内运粮为主,并采取海运与陆运相结合的运输方式,“合行保定抚臣行各府,即动该府勘用银两,分派所属州县,各一二十头,速买膘壮骡,每府二百头,则众轻易举,旬日可办。仍限四十日内解赴辽东,抚院分发各道,驮运粮饷”(《经略御倭奏议》卷二)。通过添买众多骡头来缓解辽东地区的挽运之苦。
同时,朝鲜北面多崇山峻岭,道路难以行走,遂以海运作为运粮的主要路线,对于在海上运输粮草而言,船只的需求及打造极为重要。邢玠在《募造海船以济挽运疏》中建言:“查得宽奠地方有木可采,足供船料,有匠可召,皆知船式,而一应钉铁、麻油等项,给登莱运船顺买甚便。在此打造,力省功倍,臣与辽东抚臣面相计议,办此似亦不难,仍应行该镇抚臣转行该道,委官速造运船可载五百石以上者三十只。人夫匠役取之本镇,工价银两取之备倭,陆续成造,陆续接运。” (《经略御倭奏议》卷二)以此通过建造较多的海船来增加粮草的运输。随着援朝明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军队所需要的粮食补给亦不断增多,为了保证明军所需兵食及缓解辽东、山东转运粮草的压力,邢玠在《议增天津海运疏》之中,具体分析了天津海运的可行性,他认为“以水路论之,则由临德而天津,由天津而旅顺,皆是一水可通,天津易而登莱难”。(《经略御倭奏议》卷二)通过增设天津海运,增加运送军粮的能力。
面对明军军粮不足的困境,邢玠多次上书请求增派粮草,基本上保证了朝鲜战场上的粮食供应,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户部侍郎张养蒙在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报发运实收粮数疏》中曾说:自(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本年七月初八日止,据辽东共报运过粮294740 余石,山东共报运过粮125930 余石,天津共报运过粮83180 余石,报后又几一月,不知所发几多,总三处共运过粮503850 余石,此报发之数也。[8]从明朝境内转输至朝鲜的粮草,数量庞大,以辽东、山东、天津三地输送量最多。在邢玠的高度重视和合理安排下,朝鲜战场上的粮草供应基本得到了满足,没有因为粮草问题对战争产生干扰。从而稳定了军心,为援朝御倭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保障。
其二,多兵种配合,灵活作战。邢玠注重集中优势兵力,向敌军展开猛烈进攻,同时又能根据朝鲜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水、陆等不同兵种的配合作用。首先,抽调土兵援朝。其选募的土兵,主要是当时西南土司手下的士兵。邢玠在上疏中称:“土兵则土司所以自卫其人,以兵为业,以战为事,以立功报朝廷为荣。”[9]他认为土兵骁勇善战,战斗力极强,广泛调动西南诸司土兵不但可以增加朝鲜战场的兵员,而且也能够削弱西南地方的兵力;其次,招募水兵。邢玠认为朝鲜国三面环海,日本远征朝鲜必走水路,要想扼制日本,水兵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水军加以配合,陆战就难以取得成果,并且由于缺少水兵,援朝战场上战略部署也会受到影响。邢玠多次上疏朝廷要求调拨水兵,“为今之计,须得急调浙直、淮安、闽、广舟师一二万,由近而远,陆续自外洋以抵朝鲜”(《经略御倭奏议》卷二);“长鬐水兵止五百船四只,极其单弱。此处非添兵船,水陆并举,未可轻进”(《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同时,邢阶认为福建海澄县一带贩卖的西洋商船,“其船极坚而利,其军火器械极精而锐,其人习于水战”(《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因此,邢玠鼓励福建等地的商船、水勇参加水军,按照水兵的待遇发放银两招募他们参加援朝战争,同时训练部分陆兵参加水战,以此来解决水兵人数不足的困境。
在邢玠的多次上书请求和朝廷的大力支持下,浙江、福建、吴淞等地水兵相继调往朝鲜战场,陈璘、邓子龙、李舜臣等著名将领也陆续赶赴朝鲜,朝鲜战场的水兵作战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邢玠重视水军,抓住了朝鲜战场的关键。水军实力的增强,使得朝鲜战场上水、陆等各兵种有机地配合起来,使明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
其三,注重情报,协调与各方的关系。邢玠强调知己知彼,重视收集情报。同时主动维护与明政府及各有关机构的关系,也注重调动属下将领的积极性。邢玠全面负责朝鲜战争,对当时战场上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和实地考察,并如实地向朝廷汇报。当他了解到日本水军活动频繁的时候,随即在国内旅顺港和山东登州一带进行布防,防备日军北上侵略我国沿海地区;当了解到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欲全线撤退时,随即下令各路军队全力进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此外,他要求前线领兵的将领必须在了解战场详情后,再做出部署,不可随意下令。从丁酉战争后期的情况来看,明朝军队制定的作战方案较为合理,避免了盲目作战现象的出现,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
邢玠面对“国家亦时常用兵矣,曳襟掣肘未有若今日”[10]的现状,注重协调与各方的关系。援朝战争,明军身赴异域,得到朝鲜的配合尤为重要。邢阶在刚入朝时,就严明军纪,确保军队秋毫无犯,以获取民众的支持;注重搞好明军与朝鲜军队的战略配合,使两国士兵能够协力御敌;重视与朝鲜君臣的合作,虽然邢玠对于朝鲜君臣消极避战的态度不满,在上疏中也曾指斥他们“该国各处城垣任其倾颓,不一修举”(《经略御倭奏议》卷二),但为了抗倭大局,他仍着重于团结朝鲜君臣。邢玠亦注重与明廷各相关机构的关系,尤其是维护好与万历皇帝的关系。邢玠将战场上的情况及时向明廷汇报,增加透明度,以便得到各机构的支持;援朝战争期间,从明朝各处调兵来朝,这些明军入朝前彼此互不统属,关系难以处理。邢玠处事公平,坚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原则,恩威并施,利用自己的威信,加上灵活的策略,使众将听命于己,保证了军队内部的和谐。各方关系的维护和协调,使各方得到了平衡,避免了相互掣肘,达到了高度的军事权统一,提高了决策效率,为援朝御倭战争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三、《经略御倭奏议》在援朝御倭战争中的实践及评价
《经略御倭奏议》中的军事思想在援朝御倭战争中得到应用并取得显著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威信,稳定军心。在丁酉战争初期,日军来势汹汹,明廷百般掣肘。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邢玠临危不惧、镇静自若。他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援朝御倭的决心,“公既至军中,标剑登坛乃誓曰,必破倭,有死无二”[11],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并且,在南原之战失败后,他亲自赶赴王京指挥作战,及时挽救了败局。随后,邢玠指挥明军在稷山展开阻击战,“稷山大捷”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的进攻。此后,日军开始南撤,明军南进,迫使日军退守于朝鲜东南沿海一带,极大地鼓舞了中朝两军的士气。此外,邢玠干净利索地处置了内奸沈惟敬,对于朝中的投降派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在邢玠的部署安排下,朝鲜战场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明军逐步站稳了脚跟,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虚实结合,奇正相生。邢玠善于运用计谋,强调以智取胜。丁酉战争之初,明军尚未完成集结,形势危急。邢玠大布疑兵,虚张声势,号称水陆兵七十万人,使兵力明显占据优势的日军摸不清明军的虚实,不敢轻易进攻。与此同时,邢玠还主动在蔚山一带发动了多次进攻,让日军穷于应付,没有察觉到明军主力尚未集结,以较少兵力牵制了日军主力,为援军顺利到达争取了时间,使明军化险为夷。此外,他采取反间计,利用日军统帅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等人之间的分歧,实施离间计,“是以臣玠亦将计就计,一交代即先为二檄谕安惟敬,并以安倭之心”(《经略御倭奏议》卷二)。他让沈惟敬写信与日军,提出愿意与他们和谈,利用小西行长为首的主和派的厌战心理,分化日军,成功地瓦解了敌军的攻势,延缓了日军的进军步伐,为明军的主力集结争取了时间。
第三,抓住时机,主动出击。蔚山之战失败后,明、日处于相持局势。邢玠审时度势,对在朝明军进行了调整部署,并上书请调水陆兵,他认为“陆兵可得七万有余,水兵可得二万有余,果能一时齐集,水陆分布,亦可足战守”(《经略御倭奏议》卷二)。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月下旬,邢玠接到朝廷快报,丰臣秀吉抑郁成疾,于伏见城病死。日军五大老和五奉行无心恋战,向在朝大名们发出了全线撤军的命令。邢玠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他抓住机会,命令陈璘统领明朝水军全力以赴,截击沿海日军,重点进攻顺天驻军。经过半个月的阻击战,最终取得了露梁海战的胜利,这对援朝御倭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重视后勤,有备无患。邢玠在援朝御倭战争期间始终坚持有备无患的理念。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中日和谈破裂时,邢玠就建议明廷尽快向朝鲜派遣军队、运送粮草,让朝鲜做好准备,以防备倭寇的袭击。同时,无论是在战争前还是战争期间,邢玠都一直上书请求增粮、增兵。粮食充足、兵源的及时补充为持续作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日军基本退出朝鲜之后,针对军队撤留问题,邢玠在《善后大将疏》《酌议留兵粮饷疏》中上书暂留部分军队和将领在朝,防止日军卷土重来,等到时局彻底稳定下来再全部撤军,并上疏条陈了朝鲜安定的十条建议,规划了朝鲜战争之后的重建工作。
在援朝御倭期间,邢玠临危不惧,稳定了军心,为下一步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同时采取灵活的战术,布疑兵、寻战机,为明军的主力集结争取了时间。他始终坚持有备无患的理念,重视增粮增兵,防止日军反扑。这些战略思想,对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邢玠是一位具有治兵才能的统帅,在边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援朝御倭战争的过程中,邢玠的《经略御倭奏议》所蕴含的战略思想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粮草的供应还是战术的运用及各方关系的协调方面,都对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注释】
[1]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五《职官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7 页。
[2][3][4][5]叶向高:《苍霞续草》,明万历刻本,第30、30、30、31 页。
[6][7][9]《明神宗实录》,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246、5772、6021 页。
[8]张养蒙:《张毅敏公集》,载《明别集丛刊》,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518 页。
[10]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二,民国影印明万历刻本,第1 页。
[11]孙继皋:《宗伯集》卷一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