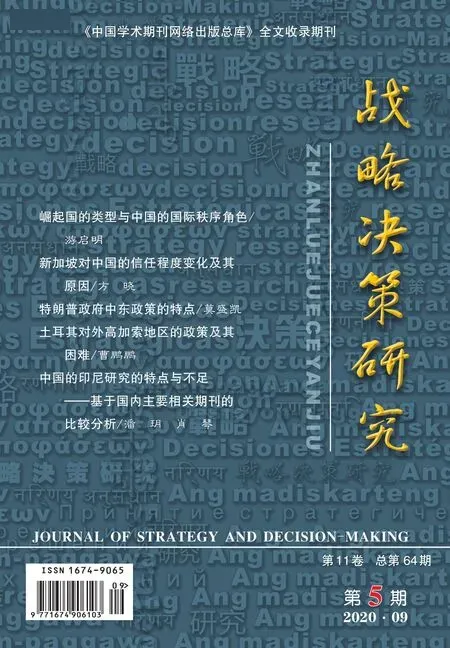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的政策及其困难
2020-11-30曹鹏鹏
曹鹏鹏
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十分重视与外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关系发展,①外高加索又称为南高加索,本文主要指高加索山脉以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所在地区。积极开展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双边关系,配合美国、欧安组织和北约的地区政策,反对俄罗斯在该地区军事存在和影响力。通常情况下,土耳其新任总统、总理和外长的首次正式访问,都会选择阿塞拜疆。②Ibrahimov Rovshan,“Turkish-Azerbaijani Relations and Turkey's Policy in the Central Caucasus“,The Caucasus&Globalization,Vol.5,No.3,2011,p15.1991年3月,土耳其总统奥扎尔(Turgut Özal)首次访问了阿塞拜疆。11月,土耳其成为国际社会第一个承认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独立的国家。1992年5月,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对阿塞拜疆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为了协调与地区其他国家关系,土耳其成立“土耳其合作与发展机构”,旨在加强外高加索地区国家的经济和外交的合作关系。2000年,土耳其政府正式声明,将外高加索地区作为其外交的重点侧重地区,并开始积极寻求在原有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的基础上扩展为突厥国家联合体。土耳其外长伊斯梅尔·杰姆(Ismail Cem)表示,“我们在外交政策的所有领域都强调并依靠我们的共同历史和类似的文化描述。虽然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确保土耳其与新独立国家的政府和商业机构密切合作,但土耳其在文化领域的努力旨在与这些国家的社会和公民建立共同的文化领域和友好甚至兄弟般的关系。”①Gaber Evgenia,“Turke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The Post-Soviet”,Central Asia&the Caucasus,Vol.12,No.3,2011,p.140.土耳其为何如此重视外高加索地区?土耳其对该地区的政策有什么特点?面临哪些困难?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的重视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苏联解体导致外高加索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大国力量在中东地区持续交织与碰撞。土耳其顺势而为,更加重视和拓展在地区的利益,最为显著的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另一方面也试图成为塑造地区秩序的大国。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lu)②其最初是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的首席顾问,2009年5月初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他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出版于2001年的《战略深度》一书。参见H.Tarik Oguzlu,“Turkish Foreign Policy at the Nexus of Changing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Dynamics”,Turkish Studies,Vol.17,No.1,2016,pp.58-67。认为,土耳其可以利用其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与欧洲和美国保持密切联系。这其实是对土耳其传统外交思想的继承。③胡雨:《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4期,第48页。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后,土耳其的安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安全概念不仅包括军事,还包括经济、能源、社会和其他方面。新政策被描述为“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外交政策的经济化”和“贸易国家的崛起。”④K.Kirisci,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9-57.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的政策是基于文化和宗教的亲和力,共同历史根源和经济相互依存将其“软实力”传播到周边国家,而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成为其在地区追求的主要战略利益。
(一)经济利益
土耳其由于与外高加索国家有着特殊的文化及历史纽带,不仅表现出对外高加索地区安全议程施加影响的浓厚兴趣,①李艳枝,常守锋:《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实践及其制约因素——基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实践》,载《中东问题研究》第2016年第1期,第112、114、123页。而且基于地缘战略优势加强与外高加索国家的经济联系。自外高加索独立以来,土耳其在该地区积极推行经济政策:每年都增加投资;在长期项目中承担财务义务;实现了国家援助计划,总体上在两个地区都取得了突出的地位。在独立初期,1170多个土耳其代表团访问了高加索国家。时任土耳其总统的厄扎尔和总理德米雷尔亲自发起了多领域的经济项目,几乎所有土耳其国家的大中型企业都参与其中。在官方访问期间,土耳其领导人几乎总是由土耳其工商会成员和大型建筑、纺织和食品公司主要负责人陪同互访。1992年,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发展署(TIKA)成立,其目的旨在向与土耳其接壤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用以建立和发展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促进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②Gaber Evgenia,“Turke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The Post-Soviet”Central Asia&the Caucasus,Vol.12,No.3,2011,p.142.
由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敌对关系使得自1993年以来双方边境一直处于封闭状况。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构想试图建立横跨欧亚的东西能源经济走廊,将里海能源和其他贸易商品出口到西方。该倡议旨在通过非俄罗斯路线和绕行亚美尼亚的方式向西方市场出口区域资源。而土耳其和格鲁吉亚之间114公里长的边界和双方的合作关系基础成为这一问题解决的路径。1993年7月在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格鲁吉亚运输委员会会议上,首先提出在卡尔斯和第比利斯之间建立“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The Baku-Tbilisi-Kars railway)作为替代方案。2004年阿塞拜疆被纳入该项目议程,扩大成为连接“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沿线的经济往来,旨在建立土耳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直接铁路运输,以便利和增加土耳其和高加索之间以及欧洲和亚洲之间陆路运输通道,并增加土耳其在区域政治中的影响力。尽管由于财政和政治障碍,该项目的实施速度有所减缓,但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国家元首最终于2007年2月成功签署了框架协议。2016年10月,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成立了“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协会”。2017年4月,上述三国又签署了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协议,为使这条线路从商业角度更有吸引力,各方简化手续,降低运价,提高通关效率和货物运输能力。上述协议被认为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高加索地区提供经济推动力,是欧亚大陆地区经济联系的关键部分之一,将使外高加索国家的触角延伸到欧洲、中亚和中国。有助于提升制造业能力。并将使土耳其有更多的机会在该地区实施其经济项目,拓展土耳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影响力。
其次,外高加索地区周边拥有巨大的能源资源,它正成为里海石油出口欧洲的门户,新的能源运输走廊的形成必将极大地改变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埃尔多安政府执政后,土耳其不断推动建设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aku-Tbilisi-Ceyhan)输油管道。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被视为土耳其成为区域能源贸易和运输中心的战略因素,也是发展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关键平台。①Russia and Turkey in the Black Sea and the South Caucasus,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June 2018,pp.18-23.并且在经济能源上,土耳其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在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建设方面的合作,以及爱琴海海岸新建炼油厂和集装箱港口的建设,将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经济伙伴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水平。2014年5月底至6月初,双方签署了新的投资协议,进一步推动了双方合作。土耳其-阿塞拜疆伙伴关系的深化正在为该区域合作创造可行性框架。②“Deepening Turkey-Azerbaijan Economic Partnership Creates Framework for Regional Bloc”,Turkish analysis,July 2014,http://www.turkeyanalyst.org/publications/turkey-analyst-articles/item/334-deepening-turkey-azerbaijan-economic-partnership-creates-framework-for-regional-bloc.html土耳其在外高地区地缘政治的基础问题是能源安全的问题,土耳其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达达尼尔海峡,俄罗斯和其他黑海国家的大部分石油贸易都是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并确保从沿“里海-黑海”沿岸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安全战略,不断整合欧亚大陆西部能源地缘版图,极大地提高自身在国际能源事务中的话语权。1990年,土耳其前驻美大使苏克鲁·埃立克达赫提出成立一个“黑海经济体”的主张。在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逐步策动下,主张渐渐迈入实施轨道。1992年6月25日,在土耳其的建议下,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希腊等11个黑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物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签署了实施黑海经济合作计划的计划协议。①奥马尔·法鲁克·根奇卡亚:《黑海经济合作计划——对欧洲一化的来自于一个地区的挑战》,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4年第4期,第115页。黑海经济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后,其不仅倡导在区域一体化,包括形成边境经济区和建设“欧亚走廊”(TraceCA),还旨在促进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但是“黑海经济合作计划”作为一种协调各方国家关系的一套经济安全机制,几乎没有为沿海国家提供实质的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也没有为外高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路径。
(二)政治利益
苏联解体导致原加盟共和国中的突厥语国家和族群地带出现,并构成地区的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土耳其试图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和睦邻政策为其在该地区的安全政策发挥作用,将外高地区的独特位置转变为一项战略资产,更好地发挥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作用,并增加与俄罗斯在该地区政治博弈的筹码。特别是打通中亚地区,通过建立"突厥语联盟",而与高加索和中亚突厥语国家形成的新政治势力建立以土耳其为轴心的“跨欧亚大陆的新地缘政治"版图。
外高加索独立之初,土耳其就频繁进行与相关国家的高层互访,期望建立政治互信,强调土耳其与高加索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相互联系。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②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土耳其国内一直认为“在宗教意义上,我们是伊斯兰人;在种族意义上,我们是突厥人;在文明,意义上,我们是西方人”。
其次,借助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组织在对高加索进行文化输出。在外高加索地区诸国国内议会代表、商人群体中拥有大量土耳其裔。①Ziya Onis,“Turkey and the Post-Soviet States:Potential and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fluence”,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No.2,Summer 2001,p.67.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试图与高加索和中亚的新国家建立影响和发展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成为影响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利益集团。其中包括能源企业以及从事文化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如创建教育机构以培养一批地区国家的未来政治精英,目的是促进与土耳其的密切互动。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基金会,如由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费图拉·葛兰领导的“葛兰组织”,②Ziya Onis,“Turkey and the Post-Soviet States:Potential and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fluence”,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No.2,Summer 2001,p.67.葛兰组织在该地区建立了一种市场经济运作下的宗教团体,其成员除了自由主义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外,还拥有较为庞大的政治运作能力和经济联系,已经成为土耳其在地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代表。
最后,利用文化联系,拓展软实力。阿塞拜疆使用的阿塞拜疆语属于突厥语系,2015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统一发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突厥通史》,下一步将推出《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学》,还提出建立突厥语电视台的倡议。众多阿塞拜疆学生在土耳其的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接受学习。土耳其电视节目受到阿塞拜疆民众的关注。讲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的人可以相互交流,虽然两种语言仍有部分差异,当说阿塞拜疆语的人接触到土耳其电视节目或土耳其语的人接触到阿塞拜疆流行音乐时,相互的理解能力就会增强。阿塞拜疆国内也有许多土耳其学校,使学生接触土耳其语的机会比一般讲土耳其语的人接触阿塞拜疆语的机会多。③Azerbaijani language-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Azerbaijani_language.土耳其推动的“突厥”世界一体化正在文化教育领域加快实施。今后土耳其将通过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等渠道继续向中亚外高加索地区扩充软实力影响。④邓浩:《中亚外高形势衍变中的中东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72页。
二、土耳其的政策变化
由于土耳其在外高加索地区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过去三十年来,历届政府都重视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和外交投入。但由于受到外高加索地区内部的政治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俄罗斯的战略挤压等原因,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的政策大致经历了试探性介入、调整过度、寻求积极创建等三个阶段。
(一)试探性介入
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凭借与外高加索国家在文化的相似的基础上,通过在政治方面,积极支持其领土完整、国家独立;经济方面,土耳其支持并帮助地区国家的经济恢复和现代化建设;外交方面,积极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抵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和主导地位。其目的是成为苏联独立以后地区政治发展走势的主导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到苏联解体前之际,由于外高加索地处苏联地缘政治版块的边缘地区,成为苏共中央权力最弱化和安全动荡频发的区域之一。这一时期,土耳其开始“试探性”的与高加索国家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建立旨在重点关注安全与防务、基础设施和能源的三方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地缘安全威胁得以缓和,土耳其开始强烈支持所有三个高加索国家的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土耳其决策者认为,如果外高加索国家独立统一后,能抵御外部压力和干预,那么土耳其有信心依靠历史、政治、经济和战略区域影响力将三国推向土耳其发展模式的轨道上。但是如果三国陷入持续动荡局面,将可能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①Aydin Mustafa,“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UNISCI Discussion Papers,No.23,May 2010,p.178.另一目的则是是鼓励高加索国家加强其国内的政治机构改革,建立自由的经济福利政策,推动外部自治和内部社会和谐。完成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部门转型,这将为土耳其拓展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并最终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地区参与者发挥关键因素。②Aydin Mustafa,“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UNISCI Discussion Papers,No.23,May 2010,p178.1991年12月9日,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塞拜疆新共和国独立的国家,还与其他三国签署了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议定书。
土耳其与格鲁吉亚之间的经济和军事交流也颇为频繁。2004年,土耳其对格鲁吉亚的投资占到外国投资总额的23%。而截止2014年,土耳其已经是格鲁吉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从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到2016年,土耳其企业在格鲁吉亚的经济投资超过10亿美元。①“Real friends? Georgia-Turkey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the July 15 coup Attempt”,The Central Asian Caucasus analysis,August 2016,http://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388-real-friends?-georgia-turkey-relations-in-the-wake-of-the-july-15-coup-attempt.html.1998年4月15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部与格鲁吉亚国防部签署了一份《相互谅解备忘录》,规定土耳其应协助格鲁吉亚建立相应的物质和军事技术基地,并为其武装部队训练士兵。这期间,土耳其-格鲁吉亚海军联合演习已在黑海多次举行,其目的是确保今后沿南部路线从里海铺设的石油管道的安全。②Ziia Kengerli,“Turkey's geo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Caucasus”,Central Asia&the Caucasus,Vol.30,No.6,2004,p.98.土耳其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帮助格鲁吉亚改革武装力量以符合北约组织的标准,双方高层互访频繁,这为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
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冲突,土耳其与区域内部分国家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加之,其国内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国民经济形态的脆弱性,安全方面又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威胁,使土耳其对于外高加索的安全政策开始呈现出间歇状态。
(二)调整过渡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11年前后,是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政策的调整时期。苏联解体后,伊朗为了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围堵”,积极向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渗透,扩大伊斯兰主义势力在该地区的作用,以图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由于土耳其与外高加索地区的地理毗邻与历史文化传统联系,且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势力不断高涨,严重挑战了国内世俗主义和凯末尔政党的统治。而土耳其重视通过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向地区国家输出“土耳其模式”和土耳其学校、各地区的土耳其媒体广播等进行颇为激进的文化扩张,激起了相关国家的怀疑与敏感。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曾私下批评土耳其这一文化输出行为是干涉阿塞拜疆内政,阿塞拜疆不需要一个老大哥。③Alexander Murinson,“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2,No.6,2006,pp.945-964.并且,这一文化输出并未给土耳其在地区影响力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为了缓和紧张关系,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在“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外交理论的基础上,推出更加务实的经贸合作来深化与地区国家关系。“战略深度”理论要求积极参与土耳其周边的所有地区体系,土耳其不能永远在欧盟门口等待,需要利用其地缘战略优势发展真正的多向外交政策。①Alexander Murinson,“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2,No.6,2006,pp.945-964.“战略深度”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新范式”。即土耳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多维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成为周边安全事务的关键力量。
首先,倡导对话解决地区冲突,建立地区安全协调机制。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军事冲突发生后,冲突增加了土耳其东北部边境安全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土耳其开始意识到,除非积极以某种方式稳定该地区安全之需,否则外高加索地区将很容易陷入不稳定和大国博弈场所,这种局面不符合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宣布创建一个旨在实现地区对话的平台—“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以积极斡旋,推动地区危机走向和平解决,该平台囊括了包括外高加索三国和俄罗斯、土耳其在内的“3+2”地区协作模式,旨在通过和平对话平台,解决地区冲突和危机形势,强化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土耳其为促进其主导的安全机制建立而进行了多次高级别外交接触。
其次,在“零”问题外交政策的框架下,积极寻求改善与地区国家的敌对关系。2008年9月6日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 (Abdullah Gül) 对亚美尼亚进行了里程碑式的访问,以出席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在埃里温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在此过程中,将“足球外交”作为打开沟通渠道的机会,作为解决双边关系中的外交和政治挑战以及促进在更广泛的区域问题上的合作的第一步。②AydinMustafa,“Turkey'sCaucasusPolicies”,UNISCIDiscussionPapers,No.23,May2010,p.179.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在2009年签订的关于《结束两国长期敌对状态并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定》,虽然因阿塞拜疆的反对,最终两国议会均未批准。但这被正发党政府视为外交领域重大突破和“零问题”外交的标志性成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土耳其对外高安全政策调整、过度和更加灵活的政策特征。
最后,将经济贸易联系作为双边关系的主要平台,高度重视能源领域合作。例如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线从阿塞拜疆途径格鲁吉亚运往土耳其杰伊汉,然后将高加索地区的能源资源出口至欧洲市场,而这只是土耳其“东西能源走廊”计划的第一步,2006年7月投入运营的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线,更是成为连接亚欧油气管线最重要的通道。土耳其希望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与高加索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成为连接欧亚能源网络的关键节点。
(三)务实导向
2011年以来,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趋于务实。这一时期,中东地区地区政治秩序受到域外大国竞争、地区内地缘政治对抗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破坏,土耳其的地区政策一度陷入战略孤立状态,其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政策也因难以“两面应对”而推进缓慢。因此,土耳其的地区政策倾向于务实合作,并希望推动与地区国家的良好关系和协调对话处理冲突问题,其目的是防止地区冲突威胁边境安全,构筑较为稳定的周边地区事务,缓和地区局势紧张带来的国家安全负担。
实质上,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众多学者将埃尔多安领导及其正义与发展党的对外政策认为是典型的务实主义或者机会主义色彩。①对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大体论述。详见Ziya Meral&Jonathan Paris,“Decod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yperactivit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3,No.4,2010,pp.75-86;Kilic Bugra Kana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JDP Governments”,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34,No.4,Fall 2012,pp.230-249;Alexander Murinson,“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2,No.6,2006,pp.945-964;H.Tarik Oguzlu,“Turkish Foreign Policy at the Nexus of Changing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Dynamics”,Turkish Studies,Vol.17,No.1,2016,pp.58-67。其对外高加索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寻求弱化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特征,在参与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过程中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和策略,寻求与俄罗斯和域外行为体在维护地区稳定的前提下,更为积极地发展与阿塞拜疆的军事同盟关系和格鲁吉亚的双边关系。虽然“战略纵深主义”是指导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在当下以及未来较长时间的思想灵魂,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突厥”文化回归和历史纵深的地缘关系思考,但是其本质是摒弃虚幻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对更为实质的战略利益考量优先,认为土耳其应该采取多向多维的积极外交,追求全球行为体目标。②刘欣:《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87-101页。
2011年阿拉伯国家变局后,中东国家卷入空前的混乱局面,土耳其原先奉行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理念被阿拉伯人视为根深蒂固的忧虑和排斥,①王锁劳:《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1-14页。而这一时期,土耳其不断硬实力介入地区事务,使得“零问题外交”变成安全形式的“多问题”状态,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俄罗斯随后在经济领域实施严厉制裁,在地区事务上形成与土耳其的战略对峙的紧张关系,一度将土耳其陷入地区事务的孤立状态。这期间,加之国内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上升为土耳其安全事务和周边外交侧重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埃尔多安政府开始抽离对外高加索地区过多关注,而侧重于更为务实的其他领域合作。
同时,土耳其则希望继续维持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传统安全合作,使其成为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地区政策的有益补充,对土耳其的长期地缘安全战略地位具有独特的重要性。2016年5月,土耳其国防部长恢复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防长会晤,而此前三方会晤可以追溯到2012年6月特拉布宗宣言。2017年6月,三国在第比利斯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2018年4月,三国国防部长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计划建立更紧密的三方国防伙伴关系。
三、土耳其面临的困难
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的有效推进面临外部性威胁和自身政策缺陷的两类困难。从传统意义上讲,俄罗斯是现今和未来影响外高加索安全走势的最主要行为体力量,也是足以威慑和改变土耳其战略方向的最主要困难,但随着土俄双方相互依赖的加深,爆发冲突可能性较小的前提下,双方更倾向于保持默契,管控分歧。就地区国家的威胁性排序,与亚美尼亚的敌对状态是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政策的重要阻碍,这也是地区国家关系紧张和对峙状态的外延;而与阿塞拜疆组成的地区同盟和与格鲁吉亚不断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更是加剧了地区关系的复杂性。就自身来看,土耳其的地区政策并没有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机遇。
(一)俄罗斯的战略竞争
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的复苏被认为是土耳其安全政策的最主要威胁。土耳其的外高加索的安全政策受制于与俄罗斯实力的非对称性,俄罗斯长期对域外势力介入独联体国家存在保持警惕性。1993年起,俄罗斯推行其“近邻”政策,防范域外国家包括美国和土耳其和欧盟在中亚、外高加索等原苏共地区的势力介入。①杨张锋:《21世纪俄土关系的两次转变:原因及影响》,载《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88页。构建由俄主导的地区军事集团,其中包括双边协定基础上的高加索军事集群。特别是2002年1月,土耳其、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就区域安全问题达成了三方协议;2017年5月,三国举行安全会议,后又在第比利斯附近举行了三国军事演习。2018年4月,三国国防部长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设想建立更紧密的三方国防伙伴关系,这些举动引起了俄罗斯的愤怒。②Yousifov,Shahin.“Turkey and Russia Faced with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The Case of Azerbaijan”,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Vol.97-98,No.1,2010,pp.18-23.作为报复,2016年11月12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式批准政府组建俄—亚美尼亚永久联合地面部队的提议。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扩大,俄罗斯领导人的安全思想旨在防止亚美尼亚等盟国西移的可行机制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加强现有军事基地,同时将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纳入其南部军区(SMD)框架,寻求加强其对亚美尼亚国防战略和国防决策有效影响,并保持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中的介入立场,而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处于战略伙伴关系和相互支持协议,显示出双方在地区问题上的战略对峙状态。俄罗斯更是对土耳其发出威胁,警告土耳其切勿卷入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③Yousifov,Shahin.“Turkey and Russia Faced with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The Case of Azerbaijan”,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Vol.97-98,No.1,2010,pp.18-23.土耳其充分意识到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安全领域占据的的巨大影响力,转而依靠经济、文化等“软实力”手段在这一地区施加影响。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在黑海的舰队规模不断壮大,且在叙利亚、亚美尼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威慑加剧了土耳其战略被包围的担忧,使得地区安全困境上升。同时,土耳其也对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感到担忧,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
虽然俄土在高加索地区形成了地缘竞争关系,但双方均未视对方为战略对手,且一直保持默契,管控地区冲突。土耳其的长期利益是促进高加索—黑海地区的多边合作,在与西方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出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与俄罗斯保持建设性关系是土耳其拓展地区安全利益诉求的动因。
(二)地区内部的敌对国家
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的敌对关系状态是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同时也成为制约土耳其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障碍。十五世纪初,亚美尼亚的大部分领土曾被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奥斯曼帝国曾设置“米勒特”制在宗教和民事上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管理。①米勒特(millet)制度,可理解为亚美尼亚内部的宗教团体自治制度,参见许晓光:《外高加索民族冲突与亚美尼亚民族问题的由来》,载《东欧中亚研究》第1993年第1期,第89页。而后,土耳其与沙皇俄国、土耳其与伊朗先后在该地区大动干戈,1828年土耳其与沙俄在土库曼恰伊村签署停战协定,致使东亚美尼亚成为俄国领土,西亚美尼亚仍归土耳其统治,将亚美尼亚沦为“帝国战场”,交易瓜分严重破坏亚美尼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1894年6月,在凡湖西岸的比特里斯,土耳其政府屠杀了二万亚美尼亚人。1905-1909年,土耳其人联合了库尔德人,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城市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大屠杀,1915年土耳其政府放逐了150万亚美尼亚人,致使100余万人死亡。②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诸长福,贾鼎治,吴厚恭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35页。因此,亚美尼亚历史上不断遭受外族入侵、奴役后,在其独立后国内民族情绪高涨,反对大国干预的呼声在新的国家局势下发展到极端,亚美尼亚整个国家对土耳其的仇恨心理也进一步导致纳卡民族冲突的出现。纳卡冲突使得地区陷入结盟、对峙和小规模冲突状态,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各为阵营。
2002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迫于国内外压力,也试图改变其在外高加索政策上的消极局面,时任土耳其外长的达乌特奥卢推出与邻邦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后冷战时期带来的动态因素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创造一种良好氛围,必须大胆的解决一些难以调和的领土问题和其他纠纷,最大限度的扩大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影响力。2008年9月6日,时任土耳其总统的居尔访亚开启“足球外交”,最终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并解除了1993年土耳其纳卡战争而关闭的边境。③从某种意义上讲,边界从来没有开放过前苏联时代,土耳其边境城市卡尔斯和亚美尼亚城市久姆里之间每周只有一班火车。1994年4月,土耳其决定不签署该议定书边境。转引自Ziia Kengerli,“Turkey's Geo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Caucasus”,Central Asia&the Caucasus,Vol.30,No.6,2004,pp.99.2009年8月,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签署了两份协议草案《建交草案》和《两国关系发展草案》暂时解冻,该议定书声明将在协议生效后两个月内开放双方边界。2009年双方在瑞士苏黎世签署和平协定,使得两国外交关系倾向于正常化发展,为双方结束历史恩怨、关系正常化迈出重要一步。尽管两国领导层保持较为密切的交流。但是双方在协定中均回避了“亚美尼亚屠杀”和“纳卡冲突”问题,导致没有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法。并且两国在关键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没有共同的政治诉求。针对土耳其反复无常的态度,和试图掩盖历史真相的言论,2018年3月1日,“亚美尼亚宣布撕毁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协议”。两国又重回军事对峙状态,严重制约了土耳其的地区安全政策实施。
(三)地区内部的复杂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外高加索周边面临“颜色革命”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双重压力,①邓浩:《外高加索地区形势演变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第2016年第2期,第80页。领土争端、民族宗教矛盾、外部势力的地缘战略争夺等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由此衍生的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并悄然影响着其地缘政治走向。而这一系列地区矛盾的根本动因都是地区内部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导致,导致土耳其难以在地区政策实施方面发挥主要影响力。大致体现为:
首先,外高加索地区国家间关系凸显的的复杂性,使得土耳其可以趁机谋求利益。由于地区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相互间的恐惧和对彼此意图的不信任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恐惧迫使这些国家选择进行一场负担沉重的军备竞赛,这将增加这些国家的普遍不安全感,②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p.167.国家间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他们联合管理危机的意愿受到这一结构性因素限制这就使得地区产生“安全困境”状态。“安全困境”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双边关系互动中表现的尤为明显,1988年起,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持续性的武装冲突,直至1994年俄罗斯介入调停中止。土耳其将阿塞拜疆定义为高加索地区战略上最重要的国家,是土耳其地区政策合乎逻辑的战略支柱,双方具有密切的文化亲缘关系、语言相近性双边经济贸易与能源合作。正如土耳其学者认为,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包括:支持阿塞拜疆的独立;支持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主权。而“选边站”成为土耳其在地区介入他国战争的策略,这样不仅可以合理的在阿塞拜疆境内驻军,也如愿将进攻能力延伸到高加索地区。
另一方面,地区国家复杂关系的演变造成了的地缘政治争夺,非传统安全问题滋生,使得土耳其难以控制和驾驭这些复杂关系,从而达不到自身的某些目标,这限制了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1990年,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爆发武装冲突;随后,阿布哈兹也卷入与格鲁吉亚的内战,直至1995年在联合国和俄罗斯的介入下中止。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高加索的族群冲突导致近5万人死亡、大量物质损失、政治动荡以及经济疲惫,并滋生了有组织的跨国犯罪。①孙超:《外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载《俄罗斯研究》第2017年第2期,第136页。而土耳其的权力介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地区国家的紧张关系,还造成俄罗斯对其意图的怀疑与恐惧,例如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冲突后,一度中断了土耳其和格鲁吉亚的铁路交通和海路运输,使得连接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的油气资源出口被迫中断,更为重要的是俄格战争后加剧了外高加索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俄罗斯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攻势,凸显出土耳其在地区影响力的乏力,战争则使地区国家认清孰轻孰重。
(四)土耳其的政策缺陷
土耳其的政策缺陷表现为:(1)过度强调传统安全与军事同盟关系。虽然地区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护土耳其地缘经济利益和进一步加深与地区盟友的战略关系,但同盟本身具有的排他性特征,容易造成地区的安全困境,容易产生与地区大国的紧张关系,更是难以实质性地推进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和解。(2)土耳其对提供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有限,限制了其拓展地区利益的话语权。
首先,土耳其倡导的是一种排他性、单一合作形式的结盟政策,其建立是制造假想敌和集团化式的、一种“零和”安全对话机制,刻意强调地区安全困境,在安全防务上排挤亚美尼亚,加剧了传统“均势”和进攻性的安全体系。如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布鲁诺·考彼尔特斯(Bruno Coppieters)所言,“所有区域行为者都试图通过与区域和非区域大国结盟来修正现有的权力分配形式”。军事政策在这种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方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产生的体系虽然旨在制衡主导力量,但并不排除霸权式的主导。①Jannatkhan Eyvazov,“The Reg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Central Caucasus:Political Structure and Conflicts”,The Caucasus&Globalization,Vol.6,No.1,2012,p.147。而这意味着一方实力加强,对一方就是重要的威胁感知,双方更容易陷入螺旋式的“安全困境”状态。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不断加强战略合作关系,就会造成亚美尼亚的恐惧与不安全感,亚美尼亚则选择安全上追随俄罗斯。2015年10月6日、7日,土耳其军用运输直升机两次进入亚美尼亚领空。随后,俄罗斯继续增援其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分遣队,据称,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空军基地部署了更多的攻击和运输直升机,2016年2月,俄罗斯又向亚美尼亚派遣了一支先进战斗机和地面攻击机分队。俄罗斯还宣布在南部军区举行军事演习,以测试应对危机局势的准备情况。②Neil John Melvin,“Middle East Conflict Risks Overspill into the Caucasus”,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March 4,2016,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blog/2016/middle-eastconflict-risks-overspill-caucasus2019年3月,阿塞拜疆军队举行近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演;9月与土耳其和格鲁吉亚联合举行“高加索之鹰”联合军演;11月,阿塞拜疆再次举行涵盖全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③邹志强:《阿塞拜疆军演背后的联动效应》,中国军网,2020年3月19日,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20-03/19/content_256925.htm俨然已经将该地区作为“结盟”与“制衡”的试验场,这种“军事化”状态大大加剧了地区安全模式的冲突性,这无助于土耳其影响力在地区政策合理输出。
其次,土耳其难以为该地区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机遇,难以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实现经济发展。这限制了土耳其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在国际政治中,生存是国家行为体的基础,发展则是国家行为体的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国家脱离发展谈生存是难以为继的,而地区脱离发展谈安全是治标不治本的。因此,土耳其对高安全政策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土耳其难以为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外高加索地区自独立以来,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合作,使得地区经济发展被边缘化,各国经济对外依赖严重,自主抗风险能力不强。2014年底至2015年初,三国货币普遍面临剧烈贬值压力,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迄今为止没有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具有一定抵御风险能力的经济体系,①邓浩:《外高加索地区形势演变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第2期,第80页。俄罗斯的汇款多年来一直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硬通货来源,如果这一收入来源中断,亚美尼亚也将面临经济和社会动荡,亚美尼亚前总理季格兰·萨尔基相(Tigran Sargsyan)曾经承认,政府支持亚美尼亚移民,因为如果人们不出国谋生,国内群众革命就很容易发生。亚美尼亚国内群众革命根源深刻,社会经济常年徘徊于低增长和负增长之间,政府部门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等。2018年4月23日,亚美尼亚通过街头政治方式,推翻萨尔基相政府,反对派领袖帕希尼杨担任总理。而阿塞拜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18年3月10日,因阿塞拜疆副总统选举,在巴库爆发抗议活动,反对派既有民生要求、也有政治要求,②侯艾君:《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风险及其规避》,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2期,第73页。且国内经济过分依赖石油等能源经济,也很难可持续发展,随着近年来油价暴跌,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可能导致阿塞拜疆和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四、结论
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事务的“边缘化”关注,是造成区域安全真空的重要原因,此外区域内部安全模式的冲突性和排他性,加剧了区域安全政治参与者的两极化倾向,造成区域安全的制衡和结盟等态势,使得和平进程演化为冲突管理机制。促进高加索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符合土耳其的利益。且该地区的经济潜力以及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成为土耳其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动机。这期间,土俄的战略竞争关系使得外高加索呈现出两极化的安全复合体模式的趋势,但也相对管控了外高加索内部国家冲突和民族分离势力。其次,外高加索的地缘政治优势与土耳其的地缘文化的趋同性成为土耳其“向东看”外交的关键平台与跳板。土耳其不断扩大其在突厥语国家联盟的存在,拓展其地区影响力。总体而言,自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希望依靠软实力的手段拓展更加务实的地区政策。但是其政策受到地区国家权力的制约、地区内部复杂关系,加上土耳其难以为地区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机遇,阻碍了土耳其高加索地区的局势施加更为积极影响,因此土耳其在地区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能源、运输和贸易领域,而其在该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作用较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