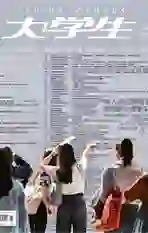公元1700这一年
2020-11-28靳潇飒
靳潇飒
公元1700年,从东洋到西洋,话不尽疯狂;自莱茵至长江,道不尽苍凉。
从东方到西方
这一年,东方太阳升起的日本海水面上,从江户赶往登州的船只络绎不绝。谁曾想100年前,这里竟是尸横遍野,印有“德川”二字的战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谁又曾想那年群雄逐鹿,笑到最后的,不是一代枭雄织田信长,更非野心勃勃丰臣秀吉,而是这所谓的忍者大师德川家康。
德川氏在日本的崛起令人始料未及,包括它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这里前几十年也风云变幻,山河失色。崇祯帝的末日哀嚎给煤山增添悲凉的味道,九宫山的云雾也早已掩盖掉李自成英武的模样,凤凰坡的老农犹自诉说着那日兵变时张献忠没落的背影。在百姓心中,扬州城头的烽火未熄,嘉定野外的血迹未干。
这一年,势力庞大的三藩、狂妄挑衅的漠西、骑兵犀利的雅克萨哥萨克,在当时的清朝帝王面前均灰飞烟灭,这位帝王唤作康熙。
这一年,南亚次大陆上,莫卧儿帝国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德干战争的残酷,马拉塔人的入侵,英法荷殖民的据点,蚕食着古老帝国每一寸富有生机的土地。
就算是沙加复生、巴布尔重活、阿克巴再现,也未必能够让它起死回生。奥朗则布已至垂暮之年,他咏诵着:“我孤身而来,孑然而去”离开的,是这片他深爱的领土,留下的,则是残缺的帝国。
这一年,伊斯兰帝国战无不胜的火枪骑士队竟然输了,输给那令他们厌恶的基督徒世界,輸给让他们烦心的俄罗斯人。哈立德铁蹄激荡在亚欧大陆的声音,阿拔斯旗帜飘扬过后的痕迹,都已无从寻觅。俄罗斯人不会顾及手下败将的感情,他们在彼得大帝的带领下,一步步地迈向属于俄罗斯人的辉煌。
这一年,俄罗斯人在北方与那看似无比强大的瑞典人进行残酷大战。蒙古人撤退的痕迹还未消失,西伯利亚的大片领土让人垂涎,波罗的海与黑海还在瑞典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上。但他们都不担心,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彼得大帝永远健康,莫斯科公国进化为俄罗斯帝国,那是早晚的事。
是辉煌是消亡
这一年,东方升起的日头照射着西方巨人的余辉,照耀着波兰立陶宛人末日的神情、瑞典帝国仓皇的面容,照耀着哈布斯堡这个欧洲最为古老的帝国家族惨烈的激斗——无论是在广袤的东欧平原,或是富饶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的威望,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光芒都在减少。有的,只是一场场王位继承战争的惨烈。
普鲁士激动了,潜伏多年终于赢来崛起的机会让霍亨索伦家族兴奋不已,让容克贵族蠢蠢欲动。是啊,柏林值得高兴,因为正是这一年,他们敬爱的腓特烈一世终于取得了普鲁士国王的称号,他们再也不是那所谓的“欧洲的沙砾罐头”。
他们带着属于德意志的荣耀和梦想踏浪而来,俾斯麦、威廉二世、施里芬、古德里安...当这些名字在后世出现时,当德国人的旗帜在欧洲大陆四处飘扬时,是否有人还记得,公元1700年勃兰登堡城门上那斑驳的色彩。
法兰西也在高兴,1700年的某一天,他们突然发觉在欧洲大陆上,他们所向披靡,无人能敌。他们的皇帝开始行动并自诩为太阳,他虽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率领的陆军却是威风凛凛无人能挡。他雄心勃勃地准备称霸大陆,却激起整个欧洲的联合反对。
多年之后,人们只记住了高跟鞋和香水的魅力,只知道巴黎时装周的声誉,却早已遗忘发明推广它们的法国大皇帝——太阳王路易十四。多年以后,一位比太阳王身材还要矮小的巨人接过了他的旗帜,却仅仅比他多走了一步而已。
自喧闹到无声
这一年,海峡对岸的英伦三岛,一片欣欣向荣。
霍布斯与洛克的学说早已风靡全岛,岛内新贵族和新教徒厌恶的前任君王詹姆斯二世逃得无影无踪,克伦威尔的威严已过去多年,辉格党的权势如日中天。伦敦白金汉宫内的圆桌会议上,威廉三世正听着大臣们信心满满地勾画未来。
机器的轰鸣声让人忘了纳西比战役的叫喊,繁茂的工厂也早已掩盖哈德良长城那静谧的庄严。伴随着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在挤满了探险者和野心家的利物浦港口上,海水正无情地拍打着从这里驶出的船只,一路向西,将他们拍打到那所谓荒凉的新大陆上。
在这一片广袤的新大陆上,弗吉尼亚刚刚建立,新阿姆斯特丹还未改名成纽约。在那里,只有被流放的新教囚徒和印第安人。
这一年,对于这片大陆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但谁又能想到,在这片大陆上形成的美利坚民族竟会从大英帝国的手中得到解放,曾经的十三州殖民地,发展成为如今模样。
江户的船只早已到达登州,准备返航;利物浦驶向新阿姆斯特丹的船也开始渐渐靠港。1700年就这样来了又过去,消逝在历史中,如同东逝的长江水、西去的多瑙河、北归的尼罗河、南下的伏尔加河。
责任编辑: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