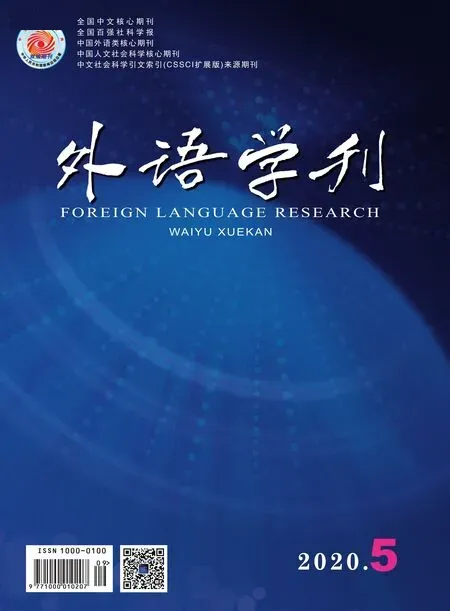集体无意识视阈下翻译价值理论的归结性反思∗
2020-11-25杨镇源
杨镇源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1731)
提 要:翻译价值理论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空前的多元化格局。 然而,其学理思维多将重心集中于外延性的价值指标,缺乏本源性的回溯反思,因而多流于“放得开、收不拢”的学理格局。 本文依托于荣格的理论,将翻译价值理论归结到集体无意识根源,以形成前者的内溯着力点,造就外延扩散与本源归结之间的张力,使翻译价值理论本末兼顾,既能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又能从深层次的本源心理状态中寻求自我修正与发展后劲,从而成就更加全面周致的学理思维。
1 引言
价值理论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经过长期发展,翻译价值理论已形成空前的多元化局面。 在这样的趋势下,对于何为翻译之“善”,理论家们能够给出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表象价值指标,形成“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理论格局,却难以从本源上确立翻译价值的依托。 《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佚名2006:1)。 如果停留于各种细枝末节的价值指标,而对于“翻译之‘善’本源何处”之类的问题做功不足,则可能在价值理论上舍本逐末,流于“放得开、收不拢”的局面,离翻译之道远矣!
诚然,“善”之定义一直困惑学界,伦理学至今尚且未得出一个公认的解答,要翻译研究明确翻译之“善”本为何物,则未免苛求。 然而这不应当成为阻碍研究者在此问题上进一步反思的理由。 笔者认为,如能依托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则有助于确立翻译“善”之本源,在翻译价值理论的多元化趋势下开辟一条归结性路线,从而造就“放得开、收得拢”的研究品质,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空间形成拓展。
2 翻译价值理论的多元化趋势
多数的翻译理论都具备一定的价值指向,也由此赋予自身价值理论品格。 随着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加深,翻译价值理论得到长足的进步,也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译坛多专注文质之争,神形之辩,以传统文艺学和美学为支撑的西方译界则多热衷直译与意译的取舍。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双方均将价值主题主要集中于忠实、通顺、美感等方面,形成相应的价值指向,如严复的“信、达、雅”,泰特勒(A. Tytler)的“三原则”,多雷(E. Dolet)的“五原则”,等等。 自20 世纪中叶,结构主义语言学试图把科学化的语言结构和意义分析注入翻译研究,以“对等”为主题衍生出各种价值理论,如奈达(E. Nida)的“形式对等/动态对等”,纽马克(P. Newmark)的“语义翻译/交际翻译”,科勒(W. Koller)关于“对等”划分为5 个层面:明示对等/暗示对等/文本范式对等/语用对等/形式对等(Munday 2016:75),等等。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翻译研究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拆解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明确界线,将“忠实”“对等”等传统套路釜底抽薪,转而从更加广阔的阐释链条中探视翻译活动的产生与演变,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价值理论扩张力。 在后现代主义凿开的巨大现代性裂隙中,功能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等翻译理论派别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此间,对于翻译的价值评判已不再局限于文本之间的对应,而是上升到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于政治层面,既极大地开拓了价值指标的范围,也进一步加剧了翻译价值理论多元化的趋势。 另外,在新理论兴起的同时,旧理论虽失势,却未完全消亡。 它们依然停留在研究地图中,与前者一道构成五光十色的学理图景。
不可否认,在多元化趋势下,翻译价值理论有力地伸展了外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并不能够遮掩一个根本性的认识缺憾,那就是少有研究能够明确价值(即翻译之“善”)由何而来,根源何处。 总体说来,当前的翻译价值理论强于描述和标榜种种翻译之“善”的价值表象,如神似原作、流畅优美、达成社会功能、反抗文化霸权、改善语言生态,等等,却弱于对翻译价值的根源性探索,显得发散有余,归结不足。 如果把当前的翻译价值理论图景比做一个正在充气的球体,那么人们多被球体表面缤纷炫目的花纹与图案所吸引,对于作为气体源头的充气口却往往关注不够。 在这种舍本逐末的思路下,研究者尽管可以进一步发掘更多的表象以充作价值指标,却无力摆脱“放得开、收不拢”的困窘,难以避免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境地中迷失翻译价值理论的根本。 对此,翻译研究有必要在元理论层面展开反思,对翻译之“善”追根溯源。
3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在谈到符号的本质时,马雷斯(K. Marais)将其描述为一种根植于人脑、源发于心理性、交互于社会性的产物(Marais 2014:71)。 作为一种符号,价值从本质上讲亦是一种源于人类内心的赋值结果。 相应地,要追溯翻译之“善”的根源,就需突破价值“是什么”的表象,寻找其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原因。 对此,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Jung)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有重要的启示。
集体无意识理论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精髓。荣格继承弗洛伊德(S. Freud)对于无意识的界定。 弗洛伊德通过大量的精神病治疗案例发现,强迫症患者通常会做出一些他们自己都完全不能解释原因的活动。 在仔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表面意识之下,还潜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一力量激发人们的行为意识,使其产生种种具体的行为,而这一力量就来自于无意识。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得出结论——精神活动本质上就是无意识,所谓的有意识只是无意识的小部分而已,如果把整个精神生活比作岛屿,那么有意识只是岛屿水面上的部分,而水面下正是占绝大多数的无意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同时也决定前者的动向(荣格2003:3)。
然而在关于无意识的属性上,荣格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前者不认同后者将无意识当作一种个体性精神暗流的观点,主张将无意识视为一种人类普遍的心理基础。 荣格偏离弗洛伊德断言的无意识个体性,转而致力于论证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层面——集体无意识。 在他看来,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精神病人,无论是来自于何种民族与文化,每个人都具备集体无意识。 对此,荣格做出如下解释:“这个层次既非源自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 我把这个更深的层次称为集体无意识……我之所以选择‘集体’这一术语,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并非是个人的,而是普世性的……不同于个人心理的是,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与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换言之,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并因此构成具有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我们大家身上”(同上:5)。
荣格在探索各种宗教与神话问题时,发现很多文化中存在着相似甚至是雷同的原始意象,如花朵、十字车轮等。 此类意象多出现在宗教和艺术作品中,或是出现在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的意识里。 更让人称奇的是,尽管相隔遥远,且在历史上无任何交集,某些民族依然有相似的神话传说元素,如不祥的妇女、睿智的预言家、天生神力的武士、为崇高使命牺牲自己的英雄,等等。 这让荣格倾向于认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人类共同神话传说和原始意象下面的心理土壤。 虽然他没有对集体无意识提出明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众多著作中可以看出:“集体无意识首先应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是一个使精神事件充满永恒活力的事实。它是意识的终极体现,是人类心灵中仍旧活跃着的祖先的经验……实际上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种遗存既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也包括文化历史上的文明的沉积”(同上:15 -16)。
荣格用“原型”(archetype)一词来表现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原型是一种经由成为意识以及被感知而被改变的无意识内容,从显形于其间的个人意识中获取其特质”(荣格2011:7)。 原型是抽象的、基本的、原始的观念,以原始意象的形式存在,存留于群体的无意识之中,但并不来源于他们的个人经验①。 在荣格眼中,原型是没有内容的形式,仅仅表征某些感知与行为的可能性。 或者说,它是一种有待激发的潜在心理事件。 用比尔斯克尔(R. Bilsker)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某些特殊经验唤醒原始经验时,有关这些原始意象的意识才能被激活”(比尔斯克尔2004:34)。 在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理论观照下,种种所谓的原始意象变成一种内在的、向远古溯源的结果,在极大程度上否认神话和艺术是对外部世界反映的说法②。
这样看来,当讨论什么为什么有价值,以及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评价建构于自己的集体无意识之上,已经把种种内容空洞抽象、有待实际语境激活的原型作为所有评价指标的根源。 这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类似甚至一致的根本原因。 譬如,无论在何时何地,助人为乐、自我牺牲、善良真诚等精神都被普遍奉为美德,而吝啬小气、损人利己、狡诈虚伪等都普遍被视作恶习。 东西南北,古往今来,集体无意识造就的原型使人们从内心对许多价值评判产生共鸣,呼应着灵魂深处来自于远古的共通原始意象。 正如荣格所说:“原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 它就像心理中一道深深开凿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在宽阔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漫淌”,因此原型“是一切‘欢乐和悲哀’、希望与憧憬、想象和情感的原始根柢”,这一原始根柢已经持续存在了若干万年,并将伴随人类继续存在下去(荣格2003:23)。
4 翻译价值理论的集体无意识归结
集体无意识为翻译之“善”提供本源性的解释可能,由此为翻译价值理论开辟一条归结性的道路。 在回溯性的眼光下,集体无意识根植于伴随人类世世代代的原初意识种子,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来源,为价值理论设立根本。 确切言之,依托于集体无意识,共通的心理认可模式得以建构,衍生出能够被公认的翻译之“善”,从而形成翻译价值理论的源发点。
荣格曾经说道:“原型中确定的并非是其内容,而是其形式,但是程度非常有限。 唯有在一种原始意象已然成为意识,并因此被填充意识经验的材料时,它的内容才得以确定”(同上2011:66)。 翻译价值理论的基础正是建构于种种价值原型之上。 原型被装填各种各样的价值认识,建构出表面上不尽相同的价值指标,但由于原型的集体性,这并不妨碍价值观在本质上取得一致的可能。 具体说来,在社会交往实践中,集体无意识的种子——原型被各种信息激发,填充自我内容,并衍生出具体的共通价值指标。 按照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观点,这是一种“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 rationaliat)的体现。 在谈到自己的价值话语基点——合理性时,哈贝马斯指出,合理性取决于交往理性——一种人类言语行为交往与协商的结果、一种“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哈贝马斯2004:10)。 由这种非强制的协商造就共识性的话语,形成人们一般认同的合理性的基石。 “通过这种交往实践(kommunikative praxis),交往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明确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的界限是由所有的解释确立起来,而这些解释被生活世界中的成员当作背景知识。”(同上:13)固然,这样的合理性并不能造就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价值观,但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指令意义,可以被当作“一种相对的应然”(哈贝马斯2005:65),使作为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具有批判检验的能力,如哈贝马斯所言:“只要行为者对诸如刺激的、诱人的、陌生的、可怕的、可恶的等谓词的使用,能够使其生活世界当中的其他成员认识到他们对于相同语境所作出的各自的反应,那么,这些行为者的行为就是合理的。 反之,如果他们过于随意使用价值标准,致使他们无法再去信赖任何一种文化观,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乖僻的……谁的立场和评论如果过于具有私人色彩,从而使得他们依靠价值标准无法得到澄清和证实,那么,他的行为就会缺乏合理性”(同上2004:17)。 这些论述揭示出,在交往中通过协商从个体性走向集体性的价值指标图景。 更重要的是,它暗示出集体无意识对于价值指标共识的支撑力量。 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存在一些怪癖行为(如某些人喜欢腐烂苹果的气味等),但在大多数文化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行为却都显得不可理喻。 那么,为什么不可理喻? 为什么多数人不会和这些怪癖人士“同流合污”? 在集体无意识的观照下,对这一切的解释变得十分容易:正是由于多数人在深层次心理机制分享集体性的原型,人们才可能具备非强制协商的基础,从而回避个别性的怪癖,趋向共同之“善”,使共识性的价值指标(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合理性)得以建构。
这样的思维能够为翻译价值理论带来归结性的反思。 纵观当今译坛,价值理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或期冀不同层次的对等(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或标榜形形色色的功能(功能学派)、或鼓吹操纵改写的权力(操纵学派)、或宣扬主体个性的解放(解构主义)、或寻求文化殖民的颠覆(后殖民主义)、或力争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主义)……此类话语尽管令人眼花缭乱,又看似各有道理,却无法使人得到价值理念的安定感。 如马雷斯就认为,翻译理论局面过于复杂化,以至于他甚至不敢做出价值判断,也不敢希求任何的“救世之举”(crusade to save the world),只敢小心翼翼地提议将各家之说“暂时悬置”(temporary moratorium)(Marais 2014:144)。 究其原因,终是翻译价值理论发散有余,归结不足,特别是缺乏对于本源的追溯力度,导致“枝叶繁多、难见根茎”的学理图景。 换言之,价值理论表面虽多姿多彩,却难以明确来自根源的支持,末显本晦,自然不足以安人心。 如把各种价值表象溯源至集体无意识,则能够打破局面,以归结姿态寻得价值理论的源头活水。
正如宋雅萍所言,“集体无意识的形成是个潜在的过程,刚开始时集体感觉不到这种无意识的存在,但客观上却巳经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只有置身于特定的情境时,人们潜意识中的某些倾向才会被触发”(宋雅萍2013:61)。 结合哈贝马斯的价值生成模式不难发现,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正是通过与翻译的交往实践发生相遇,依托不同的特定情境(包含翻译的客观环境与相关人员的主观认知)发生协商性阐释,进而触发潜意识的集体价值倾向,最终建构出种种具体的翻译价值理论指标。 譬如,零差异“理想翻译”的原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派那里生成种种对等理念;“译有所用”的原型在功能学派那里酿造不同功能导向;“凸显自我”的原型在操纵学派那里演绎反叛原文的自由,在解构主义那里策划主体的张扬;“公平正义”的原型在后殖民主义那里化身挑战文化霸权的急先锋,在女性主义那里吹响男女平等的号角,在酷儿理论那里则扛起非主流性取向的大旗……就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所谓的理论经典话语其实都处于“动态的建构” (周红民2017:2)。 在建构过程中,“相近似意象的反复出现,就是原型的作用与影响”(张松才2018:26)。确切言之,在不同的实践交往语境的激发下,集体无意识得遇各样机缘,如种子入土,发芽生长,使原型在各自的学派那里反复呈现出相近似的意象,并形成相应的价值目标。 围绕这些目标,研究者们不断动态地建构出种种理论话语,勾画出万花筒般的译学图景。
由此可见,所谓的翻译之“善”根植于集体无意识。 对于翻译价值理论而言,“善”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在社会交往实践中被激发、被公认、被发展的心理衍生物。 正是从集体无意识这个源发点,一步一步成长扩展,翻译价值理论才从无到有,由简入繁,一路走到今天的枝繁叶茂。 找到这个源发点,翻译价值理论就找到在众多枝叶下面的根,就拥有向内归结的可能性和着力点。 否则,如仅仅执于种种价值表象,而不问其根源,那么翻译价值理论便只能流于“放得开、收不拢”的状态,无论散得再开,走得再远,都只会如无根之萍一般随波逐流,无法从根部得到源源不断的养分,造成理论层面解释、支持与补充的不足。 若能把翻译之“善”归结到集体无意识,则有助于形成“放得开、收得拢”的研究品质,如放风筝一般,既能够将理论话语放至天际,又能够牢握手中线,保留其面向本源的回溯力。 在此收放之间,翻译价值理论便可本末兼顾,一方面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一方面从深层次的本源心理状态中寻求自我修正与发展后劲,从而成就更加全面周致的学理思维。
5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致力于将翻译价值理论归结到其集体无意识的根源,试图在“刨根问底”的姿态中,揭示出前者在多元化表面之下的心理始源,以求对其“知根知底”,推动从“放得开、收不拢”到“放得开、收得拢”研究格局的转换,形成本源归结与外延扩散之间的张力,进而改善翻译价值理论的学理思路。 当然,本文的研究远非充分,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开端,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集体无意识根源,但对此后的研究内容却尚未企及,如集体无意识的内涵与形态如何? 具体怎样在翻译的交往实践中产生价值指标? 如何在此层面实现对翻译价值理论的修正与补充? 如此等等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深究。但笔者深信此间蕴藏的学术潜力,若能小扣而发大鸣,协助相关研究结出硕果,则笔者倍感幸矣!
注释
①需强调的是,荣格的“原型”(archetype)代表着一种可追溯至远古的先天原初心理形式,与谭载喜、龙明慧等学者基于西方经典范畴理论阐发的“原型”(prototype)在概念和本质上都有所不同,二者不可混淆。
②荣格以旧石器时代岩画为例,其中有一种抽象的图案——圆圈中的一个双十字。 他指出,“这种图像实际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 今天我们不仅在基督教的教堂内,而且在西藏的寺院里也能够找到它,这就是所谓的太阳轮。 既然它产生于车轮还不曾发明出来的年代,也就不可能起源于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毋宁是某种内在体验的象征”(荣格2003:22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