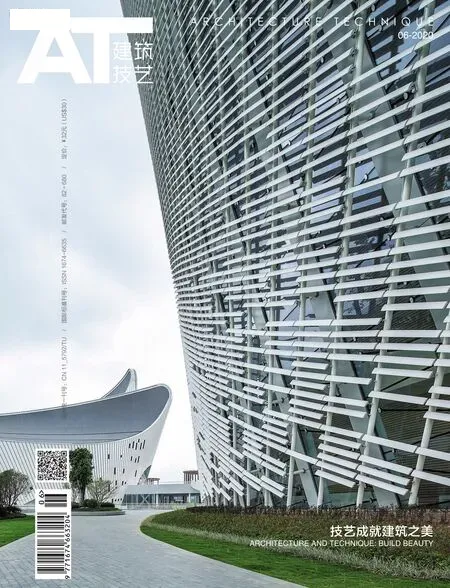公共建筑的“城市公共性”
2020-11-23马进
公共建筑的“城市公共性”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之所以“老生常谈”,就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这并非建筑师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公共建筑设计中常常运用各种手法,如大型坡道和斜坡、上人屋面和平台、架空层、有顶棚的室外“灰空间”等,彰显对城市公共性的重视。但建筑实际运行后,由于管理成本和管理意识跟不上,这些公共空间往往被后期增加的栏杆、花池、围墙等障碍物隔开,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城市规划对公共性的考虑不足。例如,很多规划中,城市绿地被四面的城市道路围合,表面上是防止绿地被侵占,明晰产权,实际上割裂了城市绿地和建筑的积极关系,造成绿地服务配套不足,活动方式单一。还有近几年建成的高铁站,几乎无一例外地设置尺度巨大的“站前广场”,将高铁站和城市割裂开,而实际上大量人流是通过整合在高铁站内部的城市公共交通到达的,完全不需要“站前广场”。第二是顽固的“本位主义”思想。除去政府办公机构,就连我国的大学都鲜有开放式校园,甚至最近频频建成的各市图书馆、文化馆、市民中心和社区医院等完全鼓励向市民开放的设施也设置围墙和大门。这样,自然很少有管理者能接受高度开放的建筑形态,即使接受了,也要加以改造。第三是商品房住宅的单一开发模式,造成几乎清一色的封闭管理居住小区,并且以专属花园和严格的安保门禁系统作为“卖点”,进行社会阶层划分的心理暗示。在这样自上而下全方位的封闭思想意识下,对空间的“城市公共性”的讨论就是奢谈。无疑,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间,我们的这种“里坊制”的城市反倒为分隔管理创造了便利的物质条件。因此,在以后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方面推动“城市公共性”的落实,恐怕又要遇到更大的阻力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所忽视的商业利益反而成为推动“城市公共性”的动力。为了维持一些公共设施的运营,目前很多新设计和更新改造的城市公共设施项目都在加入商业设施,而商业的注入自然需要空间和管理上的开放,从而促进“城市公共性”的实现。以我们团队主持设计的若干南京市社区中心为例(南京的社区中心是南京市规划局参考新加坡的邻里中心功能,加入街道管理和社区医疗养老设施等,服务人口3~5万,建筑规模3~8万m2),早期的几个项目中,业主以行政服务功能为主来定位社区中心,造成较封闭的空间模式,进入运营阶段后发现社区中心成为了服务区域居民的心理归属地之一,商业潜力很大,于是很快要求进行商业化改造。最近设计的社区中心方案,都已经将社区中心定位为一个社区服务性商业中心和若干行政服务、医疗养老设施组合成的综合体,商业部分均按照常见商业街区的空间规律来打造。同时,社区公共服务的属性又赋予商业独特的开放特征——不计较公摊面积、“灰空间”规模较大、社区公益的文化和体育设施可以被整合在商业里……这种模式下第一个建成的案例就是南京石埠桥社区中心,我们设置了一、二层完全开放的商业街,三层以上出现社区办公、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用房;利用屋顶平台设置慢跑道、篮球场和舞蹈广场;外飘的大楼梯作为自动扶梯组的补充,提供了丰富的漫游路线,使整个建筑成为一座立体公园。这种模式非常受当地居民的欢迎,最近已在几座社区中心中推广和改进。
推动“城市公共性”,我们的体会是如同大禹治水——正面对抗不如因势利导,也许能给大家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