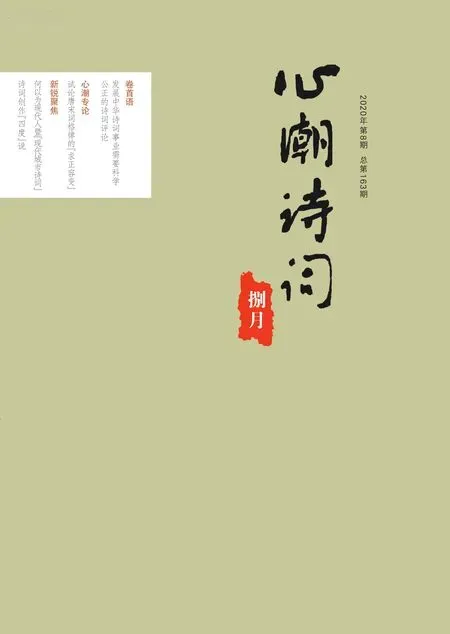中国新诗格律化独特的尝试
——论赵朴初的“自度散曲”
2020-11-19石钟扬
石钟扬
在中国当代诗坛,赵朴初是位独具风采的诗家。他以入世的身份做出世的事业,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文章。他的诗作,美刺并举,前者量大,后者质优。讽刺类作品中《某公三哭》等,堪称诗苑经典。
赵朴初于诗、词、曲皆精,其中尤以曲传神。他笔下之曲,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曲,而是一种既规范又自由的“自度散曲”。既有传统散曲之韵味,又具新体诗之洒脱。我则视之为一种新的格律诗。
一
一部文学史,实则是一部艺术形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艺术形式的新陈代谢史。中国学界则早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命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追求,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变为一种划时代的现实。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的则是白话诗的大胆尝试。
中国新诗早期尝试,大抵经历了“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到“欧化”的历史过程。因而早期之新诗多为“词化新诗”或“曲化新诗”,直到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的周作人《小河》出现才以“欧化”道路,彻底抛弃旧诗词格律的镣铐,而追求自然美的节奏。胡适自己的《尝试集》虽在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下力求把“诗的散文化”与“诗的白话化”统一起来,以获得“诗体的大解放”,被文学史家称之为“胡适之体”,但其中“真白话的新诗”为数并不多。陈子展早就说:“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作为诗人的赵朴初,他的创作虽以古体诗词为主,但他却一直关注着中国新诗的发展,并“由学古而渐想到创新,希望能在我国新诗歌的创建中起一点‘探路人’‘摸索者’的作用”①赵朴初:《片石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前言》,第1页。本文所引赵文、赵诗皆据此书,不再一一出注。。其志可嘉。
赵朴初在创作实践中,较早遇到“诗歌中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就出现了圆凿方枘,互不相入”的问题。这迫使他去思索,他看到“清朝末年已经有人注意及此,想作一点革新的尝试,可是矛盾实在太大,纵然削足,终难适履。‘五四’以后,有人又提出了语体新诗主张,打算索性抛弃旧形式,从根本上彻底改革我国诗歌。不少人曾为此从各方面付出过可贵的劳动。”对于方兴未艾的新诗运动,赵朴初又看到:“诗与文究竟不同,诗歌与口语差别更大。要做到既是全新的,又是大家熟习的;既是现代的,又是适合民族口味的;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经过琢磨锻炼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应该说这几个“既”与“又”,既是赵朴初对中国新诗困境的宏观评价,又表明了他的新诗审美理想与追求。由此出发,他说:“因之在‘五四’后的新文学中,诗歌的成就,较之其他领域,如散文、小说、戏剧等等,总觉得差着一筹。”既而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我由于个人爱好,对于所谓新旧这两种诗体都曾作过若干尝试,而结果则都不大理想。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是否可以入诗?如果可以,应当如何写?旧形式是否还可以用?如果可用,应当如何用?这些都是常在脑筋里盘旋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深刻地影响着赵朴初对新诗可行形式的自觉探索。
二
“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不断在内心中引起了强烈的激情,愈来愈觉得非倾吐出来不可。要倾吐出来,就必然要接触到诗歌语言的形式问题,而这一问题则是颇不简单的。”赵朴初对诗歌的艺术形式是何等重视。他创作、探索的结果,是倾向于从传统诗歌去寻找创造新诗格局的途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片石集》中,赵朴初有长篇谈诗的《前言》,堪称其诗歌美学宣言:
诗歌与散文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诗歌要求有节奏,有韵律(不是韵脚)。这是只有适当地运用每个民族的语言特征(即语音、语调等等)才能取得的。语言特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可以随时代的迁流而变化,但绝不能硬性割断或者任意强加。过去各种诗体,大致都起于民间,其音调之和谐总是先由人民大众于无意中取得,经过一定时间不自觉的沿用,著为定式,这就产生了所谓“格律”。格律可以突破,可以推翻,但推翻之后又必须有新的格律取而代之,而此新格律的形式,仍然要根据语言的特点,仍然要经过酝酿孕育的阶段,并且谁也没有把握何时可以诞生,更不用说长大成年了。而同时,人民又是随时都迫切需要诗歌的,“精神食粮”是一个颇为形象化的“隐比”。在全新的、比较成熟了的、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真心喜爱欣赏的诗歌形式产生之前,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又有这样一个设想:可否还是酌采人民原已熟习的传统的诗体,即诗、词、曲的形式,先解决群众的需要问题,并借此提高一般群众对诗歌语言的接受水平,同时,通过实践,检查在古典诗歌中究竟有哪些是还可以继承或者可以借鉴的东西,为创造将来新诗格局寻找途径。
从“为创造将来新诗格局寻找途径”这一宏伟目标出发,赵朴初具体细微分析了传统诗、词艺术形式之得失之后,表示对“曲”情有独钟。他指出,“曲”与“词”一样来自民歌,后来与音乐和舞蹈相结合,成为我国古典戏剧的主流,占据我国舞台最少达七八百年之久,从十九世纪起,它才逐渐退出舞台,因而也就脱离音乐舞蹈,和“词”一样成为仅供案头欣赏(最多是朗诵)的一种文学品种了(所谓“昆曲”,起于晚明,已不能代表“曲”的全部面目)。
赵朴初进而说,作为诗歌品种,“曲”有四大优点。第一,它兴起较晚,脱离群众的时间也不太长,因而比较接近现代人的情感与语言,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内吸取各种新的词汇乃至表达方法,而不至过于扞格。
第二,由于它是应用于舞台的,须要如实地刻画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情世态,逼真地模拟各种人物的神气、口吻,因之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一切足以取得预期效果的各种表现手法与作风,而不受正统教条的束缚。例如,所谓尖新、刻露、俚俗、泼辣等等,在“诗”与“词”里被视为瑕疵,引为禁忌的,在“曲”中却不仅容许,反而被认为“本色当行”。这确是一不小的解放。
第三,“曲”不仅在句型上突破了“诗”的整齐单调(仅指典型的五、七言),并且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自由使用衬字);甚至在语调上也相当灵活,突破了“词调”的句数限制,许多曲调的句数可以顺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作者长说短说,多说少说,随意所向。
第四,“曲”除了供演出使用的剧本外,另有专供阅读的“散曲”。“散曲”有一种独立的“小令”和数调组合的“套数”。“小令”可以是单章,也可以是联章,“套数”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可以异调组合,也可以同调叠用(以“前腔”或“幺篇”表示)。作者可以随自己的方便,或作速写式的即兴小品,或适应各种题材,各种时地的需要。
当然,赵朴初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曲”也有特殊的限制,即所谓“曲律”,有一些“律”甚至严过诗与词,如南曲与北曲的牌子不能混用,同为南曲或北曲中的不同“宫调”不能混用等。但这一切都由“配乐”而起,为了便于歌唱不能不如此。如果只是把“曲”作为一种诗体,不再演唱,不再配乐,“合律”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只须照顾到一般平仄,使读来顺口,听来入耳,似乎就可以通得过了。经过如此透彻的分析,赵朴初认为,“曲”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诗歌形式,对于创立我国的新诗歌,还是颇有可为的。
在摸索中实践,在实践中摸索。赵朴初在创作中渐渐又萌发奇想:既然不再为“配乐”而写曲,既然撇开了种种为“合乐”而制定的传统曲律,那么又何必一定非沿用传统“曲牌”不可呢?于是他尝试着自定调式,自定调名,姑且名之曰:“自度曲。”“自度”一词也来自古人,不过古人的“自度”,指的是自己制腔,自己作词,而赵朴初则仅作词,不制腔。他说:“自己并非音乐家,只是一名为新诗歌探索道路的工作者而已。”至于这种无律之曲,非曲之曲,是否也可以就叫做一种新体诗呢?赵朴初说:“自己没有任何把握,只好留待人民和时间来作鉴定。”我则认为这就是一种新的格律诗,或叫格律化的新诗。
为使自己创作的“自度散曲”——这种新体诗的艺术形式切实可行,赵朴初就其“平仄”与“韵脚”两个技术性问题,作了非常切合实际的设计与解说。他说,字音的“平仄”形成于大众的语言习惯,存在于每个人的口头,既非强加,更不神秘。“平仄”字音的一定排列能够产生一定的和谐这一道理,原是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与协作劳动中早已发现,并一直在无意识地应用着的东西。专家文人的贡献只是在于归纳总结,找出一些语音上的规律,使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运用,从而比较有把握地取得抑扬顿挫、升降起伏的效果。这就是所谓“格律”的由来。他认为不论中国诗歌将来会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汉语语音的特点不变,“平仄”总还是不能无视不管的。
至于“韵脚”问题,他说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因为我国人民群众对于“韵脚”已经如此熟习,如此喜爱,以致如不押韵,简直就很难使一般人承认是“诗”了。基于我国方言太多,韵部各异,赵朴初主张依照已经得到较广承认的相近音读,约略画出一个大体范围而容许小有出入,或同时定出“宽”“严”韵部,听任作者取用。他自己则倾向大体依据京剧的所谓“十三辙”。这一分法与《中原音韵》相同之处是取消了入声(此点不适合东南各省)。与《中原音韵》不同之处是:第一取消了闭口音(此点不适合闽广),第二为“庚青”“真文”与“侵寻”不分(此点不适合北方各省),第三为“寒山”“桓欢”与“先天”不分(此点大体全国可通)。这样可减少韵部数目,放宽选韵范围,并借京剧的广泛影响,以便使更多的人来接受这种新体诗。真可谓菩萨心肠与诗人情操相结合的产物,从而使诗航普渡。
三
赵朴初创作“自度散曲”,有一个从偶然到自觉探索的过程。1959年在一次出国途中,他偶尔带着一本元人散曲选集《太平乐府》,供飞机上浏览。在西伯利亚上空,随手写了几首小令,描写当时的景物与心情,这是他写曲的开始。回国不久,先后有七一节与十周年国庆,于是他又尝试用“曲”来参与庆祝。此后他又多次试用“曲”作为讽刺声讨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美刺俱佳,证明“曲”这种诗体是可登“大雅之堂”的。从此他进而摆脱传统“曲牌”,尝试着自定调式,自定调名,自觉创造着这种无律之曲——自命名为“自度曲”的新诗体。
我手边仅有赵朴初之《片石集》,以年代为序,收其自1950年12月至1977年10月的作品189首,其中有曲20题33首。《片石集》中有《观演〈蔡文姬〉剧有作三首》,正好是诗、词、曲各一首,所咏皆为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
竹枝
黥头刖足语堪哀,不道成书有女回。
了却伯喈千古恨,九原应感郭公才。
鹧鸪天
玉珮明珰望俨然,骊歌肠断草原天。忍抛稚子三千里,换得胡笳十八篇。 家再破,梦初圆,中郎志业几分传。和亲肯遣王姬嫁,毕竟唐文汉武贤。
快活三带过朝天子四换头
左贤王拔剑砍地,镇日价女哭儿啼。进门来惨惨凄凄,出门去寻寻觅觅。 千里,万里,处处是伤心地。胡笳做弄蔡文姬,怨绪哀弦难理。遣使何为?赎身何意?我道曹公差矣!谓中郎有遗书,有女儿能诵记,只消得寄个纸笔。 睦邻大计,更要将心比他意。常通声气,频传消息,何如认个亲戚?和吐番的唐太宗,和乌孙的汉武帝,都比你,有主意。
众所周知,郭沫若的《蔡文姬》,是其循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东临碣石有遗篇,魏武挥鞭”之词意,将“替曹操翻案”的观念变为舞台形象的作品,是一部天才的媚俗之作。即使是温文尔雅的赵朴初,1959年7月当郭沫若正在《蔡文姬》刚搬上舞台的兴头上,也忍不住以形象语言表示一点“不同见解”。其诗含而不露,其词略带讽喻,其曲则痛快淋漓地将郭沫若幽默了一番。曹操令文姬归汉的最大理由是代父(蔡伯喈)续书,以点缀文治之业绩。而赵朴初在曲中则谓:“我道曹公差矣!谓中郎有遗书,有女儿能诵记,只消得寄个纸笔。”让他写来即可,何必让文姬归汉,既造成新的妻离子散,又不利于睦邻大计;既有违人性,又有碍国策。这就将郭沫若《蔡文姬》之核心情节抽空了。但赵朴初所作,并非论文,而是艺文,幽默风趣,富有穿透力。与其同题诗、词相比较,可谓诗庄词媚曲更洒脱。曲于赵朴初是随手拈来,点染成趣,其艺术魅力远非其诗其词所能比拟。由此及彼,通览《片石集》,其中曲所占比例虽仅六分之一,而其影响与传播,则远胜其他作品。
在各种诗体中,“‘曲’是最能容纳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泼辣尖锐的风格的”。赵朴初深知此道。他的“自度散曲”虽美刺并举,但真正传神的还是讽刺类的作品。此类作品,最有名的是《某公三哭》和《反听曲》(三首)。
《某公三哭》,拟用前苏联总书记尼·赫鲁晓夫之口吻哭灵,“一哭西尼”——饮弹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二哭东尼”——不幸逝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三哭自己”——不幸下台赫鲁晓夫。赵朴初那维妙维肖、幽默风趣的《某公三哭》至今却仍能记忆犹新,诵之上口。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新格律诗的魅力。赵朴初所拟曲牌也别具一格,且与内容融为一体。如“一哭西尼”所拟曲牌为《秃厮儿带过哭相思》,“二哭东尼”所拟曲牌为《哭皇天带过乌夜啼》,“三哭自己”所拟曲牌为《哭穷途》。限于篇幅,仅引“三哭自己”于兹:
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上帝啊!俺费了多少心机,才爬上这把交椅,忍叫我一筋斗翻进阴沟里。哎哟啊咦!孤负了成百吨黄金,一锦囊妙计。许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太太的妇联主席,姑爷的农业书记。实指望,卖一批,捞一批,算盘儿错不了千分一。那料到,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砂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真是从哪儿啊说起,从哪儿啊说起! 说起也希奇,接二连三出问题。四顾知心余几个?谁知同命有三尼?一声霹雳惊天地,蘑菇云升起红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眼泪儿望着取下像的宫墙,嘶声儿喊着新当家的老弟,咱们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招牌换记,硬说我寡人有疾。货色儿卖的还不是旧东西?俺这里尚存一息,心有灵犀。同志们啊!还望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
通篇全用中国人熟习的典故、词汇,来写邻家的故事,令人读来一点不隔,活灵活现宛如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既幽默,又发人深思。不管今天你如何评价赫鲁晓夫(乃至三尼),但这《某公三哭》的审美价值仍在。
《反听曲》三首,写于1971年9月间,当时就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天下。我这里引用的是当年流传的版本,与《片石集》中发表的稍有差异,细心的读者若作一对比,不难发现手抄本还能更加原汁原味。
反听曲之一
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作可憎,孤人唤作冤家。夜里演戏叫做旦的、叫做净的,却原满脸大黑花。圣明王爷,偏偏称孤道寡,你说他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
反听曲之二
听话听反话,一点也不差。“高举红旗”,却原来是黑幡高挂。“四个伟大”,变成四番谋杀。“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看他耍出了多少戏法。“千年出一个”,烧香拜菩萨;“句句是真理”,念经一大挂,抬高自己是真,拥护领袖是假。管他是真是假,马克思主义,马赫主义都姓马。
反听曲之三
大喊共讨共诛的英雄,原来是最大最大的坏蛋、野心家。未料到照妖镜下,终于现出了青面獠牙。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折戟沉沙,落得个焦狗肉送入蒙古喇嘛。正剩下白惨惨的阴魂,紧跟赫光头去也。这真是“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是吗?
这三首《反听曲》是针对林彪事件的,作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作品里引号中的语言是“文革”中人人耳熟能详的林彪、陈伯达们的精彩话语;这些造神运动中的话语曾一度蒙住了天下多少人之耳目。一旦真相大白,则令天下人为之一惊。令人感慨,谎言的魔力竟如此巨大。赵朴初冷眼旁观,以极为通俗的语言,给中国人民传播一个伟大智慧,识破谎言的智慧: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听话听反话,一点也不差!令人受惠终生。
四
中国新诗产生伊始,胡适以“曲化新诗”“词化新诗”尝试着,尚未脱其母体的胎印。胡适曾自我反省云:“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①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9页。如今赵朴初的“自度散曲”,决非当初“曲化新诗”的历史回环,他对自度散曲用得出神入化,他的作品潇洒自如,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格律化的新诗。这种格律化的新诗,既无传统格律诗的僵滞,又无自由新诗之涣散,既自由又有法度,从根本上克服了新诗难以朗朗上口,难以记诵的缺陷,基本实现了赵朴初自己的诗歌美学追求,确为中国新诗格律化的独特尝试与特殊贡献。这是他深厚的诗学根基①案:其太高祖赵文楷虽为状元郎却写过传奇剧本《菊花新梦》(笔者校点,《黄梅戏艺术》1987年第2期),其母陈仲瑄也写过剧本《冰玉影传奇》(太湖拜石书屋2003年印行)。这以家学渊源让其“诗学根基”中较一般士子多了一份“曲”的元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他从佛教经文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的产物,也是他长期站在世俗社会的边缘,眼观时代风云,既以慈悲为怀,又嫉恶如仇,所磨砺出来的特殊诗怀与诗体,是其仁心与佛心的精彩的诗化表达。
赵朴初的诗怀与诗体,非常人所能模拟步武,但他的诗歌美学原则与诗体探索精神,实为一份珍贵的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去借鉴,去研究,去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