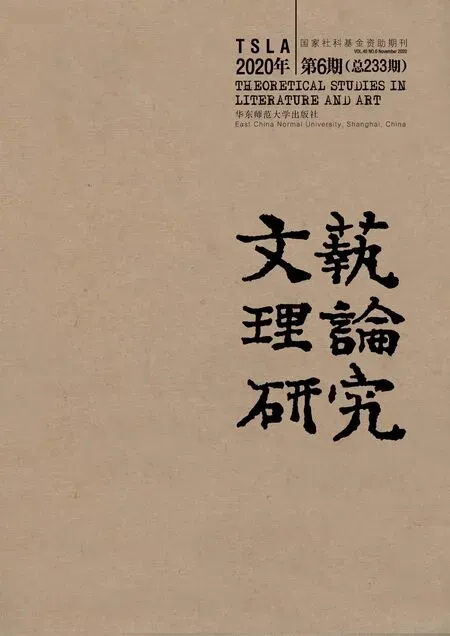羞耻、酷儿理论与情感转向: 以美国学界为中心的考察
2020-11-18杨玲
杨 玲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所谓的“情感转向”。从哲学、批判理论、文艺理论、媒介研究、性别研究到心理学、脑科学和医学等各个学科,都涌现出大量关于情感/情动(affect)的讨论。作为对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其“语言转向”的反拨,“情感转向”标志着“更广泛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突变”以及学术范式的转型(Wetherell 2-3)。目前,国内学界对情感理论的兴趣正与日俱增。①但现有的研究成果或是总体性的思潮扫描,或是局限于单个理论家,鲜有针对某个引起广泛讨论的特定主题展开的学术整理。本文以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羞耻理论为起点,梳理了美国酷儿研究领域的学者围绕羞耻这种情感形式展开的学术探讨,审视了塞吉维克之后的学者对塞氏羞耻理论的借鉴和发展。本文认为,美国酷儿学者关于羞耻的思考,为当代情感理论打上了独特的酷儿印记。羞耻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酷儿政治、伦理、历史和美学,羞耻与性别、性态(sexuality)、失能(disability)、种族等范畴的交叉也为社会和政治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工具。
本文的写作目的有三。一是通过羞耻研究的个案,探究美国学界为何、如何拥抱情感理论,对情感的关注可以打开哪些新的问题域,生产哪些新的知识。具体到羞耻而言,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选择聚焦这种隐秘的私人情感,羞耻与其他社会分析范畴能够产生怎样的联结。二是探索一种介于宏观的理论扫描和微观的理论家研究之间的“中观”研究方法,即围绕一个话题,串联起一个较长时段内与该话题相关的重要论述;通过对一手文献的阅读,了解海外学者如何通过学术对话将话题一步步引向深入,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西方学术的发展脉络,既见“树木”,也见“森林”。三是质疑国内学者对酷儿理论、情感理论过于笼统的一些断言,如宣称“酷儿理论属于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都岚岚 187),或将塞吉维克的情感理论概括为“女性主义情动理论”(刘芊玥 208)。酷儿理论和情感理论都并非单一、稳定的理论体系,与其为这些理论贴上似是而非的属性标签,不如厘清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所针对的问题。
囿于篇幅,本文没有涉及美国之外的酷儿学者对羞耻的论述。②这种以国别来划定论述范围的方式并非毫无依据。美国人文社科学者常被诟病的一点就是他们视野狭隘,很少关注美国以外的,特别是非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了论述的紧凑性,本文也没有广泛涉猎酷儿研究领域以外的羞耻研究,③这些成果有待专文探讨。
一、塞吉维克的情感转向和羞耻理论
塞吉维克不仅是性别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也是最早关注情感的当代人文学者之一。1993年,她在《GLQ》(GLQ:AJournalofLesbian&GayStudies)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酷儿操演性: 亨利·詹姆士的〈小说的艺术〉》一文,④引领了酷儿研究的“情绪转向(turn to emotion)”(Koivunen 45)。1995年,她又在著名理论期刊《批判性探索》(CriticalInquiry)上发表了与弗兰克(Adam Frank)合写的论文《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 阅读西尔文·汤姆金斯》。⑤该文与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情感的自治》(1995年)一文共同拉开了西方学界情感转向的序幕。
据英国约克大学艺术史和酷儿理论教授爱德华兹(Jason Edwards)考证,塞吉维克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就对情感议题产生了兴趣。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探讨了哥特小说中特殊的情感构型。但在此后的酷儿理论书写中,塞吉维克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欲望,而非情感。20世纪90年代初,塞吉维克被确诊患乳腺癌。与此同时,她重新开始了对情感的思考(114—15)。张楚(30)、刘芊玥(209)和郑国庆(8)等国内研究者都认为罹患癌症是塞吉维克学术生涯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的确,塞吉维克在《触摸感情: 情感、教学法、操演性》(2003年)一书中提到,化疗和雌激素的降低导致“性态越来越少地成为[学术]反思的刺激性动机”。同性恋政治“策略上的平庸化”及其对艾滋病的排斥,也让酷儿理论和同性恋权利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复存在(TouchingFeeling13)。但身体机能的变化和对酷儿理论的失望,仅仅解释了塞吉维克为何不再继续从事酷儿研究,却没有很好地解释她为什么从酷儿研究转入情感研究。
事实上,塞吉维克并非唯一一位疏远酷儿研究的知名学者。在塞吉维克转向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和藏传佛教时,酷儿理论的其他创始人也在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巴特勒(Judith Butler)开始关注正义和人权,沃纳(Michael Warner)则转向布道和世俗主义(Halley and Parker 422)。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术刊物《南大西洋季刊》(SouthAtlanticQuarterly)为此于2007年发表了一个名为“性之后?酷儿理论以来的书写”(After Sex?On Writing since Queer Theory)的特刊,专门讨论以性、性态和性别为核心的酷儿理论是否已经过时。
塞吉维克的情感转向其实是她日益厌倦主流理论,寻找其他理论可能性的结果,也是她对羞耻这一情感的兴趣使然,与她的健康状况没有必然联系。在《暗柜认识论》(1990年)中,塞吉维克意识到现有的概念工具很少能处理“人们彼此不同”这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当代批判理论仅仅提供了少量的、极其粗糙的区分主体的范畴(如性别、种族、阶级、国族等),这些有限的区分范畴远远不能描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塞吉维克接触到了汤姆金斯的著作,并立刻为之吸引(WeatherinProust144-45)。汤姆金斯提出了一个由天生的九种不同情感构成的情感系统。在塞吉维克看来,这个由“有限多(n>2)价值”结构的情感理论不仅揭示了当代理论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还有可能帮助我们“生成一个关于差异的政治视景(vision),以便同时抵抗二元对立的同质化和无限的平凡化(infinitizing trivialization)”(TouchingFeeling108)。这也就是为什么《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这样一篇关于汤姆金斯著作的导引性文章,是从历数当代理论的“四宗罪”(四个普遍假设)开始的。塞吉维克认为,不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包含着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后结构主义不过是让我们对各种二元对立有了更复杂的理解(93—94)。《触摸感情》一书的导论部分更是开宗明义地写道: 该书的目的是摆脱二元论的框架,探索“非二元论式思维和教学法”的工具和技巧(1)。
在《梅兰妮·克莱因和情感的影响》(“Melanie Klein and the Difference Affect Makes”)一文中,塞吉维克明确批评了占据学界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福柯理论的思维惯性。她指出,精神分析学说包含一系列有害的假设,如二元性别差异的重要性、欲望的首要性、童年经验的决定性影响、朝向一个特殊的成熟状态的线性目的论、零和游戏的逻辑以及对中间项(middle term)的排除。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我们和权力的关系就是权力越多越好,权力就意味着全能(omnipotence)。我们在婴儿时期以为自己是全能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认清全能是一种幻象。在弗洛伊德那里,权力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东西,在全有和全无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项。由于人类文明无法与个体的全能感和无止境的欲望共存,我们的精神活动最终是“由固有的欲望与强加的或内化的禁止之间的争斗构成的”(WeatherinProust131)。压抑问题不仅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也是西方二元对立的政治和宗教观念的源头。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将一系列西方解放话语——阶级政治话语、身份政治话语、启蒙价值观和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性解放计划——描绘为“和谐一致、相互延续的”,因为它们都“依赖于外部和/或内部的压抑的重要性”(133)。不仅压抑假说本身是成问题的,误导了我们对社会和个体境况的理解,各种反对压抑的计划也不过是充当了压抑假说的宣传工具。在塞吉维克看来,福柯的著作不但没有消除压抑假说,反而“通过替代、增殖和/或实体化”把它传播得更广(134)。
克莱因和汤姆金斯的理论之所以让塞吉维克深受启发,就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二元论所缺乏的中间项,而且都绕开了压抑理论的智识困境。⑥弗洛伊德的“欲望和禁止的辩证法”对克莱因而言是一个次要的心理发展过程,她更关注婴儿内心世界不同欲望之间的冲突,“偏执-分裂心位”所导致的内生性焦虑和恐惧(WeatherinProust131-132)。汤姆金斯区分了情感系统和驱力(drive)系统,认为情感系统类比性地(analogically)放大了驱力系统。这意味着“性欲不再只是开/关的事情,不再只有被标记为表达或压抑的两个可能性”(TouchingFeeling100-101)。在汤姆金斯看来,驱力和情感都根植于身体,但驱力在时间和对象(objects)方面远没有情感自由。比如,驱力的对象极为有限,我们只能呼吸少数几种气体,喝少数几种液体(18),但“任何情感都可能有任何‘对象’。这是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的基本源泉”(99)。情感自成目的(autotelic)、“自我确证,不管进一步的指涉物是否存在”(100)。这和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目的论(将个体的“成熟”当作精神生活的目的)正好相反。汤姆金斯的情感自我目的论,让他的学说“不仅完全没有恐同症,而且没有任何异性恋目的论的暗示”(99)。
塞吉维克自称是在“寻找关于羞耻这个话题的可用观点时”,初次读到汤姆金斯的情感理论的(TouchingFeeling97)。她对羞耻的讨论主要见于《酷儿操演性》(包括1993年和2003年的两个版本)和《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这两篇文章。⑦在这些文本里,塞吉维克摈弃了对羞耻的道德评判,也不再将羞耻和内疚(guilt)当作压抑的附属物和规范社会行为的手段。在她看来,讨论羞耻究竟是一种好情感还是坏情感毫无意义。羞耻的价值在于它与内疚、压抑的概念以及福柯的压抑假说之间的“潜在距离”(“Queer Performativity” 6)。
根据汤姆金斯的理论,婴儿在7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学习区分照料者的脸和陌生人的脸。由于不习惯这种区分,婴儿会将陌生人的脸误认为照料者的脸,并向这张陌生的脸表达兴趣(interest)和愉悦的正面情感,直到意识到错误,正面情感遭到抑制,羞耻-屈辱反应(shame-humiliation response)被自动激发(Timr 200)。塞吉维克援引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巴史克(Michael Franz Basch)的解释称,羞耻反应“代表的是接触时的微笑的失败或缺席,是对他人没有做出反馈的反应,是社会孤立以及需要从这种孤立境况中解脱出来的信号”。⑧羞耻产生于俄狄浦斯情结之前,与弗洛伊德所说的禁止无关。羞耻是在一个建构身份(identity)的认同性沟通(identificatory communication)回路被扰乱的时刻形成的,它既扰乱了认同,也塑造了认同。羞耻具有一种双重运动,既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自我,“朝向痛苦的个体化”,又让人感受到与他人的关系,“朝向无法控制的关系性”。羞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情感,“源自社交(sociability),也以社交为目标”,甚至具有传染性(TouchingFeeling36-37)。
汤姆金斯创造性地将羞耻和兴趣、愉悦关联起来。他认为,羞耻是因为愉悦或兴趣的中断、受阻而被触发的:“没有正面情感,就没有羞耻: 只有一个带给你享乐或勾起你兴趣的场景才会让你脸红。”(TouchingFeeling116)在汤姆金斯看来,羞耻并非只是一种痛苦的境况和可鄙的情感,而是“阐明了我们对世界的强烈依恋,我们与他人发生联系的欲望”,以及我们因人性的脆弱常常无法维持这些联系的事实(Probyn 14)。正因为如此,塞吉维克提出,任何简单地把羞耻当作个体或群体身份中的“有毒”部分,企图除之而后快的治疗策略或政治策略都是荒谬的(“Queer Performativity” 13)。对于某些酷儿人士来说,“羞耻是第一个、而且会一直是一个永久的、结构性的认同事实: 羞耻有着自己极为强大的建设性可能和极为强大的社会变化的可能”(14)⑨。
虽然对羞耻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这种情感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引起美国学界的重视。在此之前,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将内疚视为决定性的心理情感),⑩美国学界多将羞耻与内疚混为一谈,或将羞耻当作内疚的一种次要变体(Leys 123)。比如,在东方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人类学名著《菊花与刀》(1946年)中,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把日本文化描绘为羞耻文化,认为日本人没有足够强大的自我意识来体会内疚,内疚是更高等的西方文化的标志(Vincent 631)。1953年,皮尔斯(Gerhart Piers)和辛格(Milton B. Singer)在其合著的《羞耻与内疚: 一个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ShameandGuilt:APsychoanalyticandaCulturalStudy)一书中改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1962—1963年,汤姆金斯的《情感、意象、意识》(AffectImageryConsciousness)的第一卷和第二卷问世,该书彻底抛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随着这两部著作的出版,美国学界开始了“对羞耻的激进的再思考”。羞耻不再被视为负面的、毁灭性的,而是被当作一种具有潜在正面作用的情绪(Leys 123-24)。通过对汤姆金斯著作的发掘和整理,塞吉维克将羞耻重新阐释为与身份塑造相关的生产性(productive)情感,并将这种情感和酷儿理论结合起来。尽管羞耻不专属于酷儿群体,但酷儿经验为思考羞耻“与操演性、性别和抵抗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特别有利的视角(Barber and Clark 26)。塞吉维克的羞耻理论也因此首先在酷儿学者那里获得了积极回应。
二、羞耻与酷儿伦理和政治
1999年,现任耶鲁大学英语文学讲席教授的沃纳出版了其代表作《正常的麻烦: 性、政治与酷儿生活的伦理》,详细探讨了性羞耻的政治与美国酷儿生存现状的关系。该书的第一章“性羞耻的伦理”开门见山地写道:“几乎每个人或早或迟,或快乐或不快乐地,都会丧失控制自己性生活的能力。”作为补偿,几乎每个人都会试图去控制他人的性生活,并自以为这样的行为是道德的。控制的对象既包括有害的、非自愿的性,也包括“快感、身份和实践的最私人的面向”(Warner 1)。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喜欢性:“可能因为性是丧失控制的时刻,是个人意识与更低等的动物欲望和感知融为一体的时刻,是权力和要求(demand)赤裸对峙的时刻,性让人充满厌恶和羞耻。”(2)
性羞耻不仅是无法回避的“生活事实”,也是“政治性的”,它让某些人被污名化为不正常的人或罪犯,让某些性快感变得不被许可、不可想象(Warner 3)。羞耻的政治远不只是卫道士们的故意羞辱,而是包含了“沉默的不平等、孤立的不经意的效果、公共进路(access)的缺乏”。女性和同性恋群体最易成为孤立的受害者,在异性恋家庭长大的同性恋青少年往往感到深刻的疏离和隐秘的羞耻(7—8)。为了抵抗传统的性规范以及这种规范所生产出来的性羞耻,沃纳提出了“性自主”(sexual autonomy)的概念。性自主的培育不是单靠释放压抑、放松管制、清除文明带来的羞耻,而是需要为“新的自由、新的经验、新的快感、新的身份、新的身体腾出空间”(12)。性差异(sexual variance)是自主的前提条件,也是自主的结果。然而,羞耻不仅遏制差异,还限制了关于差异存在的知识,使得公众难以接触到挑战主流趣味的性物品。法律和政治体制常规性地生产羞耻,以此来限制性自主。没有一个人类生活领域像性领域那样是“由羞耻统治的”(17)。
沃纳借用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污名(stigma)的研究指出,普通的羞耻与不当行为有关,当事人可以为自己找借口,将羞耻遗忘。这种羞耻只影响我们的传记性身份(biographical identity)。但性倒错者的羞耻(污名)却无法轻易抹消,它是一种像命运一样降临到人身上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和个体行为无关。性差异曾经只是一个羞耻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变成污名,同性恋者不管是否发生同性性行为都将承受这份污名(28)。为了消除这种污名,一些同性恋组织主张同性恋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声称同性恋身份与酷儿性态无关,认为体面的同性恋者不应从事越轨的性行为。由于这种政治策略仅仅挑战了同性恋身份的污名,但却强化了性羞耻,它注定是自相矛盾和软弱的(31)。沃纳认为,与他人的关系“是从承认自身最贱斥(abject)、最不名誉的部分开始的”(35)。羞耻是酷儿文化的基石,贱斥是酷儿人群共享的境况,不在性的问题上自以为是、自恃清高,是酷儿社群的基本原则。如果性是不光彩的事儿,大家都有份。正是这种不光彩的共同经验将酷儿团结在一起,并培育出一种尊严感。就像塞吉维克曾说的,“酷儿”一词“以仍然让卫道士恼怒的方式颂扬它和羞耻的关系”(36)。最富成效的同性恋权利运动总是根植于这种关涉“羞耻中的尊严”(dignity in shame)的酷儿伦理(37)。
罗切斯特大学艺术史教授克林普(Douglas Crimp)2002年发表的《马里奥·蒙特兹,向羞耻致敬》一文将塞吉维克和沃纳关于羞耻的论述整合在一起,进一步阐发了羞耻在酷儿社群中发挥的伦理和政治功能。克林普的文章是其“同性恋之前的酷儿”(Queer before Gay)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旨在通过发掘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酷儿文化来反抗当下“同质化、正常化和去性化的”同性恋生活(58)。《马里奥·蒙特兹》一文重点讨论了波普大师沃霍尔(Andy Warhol)1965年拍摄的一部黑白实验短片《试镜2》(ScreenTest#2)。该短片的主人公名叫马里奥·蒙特兹。他是一位出生于波多黎各的易装者和扮装皇后,曾出演过多部地下电影。在短片里,沃霍尔的合作者、编剧塔维尔(Ronald Tavel)扮演一位导演。该导演以工作合同为诱饵,强迫前来试镜的蒙特兹做出一系列令人羞耻的动作,甚至逼迫蒙特兹掀开自己的裙子,向观众暴露出他的男人身。
尽管沃霍尔的影片让观众感到极度不适,但克林普却引用塞吉维克在《酷儿操演性》一文中关于羞耻与身份的矛盾关系(即羞耻同时界定和抹消了身份)的论述,认为影片中的羞辱场景激发了一种独特的认同过程。塞吉维克写道:“羞耻最奇怪的特征之一(我认为也是最具有理论意义的特征)就是: 对他人的虐待,被他人虐待,他人的困窘、污名、虚弱、指责或痛苦,看上去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却能轻易地——假设我是一个容易感到羞耻的人——让我被这种感受吞没,这种潮水般的感受似乎用能够想象到的最孤立的方式勾画出我精确的个体轮廓。”(“Queer Performativity” 14)换言之,羞耻是通过我对他人羞耻的共情来建构我的身份。不过,在承受他人羞耻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与他人的彻底分离。他人的差异被保存下来,没有被当作我自己的差异。在承受他人羞耻的那一刻,我把自己放入他人的处境中,只是因为我认识到我也很容易感到羞耻。羞耻因而具有“阐发被羞辱者的集体性(collectivities of the shamed)”的能力(Crimp 65-66)。
沃纳在论述羞耻的政治时,也提到了这种集体性。沃纳称酷儿社群是真正的“落选者沙龙”,在这个沙龙里,一群极为不同的人因被世俗规范鄙视和拒绝的共同经历而彼此亲近。但当代同性恋骄傲(gay pride)政治却把接受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视为同性恋社群迈向“成熟”的义务,并排斥那些拒绝被同化的酷儿分子。骄傲政治仅把羞耻视为世俗意义上的不名誉,忽视了羞耻是将个体独特性转化为酷儿尊严的情感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借助沃霍尔的短片去了解20世纪60年代的酷儿文化。沃霍尔的电影不是窥淫癖式的(voyeuristic),而是让我们直面他人的差异和羞耻。我们在马里奥·蒙特兹的羞耻中看到他不可抗拒的独特性和脆弱性,我们对他的羞耻感同身受,我们感到自己也被暴露了(Crimp 66-67)。
无论是沃纳还是克林普,都尝试从酷儿群体的羞耻经验中生发出伦理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克林普所阐释的羞耻概念尤其让人联想到阿伦特的“世界”(world)概念,因为二者都具有将个体既区隔又聚拢的双重功能。阿伦特的“世界”是一个人类事务发生的场所:“人们既在世界中汇聚、见面、交往、相互见证,但又保持各自的距离,不消失于对方,不失去自己的个体性和独立性。”(陶东风)类似地,羞耻既让酷儿人士感受到自我的孤立、与他人的隔绝,同时也让自我和他人在羞耻中发生情感联结,为酷儿社群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情感动力。沃纳和克林普用激进的羞耻政治来抵抗日趋保守的骄傲政治的企图并非特例,而是代表了世纪之交酷儿学者和活动家的普遍关切。这种关切直接促成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同性恋羞耻会议”(Gay Shame Conference)。
三、同性恋羞耻、失能与酷儿历史书写
2003年3月27—29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两位知名酷儿理论家霍尔柏林(David M. Halperin)和特劳布(Valerie Traub)在密大举办了同性恋羞耻会议,邀请学者、批评家、活动家、艺术家和媒体记者参加。会议论文和相关讨论后于2009年结集出版。由于克林普的《马里奥·蒙特兹》一文“将塞吉维克对羞耻的理论探讨与反对骄傲的酷儿转向联系起来”,会议主办方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论坛来讨论克林普的文章,还在会议期间放映了沃霍尔的短片《试镜2》(Halperin and Traub 8)。
霍尔柏林和特劳布在论文集的导论《超越同性恋骄傲》一文中说明了办会的初衷。他们写道:“自1969年的石墙骚乱和该骚乱所宣告的同性恋解放时代开始,‘骄傲’就成为一个主张性自由的广泛社会运动的口号。”同性恋骄傲也是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浮出水面的政治推手。同性恋骄傲的目标是“同性恋的彻底去污名化”,即消除同性欲望所引发的个人和社会羞耻(3)。尽管同性恋解放运动已经为实现这个目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日益乏味的自我肯定文化也引发了同性恋社群内部的不满。2000年前后,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城市相继出现欢庆同性恋羞耻的活动。这些庆祝活动被故意安排在同性恋骄傲游行之前或之后的几天。这些活动有的曝光那些利用同性恋社群来盈利或赢得选票的虚伪行为,有的高调肯定被同性恋骄傲运动边缘化的酷儿群体(8—9)。同性恋羞耻会议的召开,一方面是为了探讨同性恋骄傲概念的持续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其他方式来从事酷儿政治和酷儿研究。所谓“其他方式”就包括审视骄傲概念的对立面——羞耻(3)。尽管塞吉维克通过《酷儿操演性》一文,成功地将羞耻添加到酷儿研究的议事日程,但她本人却并没有为这个概念提供“公认的稳固性、清晰性或连贯性”(7)。
同性恋羞耻会议有两个引人瞩目的议题: 一是羞耻和失能研究(disability studies)的结合,二是羞耻与酷儿历史书写的关系。由于西方的科学话语曾一度将异常性欲归因于不正常的,或有缺陷的身体类型,导致同性恋骄傲文化(如男同群体中流行的健身文化)非常重视身体的健全和身体形态的正常性。为了审视身体形态所产生的羞耻,会议主办方组织了一个以酷儿的/失能的羞耻(queer/disabled shame)为主题的小组论坛(Halperin and Traub 12)。密歇根大学英文系教授西贝斯(Tobin Siebers)的《性、羞耻和失能身份: 涉及马克·奥布莱恩》是该小组论坛最有启发性的一篇文章。
西贝斯将塞吉维克的羞耻理论和失能人群联系起来,探讨了失能人群的性存在(sexual existence)。他发现塞吉维克在论述羞耻的伦理力量时,并没有使用来自同性恋社群的例子,而是用失能作为羞耻的例证。比如,塞吉维克的一个主要例子是让读者想象一个衣衫不整、疯疯癫癫的男子闯入课堂,在课堂上胡闹一番,然后离开。由于疯子的出现,课堂里的其他人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又抑制不住地与这个疯子产生痛苦的认同(TouchingFeeling37)。不过,塞吉维克“既没有拷问失能男子[疯子]的羞耻,也没有拷问他的身份”(Siebers 202)。西贝斯和塞吉维克一样关心羞耻的伦理,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是: 谁有资格感受羞耻?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允许某些人拥有羞耻感,这些人是否就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为此,他引用失能诗人马克·奥布莱恩的诗歌,从能动性、公私领域的分野和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体制(sex/gender system)三个方面展开了思考。西贝斯认为,失能人群通常无法拥有性或其他方面的能动性。由于丧失了能动性和社会价值,他们也无法拥有羞耻感。其次,羞耻感依赖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羞耻产生的原因通常是个体暴露在公共视线中。但生活在医疗机构的失能人群时刻都处于暴露的状态,连性行为也需要他人的协助或监管,他们不得不压制自己的羞耻感。再次,失能者的身体既不是男人的身体,也不是女人的身体,失能者的性行为也和性别、性取向无关。就如奥布莱恩的一句诗所说的,他只是“一个属于护士的、坏的、脏的东西”,既非男人,也非女人(212)。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完全是以健全身体为基础的,但这种划分及其连带的性别刻板定型对于失能者来说是无效的。
除了失能的羞耻,部分会议代表还探讨了将羞耻概念用于历史书写的可能性。社会学学者古尔德(Deborah B. Gould)的《早期艾滋行动主义中的同性恋骄傲的羞耻》一文,审视了20世纪80年代初同性恋社群面对艾滋病危机时,羞耻如何影响了社群的行动策略。该文还对社群中流传的英雄主义话语(即同性恋社群面对危机,团结一心,无私救助不幸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兄弟)提出了质疑。古尔德首先援引汤姆金斯和塞吉维克的羞耻理论解释了同性恋羞耻产生的原因。汤姆金斯和塞吉维克都认为,羞耻是在沟通的回路被打断,渴望获得认同的个体未得到他人的回应和承认时产生的。在古尔德看来,同性恋群体因为性差异而无法与家人、朋友、同事进行沟通,时刻有遭到拒斥的风险。这种孤立和不被承认的经验引发了同性恋羞耻,以及同性恋群体对于自我和社会的矛盾心理。由于同性恋群体对主流社会既向往又憎恶,同性恋行动主义常常在温和的同化立场和激进的对抗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政治学界通常将情绪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认为情绪会妨碍政治,但古尔德认为,情绪是理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情绪惯习(emotional habitus)塑造了我们对政治行动的态度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同性恋社群早期的艾滋行动主义就是被羞耻这种情绪惯习塑造的,它导致同性恋活动家们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的行动策略,强调同性恋自身的责任而非政府的责任,以游说而非街头抗议为主要行动方式(Gould 221-44)。
不同于塞吉维克、沃纳、克林普等学者对羞耻的政治潜能的肯定性态度,古尔德更关注羞耻对于同性恋社群的负面作用,以及她本人在书写酷儿历史时的忐忑和羞耻。她担心揭露同性恋群体的矛盾心理和同性恋骄傲政治的阴暗面会给同性恋社群带来更多的羞耻,害怕自己的论文会被解读成对艾滋活动家的指责和羞辱(Gould 245)。艾滋病是西方酷儿历史上颇为不光彩的一章,这场传染病的爆发几乎让同性恋骄傲运动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古尔德通过对早期抗艾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酷儿历史书写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如: 酷儿历史学者应该如何撰写社群成员渴望遗忘的羞耻历史?羞耻的历史能否有助于社群建设?历史学者自身的羞耻会怎样影响其历史书写?(Halperin and Traub 13)。
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的海瑟·拉芙(Heather Love)也在会议上提交了她博士论文中的一章。这篇博士论文后于2007年正式出版,书名是“向后感: 丧失与酷儿历史的政治”。该书探讨了早期同性恋文化中黑暗、矛盾的酷儿经验表征,以及社会排斥所导致的一系列负面情感。拉芙指出,酷儿研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强调同性恋身份是贱斥的、污名化的,另一方面又试图抵抗这种被损害的主体性,大力肯定同性恋经验,并用骄傲和可见性(visibility)来化解羞耻和暗柜的遗产。由于酷儿学者往往急于将酷儿表征的“黑暗面”转化为政治能动性的源泉,这使得他们很难处理那些过于负能量的酷儿表征。比如,霍尔(Radclyffe Hall)反映20世纪初女同性恋者悲惨生活的名著《寂寞之井》(TheWellofLoniness, 1928年)就曾被评论家攻击为过时、恐同和令人抑郁(Love 3)。
为了抵抗酷儿研究中的肯定性话语,拉芙分析了《寂寞之井》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同性恋文学文本,并特别关注这些文本中的“怀旧、懊悔、羞耻、绝望、妒恨、被动、逃避主义、自我憎恶、退缩、苦涩、失败主义和孤独”等情感(Love 4)。拉芙认为,当代酷儿群体正处于一个奇特的境地: 在“向前看”(looking forward)的同时继续“向后感”(feeling backward)(27)。向前看意即相信酷儿群体被集体压迫的历史已经过去,酷儿的未来充满希望。向后感则指的是孤独、丧失、自我憎恶等深埋于酷儿历史经验的负面情感仍然挥之不去。拉芙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拒斥这些负面情感,把它们当作个人缺陷,而是应视其为不同历史年代“在物质上和结构上的延续性的标志”(21)。也就是说,这些负面情感能让我们意识到进步话语的空洞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持续存在。
和古尔德一样,拉芙也讨论了情感和政治的关系。受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感觉结构”概念的启发,拉芙认为,情感对于我们认识社会排斥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具有“诊断性用途”(diagnostic usefulness),我们可以将负面情感视为社会创伤的指标(12)。不过,她对情感的政治作用的态度总体来说较为暧昧。塞吉维克、沃纳、克林普等人认为羞耻能够生产出身份、社交性和集体性,可以作为另类政治模式的基础。拉芙却提出,羞耻既能将酷儿聚合在一起,也能让酷儿彼此分离。我们需要对负面情感进行更全面的考察,更深入地思考将情感当作政治基础的困难之处。政治和情感毕竟是不同的领域,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psychic life)也有着不同的范围、地点和时间维度(11—14)。
四、种族与羞耻美学
同性恋羞耻会议虽然有力地推动了酷儿理论和同性恋运动对羞耻议题的探讨,但也引发了身份政治,特别是种族政治方面的激烈争议。在会议召开前,时任罗格斯大学波多黎各和西班牙裔加勒比研究系助理教授的拉·芳登-斯托克斯(Lawrence La Fountain-Stokes)发了一封致克林普的公开信,指责克林普在《马里奥·蒙特兹》一文中虽然提及蒙特兹是波多黎各人,但却完全没有处理种族和族裔的问题,也没有提及任何论述过羞耻的非白人学者。在公开信的末尾,拉·芳登-斯托克斯对克林普和其他所有参会者提出如下问题:“你如何解读马里奥·蒙特兹的羞耻中种族和族裔的交叉?殖民主义凝视是如何融入你的[思考]体系的?除了被轻描淡写提及的刻板的拉美式大男子主义和天主教虔诚,蒙特兹的羞耻中还有哪些东西和波多黎各有关?”(Halperin and Traub 27)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尼格隆-蒙塔内(Frances Negrón-Muntaner)也发了一封邮件给会议组织者,支持拉·芳登-斯托克斯的观点。她认为,讨论蒙特兹的羞耻,不可能不触及国族(ethnonational)羞耻,因为在沃霍尔拍电影的年代,波多黎各移民在纽约市是肮脏、丑陋、野蛮的代名词。克林普在文中反复使用“可怜的马里奥”一词,恰恰说明他是以白人的羞辱性凝视来打量马里奥的。尽管羞耻在文化上具有生产性,但羞耻也会导致自恋,特别是如果我们迷恋上这种情感。尼格隆-蒙塔内反对像克林普那样“向羞耻致敬”,拒绝把蒙特兹当作白人酷儿羞耻审美化的牺牲品,她更赞同尼采的观点“让他人免于羞耻是最富人性的事”(Gonzalez 95-96)。
参加会议的酷儿理论家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不仅严厉批评了同性恋羞耻会议对种族议题的忽视以及有色人种参会者数量的稀少,还声称同性恋羞耻的概念是白人男同性恋者的发明。哈伯斯坦认为,同性恋羞耻巩固了骄傲/羞耻的二元对立,并“倾向于把一个在‘羞耻构型’(shame formation)中浮现的自我普世化”(Halberstam 223),这个自我通常是一个因无法获得身份特权而感到羞耻的白人男性。白人男同性恋者试图把骄傲当作补救措施,重建被羞耻摧毁的自我,但却没有去拆解将羞耻投射到酷儿主体身上的社会进程。我们需要像贝兰特(Lauren Berlant)那样去质疑酷儿政治“从主体内部”开始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于酷儿研究和酷儿行动主义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过度聚焦内在性(interiority),以为仅仅通过自我调整就可以实现社会变革,并因此放弃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关注(224)。
犹他大学英语系杰出教授斯托克顿(Kathryn Bond Stockton)2006年出版的专著《美丽底部,美丽羞耻:“黑人”与“酷儿”的相会之处》可说是对上述种族争议的回应。斯托克顿没有像法农(Frantz Fanon)、胡克斯(bell hooks)等黑人学者那样倡导种族尊严,而是通过一系列小说、电影和摄影文本审视了酷儿羞耻与种族羞耻之间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纠葛,探索了羞耻的美学价值。书名中的“底部”(bottom)一词有三重含义: 身体的底部(臀部)、心灵的底部(心灵深处)、经济地位的底部(贫困的黑人通常位于社会最底层)。斯托克顿将贬值(debasement)视为羞耻的近义词,因为贬值直接关涉羞耻的美学价值,而且贬值的动词形式(debase)有“掺杂”(adulterate)的意思,正好契合斯托克顿对黑白种族混合(miscegenation)现象的讨论(Stockton 7)。
斯托克顿在《导论》中勾勒了一个跨学科的“拥抱羞耻”的批判谱系,援引了多位学者关于羞耻、贬值、侮辱、贱斥的思考,其中包括一些从事酷儿理论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研究的少数族裔学者。斯托克顿认为,在酷儿理论家中,塞吉维克对羞耻这个话题作出了“最脚踏实地、最精细”的阐发(Stockton 15)。就《美丽底部》而言,塞吉维克的论述提供了两点重要启发。首先,塞吉维克在《触摸感情》一书中注意到羞耻“对于新表达方式的多变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称羞耻/操演性的概念比戏仿(parody)的概念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坎普(camp)现象(16)。这实际上已经触及羞耻的美学面向。其次,塞吉维克提到,黑人男同性恋是一个极少被人讨论的话题,黑人和酷儿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结合。这等于是在呼吁学界对这个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斯托克顿称,是时候在“黑人”和“酷儿”的交叉处来探讨“宝贵的、生成性的(generative)和美丽的羞耻”,以便完成《触摸感情》中隐含的研究计划(22)。
斯托克顿主要关注的是羞耻、贬值的运作方式,如何发乎于身,发生在一个社群,如何占据心智(mind)和大脑(brain)(24)。《美丽底部》一书的结构就体现了对羞耻运作地点的追踪。第一章讨论了羞耻在身体表层(衣服、肤色)的运作,如通过《寂寞之井》考察易装的女同性恋者所承受的着装羞耻(sartorial shame)。第二章从身体表层的羞耻转到身体器官所带来的羞耻,重点考察了黑人女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苏拉》所描绘的黑人社区对酷儿情欲的偏见。饶有意味的是,该社区被莫里森象征性地命名为“底部”(Bottom)。第三章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该章围绕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中黑社会老大、黑人马塞勒斯被白人男性侵犯的场景,探讨了肮脏的视觉表征对观众的冲击和吸引。斯托克顿认为,《低俗小说》并未贬低黑人和同性恋者,反而揭示了20世纪中晚期美国主流文化的“隐藏历史”,即美国大众文化/低俗小说中包含大量同性之间的跨种族情欲的想象(108)。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考察了贬值在心智和头脑的运作。第四章关注的是“很少被研究的一种社会性自我贬值——两个男人之间的跨种族交合”(36)。第五章则从羞耻的记忆模式的角度,重读了莫里森的小说《宠儿》。
和塞吉维克一样,斯托克顿主张超越“压迫-颠覆”的理论框架,即不再千篇一律地讨论某些文化现象是否有助于“颠覆”“主导性结构”,而是去尝试提出新的问题。比如:贬值是如何用于美学快感?它为创造性的历史认知提供了哪些便利?底部的状态为何如此迷人?美和羞耻是通过什么逻辑结合在一起的?斯托克顿还重新思考了小说/虚构文本(fiction)和理论的关系。在她看来,不是小说需要理论的阐释,而是理论需要新的小说。我们不仅可以用文学作品来挖掘理论的启发性潜能,同时还可以让理论贬值,揭示理论“惊人的局限”(24—25)。
结 语
当代西方情感理论主要包含两条研究路线: 一条沿着斯宾诺莎、柏格森、德勒兹和马苏米等哲学家的理论遗产展开,另一条则源自塞吉维克对汤姆金斯理论的重读。尽管这两种研究进路都试图用基于身体的情感取代认知的核心地位,用情感理论取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但二者对身体、情感的理解颇为不同,更不用说理论脉络和研究取向上的差异(Seigworth and Gregg5; Timr 197)。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未对这两条路径进行甄别,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塞吉维克开创的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脉络。本文以美国酷儿学者的羞耻研究为线索,对情感理论的酷儿支脉进行了部分的清理,既是为了进一步回答“情感理论是什么”“情感理论有何用”的问题,也是为了展示如何从对抽象情感的关注转向对具体情感形式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学界,塞吉维克的羞耻理论既吸引到众多的追随者,也遭致了不少批评。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教授贝兰特对塞吉维克的羞耻理论一直持保留态度。她曾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质疑道:“相当多的酷儿理论[结合上下文看,此处的‘酷儿理论’主要暗指塞吉维克的理论]存在一种让我震惊和讶异的内在性取向: 酷儿计划(project of queerness)必须从主体的‘内部’开始,从内而外地扩展吗?”(Berlant 74)贝兰特还在访谈中指出,英语学界对羞耻的兴趣并非始于塞吉维克,不少女性主义著作都讨论过如何让性态不再成为再生产性别化羞耻(gendered shame)的场域。在贝兰特看来,羞耻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政治策略都存在相当的局限。塞吉维克和弗兰克将羞耻的体验描绘为依恋和欲望的“中断的回路”(broken circuit)。主体对某个对象产生了依恋之情,但被依恋的对象却拒绝给予回应,主体因此感到羞耻。但这种结构性描述与羞耻的实际体验并不相符。当我们被突然抛入孤立状态时,我们的感受是复杂的,可以包含多种情感反应,不同人的反应也不尽相同(Najafi, Serlin, and Berlant)。此外,贝兰特也不认为羞耻是理解当代社会形构和情感结构的关键所在,因为羞耻并没有涵盖个体经验和社会结构之间的所有关系(Helms, Vishmidt, and Berlant)。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出身的雷斯(Ruth Leys)教授注意到,在《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一文的结尾,塞吉维克和弗兰克写道:“在某个层面,我们甚至都没有要求自己来确定这个假说[指汤姆金斯认为存在八种或九种基本情感的假说]是否正确;我们觉得首先观察今日理论对这种假说的惯例性摈弃的自主神经系统,就能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TouchingFeeling117)也就是说,塞吉维克并不在意汤姆金斯理论的可信度,只是想用他的理论去挑战进入死胡同的后结构主义理论(Leys 147)。但汤姆金斯以及塞吉维克的反意向(antiintentionalist)或反认知(anticognitivist)的情感理论模式(即将情感当作与对象无关的身体反应)在学理和经验上都是有问题的。雷斯不仅引用一些心理学实验结果反驳汤姆金斯及其后继者的理论根基,她还指出,从内疚到羞耻的研究重心的转移,说明当代学界不再关注能动性的问题,而是关注主体的属性(attributes)。这样做的效果就是用“个人情感经验的重要性”或“个人差异的重要性”代替了“个人意向和行动的意义”(150)。
尽管塞吉维克的酷儿羞耻研究“具有高度争议性”(Halperin and Traub 7),但这条研究路径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羞耻的话题也不再局限于英文系、比较文学系、艺术史等酷儿研究重镇,而是扩散到更多的学科。2018年,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期刊《希帕蒂娅》(Hypatia)发行了一个名为“性别与羞耻的政治”的专刊,对羞耻与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进行了跨学科、跨文化语境的研讨(Fischer 371)。2019年,《女性主义与心理学》(Feminism&Psychology)杂志也发行了一个名为“羞耻的女性主义政治”的专刊,旨在重新思考羞耻与女性气质、女性身体、性别政治、社会正义等议题的关联(Shefer and Munt 145-46)。随着英语学界的研究焦点从酷儿羞耻拓展到性别羞耻,对羞耻的探讨或将成为当代情感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领域之一。
注释[Notes]
① 相关理论绍介,可参考陆扬: 《“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上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汪民安: 《何谓“情动”?》,《外国文学》2017年第2期;周彦华: 《当代批评的“情动转向”》,《艺术当代》2017年第2期;张毅: 《从西方身体理论的发展看“特朗普现象”》,《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2期;刘芊玥: 《“情动”理论的谱系》,《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6期;王冠雷: 《分裂与修复:“理论”之后的文学与情感》,《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郑国庆: 《试论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郝强: 《从“感觉结构”到“情感转向”——雷蒙·威廉斯与当代西方情感理论的关系》,《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② 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见英国学者艾哈迈德(Sarah Ahmed)的《情绪的文化政治》(TheCulturalPoliticsofEmotion,2004年)、芒特(Sally R. Munt)的《酷儿依恋: 羞耻的文化政治》(QueerAttachments:TheCulturalPoliticsofShame,2007年)、泼帕(Bogdan Popa)的《羞耻: 19世纪酷儿实践的谱系》(Shame:AGenealogyofQueerPracticesinthe19thCentury, 2017年)、澳大利亚学者普罗宾(Elspeth Probyn)的《脸红: 羞耻的多重面相》(Blush:FacesofShame,2005年)。
③ 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见瑞士日内瓦大学哲学系的迪翁那(Julien A. Deonna)等三位学者合著的《为羞耻辩护: 一种情绪的多重面相》(InDefenseofShame:TheFacesofanEmotion, 2012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祖波尼斯(Lynn Zubernis)和粉丝文化研究者拉森(Katherine Larsen)合著的《十字路口的粉都: 欢庆、羞耻与粉丝/生产者关系》(FandomattheCrossroads:Celebration,Shame,andFan/ProducerRelationships, 2012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医疗人文和哲学学者多乐泽(Luna Dolezal)的《身体与羞耻: 现象学、女性主义与社会形塑的身体》(TheBodyandShame:Phenomenology,Feminism,andtheSociallyShapedBody, 2015年)。
④ 《酷儿操演性: 亨利·詹姆士的〈小说的艺术〉》后经修改更名为“羞耻、戏剧性与酷儿操演性: 亨利·詹姆士的《小说的艺术》”,收入《触摸感情》一书,成为该书的第一章。
⑤ 《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 阅读西尔文·汤姆金斯》一文还作为导论收入塞吉维克与弗兰克合编的《羞耻及其姐妹: 西尔文·汤姆金斯读本》(ShameandItsSisters:ASilvanTomkinsReader)一书,后成为《触摸感情》的第三章。笔者已将该文的主要内容翻译成中文,发表于《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⑥ 这个智识困境类似一个禅宗公案: 你说这个棍子是真的,我用它打你,你说这个棍子是假的,我用它打你,你什么都不说,我用它打你。摆脱困境、不被挨打的方式只有直接把棍子扔了。压抑理论就是这个“棍子”,克莱因和汤姆金斯都把这个棍子扔了,另起炉灶,创建新的理论。
⑦ 英语学界在讨论塞吉维克的情感理论时,通常引用的是这三个文本。国内研究者则主要参考的是塞吉维克20世纪90年代后期访台时的演讲《情感与酷儿操演》的中译本。这篇演讲稿的内容大体可以在《触摸感情》的导论、第一章和第四章中找到。
⑧ 此处的引文翻译参考了金宜蓁、涂懿美的译本(102),根据原文略有改动。
⑨ 此处的引文翻译参考了金宜蓁、涂懿美的译本(107—108),根据原文略有改动。
⑩ 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关注过羞耻。他和布洛伊尔在1895年合作出版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一书中称,歇斯底里症是由包括羞耻在内的一些隐秘情感引发的,羞耻是一种导致压抑的抑制性(inhibiting)情绪。也就是说,羞耻不仅诱发了歇斯底里症,还可能是所有精神疾病的诱因。1905年,随着《梦的解析》一书的出版,弗洛伊德转向对驱力的研究,并开始对羞耻产生偏见。在他看来,焦虑和内疚才是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尤其是成年男子应有的情感,只有儿童、女人和野蛮人身上才会出现羞耻这种退化(regressive)情绪(Scheff 85-86)。关于羞耻和内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美国社会学家林德(Helen Lynd)在《论羞耻与身份的追寻》(OnShameandtheSearchforIdentity, 1958年)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区分: 内疚关乎行为,羞耻关乎自体(self);内疚让人感觉自我(ego)是强大而完整的,羞耻则让人感到软弱和自体的瓦解;内疚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情绪,肯定了孤立的个人的重要性,羞耻则是一种社会化的情绪,重申了人与人之间在情绪上的相互依赖性(Scheff 92)。此处为了区分“self”和“ego”这两个术语,将前者译作“自体”。正文中提到的“自我”主要指“self”。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rber, Stephen M., and David L. Clark. “Queer Moments: The Performative Temporalities of Eve Kosofsky Sedgwick.”RegardingSedgwick:EssaysonQueerCultureandCriticalTheory. Eds. Stephen M. Barber and David L. Clar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1-53.
Berlant, Lauren. “Two Girls, Fat and Thin.”RegardingSedgwick:EssaysonQueerCultureandCriticalTheory. Eds. Stephen M. Barber and David L. Clar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71-108.
Crimp, Douglas. “Mario Montez, For Shame.”RegardingSedgwick:EssaysonQueerCultureandCriticalTheory. Eds. Stephen M. Barber and David L. Clar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57-70.
都岚岚:“酷儿理论等于同性恋研究吗?”,《文艺理论研究》6(2015): 185—91。
[Du, Lanlan. “Is Queer Theory Equal to Gay and Lesbian Studies?”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6(2015): 185-91.]
Edwards, Jason.EveKosofskySedgwick.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冯瑶:“塞吉维克的酷儿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Feng, Yao. “A Study of Sedgwick’s Queer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MA thesi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4.]
Fischer, Clara.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Shame: A Twenty-First-Century Feminist Shame Theory.”Hypatia33.3(2018): 371-83.
Gonzalez, Rita. “BoricuaGazing: An Interview with Frances Negrón-Muntaner.”GayShame. Eds. David M. Halperin and Valerie Traub.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88-100.
Gould, Deborah B. “The Shame of Gay Pride in Early Aids Activism.”GayShame. Eds. David M. Halperin and Valerie Traub.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221-55.
Halberstam, Judith. “Shame and White Gay Masculinity.”SocialText23.3-4(2005): 219-33.
Halley, Janet, and Andrew Parker. “Introduction.”SouthAtlanticQuarterly106.3(2007): 421-32.
Halperin, David M., and Valerie Traub. “Beyond Gay Pride.”GayShame. Eds. David M. Halperin and Valerie Traub.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3-40.
Helms, Gesa, Marina Vishmidt, and Lauren Berlant. “Affect & the Politics of Austerity: An Interview Exchange with Lauren Berlant.”Variant39/40 (Winter 2010).17 August 2019 〈http://www.variant.org.uk/39_40texts/berlant39_40.htm〉
Koivunen, Anu. “Yes We Can? The Promises of Affect for Queer Scholarship.”LambdaNordica15.3-4(2010): 40-64.
Leys, Ruth.FromGuilttoShame:AuschwitzandAf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刘芊玥:“‘情动’理论的谱系”,《文艺理论研究》6(2018): 203—211。
[Liu, Qianyue. “The Genealogy of Affect Theory.”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6(2018): 203-11.]
Love, Heather.FeelingBackward:LossandthePoliticsofQueer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Najafi, Sina, David Serlin, and Lauren Berlant. “The Broken Circuit: An Interview with Lauren Berlant.”Cabinet31 (Fall 2008). 17 August 2019 〈http://www.cabinetmagazine.org/issues/31/najafi_serlin.php〉
Probyn, Elspeth.Blush:FacesofSham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Scheff, Thomas J. “Shame and the Social Bond: A Sociological Theory.”SociologicalTheory18.1(2000): 84-99.
Sedgwick, Eve Kosofsky. “Queer Performativity: Henry James’sTheArtoftheNovel.”GLQ:AJournalofLesbian&GayStudies1.1(1993): 1-16.
- - -.TheWeatherinProust. Ed. Jonathan Goldber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 -.TouchingFeeling:Affect,Pedagogy,Performativ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维克:“情动与酷儿操演”,金宜蓁、涂懿美译,何春蕤校订,《性/别研究》3—4(1998): 90—108。
[Sedgwick, Eve Kosofsky. “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 Trans. Jin Yizhen and Tu Yimei.WorkingPapersinGender/SexualityStudies3-4(1998): 90-108.]
Seigworth, Gregory J., and Melissa Gregg. “An Inventory of Shimmers.”TheAffectTheoryReader. Eds.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1-25.
Shefer, Tamara, and Sally R. Munt. “A Feminist Politics of Shame: Shame and Its Contested Possibilities.”Feminism&Psychology29.2(2019): 145-56.
Siebers, Tobin. “Sex, Shame, and Disability Identity: With Reference to Mark O’Brien.”GayShame. Eds. David M. Halperin and Valerie Traub.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201-16.
Stockton, Kathryn Bond.BeautifulBottom,BeautifulShame:Where“Black”Meets“Que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陶东风:“解读阿伦特‘公共性’的基本含义”。2013年11月27日。2019年8月17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2egun.html〉。
[Tao, Dongfeng. “The Basic Meaning of Arendt’s ‘Publicity’.” 27 November 2013.17 August 201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2egun.html〉]
Vincent, J. Keith. “Shame Now: Ruth Leys Diagnoses the New Queer Shame Culture.”Criticism54.4(2012): 623-32.
Warner, Michael.TheTroublewithNormal:Sex,Politics,andtheEthicsofQueer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Wetherell, Margaret.AffectandEmotion:ANewSocialScienceUnderstanding. London: Sage, 2012.
张楚:“塞吉维克酷儿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
[Zhang, Chu. “A Study of Sedgwick’s Queer Theory.” MA thesis. Nanjing University, 2017.]
郑国庆:“试论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9): 6—11。
[Zheng, Guoq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edgwick’s Affect Theory.”JournalofGuang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4(2019): 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