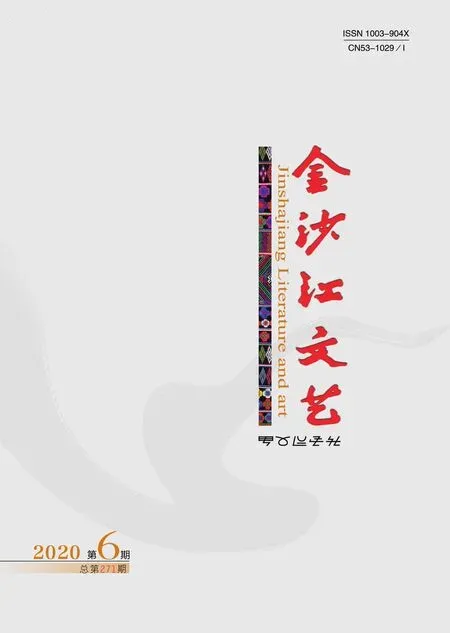断翅的天使
2020-11-18
林小荞
那年,我十二岁。我被白水乡中学录取了,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学生。与我一起考进白水乡中学的,是村子里与我最要好的朋友田小米。
十二岁前,我和田小米几乎是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去村小学上课,一起到田野里给兔子找草。一起到村子后山的果园里偷梨、偷枣、偷桃子。
每次和田小米分享战利品的时候,看着她一脸甜蜜地品尝偷来的梨、枣、桃子,或者是地里栽种的红薯、胡萝卜,我的内心是悲凉的。
田小米有一双猫咪般的大眼睛,笑起来甜美可爱。而让我感到悲哀的,却是她好听的名字。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米是甜蜜的,让人幸福的想象。而我的父母,却给我起了一个令我抬不起头来的名字。林小荞。荞是苦涩的,难以下咽的。而村子里的人,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叫我苦荞粑粑。苦荞粑粑是每家人的口粮,不吃这难以下咽的荞粑粑,饿死的可能性很大。
我羡慕田小米的名字。就连村子里的人,看她的目光和看我的目光都不一样。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觉得米是甜的,荞是苦的吧?
我讨厌我的名字。
每当我被小朋友欺负后躲在角落里哭泣时,田小米都会挺身而出,赶走那些围着我大声嘲弄我的捣蛋鬼。然而,田小米的命运,在我们十二岁那年,发生了天崩地裂。
那一年秋收过后,田小米的母亲和村子里的一大波人,被二流带到城里打工去了。二流的真名叫胡四友,是村子里唯一进过城的人。从城里回来的胡四友穿花里胡哨的衣服,戴两个黑圈圈眼镜,嘴角的胡须看着让人生厌,时不时吹一两声口哨,一副典型的二流子形象。村里人都叫他二流,他也不生气,呵呵地见人就笑,见男人就发烟,见小孩子就散糖。这些小恩小惠并不能吸引人,吸引人眼球的,是他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一台大彩电,一套把整个村子震得发颤的音响。
我和田小米从学校回来,牵着手悄悄地混进人群,挤在二流家狭小的院子角落里,听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
第二天,田小米哭哭啼啼地来找我,说她妈妈要跟村里的人一起进城打工,把她和跛脚的爹留在家里。
我当时并不明白田小米对母亲进城打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绪。看着她伤心的样子,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
返回白水乡中学的路上,田小米不再像以前一样叽叽喳喳的。这一周,课堂上没有了田小米的活跃,她猫咪般的大眼睛也不再顾盼生辉,这让我很不习惯。一直以来,田小米都是主角,我就是她身边的配角,她像大小姐,我就是她身边的小丫鬟。
周末我们一起回家,整个村子都是沸腾的。二流家的音响依然震得村子发颤,村子里的人纷纷拥向二流的家门口,每个人走路都急得像赶一场亲人的喜事,或是丧事。吃饭的时候母亲告诉我说,那些在二流家窜出窜进的人,都是想跟二流进城打工的。
我怯怯地问母亲,你也去吗?母亲把鸡蛋夹到我碗里说,我不去,我丢不下你和这个家。
我的内心被甜蜜充斥着,有一种稳妥的幸福感。我欣喜地把鸡蛋夹到母亲的碗里,第一次在母亲面前撒娇。母亲又一次把鸡蛋夹回我的碗中说,你正在长身体,该给你吃。母亲的话不多,不够温存。但我却忽然发现,原来她是多么的温柔,多么爱我。
第二天,村子里的人都拥着二流准备随他进城,生怕二流会抛下他们似的。田小米的妈妈也在其中,她穿了一身新衣服,衣服好看合身,让她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田小米远远地站在村尾,不像其他小孩一样哭喊着不让父母离开。她神情漠然,望着嘈杂的人群,却又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般。她的妈妈向她招手,唤她的名字,她仿佛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脚始终没有移动一步。她没有哭,也没有掉一滴泪。
那天下午返校,我的母亲一直将我们送到学校门口。路上母亲一直牵着我,我也乖巧地从未挣脱过母亲的手。田小米依旧寡言,母亲时不时找话逗她,她也不大理睬。而我,被母亲的气息笼罩着,她温柔的手让我感到安全。母亲身上的气息有尘土的味道,有阳光的味道,有爱的味道,还有苦荞的味道,令人踏实。
我和田小米,在不经意间就生出了嫌隙。
临近春节,进城打工的人都陆续回村了。那段时间村里的孩子们都在村口等父母回家。田小米一次都没去过,直到除夕那天,她的母亲也没有出现在村口。
村庄因过年变得喜气洋洋,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了新对联,挂起了红灯笼。唯独田小米家,看不出过年的样子。我和父亲正准备放完鞭炮进门吃年夜饭,远远地看见田小米跛脚的父亲朝我们跑来。
他气喘吁吁地问我,你看见小米了吗?
我摇头说没有,这个假期她都没来找过我,我去敲了你家几次门都没有见着她。
我不顾父亲的阻止朝村头跑去,黑暗里,一个瘦弱的身影立在风中。隐约间能听到她痛哭之后的喘息声。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生怕她会甩开我的手跑掉。这一次,她却温顺地靠在我的肩上,喃喃地说,她不会回来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走的那天我就知道她不会回来了。
十二岁的我,突然觉得十二岁的田小米是多么的聪明啊。她怎么会知道她的妈妈不会回来了呢,难道是她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她的。那她为什么不阻止她,不让她到城里去。又或者,她可以跟着去城里,只要能和妈妈在一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可是田小米明明已经知道妈妈不会回来了,却没有阻拦她,也没有缠着不让她走。甚至走的那天,连哭都没有哭。
春节过完,回乡过年的人又陆续进城去了。田小米的父亲凡是见到进城打工的人,都挨个儿说,见到小米妈妈,捎个信让她回来看娃,我和娃想她呢。此时的田小米,正厌弃地看着父亲猥琐的模样。
我天真地以为,我和田小米又回到了从前,又可以成天形影不离的一起去上学,一起去村子后山的果园。
这个学期,田小米频繁地被老师留在学校补课。令人不解的是,老师越给她补课,她的成绩越下降。我们曾是势均力敌的黄金搭档,而如今,她却徘徊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上课的时候,我常偷偷地转身看她有没有好好听课,而她看上去是多么的认真,专注。腰杆挺直,目视黑板,不与同桌讲小话。可是,她的成绩为什么会下降得如此离谱呢。我找不到可以质问她的理由,我们之间,已经被一种莫名的隔阂分开了。
我多么怀念和田小米讨论老师一直挂在嘴边的“温良恭俭让”。我说温是温和,田小米说是顺从。我说恭是恭敬,她说是服从。我说让是谦让,她说是放弃。真不知道她脑袋里装着些什么,总是答非所问的。
田小米的话越来越少,课间也是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她猫咪般的大眼睛里,有一潭深深的泉水,仿佛随时都会溢出眼睑来。
快要中考的时候,我越来越担心田小米,因为她有可能连县上最普通的高中都考不起。而她也越来越恍惚,失神,甚至默默地流泪。
而在此时,田小米的妈妈回来了。一个时尚潮流的都市女性打扮,全村人都几乎认不出她来。她没有给田小米母亲式的拥抱,却带回了很多好看的衣裙,带回来了印了水晶娃娃的粉红色书包,还带回来了我和田小米梦寐以求的扎头丝带。
田小米妈妈带回来的这些东西,是能满足每一个女孩的少女心的。可是,田小米一样都没有要。就算是那条穿起来像公主一样的裙子,田小米连试都没有试。这让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告诉我,田小米的妈妈真没良心,她是回来离婚的。
母亲又补了一句说,她怎么会舍得小米呢。我并不知道离婚意味着什么,但我懂“没良心”和“舍得”这两个词的含义。
那天,田小米家里有很多人,我和妈妈也在场。劝离劝和的人都有,闹哄哄的。田小米佝偻着背的父亲在乞求小米的妈妈不要和他离婚,不要丢下他和小米。他几乎要跪在地上了,一脸的猥琐样。
田小米嫌恶地吼道,让她走。
田小米稚嫩的声音带着力量,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震住了。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汗水渗透了手心。我在心里想,你怎么这么傻,你让她走了,你就永远没有妈妈了。如今,我终于明白。是绝望,是绝望让田小米变得歇斯底里。那是对亲生母亲的绝望,对命运的绝望。
而我,只是单纯地认为,田小米的恍惚,失神,默默地流泪,都源自母亲与父亲的离婚。
像被预言击中似的,田小米连最普通的高中都没有考上。
十五岁的田小米与十五岁的我,怎么看都觉得我们不是同龄人。我扁平而方正的五官上星星点点地洒满了雀斑,挺了半天都挺不出个胸来。田小米鹅蛋脸,大眼睛长睫毛,眼睛大得有一种惊吓之情,睫毛长得有一种沉重之意,皮肤白得像童话故事,也像童话故事隐约透着血色。她的胸部已经微微隆起,将单薄的校服撑出两个小山丘。她的双眼总是沾着薄雾,扑朔迷离般令人垂涎。
我进了县重点高中,田小米去了职高。
开学前一天,我们破天荒地去了后山的果园。田小米的神情依然是恍惚的,就算满山的苍翠与成熟的果园,都提不起她的兴趣。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田小米。她坐在田埂上,漠然地看着我跳上跳下地摘梨,摘苹果。我唤她也不应,当我把摘下的梨拿给她吃时,却见她苍白的脸上全是泪水。我不知所措地认为,她一定是想她的妈妈了。我坐在她身旁搂住她的肩,她没有推开我。她像低血糖发作那样,浑身无力,额头和手心都在出汗。她趴在我的肩上,痛哭不已。
母亲离开的时候,田小米没有掉过一滴泪。而此时,她却哭得如此伤心。年少的我,又怎会知道这份伤心的由来呢。
刚刚开完会,就看见有五个未接的陌生电话。正在犹豫着回与不回,电话又打了进来。
电话那端问:请问是林小荞?
我答不是。挂了电话。
上大学前,我已经改名叫林沫了。已经将那个带着苦涩和羞涩的林小荞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划去了。
但立即我就想到了她,我儿时的姐妹,田小米。那次见面时她说,她还是想叫我林小荞,她说那是她记忆中最美好的东西,她不想遗忘掉。我没有反对,将这唯一的称谓留给了她。
我把电话反拨了过去。对方说是龙城派出所,有一个叫田小米的女性,联系不上家人……
我来不及回家,也来不及向单位请假,匆匆打了出租车,直奔龙城派出所。心跟着蜿蜒的路,耳边是呼呼的风,脑海里是那个在后山果园里哭得歇斯底里的田小米,是那个像得了低血糖,近乎昏厥的田小米。十二岁前,我们在乡村空旷的小山头上踮着脚尖摘星星。田小米怎么了?她为什么会在派出所?几经辗转,在太阳快要落尽的时候,我来到了民警值班室。值班民警告诉我,他们在一座烂尾楼里发现了田小米。
“发现”,多么不祥的词。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怎么了?我失控地尖叫起来。
民警告诉我说,他们发现田小米的时候,她已经昏厥了,身边有一个脏兮兮的包,包里只有她的证件和一个电话。说来奇怪,她电话的通讯录,都是用数字排列的,共有27个电话号码,却只有一个电话有名字,我们就联系了有名字的那个号码。
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龙城见到了田小米。那是一次文学创作的读书会,我在龙城的一个咖啡厅与书友们会面。在读书活动讨论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我感觉有一束冷冽的光一直在扫射着我,我的后背微微发凉。我转身寻找的时候,又觉得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都那么的自然而然,平和得近乎亲切。
“荞粑粑”。一个声音灌入耳底,将这个带着苦味的名字呼之而出。这个声音极小极小,却盖过了激烈的讨论声,震得我耳膜生疼。我寻声而去,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我见到了她。
她不是书友,没有坐到我们的圈子里。她冲着我微微一笑,将手扬了扬。她的笑容里有一种迷路的表情,我猫着身子走出人群朝她走去。她的笑容收了起来,但是迷路的神色搁浅在眉眼上。
我以为她会过来和我拥抱,或者亲昵地与我纠缠在一起。十多年来蕴藏着的情感,会在我们都长大成人的时候变得更加热烈。而她只是微微地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坐在她对面。
自从那天我们在后山的果园里分手后,我再也没有和她这样近距离地对视过。但她那双猫咪般的大眼睛,只是看着你就仿佛要承诺你一座乐园似的。我的内心荡漾着欢快,失而复得的友情让我的感情像烧开的滚水,不经意地在脸上蒸散开来。
田小米说,我知道你今天会来这里,我是来等你的。我看过你在报刊“寻亲”专栏上写的文章,就算你已经改了名字,我还是从字里行间看到了我们的曾经。
田小米没有面对着我,她将脸转向窗外,但我感觉得到她即使好像在注视着窗外,她视野的边缘也会扫到我的脸上。也许她只是对着桌子上渐凉的咖啡说话,或者是精巧的小花瓶里绽放着的玫瑰,又或者是橱窗墙壁上写意的山水画。她的语调冷淡,就像在谈论当天的天气或菜肴的味道。但我却能感觉到,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刚刚磨快的刀刃。
你过得好吗?这是我们分开十多年后,我第一次对她表现出的关怀,内心充满了亏欠。
田小米避开了这个话题。
高考结束后,田小米就离开了村子。她是一个人悄悄走的,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这十多年来,我也会梦见十二岁前的我和田小米,出现最多的,依然是那个在果园里哭得歇斯底里的,像得了低血糖一样虚脱的田小米。十多年的记忆,如同一滴藏在水底的油,此时浮上来,在水面氤氲,扩散,呈现出奇异的色彩。
在偌大的病房里,田小米被铐在一张病床上。她的长发缠结成一条一条的,脏而乱地盖住了她的脸。裸露在外的肌肤上,到处是晒伤和抓伤的痕迹。
为什么要把她铐起来?我惊恐而愤怒地吼道。
我冲过去,撩起她遮盖着脸的头发,她的脖子似折断地歪倒着,鼻涕和口水一起滴下来。她先是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一分多钟后,她的脸上突然绽开一个空洞的笑容,且收不回去。
那不是她的笑容,它没有内容,没有温度。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她死灰般的脸,所有光芒都熄灭了的那双沾着薄雾迷人的眼睛。
田小米疯了。
医生的诊断令我四肢麻木,双耳失聪,眼所能及的视线瞬间变成黑暗。
三年前,田小米似乎就在向我透露着某种不祥的信息。却只字不提这十多年来关于她生活的任何痕迹。我们只是短暂的相聚了近一个小时,她却问了我三次,如果我出事了,你会来看我吗?如果我需要有人救赎,可以是你吗?可是她每次问完,都会露出玩世不恭的笑,像在讲一个天大的笑话,令人分不清真假。
我把电话号码给了她,告诉她随时都可以打给我,但千万不要有事了才打。我又补充一句说,我们是姐妹,永远的。我将手伸给她,与她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得生疼。她的手柔而软,汗津津的,一用劲,就生怕将她折断。我跟她要号码,她却说她会打给我的。可是三年来我从来没有接到过她的电话,偶尔有未接的陌生号码,都生怕是她,一律反打回去,却从来没有一个是她。
田小米的出租房里,墙上的挂历是两年前的。一个连日历都不想再翻的人,她的日子是多么的晦暗无光啊。我的心痛了起来,在这个蝉叫得像电钻螺丝钉的夏天,我的后背全是冷汗。
床边柜子的抽屉里,一红一黑躺着两本笔记本。红色的那本看上去年代久远,封面是陈旧过时的塑料封套,左下角是花草图案,右上方有一只蝴蝶在翩翩起舞。黑色那本是纯黑,有肃穆的庄重之感。旁边的一个文件袋里,装着全是林沫写的文章。大大小小的纸片,有的是报纸上剪下来的,有的是杂志是剪下来的,有的是一整本的……在这个狭小的出租屋里,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中,汗水和泪水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
翻开第一页,田小米娟秀的字体被时光打磨得陈旧。但这个字体,曾是我缠着她求她让我模仿着写的字体。翻阅着她的日记,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喘气,镜片后面的那层薄膜早已溃败。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聚拢在了一起,吵得我难已喘息。我感觉很饿,仿佛有好久好久,甚至更久的时间没有吃过任何东西。那是一种可以把生米,生肉,甚至霉变的食物都吞下去的饿。
田小米
林小荞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她的名字。可是她却常常为她的名字苦恼。原因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每家的饭桌上,主要食物都是苦荞面做的。食物是苦涩的,生活也是苦涩的。
所幸的是,我和林小荞却像一对灵魂的双胞胎,她不喜欢的,恰好我喜欢,她害怕的,却是我不怕的。所以,当那些讨厌的家伙将林小荞堵在墙角欺负她时,我便勇敢地挡在她的前面,将他们赶跑。
林小荞最喜欢后山的果园,我们每次密谋着躲开家长出去玩时,林小荞都会说要去果园。我真不知道那个果园里有什么吸引她的东西,可是她却充满了好奇。她会给果园里的第一朵苹果花系上小红线,也会给刚发芽的红薯苗做上记号,然后等待着它们的成长。
在大人们的眼里,我们这对灵魂的双胞胎,都是我在保护林小荞。他们一致认为我鬼主意多,我主导着林小荞的一切。可事实上,我却是林小荞的跟班,我喜欢她对一切事物产生的好奇,喜欢她看一切都是那么的单纯美好。哪怕是在她生气时踩死青虫、蚂蚁、折断刚发芽的新枝,在我眼里都觉得是多么的美好。
我讨厌二流,也讨厌妈妈。是二流带走了妈妈,是妈妈抛弃了我。
那天晚上,我看见二流和妈妈从房子背后去了,我跟着去。我听见了他们的说话,也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一切。曾经多么爱我的妈妈,在她起身的那一刻,却恶狠狠地将我推倒在草堆上说,滚一边去。
第二天她就走了,她穿着二流给她买的新衣服,非常的好看,可是我却感到恶心。
林小荞的妈妈送我们去上学,她一直牵着小荞的手,也来牵我的手,我不让。我都没有妈妈了,以后要一个人坚强起来,我这样想。
快要过年了。她离开我已半年多了,我都读完了一个学期的初一。村庄忽然在某一天就热闹了起来,有人背着大包有人背着小包陆续地回到了村子里。好多小朋友天一亮就到村口去等爸爸妈妈。我不敢去,不敢抱着希望去,又抱着失望回来。我甚至已隐约感觉到,她不会回来了,她那天晚上将我推倒在草堆上,力气很大,也很决绝。
她果然没有回来,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了,她还是没有回来。我站在冷冽的寒风中,眼泪都忘记流了。这时林小荞来了,她是哭着跑着来的,她一把抱住了我,比我哭得更伤心。我在心里想,你这个傻丫头,你爸爸妈妈都在家,你家都放过鞭炮要吃年夜饭了,你哭什么。可是,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抱着她哭了。
最近,我感觉老师总是笑眯眯的,对我们无比地温和。课堂上他念课文的时候,都喜欢站到我的身边,他衣服的脚边会触碰到我正在写字的手背上。自从她走后,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般的欢欣。
我似乎越来越爱上语文课了。我和林小荞都说过,老师真好。我还和林小荞讨论老师一直挂在嘴边的“温良恭俭让”是什么意思。我们都顽皮地伸伸舌头表示不懂,也不敢去问老师。
今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让我把同学们的作业抱到他的宿舍去。我非常地快乐。在走向老师宿舍的路上我想,我要鼓足勇气问老师“温良恭俭让”是什么意思?然后去向林小荞炫耀答案。我来到老师宿舍,看见老师的书桌上放着棉花糖和粉红色的小手帕。
我放下作业本,握起拳头给自己鼓劲,正要开口问老师,老师却不由分说地将桌上的棉花糖和粉红色的小手帕塞到我手里。然后,他像拎小鸡似的将我拎起,他的手力气真大,一只手就可以把我提起,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另一只手扯下了我的衣服。我想哭,可是喉咙被拧紧的衣服堵得发不出声音。我像一个被牵线的木偶,整个身体被一双大手拧扭着,老师将他的嘴巴凑近我的身体,刚刚长出的胡茬磨破了我胸口的肌肤,同时也不由分说地把他自己塞给了我。
那一天,是我和林小荞去白水乡中学的第二个学期,春节刚刚过后的那个春天。我和林小荞,都还不满十三岁。
自从那天过后,我又被老师叫去了好多次。老师不叫我去的时候,会叫王丽丽,也会叫刘艳梅,还会叫比我更小的张娟。老师都是以抱作业、改作文为借口。没有被叫到的同学,多么地羡慕常常被老师叫去的我们。我知道王丽丽、刘艳梅、张娟和其他被叫去的女同学都像我一样,被老师脱光过衣服。我仔细观察过她们,只有刘艳梅被叫去后第二天没有来上课,后来就一直都没有来上学。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老师会叫到林小荞。庆幸的是老师一直都没有叫她,她是极少没有被叫到的女同学。我宁愿老师叫的是我,也不要叫她。我不敢和林小荞走得太近,我怕老师看见我们在一起时,会忽然改变主意叫林小荞去抱作业或改作文。但很快我就有了主意,万一哪天老师想起了林小荞,我会义无反顾地替她去。
最近上课老是分神,害怕上最后一节课,更害怕听见老师笑眯眯地说,田小米,放学后把同学们的作业抱到我宿舍。那是一种要死的感觉,可是却有同学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他们觉得老师对我真好。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我们几个被老师叫去的女同学,在一起抱头痛哭。
我们哭什么?是对命运无力反抗,还是什么……我们都不懂。
林小荞在课堂偷偷地看我,我知道她是想看看我有没有好好听课,因为我最近的功课下降得离谱。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曾拉钩说要好好读书,要到县城去读高中,到大城市去读大学,也要在大城市工作。多么美好的愿望啊。
可是现在,一切都离我远去了。
林小荞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我真为她高兴。三年的初中,老师一次都没有叫过她去抱作业。而林小荞,也不知道去抱作业意味着什么。她还是那么的单纯美好。
我决定要离开了。这几年我和林小荞走远了,因为我害怕与她走得太近,她会洞悉出一切。我也害怕因与她走得太近,会被老师忽然想起她的存在。
三年的职高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停留在十二岁那年的记忆,却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我。
我要走了,总得跟她告别一下吧。
我主动提出要去果园,林小荞欢天喜地地来了。她还是那么快乐,像天空飞翔的小鸟。而我,却被一把无形的枷锁捆绑得难以喘息。林小荞翘起兰花指,将一个熟透的小梨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分明看见了那是老师的喉结,在我面前晃动着梦魇般挥之不去的喉结。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她面前,在她的肩上,肆无忌惮地哭了。也许只有哭,只有哭才能救赎我。可是天真的林小荞,她哪里知道,我哭的是什么。
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温良恭俭让”。而这几个字,却在我十二岁那年,就已根植于我的体内,在我的血管里恣意地游走。我将这几个字拆分,合并,合并,拆分。我感觉我要死了,只有死了,才会从这几个字中解救出来。我哭了笑,笑了哭,直到浑身像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才平息下来。
那时,是我离开村庄,离开林小荞两年之后。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连生存下去都难的城市里,却还要夜夜在噩梦中惊醒。第一次抱作业本去老师的宿舍,轻轻握起的小拳头,直到从老师那里出来,又或者,是老师从我那里出来,我第一次失去片段记忆。
“温良恭俭让”。多么讽刺的存在啊。
后来,在很多夜场和欢场,在与人周旋中,我也已经习惯了将“温良恭俭让”挂在嘴边。它深深地烙入我的骨髓,整个中学时代,被老师叫去的无数次,都是这几个字陪伴着我。老师在折断我翅膀的时候,也不忘记要先背诵一遍。也不只是老师,戳破我童年的,还有这几个字。
林小荞应该大学毕业了,她应该在大城市里工作了吧。这是我们儿时的梦想。可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却只有她一人。前几天看了一个叫林沫的人写的文章,我忽然非常非常想念林小荞,想去看她,或者想要她来看我。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刻意不敢去想,也不敢让她知道我在哪儿。在“寻亲” 专栏上读这篇寻找失散已久的儿时伙伴的文章时,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就湿了眼眶。我感觉到了亲切,温暖的存在。原来,一直支撑着我支离破碎的灵魂的,竟然是林小荞。
我感觉整个人都有感情。仅一秒钟,这份感情就被我打碎了。林沫是她吗?她寻找的那个人,是我吗?
我开始关注林沫的所有文章,开始收集林沫写的文章。每一篇都被我读无数遍,每一次都将泪水洒在纸张上。一个人生命中会有很多重要的人,但对我而言,却只有林小荞一个。或许这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吧。像我这样的人,只敢在肮脏的灵魂触及不到的地方,将这个重要的人悄悄地藏起来。如果她知道了我的一切,她会瞧不起我吗?又如果,她早已经将我忘记了……不敢再往下想。如果连她都忘记了我,我的生存就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像我这样一个浑身沾满污垢的人,怎么配去要求天使般的林小荞记得我呢。
白天在噩梦中挣扎,夜晚像游魂般行走。
他死了。那个无用而猥琐的男人。他早该离开人世了,我在心里咒骂着他。
可是今天,我却忽然觉得心被掏空了似的。这么多年来,我刻意要忘记他,一次也不去想他,可是我左右不了我的梦,在梦中还是会看到他下跪的样子。再后来,梦中也没有他的影子了,我已经彻底地清除了他。
十二岁那年,我把与老师的事告诉了他。我多么希望他会出面去找老师理论,或者把我转到别的学校去,又或者,他可以让我待在家里。我宁愿每天跟他到地里去干活,去山上放牛放羊。可是他却无动于衷地在家里喝了一整天的闷酒。他酒气熏天地叫我不要声张,他泪流满脸地叫我不要给他丢脸。他是能拯救我唯一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却毁灭在自己亲生父亲的手里。从那天起,我没有再叫过他一声。
我的心流着血,我用血写下四个字:你有脸吗?
是他们毁了我。是那两个给了我生命,却对我不管不顾的人毁了我。是他们的无情和无能,让我在本该成长的年龄,过早地折断了羽翼。
……
得知林沫要来龙城参加书友会,我激动了好几天。那天在海报上看见她的照片,我当时就哭了。她真的是林小荞,她的眼神是那么的专注,充满了自信。
我去买了新的衣裙,将自己清洗了五遍,或者是八遍,甚至是十遍。也许只有这样,我才有勇气面对她。
林小荞真的来了,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她。光只是看着她,就觉得内心丰盈而甜美。
我用极小极小的声音叫了一声“荞粑粑”。她最讨厌的称呼。我也曾为这个称呼和村里的小伙伴打过无数次架。
她朝我走来,轻盈的步履,甜美的笑脸,自信而阳光。我多想去拥抱她,多想死死地纠缠着她。可是我不敢。
我们十多年没有联系过了,我不确定她是不是还待我如初。她生活在美好里,有阳光,有爱,有很多重要的人。而我却只是她的反面。
当她的手与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不争气地出了一身冷汗。那年在果园里,我哭到要死的时候,也是浑身是泪,浑身是汗。她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说我们是姐妹,永远的。那一刻,我多么想把离开这十多年的经历告诉她,多么想把我们十二岁那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告诉她。可是我不敢。
我怕她看出我的心思,于是在她面前肆无忌惮的笑。我问她:如果我需要有人救赎,可以是你吗?
林小荞没有回答我,但是她握紧了我的手,那一份力度,是承诺,也是期许。
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电话号码,我是一个辗转流离的人,这十多年来我换了不下十个号码。每一段厌倦了的日子,我都像丢掉电话卡一样,丢掉。
我以为我至死都不会需要用到救赎这两个字。我活着的意义,只是因为天亮了,我还活着。我还要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我遇到了他。或者说是他一直纠缠于我。又或者说也不是纠缠,只是有一份喜欢吧。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可是今天,我要把它记下来。我怕明天我就会忘记掉。
在这个黑色的笔记本里,记载着我黑色晦暗的过往。而今天,我却记下了属于我的美好的一页。
“他摘下树枝上一朵娇嫩的花蕾插入我的发间,这是一朵很小很小的花,小得弱不禁风。我只需要轻轻地扬头或用手轻轻一撸头发,这朵小花就会被我的头发遮掩掉。但是他说,正是因为它简单,毫不矫饰,才会令人怦然心动。”
真的是这样吗?我多想站在楼顶,对着空旷的天空,寻找答案。
他说,他爱我。我似乎忘记了世间还有“爱”这个字的存在。我和林小荞曾经争执过,她说爱是动词,我说爱是名词。她说爱是一种能力,我说爱只是一个名称。
就像我们一起讨论过的“温良恭俭让”,林小荞说的是对的,我说的是错的。而现在,我也确信爱是动词,爱是一种能力。
“我被卷入浑浊的旋涡,在谎言的丛林里找不到出路。我还要继续说谎吗?谎言像玻璃一样脆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碎成一地。在这个欺骗、背叛、精神匮乏的世界里,一切不可示人的,都只属于我一个人。我还配拥有爱情吗?”
配吗?配吗……
在日记本上,我将这两个字写满了一页纸。我的字从好看到难看,再到扭曲,模糊……
他对我越好,我的罪恶感就越深。好多次,真的有好多次,我差一点就妥协了。
可是,我却连爱的能力都没有了。
拯救天使
田小米的日记本,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火焰,像钢针,将我焚烧,穿透。
我再也无法继续读下去了,我的心被锯成碎片,鲜血淌了一地。这种近乎窒息的痛苦,让一个未满十三岁的小女孩去承受。命运将她置身于一个孤岛,周围的水慢慢地涌上来,而她却无处逃亡,连呼救的本能都被剥夺掉。
十二岁那年的经历,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从身体的要害部位扎进去,再也无法拔出。无数次的噩梦,一个人被丢弃在荒野中,恐惧、无助,连呼救的人都没有。而田小米,却用与我疏离的方式,保护着我。
我的心被刺得千疮百孔。在真相面前,我多想拿刀杀人。多想将那个满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 的老师千刀万剐。多想将那个跛脚的父亲千刀万剐。
我要去那所学校,去看看那个毁了田小米的老师。我要把田小米的日记公之于众,将这个人面兽心的人鞭打得体无完肤。
童年的村庄,正安静地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中。这个我们度过童年时光的村子,如今正在荒芜和废弃中变得死气沉沉。如果记忆可以用橡皮擦去的话,田小米已经无数次在脑海中将这个村庄连同与其有关的记忆擦去了。我也宁愿将这一切都擦去,将田小米日记里清清楚楚记录着的一切,擦去。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十二岁的田小米并不是因为聪明才知道她的妈妈去打工后就不会回来的事实。而是在她十二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她亲眼看见她的妈妈和二流在她家房后的草堆里发生的一切,也听见了他们在密谋着私奔的话。
十二岁的田小米,她用那双比黑夜更黑的眼睛,直视着草堆里的两个人。直到他们起身,才看见田小米夜猫般的瞳孔里放射着能灼瞎人双眼的怒火。
我忽然就想到了一句话:方求黑时嫌漆白。
我见到了校长,一个刚四十出头的中年人。
“温良恭俭让”。我端起校长为我沏的茶杯时,嘴里不经意间蹦出这个词。
人渣。败类。教师队伍中的耻辱。校长有些激动,愤怒地骂道。
在那个学校,以及整个教育界都传开了,那个把“温良恭俭让”挂在嘴边的老师,蹂躏了多少无辜的女孩。“温良恭俭让”的原意已经被践踏了,成了那个时期真实意义上存在着的一种讽刺,也成了那些在梦魇中惊醒的曾经天使般的女孩们一个可怕的魔咒。
孔子在创造和传教“温良恭俭让”的时候,是否曾想过,几千年或几万年之后,会有人在嘴里念着,灵魂却如魔鬼般邪恶。
校长告诉我,那个老师被抓起来了,判了无期。
这种人抓起来就算了,他死有余辜。他满嘴的仁义道德,却做着猪狗不如的事。我耿耿于怀,愤怒地说。
校长说:他死了。去年死在了监狱。他的家人都不认他了,尸体都是监狱直接送去火化的。他罪有应得。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刚刚喝进了一口茶水。温度适中的茶水凝固在了口腔里,一股血腥呛得我泪珠四溅。我将手中的纸杯捏扁,揉碎。杯里的水溢出,溅湿我的衣衫。我的双眼喷射着火焰,似要将校长室里的一切都焚烧殆尽。
他怎么可以就这样死了呢。他应该承受更多、更大、更重的惩罚。我要将田小米红黑分明的两个本子拿给他,让他在已垂暮的年龄里,去回首自己衣冠禽兽的一面。让他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之后,依然要将这两个红与黑的本子,像枷锁一样捆绑在他身上,让他的灵魂得不到救赎。
愤怒能摧毁一个人。
从学校出来,我一直走,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丝毫不觉得累,也毫无感情。只是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使着。双脚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几个小时,几天,几年……
忧虑就像不停往下滴的水,而那不停地往下的滴答、滴答、滴答的滴水声,通常会使人精神失常而自杀。
杀死人的不是水滴,是自己的忧虑和恐惧。
田小米已经被这种恐惧和忧虑杀死了无数回。那么,曾经和我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王丽丽、刘艳梅、张娟,以及更多的女孩子,她们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灼伤与煎熬。
时间慢得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
我感觉自己老了,被时间煮透了。
田小米的红黑日记本,像水银一样注入了我的身体。它像一条庞大不安的蛇,在我吸气或呼气间,都能感觉到它在我体内到处游走。
很多时候,我会站在一阵狂乱的风中,想起童年的村庄。想起奔跑的鸡鸭,田埂上的野花、悬崖、干涸的水塘以及山坡沟壑边一根营养不良的苦荞。这些事物充斥着我的记忆,令我不安。
不论生活看上去多么的安静,心灵仍然飘荡,空落,宿命般无根无涯。更可悲的是,那些同我一起生长的同伴,在岁月的敲打中已经凋落。
上帝可能会原谅我们所犯的错,可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却不会。
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从来没有小女孩被强暴过。你可以假装世界平安喜乐,假装世界从来没有邪恶。而我,却不能假装没有田小米,不能假装从来没有看过田小米的日记。
……
我开了一个公众号,起名:拯救天使。
我将田小米的日记整理归类,在这个公众号里发布,寻求更多的人关注女童的成长。呼吁那些愚昧无知的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勇气。同时也发动网民,让舆论将那些充满邪恶念头的火焰掐灭。也是推动社会对性侵的重视,甚至推动立法,推动自我保护意识。我想,这就是我唯一能为田小米做的。
公众号还开辟了另一个功能,只要有人求助,就承诺一定发起拯救信号,保护我们的天使。
当天,点击量过万。
在田小米就医的精神病院里,紫薇花爬满了白色的栅栏。在明媚的阳光下,栅栏旁的轮椅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大而空洞的眼睛直视着初升的太阳,似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遗忘什么。她曾经在那条似有若无的道路上,像个游魂带着执拗的愿望,孤独而痛苦地挣扎。
一个男子朝她走去,在栅栏上摘了一朵小小的紫薇花插入她的发间。他蹲下来帮她整理衣裙,温存地将水递到她的唇边,而她却依然直视着太阳。
应该就是他吧。田小米日记中的他。
我的心荡出一圈一圈的涟漪。在田小米的世界里,这样一份温暖的存在,都是她从来不敢想也不敢奢求的。而这一份宁静与坚守,正如他说:正是因为它简单,毫不矫饰,才会令人怦然心动。
当一切都尘埃落尽,我依旧坚守着旧梦最初的模样。
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