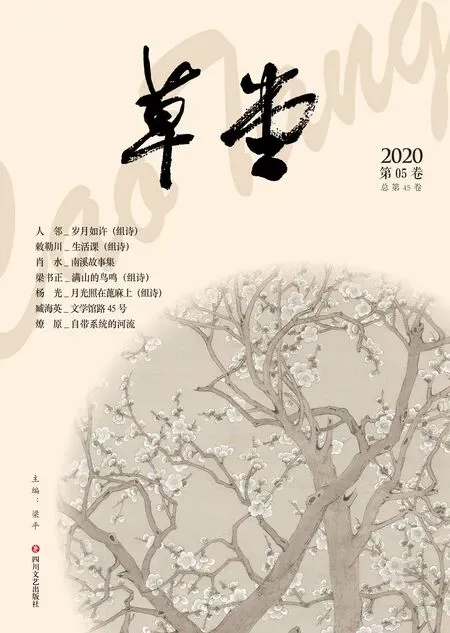溯源探寻之下的诗写变向
——人邻读解印象
2020-11-18黄昌成
◎黄昌成
一
一个人诗写的特征,很多时候都会与地域相关,渗入地域因素,地域可以说是一个人诗歌显性或隐性的印记,甚至反过来,通过阅读诗歌,我们可以看到或预测到诗人所处地域和大致生活方位。故而,地域与诗人可谓是在相互导航相互定位相互定义。地域因素对诗写凸显重要意义,甚至统领全局,不少诗人一生就专注抒写吟唱身边的地理风貌,对地域的关切就像对亲人一样,热爱使事情获得悠长关注亦无可厚非。作为身处甘肃的诗人人邻,其诗歌让我大为意外的,是地域特征的消失,西部特点相当不明显,诸如茫茫戈壁、滚滚风沙、浩瀚草原、风吹草低现成群牛羊等西部场景都不存在。
多年以前,我的拙作《诗歌的事情》曾对西部诗歌做了一个简略的观察概述,事实上,这个观感对于现下而言依然具有可行性: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西部的诗人都善于在自己的“身边”寻找意象,一个西部意象群也因之自然而然地存在且丰富着。这是地域因素决定了写作的特征和共性。按照福柯所论述的那样,“如果说意象的本质在于被当作现实来接受,那么,反过来现实的特点就在于它能模仿意象,装作是同一种东西,具有同样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实的影像也有可能带来了某种弊端,即存在着的事物容易让人的思维定型直至固定化,及至以后的应用也容易概念化习惯化,并逐渐地形成一种视野的局限。不少西部诗人常常把草原羊群马匹等西部事物当作实物抒写,当作必然的地理特征充斥于诗中,这种现象甚至出现了一种泛滥的态势,致使西部诗歌经常只以一种自然化人文化的面目出现,而不同角度和深层的呈现并不多见,不自觉地把西部诗歌单一化套路化了,对质感化个性化的寻求却慢慢地忽视了。这种所谓的“特色”对于多元的发展却是一种无意的伤害。
如果我上面的言论是可信可把握的,那么,回到人邻身上,当中的观点(有点像我提前为他写好了似的)已然形成了一种反证,与其诗写颇有不谋而合之处。换言之,一个西部诗人不以西部地理风物作为深度的诗写特征,而选择了其他视角的表达路径,则至少有着独辟蹊径的诗写意志,其内核无疑是一种个性化异质化的率性寻求所为,从这个角度可以确信,人邻的诗写至少是特立独行甚或卓尔不群的,而从诗写原则性看,这绝对是重要的,当中所指涉的是诗写的核心价值:原创性、原创的无可替代性。也即是说,人邻的诗歌,完全能够以一种诗文本范本秀立当代诗坛之中。
支撑人邻一直以在场姿态持续不懈诗写的,无疑便是人邻自己内在的诗歌美学理念,这也是一个真正成熟诗人必须持有的诗写立场。在人邻的一篇分享写作经验的文章里,其表白性释放了部分诗观话语:“我是倾向于内心化的人。明显的地理特征,在增强了诗性特征的同时,似乎也会削弱了诗的纯粹性。可是在我的诗歌深处,还是有着一些地理性的痕迹,那些耐心品味的读者还是能咂摸出来。”这段话,有几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人邻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自己的诗歌特点、取舍方向及对地域诗歌的个人化看法。窃以为人邻取消明显的地理特征风貌式的抒写,只有一种解释,其认为诗意不是简单的表象的描绘,因为这种光鲜亮丽的“色彩”组合,有可能是一种制造式的诗意,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字本原性的呈现能力,无法让字词诗句有效地缔造所指张力。如果诗人们一直热衷于对景物的描绘,则往往只是让诗歌呈现了固有的“美色”,而无法感受到景物背后和景物“内部”的机理,无法产生宏大深邃的诗意。而人邻注重“倾向于内心化”,则恰好是指注重内在感受,表象的可存在性不可存在性,都不影响其对事物的诗性悟道,诗意的诞生侧重于心灵流动的冥想式的体验,内心即事物的根本、隐喻深处及诗意扩张。事实上,这个也恰恰是人邻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以下的诗歌文本例证分析里,我会着重谈及这一方面话题。最后,人邻对自己的诗歌做了一个小辩解,表明其地理性的存在,比如《草原之夜》《凌晨的鹰》等,人邻还有两首写马的诗歌,两匹夜马之诗。如果以上都归属一种地理性事物,或者说西部涵盖的诸种风情要素之一,那么人邻所说的地理性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但是人邻笔下的草原,没有丝毫的草原景色呈现,只是写在草原过了一个夜晚的感悟:夜真的又美又宁静。/似乎谁醒着,草原就是谁的。而人邻“出产”的马,也不是草原上迎风跃动狂野疾驰的马,他的马是那种角度奇怪的静态的马,与常态不一样的马——白马,/白天看起来有点灰白的那匹马,此刻/在星光里。/夜晚/马的白,缓慢,奇怪,孤单,/尤其,整个的夜轻轻软软地含着它。/整个夜晚,那么珍重,一动不动(《夜晚的白马》)。因为含住了一匹白马,夜晚变得寂静而析出“珍重”的价值。另一“匹”《夜色里悄然吃草的马》在抒写角度上有微量差异,但二者回返的感觉几乎一样:马好像是主要的,又好像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次要的。
人邻的草原和马都是一个纯粹意象,或者一个抒写客体,而不是游人与其他诗人所向往描述的景色、景象。在人邻诗歌不多的西部自然资源或元素的呈现里,具有地理性的物象仅仅是借助或辅助性质的,它们被勾勒成一首诗的前因后果,但唯一不能以修饰修辞的形象出现,占领细节的现象性描述主体。人邻的地理性,是他把地域内的事物直接作为意象或点映诗意形成的介质而加以利用,并从中施予其陌生感,最终由此产生多种可言传可意会的诗意因子。所以并非人邻排斥地理性质的诗歌,而是其有自己的“西部”诗歌抒写渠道及看法。人邻只写有自己属性的那种地理特征诗歌。诚如评论家燎原所言:“人邻是领悟了诗歌内在奥秘并醉心于这一奥秘的写作者。他断然略去一般写作者眼中恒定的自然物象,等待并只捕获那种瞬间一现的诡奇异相,继而以最为简约的文字使之具形。正所谓把闪电还给闪电。”
有一个问题应该是诸多评论家容易忽略的观察视角,地域的随机性,而这也可能导致地域的不可信性。应该说,地域的可信性前提,是一个诗人对生存之地的关注以及倾注的热情,并与之“携手”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和见证,这样对其描述及感受无疑具有真确性,所以事物作为意象也可能是一种本能性反应。但如果单纯以地理上的事物作抒写和意象认知,则可能存在着某种含混或混淆,直接影响抒写地域的可信性,比如一个造访西部的游客经过游历以后产生的表达欲望,或者一个酷爱国家地理的爱好者用视野收集西部的图片萌发的诗感。这个时候,地域只是一次性、浅表式体验,感官的意义更大一些,不足以深刻诗写之,同样也肯定不会有生存之地上的诗人们对所处地理的体会力度,这时所谓地理特征从根本上说,极可能是浮光掠影式的观光印象,存在着随机性、不可信性。
人邻或许一早就看出了这种端倪,所以他在诗中干脆摒弃了地理意义上的自然景象与抒写需求,而更注重“整个”事物浓缩性传达到个人内心的品质反映,所有的地理特征,碎片化或片段式的地理现象、景象,人邻只是取其或达到其内质性的诗意需求结果。毕竟任何地理现象都难以进入绝对化的深刻。或许在人邻的眼里,这是一种有效的诗意开拓、撷取甚或攫取手段。但无疑,这恰恰又成为人邻诗歌夺目的另类标志。
窃以为这个标志高端而有玩味,甚至有些悖论化,因为实质是在取消地域影响。倘若把人邻的诗歌从西部抽离单独置放,你能清晰看出面前是西部诗歌吗?这样看来,地域因素顶多是一种间歇性的因素,诗歌与地域有关,但又不是必然决定性因素,其可以是地域大环境操作,也可以是大环境下的小环境操作,甚至不排除与地域范畴之外存在同一性,甚至诗人的写作理念可以完全脱离地域的限制性。
超越地理性的诗写同样是一种“超我”。最终,一切还是要回到诗本身。
二
《岁月如许》这组诗,所写是岁月治下人与事物的各种情状,包括生死、亲情、日常等相关性现象。这组诗有性灵小品的味道,真实,意味盎然,易读的外围耐读的内里,大抵短小精悍,诗句简约、呈现其本原效能,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简约手法还有一个属性,难以模仿,或者仿无可仿。我不知将其称为性灵小诗是否适合,反正每首诗的所指归宿,都是一种人生况味的回流,还有人性关怀下衍生的微妙温情。
前面已经说了,人邻注重内心感受,此过程演绎为诗写过程则是,对所见事物进行描述,单向或复合地逐层深入,然后把个人思考、内心体验附着或嵌入事物之中,保持内在行进,或让事物代言自己内心,二者拓展都等同于感悟所得。人邻的这个处理方式值得称许的,是抒写的对象性存在,其以事物现实为基调,因而即便经过感受过滤,却不会让人觉得诗歌虚空,感受和感悟最终都似乎有实体支撑或者就是一种实体。整组诗的构架基本如此,其中《这世上》《羊》《一个普通人的悼词》等都各有类似形迹可辨。尤其是《山坡上》的这首诗,简直有如度身定做。
骨头/那灰白、皲裂的,历历在目/亲人过的/雨水过的/日月过的/神/也过了的//注目良久/我不忍离去/不忍离去那染着微微草色/灰白的洁净,无尘的时光/也许,这即是前世/这白骨,将轮回成另一个谁//只是他复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已经在去远方的路上
诗人由山坡上所见的骨头开始,然后进入冥想,并与之混合,骨头这个核心意象,被想法反复贯穿,转而贯穿全诗,所见、想象与生死感悟,后续或最终的唯美的唏嘘叹息、人世的释然与轮回,构建了一首现实与超现实组合之诗——即便最后成为白骨,复生时我们都无法回到原来的白骨(自己)。我倏然想起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里列举的一个“确定”:举例说,这样一个命题也许就是:“我的身体从未在消失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出现。”这段话表明了一个意思,身体在现实里是一直存在着的,不管消失不消失,所以无所谓重新出现。但是当我们在尘世里消失,身体会不会又重现?重现的还是不是尘世那个身体(自己)。这个事情是确定的吗?其实未能确定。但诗人用诗作了意味性的回复。诗是前瞻性可能性的创设,内心感受将使一切诗意获得落实。诗意不一定是答案,当然,诗意也可以是答案。
人邻营造一些空灵的元素,动态抒写里有时还产生一种超然的禅意效应,事实是一种神秘性的隐现,如《老琴师》《夜》《断章》这三首。从总体性质去看,应该都归属内心臆想或顿悟一类诗。前者有“高山流水”之喻,知音的倾听里,娓娓琴音道尽人世(之禅):在世外悲悯人世。而后者——一个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参透一棵树的秘密//虽然整片森林/他可以/一次次穿过(《断章》),似乎还明确悟出了禅理:当一个人仅仅在事物的外部,不管外部多么强大,获知与否,都无法深入了解事物紧闭的内在性,内部决定一切。
而《父亲二题》《父母的餐桌照片》《很多年了,忽然想起》等诗,则关涉亲情、爱情等情怀伦理,人邻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并没有打那种一目了然的感情牌,而是直接如实抒写事件,以静制动,巧妙地隐藏了骚动乃至汹涌的情愫。其把意旨从字里行间更多地默默传递赠予读者,所有获取的动人情怀都是文字符码发出的回旋余音。这也是声色不露的叙述的反驳应和。
或许还可以再回到西部诗歌看问题吧。从惯常经验传递过来的信息,西部诗歌自有其特征,比如大气,豪放,雄厚,宏阔等大开大合诗风。人邻的诗歌在外观的表现上,应该与此无关(如果一定要说有关,是其相对硬朗的行文风格,但这是叙述的一种常态),但是在主旨和诗意的呈献上,却常常彰显这一效果。而收到这一客观放送事实,我想原因不外乎是人邻诗歌的及物性。及物性的夯实与高明运转,可以使诗歌充盈质感,抵达一切诗意桃源;及物性决定了诗意的层次。另外,诗意的真实无懈可击。
世界诗坛上有一个传播相对广泛的诗歌事件,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诗写的蜕变传奇,并且这种蜕变的结果直接导致拉金拥有了可与艾略特比肩抗衡的诗坛地位。在当时,英语诗坛正流行着以艾略特为主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倡导的现代抒情诗写作。拉金在短暂的追随以后,突然掉转了诗歌方向,其向传统诗人托马斯·哈代致敬,重新回归英诗传统风格。当然,拉金的这个传统,已是一种传统的蝶变,在精准叙述语言的抒写下,拉金还引入了口语化叙述等相关手段。一句话概括,在一个表面传统的诗写框架里面,事实上已植入后现代的基因,换言之,拉金的传统,是传统与后现代相结合的产物。
以上文字,当然不是为了要重述拉金的盖棺论,我只是想以此作为一个参照,回到诗写源头之处再看人邻的诗歌创作,我隐隐觉得,人邻的诗写貌似与此有相似之处,另外,你很难把人邻的诗歌划入某种单一的风格主义流派。这种草率判定往往缺乏严谨性、不具备精准性。
人邻的表达通常在一个扎实朴素的语言平面上展开,表面上看倾向于传统,其中叙述是这类诗歌的特质,但恰恰也由于叙述,使诗歌产生微妙的改良,换言之,叙述决定了诗写的裂变。人邻所做的事情是,注重叙述的撕裂、断句,一方面加强节奏感,另一方面则避免了传统抒写的平铺直叙。在细节处理上,人邻亦有所节制,让语言恰到好处呈现,点到为止与细腻铺陈交错进行,再加上人邻以唯心冥想推动的隐喻、隐寓效果,诗句或全诗最后留存宏大的诗意场域。这无疑迥异于传统的抒写结果。事实上,叙述的有效与否,或者干脆说甄别传统的标志,恰恰是最后诗意的张力疆界拓展。可以说,人邻利用了传统,却铸造了自己的新传统,实质上是传统的有效质变;人邻极为注重日常性抒写,传统与当代生活的紧密契合以后,所有结果的汇合指向,就是赋予了人邻诗歌的当代性切换和坐实。无疑人邻掌握了一个根本或决定性的诗写原理:传统的重要性恰恰是传统的可变性,其能够结合任何形式主义一起践行。推本溯源,恒定的诗歌是永不恒定的诗歌;诗歌拥有重塑性也即重生性。这是另一种维度的复古原理。
“我的诗歌,还在一个过程中。我希望能写到很老的时候,到80 岁那个时候还能够拥有诗的创造力,能为自己写下的诗句所感动,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所渴求的。”这同样是人邻质朴的愿望或最高的要求,自然也包括了前行中多方位的实验、诗写的不确定性;拭目以待的同时,我祝愿这个目标能完美实现,祝愿诗坛能够悠然接收到这样的福音。
一个题外话做结语?在我的诗评生涯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引用作者的言论作论述过渡和依据,如果我说,这是受批评家海伦·文德勒写作评论手法的启发,你信不信,其经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而“治”在这个文章里,是还原,诗性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