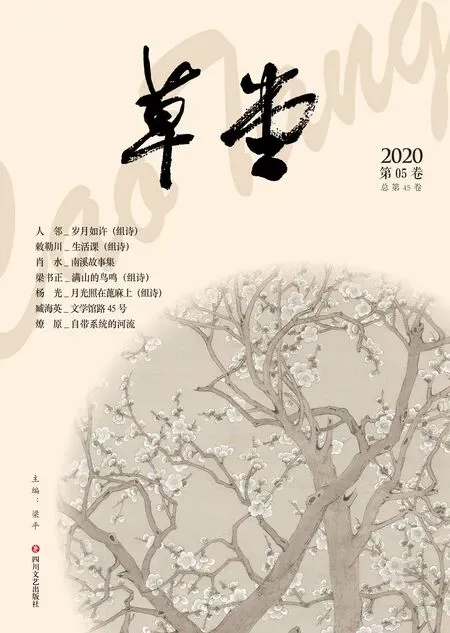自带系统的河流
——现代诗歌与先锋精神
2020-11-18◎燎原
◎燎 原
[一]
2017年,中国诗坛有关新诗百年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标志着1917年由胡适八首白话诗肇始的中国新诗,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一年的诗坛,“中国新诗”也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语。但由此往后,这一概念却逐渐淡化,在对当下诗歌的指称中,它已基本上被“现代诗歌”所取代。
在一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每一个大概念的出现和变更,都意味着诗歌写作理念和艺术形态的重大变更。而这一变更的依据和动力,则来自时代内在因素与外来因素的变更。此外,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都是以与之相对应的旧概念为前提,并且是对旧有艺术形态的颠覆与革新。比如新诗的诞生,就是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门槛的五四运动前夜,由白话文运动形成的诗歌革新成果。它所针对的,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格律诗。格律诗原本就是格律诗,但因为新诗的命名需要,此前一切以格律形制产生的诗、词,包括散曲,此后都被统称为“旧体诗”。一旧一新,一目了然。
那么,新诗和现代诗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这两个概念一直到现在,都是被混用的,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和界定。而所谓的现代诗,又有两个不同的内涵,其一它是一个时间概念,一般是指1979年新时期诗歌开启以来直到今天的诗歌,实际上就是指现代人所写的新诗,故而经常与中国新诗这一概念相混杂。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它是指不同于新诗的实质意义上的现代诗歌。这也是随着新时期诗歌中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出现,才被意识到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不只是指现代人所写的新诗,而且是指诗歌中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现代语言形态和艺术形态。它更确切的内涵,是指融汇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的先锋诗歌。而先锋诗歌,又因为它所从属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所以又被称作现代诗歌。接下来,本文将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现代诗歌这一概念。
而现代诗歌的颠覆对象,则是新诗写作中被视之为守旧型的“传统诗歌”。这一时期,先锋诗歌成为现代诗歌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基本上等同于现代诗歌;而守旧,则成为传统诗歌的标志或代名词。但此后我们将会看到,许多概念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就像游标卡尺上游标的前后移动,其性质或重要性会随着时间刻度的前后移动而变更。
什么意思呢?相对于传统的旧体诗,新诗原本就是对于传统的颠覆和革新,那么在多少年之后,新诗中的一大部分写作,怎么又变成了守旧的传统诗歌?是的,旧体诗代表的那个传统,并不等同于新诗的这个传统,但两者的性质却完全相同,都是被用以指称旧有的和守旧性的写作。具体地说,当新诗从出现伊始生气勃勃的变革,到它在不断地发展丰富中逐渐稳定成一种模式,再在一个相应的时间长度内继续延伸,这种模式就演化成了传统,变成了传统模式。而模式,是指某个事物在原先变动不居的发展中,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进而成为可以效仿的标准制式或样板。模式的最大特征和功能,就是它既提供了样板,又便于复制。社会管理学上的模式复制和样板推广,就是基于这一原理。然而,任何一种先进的模式只在一个相应的时间段内有效,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所有事物的发展所遵循的,则是另外一个原理:开创模式、打破模式、创造新的模式。这对于诗歌和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尤其如此。当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模式趋于成熟,它需要一个盘整期来巩固这一成果。但这也同时意味着,这一模式已接近固化,再继续平面移动,它就成为一种惯性,进而成为约束艺术创造力的套路或桎梏。
所谓新诗中的传统诗歌写作,就基本上滑动在这一惯性写作区段。对于这类写作者,这是一种熟门熟路的写作,也是最为得心应手的写作。又因为这一套路中的写作参与者众,也被他们认为是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写作,因而是最好的写作。
[二]
但所有的诗歌艺术史,都是在不断的守恒与创新中写成的。创新的根本理由有两点,其一是基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明显的重大变化和不易觉察的内在变化,在诗人们内心触发“蝴蝶效应”风暴。其二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人性、人心和人的意识世界无穷奥秘的认识,永远都有待深入。对于这些新的变化和认识,旧有的语言方式和艺术方式已无法有效表达,所以,必然有赖于新的理念和手段。比如关于人类的意识世界里我们虽然知道它的复杂,但也就是停留在这一笼统的感觉层面而已,当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人的意识世界里区分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尤其是把意识最深层这个最为不易被觉察,但却支配着人的一生的“潜意识”强调出来,这一精神分析领域的伟大发现,遂成为包括了“意识流小说”等世界现代文学艺术运动的源头之一,也使诗人艺术家们获得了探求与表达人的深层意识世界的依据。
诚如前边所言,中国的现代诗歌是在1980年代往后才被意识到的一个概念,虽然它与新诗的概念一直被混用,但此时相继登场的先锋诗人们内心很清楚,他们对早已固化为模式的这种传统新诗,已经不胜厌烦。因为由它所配置的模式系统,根本无法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复杂感受。所以他们所要做的,正是对这一模式系统的颠覆。尽管这种颠覆性的写作,此时以朦胧诗和第三代的名号为标识,但随后却被理论界和他们自己发现,这种写作的大背景,则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而此时的先锋诗歌只是统摄于这一大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潮流,几乎不留死角地涉及小说、美术、话剧、音乐、电影乃至稍后的书法等所有文学艺术领域,而1979年前后出现的朦胧诗和美术界的“星星画展”,则承担了这一大潮中的领潮者角色。这也是诗歌为什么被称作时代敏感神经的一个实证。
从新诗的诞生到现代诗歌的出现,其背后的变更依据和动力法则除了内在的时代变革因素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动力,这就是外在的世界文化艺术思潮的加力与推动。而从形态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大潮,则是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一次补课性质的滞后反应。
[三]
发生在20世纪前后这一世界性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本质,是基于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兴起后,这一原本是物质革命的成果,却反过来对人形成了异己化的力量。人不再是他们自己,而成了机械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冰冷、隔膜,而使人陷入不可挣脱的孤独;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于人类噩梦般的现实,不但击碎了人们对于世界的原有认知,也使他们陷入噩梦般的恐惧和一切都不可预知的荒诞幻觉中。此中情景,正像挪威画家蒙克在1893年的《呐喊》中,对于无妄之灾的提前感知和惊恐,以及此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由残缺的肢体等元素符号拼贴的战争灾难。是的,由原先一切文学艺术形式提供的经验、信念都不再可信,甚至连经典油画中蒙娜丽莎那永恒的微笑,也绝无永恒可言,噩梦般的世界不再有温暖与美,只有冷酷与丑陋,因而微笑的女神被画家杜尚硬生生地涂抹上了两撇胡须——美的被摧残、被亵渎才是世界的本质。这一切都意味着,人们之于世界更为复杂、隐秘、荒诞的感觉,以及支离破碎的精神境况等等,传统的文学艺术既从未遭遇过,因此更无法表达。于是,以颠覆传统为主旨的现代主义运动勃然兴起。先知般的蒙克和毕加索、杜尚等代表性画家横空出世;立体派、野兽派、抽象派、达达主义等现代主义绘画流派横空出世。
而在包括了小说、诗歌、戏剧乃至哲学领域,一个更为庞大的银河星系横空出世——象征主义系列的艾略特与《荒原》、瓦雷里与《海滨墓园》;意象派系列的庞德与《地铁车站》;表现主义系列的卡夫卡与《城堡》《变形记》;意识流系列的乔伊斯与《都柏林人》、伍尔芙与《墙上的斑点》、普鲁斯特与《追忆似水年华》、福克纳与《喧哗与骚动》;存在主义系列的加缪与《局外人》《鼠疫》、萨特与《恶心》《死无葬身之地》及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波伏娃与《第二性》;荒诞派系列的贝克特与《等待戈多》、尤奈斯库与《秃头歌女》;黑色幽默系列的海勒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内古特与《第五号屠场》、托马斯· 品钦与《万有引力之虹》;魔幻现实主义系列的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直至垮掉一代系列的金斯堡与《嚎叫》,自白派系列的西尔维亚斯·普拉斯、安妮斯·塞克斯顿……
对于当时的高校学子和年轻的一代诗人艺术家,这是一群大神级的人物,或者直接就是大神。由这一系列作家作品带来的现代艺术观念和手段,成为这一代人的核心资源,甚至直到今天,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
但如果不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世界文学知识谱系,将会只有教科书上的契诃夫、果戈理、巴尔扎克……以及由他们代表的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
但以迈向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这个1979年终于来了。已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这一现代主义运动,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而终于到来。它不仅是对一代人视野的全面刷新,一次升级换代性质的扩容,更对接了一代人的潜在感受,以及表达的渴望与好奇。兴奋的接受阀门,由此朝着一个陌生新鲜的世界打开。发生在1980年代沸腾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由此全面展开。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一切都被称作先锋艺术:先锋诗歌、先锋小说、先锋绘画、先锋戏剧……与先锋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还有一个略为谨慎的指称:“探索”或者“实验”。这一带有委婉意味的指称表明,最初的这一先锋,仅仅只是少数,并且饱受压力与诟病——而这两点,恰恰正是先锋艺术的标志性特征。
所谓先锋艺术,就是先行者的艺术,是少数人超越一个时代认知疆域的超前行动,因而也是对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既有观念和艺术定式的对抗与反叛。如果不是少数,它就谈不上先锋,先锋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不饱受压力与非议,它也就不是先锋,所有的先锋艺术都是从不被习惯、不被理解,因而横遭非议的地方开始的。而关于这类先行者,文学艺术史上也因此留下了一系列令人痛惜的个例,被视作哲学超人的尼采因为其超前性的思想不被理解,因而宣称“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伟大的凡·高由于超前性的画作无人接受,一生过着清贫潦倒的生活,以致精神错乱而自杀。然而,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却指向一个时代无法辨认的事物的本质,指向未来。因而往往直到他们死后,才被后知后觉的公众大梦初醒般地视为奇珍。
由此再回到1980年代起始的中国先锋诗歌,诸如北岛《我不相信》中的激愤基调和冷峻犀利的质疑精神;芒克那棵阳光下的向日葵,意欲一口咬断太阳套在脖子上绞索的个体觉醒者形象,包括朦胧诗在当时被视作朦胧复杂的意象方式,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态上,都与此前通俗易懂、豪迈浪漫的集体主义流行模式背道而驰。它们由此遭受的“看不懂”、全盘西化、数典忘祖的非议与打压,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当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视野回头再看,它无论如何都是当代诗歌史上一个具有断代性质的重大拐点——中国新诗史上“现代诗歌”的时间之窗就此打开。而仅仅是十多年之后,它的理念与手段已由横遭打压的“看不懂”,转化为诗歌写作的基本方式或曰大盘底座,垫高了当代诗歌的写作起点。这正是这一时期的先锋诗歌,一个历史性的奉献。他始之于少数的若干人,继而是少数的一群人,再接着转换为由一代新锐群体共同参与的先锋诗歌运动。这也是它在时代变革背景中,由运动形态修成的一个历史性正果。但对于先锋艺术而言,它既呈现为群体性的艺术变革运动,更存在于那些独立不群者,各自的独立前行。
[四]
当先锋诗歌运动终于修成正果,很快也就变成了人人唯恐先锋不及的时尚。大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仿制之作汹涌而至,但它们已不再属于先锋诗歌的叙事范畴。这也反证出它的另外一个特征,所有的先锋艺术都是不可复制的。它有自己的起始动因,它是一小群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由共同的精神问题和思想艺术资源所激发,非如此不可的一次精神艺术探险。当它在这一轨迹中发展成熟,成为被模仿的对象,意味着它至此已成为一个时代新的艺术资源,这无疑是它的荣耀,但也只是它的荣耀。由于起始动因的时过境迁,集结于先行者内心那种巨大的精神艺术冲动,后来者已无法重临,所以他们的模仿只能是有形无魂的模仿,似是而非的照葫芦画瓢。这也就是说,它只能作为资源被吸收转化,而不是作为时尚被复制。
其实尚还在先锋运动行进到中途,在部分先锋诗人和作家中,一个新的艺术向度与写作潮流已经出现,这就是以文学“寻根”为主旨的寻根文学。这一潮流,虽然与南美高地上崛起的寻根文学存在着潜在的呼应关系,但在更大程度上却出于中国作家的自觉。这便是针对此时在世界现代主义潮流的覆盖中,中国的文学艺术几近被同化,以致丢失了自己,因而寻找并回归到自己民族文化的根脉与传统,以作为新的资源与动力,确立现代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形象与标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此前被排斥、被反叛的“传统”,此时则成为被致敬的对象。
然而这里所说的传统,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中国文学传统。这个传统之所以需要“寻找”,就是因为它并不是指向现成的、普泛性的传统文学与文化,而是一个远为庞杂深邃的概念。它指向远古神话,指向包括了《诗经》《易经》、诸子百家的哲学寓言等等,缔造了生机勃勃中华文明的源头性文化。更重要的,它并不只是对这一切经典的补课,而是带着已经获具的世界文化眼光,对这一根脉性传统的深度观照和激活,以使这一沉淀已久的源头文化大块在重新激活中,成为当代文学艺术新的资源。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先锋作家韩少功,及其此后标志性的长篇《马桥辞典》。它在诗歌界的代表性人物和标志性作品,则有江河《太阳和它的反光》,杨炼的大型组诗《礼魂》及此后的众多诗作,四川同一时期诸多先锋诗人的一系列作品……它们在当时又被称作文化史诗性的写作。而这一系统的另外一位诗人,则是在稍晚一些时候出现,并把这一写作推向极致的海子。尚在1983年,年仅19 岁的海子所写的第一部长诗《河流》,以及《源头与鸟》的后记,就将由源头与河流所象征的传统,以及与大地实体相对接的民间主题,作为他整个写作的出发点,恍若一位诗人的归根复命。
也就是从此开始,传统的旗帜重新招展,不断被重新认识的传统文化,包括作为传统的古典文学,在当代诗人的写作中成为一个新的支点。
但这仍是此时的先锋诗人们所干的事情,并且是只有他们才能干的事情,因为这是只有在洞悉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系统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的对比与反应。没有这一环节所赋予的视野和眼光,所谓的传统,只能是原先那一被简陋概念所定义的干瘪传统。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先锋诗歌,绝不只是一种激进的极端性写作,虽然它在每一个区段,总是表现为写作的激进与极端,但它是由一个又一个区段构成的线性系统。仅从区段的形态看,由于每一个新区段的出现,都是以与前一区段的对抗为前提,因而它是极端的,不极端就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对抗;但从整个系统看,它却是这一区段对上一个区段极端部分的矫正——以“矫枉过正”形态做出的矫正,所谓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而这一次次对抗矫正的结果,便是这一系统不断更新中的升级换代。由此我们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先锋诗歌,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态运行系统,也是一个不断革故鼎新的自我完善系统。一方面,它以激进的方式把陌生新鲜的艺术理念强行带入诗坛,并冲击着诗坛;另一方面,在这一系统内部,又一直存在着一个矫正更新机制。冲击与对抗的本质,也是诗歌自身的本质:它拒绝一切的陈腐与平庸。而矫正与更新,则是它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对同一事物的反省与再认识,并带着这一更为深入的认识成果,开启新一轮的艺术更新。中国的现代诗歌,如同一条自带系统的河流,就是在先锋诗歌运动这一轮又一轮的革故鼎新中,一直走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再回头来看,当代诗歌中的传统性写作,基本上还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面目,但已不再成为垄断性的主流;而现代诗歌,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并逐渐从异端另类的边沿化角色,成为主体性的写作。
至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新诗建立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的形制与模式,此后主要由传统性写作者来继承;现代诗歌从1980年代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它同样来自中国新诗,但它所继承的,则是新诗的灵魂,在一个始终敞开的端口,生气勃勃地不断变革。
[五]
然而,在时间进入21世纪初期稍后,你又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以后别再给我提先锋,别再给我口口声声地现代意识、现代主义。这一似乎要与先锋撇清关系的表达,未见得就是受了先锋的什么伤害,而是对已经存在的诗坛共识,再喊上一嗓子的高调聚光。这种共识,首先是对众多先锋诗歌的仿制者,动辄以先锋来标榜的反感;更重要的,则是在那些已经建立了自己写作根基的诗人心目中,此时的先锋,已不复它作为创造力象征的那一荣耀。因为由它相继开创的那一切,于今已成为一种大众化了的基本方式。所以,其实从更早的一些时候开始,以此起彼伏的潮流对抗展开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基本上已偃旗息鼓。除了渴望快速升起的后生们,尚还有心思制造一些潮流的动静,没有人再热衷于群体性的潮流与运动。当你如今再提到先锋,竟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但实质性的先锋写作,或曰先锋精神的写作,并没有终结,且永远不会终结。在潮流和运动终止的地方,是一个个底气饱满的独立不群者,不事张扬地独自前行。这显然也暗合了这样一种现象:大自然中凡习惯于群体行动的,都是小型物种,诸如鹰虎之类的猛禽大虫,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先锋在当今之所以不易察觉,是因为它已淡化了原有的标识,而它原先最醒目的标识,就是世界先锋艺术和经典诗人作家,在先锋写作中投射出的新锐与陌生。而如今,这一资源已被更多的写作者所熟悉,新的资源非但不像当年那般难以获得,且基本上就是同步传入。21世纪以来诸如特朗斯特罗姆、阿多尼斯这些经典诗人,则形同住在中国诗人隔壁的熟人。当原先的稀缺资源不再被独享,由此转化出的先锋标识也就自然不再醒目,以致迹近于消失。但这种外在表征的消失,却是作品之中更为充分的内化。至此,不只是外来的世界现代资源,更包括本土的传统资源,这曾被历史强行分割成泾渭分明的两大块体,终于合流出同一个属性:它们都是人类精神艺术的杰出成果,给予诗人以滋养的丰厚资源。
也因此,新世纪以来那些优秀诗人的写作,实质就是在这两大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再出发。在这些作品中,不再有明显的资源分野痕迹,而是不分彼此的深度混融;而对于那一个个的独行者,你也不再能感觉出他们的来路和归类,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在由现代诗歌不断抬高的当今这一写作平台上,阅读与眼界比以往更为重要;写作中的现实出发点和问题意识,也比以往更为诗人们所看重。但这两个因素表现在不同层面的写作者中,却存在着悬殊的差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普通层面的写作中,通常会表现为基于阅读的写作和基于内心诉求的写作这两种不同类型,前者的阅读就是为了写作,其写作依据主要来自阅读而非个人经验;后者的写作则主要来自诉求冲动,它并不太在乎艺术的观照而呈现为直抒胸臆的倾泻。而那些优秀诗人的写作,则是阅读与诉求表达的统一体。两者更为悬殊的差异还在于,前者的阅读是一种即时性的就近阅读,其阅读载体主要是报刊网络,是对眼前那些唤起了自己写作冲动的同代诗人的阅读;后者的阅读则是世界范围的阅读,是不只限于诗歌的,包括了历史哲学文化的综合阅读,并且是不断发现不断刷新的阅读。一个大概率的结果是,即使在这类诗人中,谁在这一阅读中走得更深,也就会在写作中走得更远。
但这种阅读,又是与其内心方向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一个诗人的内心方向决定了他的阅读方向;反过来,这一阅读又激发深化了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写作。没有这一内心方向的驱动,也就没有这一阅读的持续延伸。一个极具意味的现象是,从尚还是本世纪之前直到现今,中国诗人阅读名单上的外国诗人,已经悄然更换。早先统摄于现代主义运动各路流派中的大神,已经不复当年那样重要,代之而来的,则是布罗茨基、米沃什、佩索阿、保罗·策兰、阿米亥、巴列霍、沃尔科特等等,这类孤岛式的,与身份困境、内心困境、语言困境相搏斗的诗人。而这一名单的更迭,正是缘之于诗人们在新的现实情境中,内心方向的驱动。
那么,这一内心方向又是基于什么?这就是依据自己不同时期的现实处境和文化处境,对人的生存症状不断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做出回应。这也就是说,在群体性的先锋运动结束之后,这种个体的先锋精神的写作,同样会在每个不同的时期,转换为不同的文化针对性和社会针对点。而这种针对点,有的指向已趋显豁的现实问题,有的则是基于某种前兆鬼使神差的预感,当诗人骆一禾当年惊悸般地喊出了“我们无辜的平安没有根据”(《黑豹》),我们大概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如今,在我们经历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与不安,又在2020年伊始这场突袭的病毒中遭遇更大的不安,才发现这种不安已成为普遍的心理事实。
的确,与早先先锋诗歌潮流中的语言狂欢和文化高蹈相比,当今的诗人们比以往更为关注现实。然而,当今的公众非但同样关注现实,且就对于现实的敏感度以及通过自媒体表达的尖锐度而言,也丝毫不弱于诗人。因此,所谓诗人先知与启蒙者的角色,已变得暧昧而含混。但诗人之所以仍然是诗人,既包含了这种认知的敏锐性,还在于他把这诸多的现实事象,纳入一个纵向文化系统的综合考察与处理。在这一纵向系统中,它们只是一个又一个的事件,一个又一个的现象,而这一系列现象背后所伏藏的根源与本质,才是诗人们眼中的真问题。因此,他们对于现实的回应有时虽然是直接的,但更多的时候不是,尤其不是自媒体写手那种狂喷式的表达,而是经过综合处理的艺术回应。在这类作品中,某一具体事件已淡化缩小为一种元素,或至多是一种主体元素,与之同场的,是其他相关元素有形或无形的气息性介入。因此,一个声音内部是一系列幽灵式的声音,是活在一个人身上众多幽灵的发声。由此形成的这首诗作,既远远大于这一具体事件本身,也全然有别于通常性的公众经验。它让你陌生,又让你惊奇;既对应了你的部分经验,又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这就是诗人的表达,而不是自媒体时代写手们的表达;这样的写作,也正是超出了一个时代普泛诗人层面的,那些保持着先锋精神者的写作。
这样的诗人虽然不多,但也并不罕见。有的一直就在你的视野中,有的则是沉潜游离形态中,不时让你眼前一亮地存在。而诸如诗人于坚,则日益趋向 “大象的城堡站在沉思的平原上”,那种笨重阔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