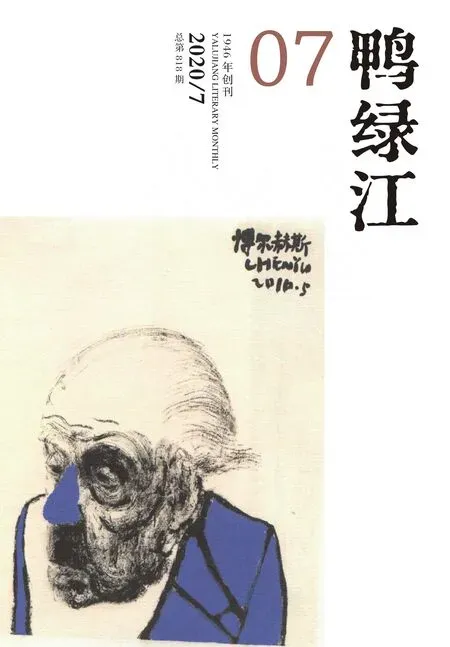以温情和敬意点亮历史
——关于长篇小说《大辽诗后》
2020-11-17高海涛
高海涛
当轮到苔丝狄蒙娜歌唱的时候,
生命对于她已所剩不多,
她哭泣,看不见爱的星光,
眼前只有垂柳,随风摆过。
——帕斯捷尔纳克《英语课》
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建立的大辽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尽管它疆域广阔,雄踞北方,遗迹昭昭,但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书写,都多少有点边缘化的味道。以历史小说为例,有关辽代的长篇虽然不乏佳构力作,但整体上还是显得不入主流,反响寥寥。与之相比,人们似乎更津津乐道于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宋辽关系,以及萧峰和耶律洪基之间的恩怨纠葛与悲情往事。
萧峰是否实有其人暂且不论,仅就辽道宗耶律洪基而言,也并不是像金庸先生所写的那样雄才大略,展翼图南。作为辽代第一位以嫡长子身份承继大统的皇帝,他其实始终信守了宋辽之间“澶渊之盟”的政治承诺,致力两国修好,其在位凡四十六年,不用说兴兵犯宋,就连契丹人“胡骑如云掠蓟东”的“打草谷”习俗,恐怕也难得一见。总的看,耶律洪基是个守成的皇帝,他能够被后世记住的也许只有两件事:一是平定重元之乱;二是听信奸佞之言,赐死懿德皇后萧观音,继而废除太子并导致其被害。这才是他真正的悲情往事,如果说前者是顺应历史大势的一幕正剧,后者则是昏庸和刚愎所造成的悲剧,并成为大辽国祚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女作家赵颖的长篇新作《大辽诗后》,正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构了这一段悲情往事。作者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品格和正史、良史的风范,在实地考察和参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辅以民间传闻,移情想象,历时近两年,凡二十阅月,写出了这部50多万字的史传体小说,为一代诗后、契丹才女“发皇心史,代下注脚”,而且可读性极强,艺术地再现了辽代女诗人萧观音的生平历史和性格形象。
作者以深情、细腻的笔触,叙述了萧观音的成长历程。她生于宰相之家,幼承家学,温柔蕴藉,有着牧歌般美好的童年和露珠般纯洁的初恋,既能骑射,尤擅诗文,所以当她玉立朝堂,其“孤稳压迫,女古华革”的气度立即赢得了人们由衷的赞美:“菩萨来做特里蹇,观音来做辽皇后。”然而,读者始终不会忘记小说开头,即萧观音诞生前其母槊古公主那个不祥的梦兆。正是这个梦兆以及封后册立仪上从天边飘落她脚下的那幅白绫,伏脉千里地提示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女主人公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
小说这样写,我觉得很自然。辽代是个宗教氛围复杂浓郁的社会,尤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因果命定之说盛行,所以这种一梦成谶的写法,不仅有民间传说的依据,也为萧观音后来的结局赋予了凄美的神话色彩——年轻的神,她终如预言所说,香消玉殒了。但是,辽代毕竟不是古希腊,萧观音也并非女性版的俄狄浦斯,其悲剧的诞生无疑也和她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有关,小说对此并没有回避,包括她的诗作,《谏猎书》和《回心院》显然也都是引起猜忌的根由。但是,如果按辽代笔记《焚椒录》所言,把萧观音的不幸完全归咎于她的诗文与音律才华,也是过于简单和片面的,里尔克说生活与杰作之间,总有某种“古老的敌意”,但真正的敌意,无疑也会有其社会历史原因。
大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帝国,不仅在政治上“蕃汉分离”,辽人部落制,汉人郡县制,形成了南北两套行政体系,在权力分配上也是“帝后共治”。如果说历史本身,在词源学上意味着“男人的故事”(history)的话,那至少辽朝应是某种特例。由于耶律皇族和萧氏后族是两个固定的通婚集团,契丹贵族女性的文化和政治地位相对是比较高的,可以说,辽代初期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并肩驰骋的故事,萧氏后族的杰出女性往往也能深度参政并叱咤风云。但君权毕竟是第一位的,男性话语始终是难以逾越的权威,而且,前现代民族从较低的社会形态向较高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也必然要伴随着一个去氏族民主的过程,正如皇权继承的兄终弟及传统当时已经被父终子及所取代一样,“帝后共治”的传统也开始走向没落和式微。在这个意义上,萧观音的悲剧既是个人的和女性的,也是家族的和历史的。她的诗作就内容而论,其实也多是应制之作,无论是《伏虎林应制》还是《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都是君权与男权之下的受控表达,而一当她所要表达的话语与君权圣意相抵牾,就自然要走向悲剧和毁灭,宋国的渗透和奸佞的谋害只是推波助澜而已。特别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当萧观音获罪临刑之际,尽管有皇太后萧挞里为其辩诬,仍被耶律洪基阳奉阴违,执意赐死。而纵观辽代历史,在萧观音之后,她的皇孙、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文妃萧瑟瑟也同样因诗获罪,被诬致死。一代诗后,两代风华,足以标志“第二性”在辽代的真实命运,或者说,她们也恰好是萧氏后族历史命运的承担者。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可以与萧观音的故事构成直接比较的显然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而如果说耶律洪基贵为帝王,却仍然有着摩尔人奥赛罗的精神因子,即“看似自信,实则自卑不安”(兰姆语)的话,那么萧观音,尽管其悲剧可以部分地解释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整体形象而言,她无疑正是中国辽代的苔丝狄蒙娜:纯洁无辜,柔弱无助,蒙受奇冤,无语而去。千百年来,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黎民百姓,人们始终对这位才貌非凡的契丹女子给予特别的同情,甚至有人认为,历代对萧观音及其诗文评价颇高,可能和这种出于同情的审美接受不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萧观音的同情或许也影响了人们对耶律洪基的历史作为及整个辽代后期的评价——蛮荒的、蒙昧的、暴戾的、混乱的,尽管只隔着“燕云十六州”,却仿佛与中原“赵宋之世”那种“清明上河图”般的繁荣、理性、文明和秩序相距遥远。
历史大于所有的人,但一个人就可能超出历史。实际上,随着女主人公萧观音的悲剧结局,相关人物也都相继走向了悲剧。耶律洪基,他在杀妻灭子之后的痛悔和醒悟,使他兼备了奥赛罗和伊凡雷帝的双重形象。而太子耶律浚则更像是一个失败的、反向的、弱化形式的哈姆雷特。这里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宫廷事件,竟然汇聚了如此多的悲剧原型,《大辽诗后》的悲剧几乎是整体性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历史悲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生死集中上演,在作者不动声色且不乏温婉的讲述中显示出令人震撼的张力。
作为一部女性历史小说,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是息息相通的。不仅如此,萧观音出生的辽西懿州恰好是作者的故乡,因此在小说中,我们通过那些风情画的描写,似乎能看到作者自身的故乡情结与心路历程:一种诗意的记述,一种好奇的探究,一种遥远的怀念,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一种同乡音、共乡情的亲切以及隔代知音般的感伤。钱穆先生说,我们对中国以往的历史应该怀有“温情与敬意”,我觉得这也正是《大辽诗后》的叙事态度。虽然年代久远,瑶瑟凝尘,但这种温情和敬意却点亮了那段幽暗的历史,也弹响了那个契丹女子遗恨千年的琴弦。
这部长篇的语言别具特点,作者并没有像当下一些历史小说那样,刻意追求去文言化、去修辞化,而是在借鉴民间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基础上,文白互现,文史焕然,走笔恰到好处。在小说结构上,最明显的是辽代诗词的嵌入,包括萧观音的诗,耶律洪基的诗,乃至宋人的咏辽事诗,这些诗作的引入当然与史实和人物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自觉承袭了中国文学以诗证史、以史传诗的传统,从而使整个文本别开生面,可以说既是一部史传小说,也是一部诗传小说。不仅如此,《大辽诗后》的叙事,在结构上还具有全景性的特点,我觉得这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以萧观音的生平为情节主线,斜枝旁逸地串起了众多历史场景,其中既有军国大计、辽宋关系、兵变缘起、春水秋山、歌舞庆典、帝王威仪,也有地理山川、通婚嫁娶、佛道信仰、市井贸易、求医问药、物产民风,可谓林林总总,几乎说尽了 “辽朝的那些事儿”。小说从帝后写到平民,从契丹写到汉人,从懿州写到上京,从流亡写到信仰,从史证写到传奇,叙事的转换非常自然,嫉恨与复仇叠加,阴谋与爱情交会,整个叙述疏密有致,既有精细的描绘,也有旷简的写意和留白,其中间杂生动的比喻和浪漫的抒情,就如同边地草原上的野花,在平实质朴的叙述中摇曳生姿。
总之,长篇小说《大辽诗后》是况味别传的,小说的震撼力伴随着人物的命运感与历史的沧桑感,以及边地草原特有的人情味和风土感,给人留下了特殊的印象。我知道赵颖几年前有工业题材长篇《大矿山》问世,并拍成电视剧产生反响,现在突然又写辽代,而且写得很成功,这是出人意料的。特别是作者让一种悲剧精神贯穿整个叙事,这在近年的历史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赵颖对这一题材的选择和处理都很用心,这需要涉足荒僻和古远的勇气,也表现了她出色的感悟力和移情才能。契丹远去,诗后绝尘,但那种华夷同风的家国之思、向往文明的诗性智慧长存。而这部作为史传和诗传的长篇书写,也应该能为我们了解辽代的历史和历史的辽代,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