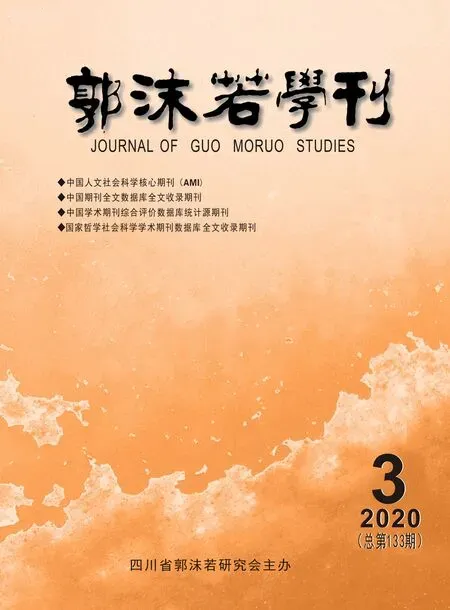天津《大公报》郭沫若研究资料综述
2020-11-17陆远霞
陆远霞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大公报》在天津先后有近40年的出版历史: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其宗旨为“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创办人为满洲正红旗人英敛之。1916年9月,安福系王郅隆接手《大公报》,由于内部人才流失、外部政府限制,加上日积月累的颓势和突发的战争,不得不于1925年11月27日停刊。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于1926年6月成立后,同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续刊第一天的报纸署号8316号,报头仍用《大公报》三字,由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于7月28日晚大举进攻天津,7月30日天津陷入敌手,《大公报》天津版苦苦挣扎四天后于8月5日停刊。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1日在天津复刊,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时停刊,后易名为《进步日报》于同年2月27日出版。①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114-124、175-177、230-231、284、325-329页。据查,天津《大公报》共发表与郭沫若有关的文章27篇,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这27篇资料进行研究综述。
一、围绕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争
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此书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一本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书贾言,该书销路颇广,青年学生购买是书者尤多,其在近代出版界之价值于此可见一斑。”①讯:《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5日第11版。不少人读了该书后,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天津《大公报》共发表7篇相关文章,查读秀学术搜索,仅有嵇文甫、素痴(张荫麟)两人的文章曾被收录或引用。笔者拟从八个方面介绍各自的主要观点。
(一)关于原始共产制的论争
郭沫若曾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是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作,由此观之,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在恩格斯和摩尔根的著作中都认为在私产没有之前存在共产制,郭沫若继承了二者的学说,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私产没有之前也有原始共产制。但是,张纯明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他提到在草昧时期,每个民族都会有各自的猎场,而这些猎场又往往会划分为一个个的小块儿,这些小块儿是私人所有的。且在渔猎社会里,个人所得的猎物就是个人的,虽然会分一些给酋长或者给老人,但那只不过是“习俗上的客气,不见得就是共产”。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里找不到郭沫若所举的关于原始共产的事实。素痴(张荫麟)从另一个角度质疑原始共产制的存在。郭沫若提出在卜辞和殷金中没有证据证明殷代有土地分割和货财及奴隶的私有,所以私产制在殷代未曾发生,当时应是共产的。素痴指出郭沫若的这种论证方法——“默证”有很大缺陷:“我们从现存的过去遗迹来推测过去的普遍情形,第一要注意这些遗迹所能代表过去的程度,违反了这个限度的推测只是幻想。”他认为郭沫若在现存的殷代龟契及金文中找不出土地分割和货财及奴隶私有的证据,就证明殷人的社会是原始共产社会的论断只是推想出来的,没有事实依据,焉知在未发现的龟契及金文中没有土地分割和货财及奴隶私有的证据?
由上可知,张纯明和素痴对于郭沫若的中国西周以前的社会是原始共产社会的观点是怀疑的。不过,讯却赞同郭沫若的观点:“他(郭沫若)在本书里主张中国西周以前的社会形态是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西周时代是奴隶制;春秋以后才是封建制。这在大体上郭先生的论断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可见在当时,郭沫若提出的西周以前的社会形态是原始共产社会这个论断在学界没有达成共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关于西周是否是奴隶社会的论争
郭沫若认为在封建社会以前必须经过奴隶社会,如果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就与社会进展的程序不合,因在氏族制崩溃以后,必须有一个奴隶制度的阶段,即国家生成的阶段。西周正与这个阶段相合,所以他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诗经》里面的材料最多,有《七月》《楚茨》《大田》《甫田》等。这些诗里都有关于农夫受苦和贵族享乐的描写,以《七月》最为突出:“农夫们一天到晚,周年四季的生活,这是不是奴隶呢。”根据这些诗里找到的证据郭沫若总结道:“总之当时的农民就是奴隶。这些奴隶平时不仅做农夫,还要做工事,供徭役。”张纯明和嵇文甫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虽然这些诗里虽然都体现了农奴的存在,但并不代表西周就是奴隶社会。张纯明认为:“以我们的眼光看来,那《七月》等诗所描写的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不是奴隶社会下之奴隶。”嵇文甫认为:“他所描写奴隶的种种情形都只可归之‘农奴’,并不见得是奴隶制的特征。”他们都例举了汉代的奴隶作为反证:“与其说西周是奴隶社会,还不如说西汉是奴隶社会为恰当。”“汉代大规模的使用奴隶不比周代更为明显吗?”并且,他们还批评了郭沫若机械地继承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一书当中关于奴隶社会的理论,而不考虑实际情形的行为。除此之外,嵇文甫就徭役这一点也进行了反驳。郭沫若认为西周徭役很繁重,给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这是压榨奴隶的表现,体现了西周奴隶制度的严酷。但是嵇文甫提出徭役繁重并不是西周一个朝代的特点,在秦始皇、隋炀帝、杜甫、白居易等时代,徭役同样繁重,但它们都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这又如何解释?
(三)关于封建社会形成时间的论争
张纯明和嵇文甫还对封建社会在秦时得以完成的观点提出质疑。嵇文甫提到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而不是完成,这在当时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中是达成共识的,郭沫若要推翻这个观点必须有充足的证据。郭沫若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潮上的反映》篇中论述东周时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分为三部分:一是宗教思想的动摇,二是社会关系的动摇,三是产业的发达。嵇文甫对这封建社会建立的三个证据都进行了批驳:第一,宗教思想的动摇与封建社会没有太大的关系,郭沫若在文中描写的不信天、不信祖宗、高扬人的价值等这些不是在讲封建社会,而是在讲欧洲近代思想史;第二,社会关系的动摇诸如阶级意识的觉醒、新有产者的勃兴等这些都是证明了封建社会的动摇而不是封建社会诞生的象征;第三,在产业的发达中,郭沫若提到工商业的发达,工商业的发达明明是破坏封建社会的,不可能促成封建社会。张纯明和文甫观点相似,这里就不再赘述。
(四)关于殷代是否是母系社会的论争
郭沫若认为殷代是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对此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其中最大的一个质疑点在于:殷代既然是母系社会,且郭沫若也曾经说过“母系的酋长多是女性”,所以殷代的继承方式应是“母女相承”,他在后面却说殷代帝王是“兄终弟及”,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的例子,这显然是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张纯明、嵇文甫和素痴都提出了批评。此外,他们还对郭沫若证明殷代是母系社会的一些证据提出批驳。张纯明和嵇文甫认为郭沫若虽然在甲骨文里找到了“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毓即后字”等证据,但是这只能说当时有母系的痕迹,不能证明当时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素痴则对郭沫若所举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予”的证据提出批评。郭沫若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古公)骑着马儿,沿着河流走来。走到岐山之下,便找到一位姓姜的女酋长,便做了她的丈夫。这不明明是母系社会吗?”素痴认为郭沫若直接把“姜女”写成“一位姓姜的女酋长”不符合实际,显得牵强附会,出人意表之外,这个论据不可靠。除了以上两方面之外,嵇文甫还提出了一个较新的论断:“郭先生断定殷朝尚在氏族社会之末期,这大概是不错的”;“母权制虽是氏族社会的主要特征,但当氏族社会的‘末期’,已为父权制所取而代之了”。嵇文甫认为殷代当时应是父系氏族,这与郭沫若的论断截然相反。
(五)关于亚血族群婚制度的论争
郭沫若提到亚血族群婚制度存在于殷代,但是他关于此举出的证据遭到了质疑。素痴总结郭沫若认为殷代有亚血族群婚制度的存在的三个证据:(1)卜辞中一祖配数妣的记录;(2)卜辞中有“多父”,“三父”之语,又有连举二父三父之名者;(3)商勾刀铭云:“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素痴认为,这三个证据并不十分准确,前一个证据可以用一夫多妻制度来解释,且如果是群婚制,为什么没有数祖配数妣的记录。后两个证据可以用“袭嫂制”来解释,并不一定就是亚血族群婚制。另,素痴还批评了郭沫若的亚血族群婚制度观点全袭自摩尔根,而摩尔根推断亚血族群婚制度的方法和结论已被人类学者所摒弃,已经不可靠。嵇文甫也认为郭沫若证明殷代亚血族群婚制的证据不充分:“最大的证据,不过是殷墟卜辞中‘多父多母’的记述,但是那也只能认为亚血族群婚制的遗习,而不足为当时还实际施行着亚血族群婚制的证明。”嵇文甫还提到了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摩尔根发现易洛魁人也有“多父多母”的现象,却不是实行的亚血族群婚制度,而是更先进的对偶婚。嵇文甫认为殷朝的情形和这相似,虽然有多父多母的称谓,但不是实行亚血族群婚制度。此外,讯也对亚血族群婚制存在的证据提出反对意见,他反对郭沫若用古代帝王的诞生来证明社会的初期是男女杂交或者亚血族群婚制度。他对郭沫若提出的“皇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的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的观点进行强烈反驳。讯举了汉高祖的祖母梦见赤鸟而生了他父亲,母亲梦见赤珠而生了他的例子进行反驳,如果帝王感天而生证明当时是野合的杂交或亚血族群婚制度的时代,那么汉代也是一个实行杂交或亚血族群婚制的社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讯认为,感生说的存在只是说明帝王是天的化身,借了一个女子的肉身来下凡,并不是说帝王的母亲跟人杂交,故不可知其父,感天而生和杂交或亚血族群婚之间并不是充分条件关系。
(六)关于舜、象共妻娥皇、女英问题的论争
南社成员潘蕙畴读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后,对郭沫若的一段话产生质疑,这段话是:“尧皇帝的两个女儿同嫁给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共妻这两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说的话,要‘二嫂使治朕栖’……所以舜与象是娥皇、女英的共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与象的分妻。”潘蕙畴认为《孟子》上记载象的这段话不是那么简单:“象所以说这话是在害了舜而不知没有害死时,想占有娥皇女英为妻时出的。”之后他又用了辩证法的观点去反驳这句话,他认为象与娥皇女英是夫妻,那么“治朕楼”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还要冠以“使”字;并且娥皇女英是舜与象的分妻,那么象为什么要称娥皇女英为“嫂”,这不合常理,所以象不是娥皇女英的公夫,他说郭沫若使用的是形而上的观察法。非白和仲和针对潘蕙畴的批评提出了批评,他们二人赞同郭沫若的说法。非白认为郭沫若是用这段话来证明舜时代是彭那鲁亚社会,至于《孟子》称象与娥皇女英为叔嫂关系,是为后人所隐蔽和修改过的,郭沫若对《孟子》上那段话并不相信,只是由《孟子》的传说进行一二推测。仲和举《楚辞·天问》篇上“眩弟并淫”来反驳潘蕙畴认为“二嫂使治朕楼”不可靠的观点,并且也说郭沫若的这段话是证明舜、象、娥皇、女英是混合的夫妇,与摩尔根的“彭那鲁亚”相吻合,说明各文明族的祖先都是经过血族结婚的;至于“使”字和“二嫂”二字,仅是形式上的称号和命令语;此外,仲和还提出郭沫若的结论引有两个例来佐证,潘蕙畴以为有一个可疑,便把整个的结论推翻是很不合理的。最后,非白和仲和共同批评了潘蕙畴只读导论,而不读全篇就妄自批评的行为。
(七)有关《易经》《易传》的论争
署名“讯”的作者对郭沫若考证的《易经》《易传》的著作年代和著作者提出疑问。根据郭沫若的研究,《易经》写于殷周之际,并且孔子研究过,《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孔门弟子所作。关于著作者,讯引用了钱玄同、顾颉刚、欧阳修和冯友兰的观点来做反证,他们都主张《易经》《易传》不是孔子或孔门弟子所作。关于著作年代,讯引用顾颉刚先生的观点:《易经》的著作年代是西周,且那时没有儒家,《易传》著作时代至早不过战国,认为顾颉刚的说法较为可信。
(八)有关殷周社会变迁原因的论争
素痴对郭沫若认为殷周社会变迁的基本原因是“铁耕”的新发明提出质疑,素痴认为铁耕在周初已经发明是没有证据的,且现存的铁耕的历史尚不出战国时代,用“铁耕”的发明来解释殷周社会变迁显得牵强。他认为殷周两代的社会变更可能是民族迁徙的原因,因为周在克殷以前文化程度和社会组织与同时代的殷不同:卜辞中所见殷代以牧畜为主要生产方式,而周是农业社会,且武王以前的周室没有殷室的兄终弟及的习惯。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此书在面世时存在着一些失误,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了:“我在一九三○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①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他创建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为研究古史开辟了一条大道:“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并且郭沫若后来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花了15年的时间对古代社会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研究,写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书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这种致力于学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二、对郭沫若历史剧的评介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剧作家,他创作了《屈原》《虎符》《孔雀胆》《棠棣之花》等脍炙人口的历史剧作,这些作品歌颂了历史上的仁人志士,表达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时代主题。天津《大公报》刊载了有关《孔雀胆》的一篇书评、两篇通讯,有关《虎符》的一篇通讯,五则广告。1947年10月8日唐轲发表的《〈孔雀胆〉》,高度评价了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孔雀胆》:“初读《孔雀胆》似乎只是一个男女之间争风吃醋的故事,然而当我们读完这一本书闭目深思,探究其中意义时候,就觉得意味深长了。”1947年11月9日发表的《〈孔雀胆〉二队定期公演》预告演剧二队“决定于二十一日起另上演《孔雀胆》”,1947年11月20日发表的《〈孔雀胆〉演剧二队今日预演》报道了演剧二队预演《孔雀胆》的情况:“定今日下午四时预演,招待本市各界”。1948年6月17日发表的《〈虎符〉祖国剧团今上演》介绍了《虎符》的故事梗概,认为该演出“为《岳飞》一剧后最豪华的演出”。在五则广告中,6月16日的广告题目为《祖国剧团、军剧一队合作〈虎符〉》,6月 17、18、19、20日的广告题目为《文化会堂公演〈虎符〉》。在这些广告中,除介绍演出者为贺镜清、编剧为郭沫若、导演为石岚外,还高度评价了该剧:“历史宫闱悲壮伟,旷世无俦千古悲剧”。
三、对郭沫若译作的评介
天津《大公报》发表评介郭沫若译作的文章一共两篇,一篇介绍《鲁拜集》,另一篇评论《浮士德》上部。天津《大公报》1948年6月14日第4版《〈鲁拜集〉新版》中提到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泰东书局),是根据英国诗人Fitzgerald的英译而转译的,而Fitzgerald的英译版本曾四易其稿,而且侧重于意译,在英国诗歌中是一部伪作。1928年张荫麟以笔名“素痴”对郭沫若译歌德的《浮士德》(上部)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对郭沫若译作批评主要有三点:第一,翻译匆促,用时很短,初译一暑假,改译仅仅十天;第二,这般大著作,初次介绍于国人,没有序引,没有关于作者的生平和原书的一些介绍,使读者对于此书没有足够的认识;第三,错误很多,这也是全文批评的重点。他提到:“适于友人案头见过译本一册,因取以原书较,其谬误荒唐,令人发嘘之处,几于无页无之。”如果写一本《郭译〈浮士德〉上部纠谬》,篇幅可与译本相较。在文章中他例举了郭沫若译作舞台上楔子两段的谬误13处,以见一斑。
四、有关郭沫若的其他文章
在天津《大公报》上对于郭沫若的生活情况的报道一共有9篇,横跨了1927年到1947年共20年的时间。1927年7月27日刊载了电通社2月25日电,主要内容为:“左派分子陈公博郭沫若”将以党代表身份“前赴南昌”。1928年12月16日刊载了12月15日福州专电:“闽省垣公安局同省党指委会职员,十二日晚八时在第一高中捕获共党嫌疑学生二十余人,闻有读郭沫若著作者,亦被逮捕。”在1934年9月18日刊载的《周作人谈留日印象》中,谈到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情况:郭沫若在日本研究考古问题及古文字问题,但是由于在日本沪川出版作品难得到酬金,并且日本出品物不能有大量收入,生活比较困窘。1936年11月2日报道了政委会查禁《沫若文集》的情况,查禁理由为:“内有两段文字,涉及古贤孟轲离婚问题,与孔夫子吃饭问题,政委会认为有侮慢之处”。1945年12月3日刊载了《“愿同声一呼反对内战”——傅作义长官致郭沫若等电》,该文首先交代了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来电的原因:“郭沫若罗隆基等十九日在渝召开‘反对内战’大会,发表宣言,消息传到此间后,傅作义司令长官,深有所感,特以‘愿同声一呼反对内战’为题,指点郭罗等”,然后刊登了电文的具体内容。1946年2月10日,陪都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民主建国会等二十余团体,定于晨九时在较场坝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却意外发生血案,李公朴、郭沫若等被打伤。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天津《大公报》接连报道了相关情况:2月11日以《陪都怪现象——铁棍打散民众集会李公朴郭沫若等数十人受伤警宪多人在场并未制止动武》为题报道了事情经过;2月12日以《郭沫若等被殴事件——政协代表一度集议推周恩来等谒蒋主席报告》为题报道了政协代表孙科、邵力子、周恩来、沈钧儒等于10日晚在民盟总部集议的情况:“最后协议,推周恩来,张君劢,陈启天,李烛尘往谒蒋主席,当面报告经过情形,由梁漱溟草函,请蒋主席约期往见”;2月13日以《郭沫若等被殴案政协代表请谒蒋主席》为题报道了张君劢、陈启天、周恩来等“请谒蒋主席”的情况,其中全文抄录了2月11日晨送给蒋介石函件的内容。1947年8月7日刊载的“本报上海通信”首先介绍了“郭沫若全家困居上海”的情况:“贫得难以聊生,由友人建议,卖字维持家用”,然后详细地罗列了大致的润格。
综上所述,天津《大公报》共发表郭沫若研究资料27篇,主要包括围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争、对郭沫若历史剧的评介、对郭沫若译作的评介等内容,这些研究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知道当时人们对郭沫若及其作品的评价、介绍。
附录:天津《大公报》郭沫若研究资料目录
1、《南昌总部添党代表陈公博或郭沫若》,天津《大公报》1927年2月27日第2版。
2、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译〈浮士德〉上部》,天津《大公报》1928年4月2日第9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3期。
3、《福州大捕学生——阔哉郭沫若读其书者被捕》,天津《大公报》1928年12月16日第2版。
4、讯:《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5、18日第11版《社会科学》第13、14期。
5、潘蕙畴:《读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致郭沫若书》,天津《大公报》1931年7月24日第11版《读者论坛》。
6、非白:《读了〈潘蕙畴先生致郭沫若书〉——关于舜与象共妻娥皇女英问题》,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2日第11版。
7、仲和:《读了〈读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致郭沫若书〉以后》,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7日第11版《读者论坛》。
8、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12日第10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96期。
9、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4日第8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
10、《创造十年(广告)》,天津《大公报》1932年 10月8日第1版,又载 9、10、14、15日第1版。
11、张纯明:《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8、15日第11版《经济周刊》第2、3期。
12、《周作人昨谈留日印象——日日人兼有游乐苦干精神收复失地仍待国人努力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感觉窘迫》,天津《大公报》1934年9月18日第4版。
13、《政委会查禁〈沫若文集〉认为有侮孔孟》,天津《大公报》1936年11月2日第6版。
14、《“愿同声一呼反对内战”——傅作义长官致郭沫若等电》,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3日第2版。
15、《陪都怪现象——铁棍打散民众集会李公朴郭沫若等数十人受伤警宪多人在场并未制止动武》,天津《大公报》1946年2月11日第2版。
16、《郭沫若等被殴事件——政协代表一度集议推周恩来等谒蒋主席报告》,天津《大公报》1946年2月12日第2版。
17、《郭沫若等被殴案政协代表请谒蒋主席》,天津《大公报》1946年2月13日第2版。
18、《郭沫若〈青铜时代〉已出版》,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3日第6版《大公园地》第143号“艺文往来”栏,标题为编者所加。
19、《郭沫若卖字困居上海难以维生》,天津《大公报》1947年8月7日第4版。
20、唐轲:《〈孔雀胆〉》,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 8日第 6版《文艺》新第31期。
21、《〈孔雀胆〉二队定期公演》,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9日第5版。
22、海生《《“祖国”剧团在建国东堂演出〈虎符〉成绩相当不》》,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19日第6版《游艺》“北平艺讯”栏,标题为编者所加。
23、《〈孔雀胆〉演剧二队今日预演》,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20日第5版。
24、《〈鲁拜集〉新版》,天津《大公报》1948年6月14日第4版《图书周刊》第53期“海外书讯”栏。
25、《祖国剧团、军剧一队合作〈虎符〉》(广告),天津《大公报》1948年6月16日第4版。
26、《〈虎符〉祖国剧团今上演》,天津《大公报》1948年6月17日第5版。
27、《文化会堂公演〈虎符〉》,天津《大公报》1948年6月17、19、20日第4版,6月1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