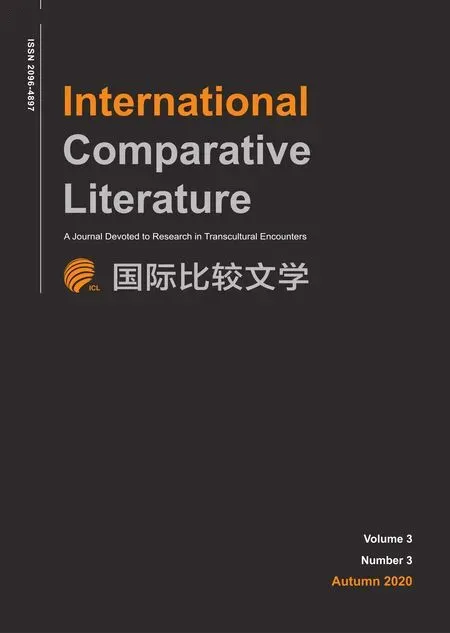法国知识空间中的《西游记》:从耶稣会士到泰奥多尔·帕威*
2020-11-17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引言:知识的获取
在《知识考古学》中,米歇尔·福柯这样定义知识(savoir):
话语实践有规律地产生了对于建立一门科学不可缺少的各种要素,但它们不一定能构成科学;我们将这些要素的集合称为知识。知识是我们在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而在此过程中话语实践也变得明确:知识是个由不同对象——无论它们能否获得科学的地位——构成的领域;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其中主体可以选取某一位置,以谈论他的话语涉及的对象;知识也是一个诸陈述或并联或从属的场域,在其中各种概念出现,被定义,被应用,发生变化;知识被话语所提供的诸多使用及适应的可能性定义。有的知识独立于科学,但没有知识不具有相应的话语实践;所有的话语实践都为它自己构造的知识所确定。1Michel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aris:Gallimard,1969),238—39.本文中如非特别标明,外语引文皆为笔者所译。
在如此定义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知识本身的空间性(领域、空间、场域),二是主体在知识空间中选取的位置。前者可以让我们发现各种知识间或毗邻或隔离、或联合或对抗的关系。后者则促使我们考察求知者观察的角度,因为角度不同,获取的知识也有所差异。此外,我们应该厘清使知识生产成为可能的诸多条件,这些条件是历史上实际发生且可以证实的。我们一方面应该清楚求知主体所选取的角度,另一方面也当注意到待认识的事物如何呈现在其眼前,如何与观察者的目光相遇。而这两者的相遇并非一直是平静而和谐的,它也可能伴随着惊奇、讶异和不安,乃至冲突。故而关于事物的知识并非是“无所偏私”的。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知识史和科学史研究,便如此着力于知识具体的产生过程,其研究范式分为两个方面:知识话语论视角关心不同学科间话语的衍生与流通、敌对与联合,历史社会视角研究武力的征服,知识机构的设立,王权与教权的支持等具体的事件,而这两者间界限甚为模糊。2这一方法的纲领详见于Stéphane Van Damme 于2015年为《科学知识史》第1卷所作的导言:«Un ancien régim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 (A Former Regime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in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I.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I.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Paris:Seuil,2015),20—40.
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处于如上描述的知识的角力中。首先在认知的主体(西方)与待认知的客体(中国)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这种张力一直存在于知识的形成与形式化过程中。如果以这个视角去研究《西游记》在法国19世纪的接受,首先要做的是揭示在法国关于《西游记》的知识产生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这就要追溯到西方现代世界的开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不久后,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颁布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新世界一分为二,西边归于卡斯蒂亚王国,东边归于葡萄牙王国。之后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而在葡萄牙王室庇护下的耶稣会的成立则可视为天主教对其回应之一。而依那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1491—1556)的同伴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1506—1552)意欲来中国传教,不得着陆,终客死于珠江口的沙川岛。此时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中西交流要等到晚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才渐变频繁。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耶稣会的权力中心由罗马转移到法国。3参见艾田蒲René Étiemble,L’Europe chinoise (The Chinese Europe),2 t.(Paris:Gallimard,1988—1989)。Antonella Romano 从科学史和全球史的角度研究了16~17世纪的中西交流情况,见其著作Impressions de Chine.L’Europe et l’englobement du monde (XVI e—XVII e siècle) (Impressions of China:Europ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16—17th Century]) (Paris:Fayard,2017) ;关于传教士的知识,见其文章 “Les savoirs de la mission”(Knowing the Mission),in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I,347—68.故而在18世纪,在法国陆续出版了两部恢宏巨作:《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curieuses et édifiantes,1702—1766,34卷),以及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以此为基础整理出的《中华帝国全志》(La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1735,4卷)。在这部耶稣会士撰写的中国百科全书里,潜藏着由法国国王和罗马教宗所代表的两种“求知的意志”,因为没有他们,该书的出版不可能实现。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教宗克莱芒十一世在1715年下令禁止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教。最后一位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于18世纪末逝世,中法文化交流由此暂时断绝。1814年,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席。在法国学术的体制化进程中,有关中国的人文知识的学科姗姗来迟,落后了致力发展自然知识的学院一百多年:研究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4法文作“histoire naturelle”,或依中国传统,取晋张华书名,译为“博物志”。此概念为罗马帝国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所创,拉丁文为“naturalis historia”,“naturalis”意为“自然的”,“historia”有两解,或作记事(志),或作历史。因为在18~19世纪,这个学科包含了历史的维度,所以这里译为“自然史”。的皇家药用植物园(Le Jardin royal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成立于1635年,研究物理和化学的皇家科学院(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皇家医学协会(La Société royale de la médecine)成立于1678年,而这些机构的成立都依赖于法国王权的庇护。另一方面由于18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削弱,人不再是上帝的神圣造物,进而成为了自然史的研究对象,进而衍化出了科学人种观。5关于科学人种论是如何建立黄色人种的理论,可参见Michael Keevak,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ter 2,“Taxonomies of Yellow:Linnaeus,Blumenbach,and the Making of a ‘Mongolian’ Ra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43—69.这一点最好的证明便是18世纪中叶自然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建立的自然分类法中将人包括了进去,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经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后,西方知识的生产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世纪末的大革命剥去了知识的王权外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历史的运作中,思想与知识不可能经历完全的断裂,它们总是与过去或多或少气脉相连。所以,为了描绘出西方知识的谱系,我们不但要关注基督教的精神史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而且也要关注欧洲王权的尘世争斗史。从这个角度看,知识的生产牵扯到了利益的分配。
即使我们在研究过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后,难以辨清其导致的后果,对其行为定性然后进行批评,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文化空间的描摹受限于权力之眼,无论后者隶属于教权或是皇权,无论它产生于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国家。正是如此的权力之眼构建出了18~19世纪之交的知识型(épistémè),6Michel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249—50.也就是说在这一时代的法国学者的思考方式和认识问题的整体角度。此外它还限定了《西游记》在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里的位置。
一、教宗与国王的荣光
在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16~17世纪之交的耶稣会士是如何生产出他们的中国知识的,以为研究19世纪初设立的知识机构作铺垫。7Paul Dem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Historical Overview of Sinological Studies in France),Tokyo,The Toho Gakkai,1966,n° 11:56—110.
1685年,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在一封信中如此表达了对于应康熙要求而远赴中国的“国王数学家”的期待:
我的神父,对于科学的求索并不值得您辛苦渡海,飘零异乡,远离祖国与亲友。规劝异教徒皈依并拯救灵魂的心愿驱使各位神父踏上漫长的旅程,我希望他们(国王数学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他们倘若不忙于宣扬福音,也可以多观察当地的人情事物,因为这是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缺乏的。8转引自吴蕙仪,WU Huiyi,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Les jésuites traducteurs de textes chinois et le renouvellement des connaissances européennes sur la Chine (1687—ca.1740) (Translating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Jesuit Translators of Chinese Texts and the Renewal of European Knowledge about China[1687—ca.1740]) (Paris:Honoré Champion,2017),373.
杜赫德写给路易十五的《致国王书》可视为对于柯尔贝尔信件的五十年后回应。该信被置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卷首:
在上一个世纪,我们见证了为了帮助和保护福音传播者,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和东方最伟大的皇帝之间的竞争。因为康熙皇帝表现出了对科学的无限热忱,传教士们非常容易接近皇帝本人,而且免受基督之名的敌人的侵犯。
在另外一方面,路易大帝(即路易十四)虽然日理万机,身处战局,仍旧放眼于亚洲尽头。他不但渴望着扩大耶稣基督的王国,而且希求能从其中获得促进科学进步的知识,因此他垂青于诸多他了解德行与能力的耶稣会士。在他们临行远赴中国之际,他赐予了他们“国王数学家”的荣耀头衔。他委托他们的部长,拨款供他们使用,处处给予他们方便。9Jean Baptiste Du Hald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Paris:Le Mercier,1735),iii—iv.在上述两段引文中,我们不难察觉是王权和教权驱动着耶稣会士远赴中国;而在他们的眼中,传教是首要的,搜集知识是次要的。而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的初衷只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信仰,虽然他们的动机到了以后会有所改变。而他们学习汉语则是为了检验孔夫子的语言能否忠实地传递天主的消息。
然而在明万历朝出版于金陵的《西游记》却从未入耶稣会士的法眼,从未在17和18世纪的西文文本中被提及。而由《西游记》成书历史,10有关这一点,详见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CAI Tieying,Xiyou ji de dansheng(The Birth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我们可推测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故事当于民间流传甚广,耶稣会士对其的忽视应是刻意为之。而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文学这一范畴内只介绍了诗歌和戏剧,而没有通俗小说。
二、学术体制中的东方学
在法国文化知识界,《西游记》首次登场于学术“场域”(champ)11我们在这里以布迪厄的社会学意义使用该词。中。在19世纪中叶法国语文学(philologie)界享有巨大影响力的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在1868年以法兰西公学院为例子,如此描述学术场:
实用的围栏会成为科学的障碍;为了结出硕果,科学研究的首要要求就是自由。我们应当在保存有既得知识的学校旁边设立独立的教席,它们允许人教授正在成型的科学门类,而不是现成的学术科目。这样的话,学术的原创性即使不是一般教学机构的必要要求,也能得到这里得到保证。12Ernest Renan,Questions contemporaines (Contemporary Questions)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1868),144—45.
勒南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兰西公学院的情况:学术的自由与讲席的独立得到了保证。此外,法兰西公学院于1814年同时设立了汉学教席与梵语教席也证明机构自身的学科创新精神。或许勒南的断言还有待更仔细地检验,然后不可置疑的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体制化,享有它的自主独立,而不再处于“科学与知识的旧制度”13该表述借鉴于法国科学知识史家Stéphane Van Damme,见同作者上文所引文章。在这里,“旧制度”是对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概念在于科学史领域的移用,具体指法国大革命未发生前,知识领域里各个学科没有分化,多有叠合的情况,以及如此的知识场域包含的权力关系。中。涉及遥远世界的学术话语(也就是说梵语研究、埃及学研究、西亚文明研究等学科)的内在动力在语文学领域里逐渐演变。语文学研究首先成型于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德国,其领军人物有施莱格尔兄弟(Friedrich et Auguste Schlegel)和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以及后来的格林兄弟(Jacob et Wilhelm Grimm)和弗兰兹·波普(Franz Bopp),后传到法国,14关于这一点,参见Christophe Charle and Jacques Verger,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XII e—XXI e siècl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12th—21st Centuries) (Paris:PUF,2012),84.其特点是强调语言的自治性;而语文学家则痴迷于从对新近破解的古老语言的研究中解释世界的本源。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正因为人类从时间肇始开始言说,这一切关于语言的知识将会在深厚的人类普世历史中汇集起来。15Yves Chevrel,Lieven D’hulst and Christine Lombez eds.,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XIX e siècle(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in the French Language,19th Century) (Paris:Verdier,2012),chapitre III.«Une Antiquité nouvelle» (A New Antiquity),section A.就在此时,开始了“东方文艺复兴运动”(La Reconnaissance orientale)。16这一表达出自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在1842年出版的《论诸宗教的真谛》(Du génie des religions)。意大利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发掘出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而欧洲十九世纪的文艺复兴代表了东方学研究的风气,这一称谓由此得来。
法国第一批学院汉学家学习中文的方式与以前的耶稣会士完全不同。因为这时的中法联系已经被切断了,他们只能在存有传教士带回欧洲的中国书籍的图书馆里获取相关的知识。这一情况持续到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7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XIX e siècle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in the French Language,19th Century),205.在前人的学问基础上,新的中国语文学成立了,这个新学科关注的不仅是知识的获得,还有知识的传授。18Ibid.,202.而它的体制据点有两种,一是教学机构:法兰西公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二是学者协会,也就是亚细亚协会(La Société asiatique)。19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History of Universities),81.汉学知识的体制化保证了自身的双重自治性,既因为它不再受外界权威(国王和教宗)的影响与胁迫,又因为它失去了和中国的联系,诞生于保存在欧洲的文本中。
三、语文学:在精神哲学和自然哲学之间
那个时期的语文学的学科发展情况如何呢?首位体制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在1815年于法兰西公学院的就职第一课中感谢了王权的庇护(此时正处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强调了与他国相比,法国人文知识研究的优越性。他同时也陈述了19世纪汉学研究与18世纪的哲学和自然思想的一脉相承:
(在汉学研究中存在着)对于形而上学家而言极大的乐趣:在分析《易经》和《书经》时发现特别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它们不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凭借直觉来理解周公和孔子的伦理;一言以蔽之,在辨识出人类理性的第一步的同时,在与人类理性意外相逢的同时,实现布封和孔狄亚克的愿望!20Jean-Pierre Abel Rémusat,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 ;précédé du Discours prononcé à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ce Cours,dans l’une des Salles du Collége royal de France,le 16 janvier 1815 (Course Program of Chinese and Tartar-Manch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receded by th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ourse,in One of the Hal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France,January 16,1815) (Paris:Charles,1815),21.在这里,自然学家布封(Georges Leclerc de Buffon,1707—1788)和哲学家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4—1780)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布封在他的《自然史》(1749)第2卷《论人的本性》中提到了精神、思想和语言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把人和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21Buffon,“De la nature de l’homme”(Of the Nature of Man),in Histoire naturelle (Natural History),t.2 (Paris:L’Imprimerie royale,1749),429—44.孔狄亚克在他的《人类知识起源论》(Traité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1746)里特别提到了中文,他认为欧洲语言里所丧失原初语言的性质,中文将其保留了下来,例如用同词异调来表达不同的观念。22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Essay on the Origin of Human Knowledge) (Paris:Vrin,2014),204.18世纪欧洲知识型给19世纪语文学思想打下了基础,有关前者,参见张西平:《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2卷第3期,第411—427页。[ZHANG Xipin,“Zhongguo wenhua de shijiexing yiyi—yi qimengsixiang yu zhongguowenhua guanxi wei shijiao”(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Culture),Guoji bijiao wenxu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no.3 (2019):411—27.]故而这时指导汉学研究思想的,是通过语言对于人类本源的探寻。
1832年,雷慕沙逝世,弟子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接过了他的法兰西公学院教席。同年梵语教席也发生了更替,新选上的教授欧仁·布尔努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3)在就职演说里如此说道:“没有哲学与历史,就没有真正的语文学。对于语言运行的分析是一门有关观察的科学;如果它不是人类精神的科学,它至少是研究人类精神最让人吃惊的能力的科学,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人类精神就不可能存在。”23Eugène Bournouf,“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sanscrite”(Sanskrit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Review of the Two Worlds),1er février 1833 (February 1,1833).
虽然汉语语文学和梵语语文学术业有专攻,但是两者为同一指导原则所统领,这一原则就是展现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哲学,其代表为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1743—1794)于1795年出版的遗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该书如是评价亚洲诸文明:
在这些辽阔的帝国里,人类精神沦陷在无知和偏见中,与可耻的谦卑联系在了一起;许久以来,这些帝国断断续续的存在使亚细亚丧失了它的荣光。只有在这些帝国的人民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的文明与如此的堕落共存。而生活在地球其他(与作者相对而言)地方的人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他们给我们描绘出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景象。24Nicolas de Condorcet,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Paris:Flammarion,1988),120.
下文我们可以见到在语文学学科里上述历史哲学存在的痕迹。直到1878年,情况仍未改变,勒南给亚细亚协会所做的年度报告便是很好的证明:
希腊与罗马的文学一直被用来教育年轻一代,借此培养他们的品味和风格。中世纪也于现代的我们有很大的教益。但以人类精神史家的角度来看,东方对我们的教益更大,因为它保存了万物的本源。由于和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相比,科学在东方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它留给研究者许多有待发现的事物。然而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一种能够看透表面而直接的学术成果的哲学精神。25Ernest Renan,“Rapport sur les travaux du conseil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Report on the Works of the Board of the Asian Society),Journal asiatiqu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7e série,tome 12,1878:15.关于勒南与东方学之间的关系,参见Edward W.Said,Orien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123—48.
但是这里的东方似乎并不包括中国,它指的是近东一带,也就是印欧人的东方。勒南在著作《论语言的本源》(De l’origine du langage,1858)中如此评论他的东方:
与闪米特语言相反的是,对于真理的深刻的、独立的、勇敢的、(概言之)哲学的追寻似乎为印欧人种所共享。印欧人的足迹从印度深处发端,远至欧洲西北尽头,从遥远的古代直到现代一直在尝试着解释神、人类和世界,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遵循理性发展法则的思想体系,展示出了不同的历史进度。同理,这个家族的各种语言似乎是由抽象的形而上学法则创造的。
在高度赞扬印欧文明之后,他话锋一转,这样评价中国文化:
中文的结构没有组织,不够完备,它难道不是中国人种精神和心理的枯燥特征的形象体现吗?中文足以满足日常使用、手艺技术和轻浮的劣质文学的需求,它表达的哲学不过是实用精神的精致而不够高尚的表达;中文其实排斥我们(西方人)意义上的一切哲学,一切科学,一切宗教。上帝之名不存在于中国……26Ernest Renan,De l’origine du langage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in Œuvres complètes (Complete Works),t.VIII(Paris:Calmann-Lévy,1958),98—99.转引自谢和耐(Jacques Gernet),La Raison des choses.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de Wang Fuzhi (1619—1692) (The Reason of Things:Essays on Philosophy of Wang Fuzhi[1619—1692]) (Paris:Gallimard,2005),46—47.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法国语文学知识空间的构成,它的结构其实是由人种划分的,印欧人种(雅利安人)最受赞扬,而闪族人(犹太人)与之相对,而亚洲人种实际上处于边缘位置。这就是19世纪法国知识界流行的科学人种论(le racialisme scientifique)。27关于此等论述,可参见Gabriel Bergounioux,“‘Aryen,’ ‘indo-européen,’ ‘sémite’ dans l’université française(1850—1914)”(“Aryan,” “Indo-European,” “Semitic”in the French University[1850—1914]),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 (History,Epistemology,Language),tome 18,fascicule 1,1996.La linguistique de l’hébreu et des langues juives(The Linguistics of Hebrew and Jewish Languages):109—26.对于中国文化,19世纪的语文学者们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如雷慕沙一般持肯定态度,要么如勒南彻底地否定。无论肯定与否,汉学知识实际上和有关“本源”的神学思想紧密相连,正如上文所展示的。而当时汉学的发展程度,我们可以从儒莲1842年的论断中窥得一斑:“我们对于孔夫子语言的研究在最近得到了如此进步,乃至于对一本汉文书的法语翻译对熟练的人来说显得如此轻松,如同将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书翻译成法语一般。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现代的文章,例如小说、故事和喜剧。”28Stanislas Julien,Simple Exposé d’un fait honorable odieusement dénaturé dans un libelle récent de M.Pauthier(Explanatory Note on an Honorable Deed Hideously Distorted in a Recent Libel against Mr.Pauthier)(Paris:Benjamin Duprat,1842),35.
四、法国知识空间中的《西游记》
正是在如此的语文学背景下,同时为梵文学者和汉学家的泰奥多尔·帕威(Théodore Pavie,1811—1896)给出了第一个《西游记》节选的汉文翻译,它被收录于题献给儒莲的《民俗故事选》(Choix de contes et nouvelles,1839)。帕威在法兰西公学院在1835—1839年间随欧仁·布尔努夫学习梵语;在后者死后,于1853—1857年间,他担任了法兰西公学院的代课老师,此时他的汉语老师儒莲也会去听他的梵语课29Alexis Crosnier,Théodore Pavie,le voyageur,le professeur,l’écrivain,l’homme et le chrétien (Théodore Pavie,the Traveller,the Teacher,the Writer,and the Christian Man) (Angers:Lachèse,1897),49.。而他作为亚细亚协会的成员,也参与了《两世界评论》(La Revue des deux mondes)和《亚细亚学报》(LeJournal asiatique)的审阅工作。故而他可以说是一位体制内的语文学学者。不容忽视的是,他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正是他的信仰指导了他对语言的研究,因为他在给一位亲戚的信中写道:
信仰与宗教仿佛姐妹,如语言一般:它们都是由原初的启示衍生出来的;并且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科学发现虽然正确,但它们带来的哲学判断却是错的。科学越是自以为削弱了宗教原则,实际上越是使它牢不可破。这种我们每天见证的生命原则的统一,难道不是越来越明显的神的能力的证明吗?神的能力赋予万物灵魂,通晓一切,用祂的话语丰饶万物。30Lettre à M.Eusèbe Pavie (Letter to M.Eusèbe Pavie),16 mars 1862,citée in ibid.,116.
因此帕威用普世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虽然中国人不太重视这些末流的“民俗故事”,他的选集所收录的文本在他看来具有两种特别意义,一是普世意义,因为构成了世界文学的浩瀚文库,二是民族意义,因为给出了对于中华文明的启发性描述。
中国人即使在写作最为琐屑的作品时,总是从一个历史事件,一个传说,或是三教的某个教义中汲取灵感。他们的小说集子如此繁多,如此丰富,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成型,也没有作者署名,但是仍然历经几个世纪流传至今。所以这些中国故事集完全可以和同种文类的匿名文集相提并论。这些文集,无论其文体是散文还是韵文,不但为所有民族所共享,也是展现书写它们的人民的风俗和信仰的忠实而刺激的画卷。而为了给读者提供丰富的风俗面貌,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童话故事的简易而精致的文风,我们选取的文本有着不同的来源……31Théodore Pavie,Choix de contes et nouvelles (Selections of Fairy Tales and Short Stories) (Paris:Benjamin Duprat,1839),II.
对于《民俗故事选》中的《西游记》选段,他作出了如下解释:
我们从佛教小说《西游记》(“西”在和尚眼中指代印度)中,抽取了两个片段:“江流僧”和“斩龙王”。在两个该小说的不同版本中,它们构成了第九回的内容。而小说本身由于太过冗长与琐屑,难以全文译出,但是它包含了丰富的地理细节和惊奇冒险。不幸的是,兵工厂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32该图书馆坐落于巴黎旧时兵工厂旁,因此得名,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分馆之一。所存的版本损坏过于严重。33Choix de contes et nouvelles (Selections of Fairy Tales and Short Stories), II—III.然而帕威所谓的《西游记》的佛教性质当成问题。
帕威在这里提到的两个版本是清朝流通甚广的道士陈士斌撰写的《西游真诠》,与另外一本题为《西游记》的版本。帕威拥有的《西游真诠》为儒莲所赠,而上文所提的《西游记》藏于兵工厂图书馆。34关于儒莲赠书,见Journal asiatiqu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57,cinquième série,tome IX:366,n.2.查阅汉学家古郎(Maurice Courant)于20世纪初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拟的中文书目录可推知,以上两个版本是《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和《金圣叹加评西游真诠》,前者于1661—1665年间进入馆藏。35Maurice Courant,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japonais,coréens,etc.(Catalog of Chinese,Japanese,and Korean Books,etc.),t.1 (Paris:Ernest Leroux,1902),401.法国国家图书馆在线资源: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209140j/f410.item,[May 20,2020].
帕威所录两段《西游记》故事一叙陈光蕊遭水贼杀害,其妻流子(玄奘)于河,为僧人所救,抚育成人,描绘出了中国古时关于士人、贼盗和僧侣的民情;二叙龙王违抗天条,魏征奉旨斩龙,唐太宗入冥府,刻画了中国帝王将相的情貌和信奉龙王的民俗。两者互为补充,提供了帕威所说的关于中国“人民的风俗和信仰的忠实而刺激的画卷”。其实如此将中国小说视为风情画卷的传统实为雷慕沙所建立,他在1826年翻译的《玉娇梨》前言中便强调中国小说并非想象的产物,而是风俗人情的历史见证。36Jean-Pierre Abel Rémusat,«Préface» à Iu-Kiao-Li,ou les deux cousines ;roman chinois (“Preface” to The Two Fair Cousins:A Chinese Novel),t.1 (Paris:Moutardier,1826),6—9.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个时候的汉学家并没有对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故事给予重视。
1857年,帕威在隶属于亚细亚协会的《亚细亚学报》连续刊登两篇文章,总标题为《对中国佛教小说〈西游真诠〉的研究》。37Théodore Pavie,“Études sur le Sy-Yéou-Tchin-Tsuen,roman bouddhique chinois”(Studies on Sy-Yeou-Tchin-Tsuen,a Chinese Buddhist Novel),Journal asiatiqu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57,cinquième série,t.IX:357—92 ;et t.X:308—74.与之前的《民俗故事选》不同的是,这是一篇学术文章,符合语文学研究的规范,流通于当时东方学知识的体制之中,一般读者难以见到。这也是《西游记》在西方第一篇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在简要介绍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背景后,帕威给出了带有注解以及个人评论的《西游记》前七回翻译。在他所撰写的导言中,我们不难看到科学人种论的影子:
(在该小说中)我们可以处处发现为中国精神所阐述和修改的印度观念。在赋有宗教本质的雅利安人民身上,(形而上的)超自然事物领导着诗歌和哲学;相反地,很早便熟悉实践生活具体细节的中国人,则倾向于奇情异想。奇异之于超自然,便如同迷信之于宗教情感。前者总是能吸引开始衰老的社会。38Ibid.,t.IX:357.
这段话描述了印欧人种(印度人、雅利安人)与中国人种的对立:在天主教徒帕威眼里,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高于中国人的世俗迷信生活,中国社会是“开始衰老的社会”。帕威接着简要介绍了中国三教。他提及了儒家经典《左传》中的卜占记录(左丘明被他解释成了一位博士兼魔术师),道教《太上感应篇》里的善恶报应论(该书当时已被儒莲翻译),以及沦为迷信的汉化佛教。他从这三者提取出了信仰和巫术的共同元素,以便“简要地解释——至少在古籍中——起初刻板而重形式的中国人民如何(在现在)犯下了想象力过剩的罪过”。39Ibid.,t.IX:365.接下来,他如此形容《西游记》:
《西游真诠》(原文此为中文标题法语音译),也就是说西方游历记事(即标题意译,然而刻意忽略了“真诠”二字),是一篇有关传奇僧人玄奘为了寻求佛教经典,在锡兰岛游历的奇幻故事。尽管小说的想象成分远远多于现实成分,事实上其作者的深意在于教诲民众。40Ibid.,t.IX:366.
在这里《民俗故事选》侧重的两个主题——信仰的想象和道德的教化——再度出现了。然而在文章里,帕威又提出了理解小说的第三个维度:神话学理论。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他所结识的神话学家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的影响。在他的介绍与评论中,帕威用神话学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解读《西游记》,意图贯通希腊、罗马和中国文化。他作了如下粗略的对比:开天辟地的盘古和《摩奴法典》中的国王,孙悟空和普罗米修斯,琼浆玉液和希腊诸神的饮料,不一而足。所以在这里,帕威的解读角度从风俗志转换成了神话学。
帕威给出的翻译并不详尽,因为有所缩略和删减。而且出于当时文本材料缺少的历史性局限,他的翻译在今人眼里有颇多可供商榷之处。然而他认真翻译的态度,和为之做出的努力是值得钦佩的。此外他也没有忽视陈士斌对于《西游记》做出的基于内丹修炼的解读,并将其解释给欧洲学界,或许是这一点加强了他对于中国人迷信的印象。此外他也察觉到了佛教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但同时也强调了印度佛教汉化时,由小乘转为大乘的堕落。
小结:辉煌的文明画卷
那么,在法国19世纪的人文知识空间里,《西游记》究竟被安置在何处呢?我们不必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姑且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时期法国的知识型是如何形成的。此时,耶稣会时代的国王和教宗早已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大革命后学术机构催生出的绝对话语,这话语寻求着本源,在我们眼前缓缓地、谨慎地铺开了关于诸多遥远的古文明的宏伟画卷。这画卷阐释了精神的历史和人类的进步。但是,研究他人的欧洲文明和被欧洲人研究的东方文明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41Walter D.Mignolo,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Coloniality,Subaltern Knowledges,and Border Thinking(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304.语文学家发掘出古老文明的遗迹,解读起源的谜团,以描摹出人类精神的发展;而同时期的自然学家,譬如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醉心于研究古生物化石,以勾勒出物种的进化。在这个时代,关于人类的知识赶上了关于自然的知识的步伐,并暗中结下同盟,42关于19世纪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相互影响,参见Raymond Schwab,La Renaissance orientale (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Paris:Payot,1950,rééd.,2014),“Parallélisme entre la linguistique et la biologie”(A Parallel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Biology),415—20.提出了令人心神荡漾的历史进化论。而关于人的自然知识被移植到了人文学科,自然的不同解释了文化的差异,继而发展出了科学人种观。
在时间的维度上,《西游记》没有解释人类的进步;在空间的维度上,《西游记》的创作者不是虔信宗教的印欧人,而是实际而迷信的中国人。在如此的前提下,《西游记》不能道出关于人的真理,而只能是对于中国风俗人情的见证;对它的了解或许是学者博闻强识的标志,与其好奇心的满足。虽然帕威提出的神话学解释试图把《西游记》嵌入印欧宗教的拼图中,但是他的研究终为历史的尘埃所埋没。而事实上,19世纪的法国普世主义(universaliste)的知识型依然继承了天主教的遗产:从词源学上来说,“catholique”43“天主教”一词是耶稣会士对罗马大公教的翻译,而“基督教”一词则为英国传教士对新教的翻译。意味着普世的(universel)。经历了启蒙运动后,到了19世纪,法兰西思想从天主教精神变成了到侧重历史进步论和科学人种论的普世主义;44法国语文学领军人物勒南即被尼采视为天主教的代表,见《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第2节。而在此背景下,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毫无疑问地处于欧洲知识空间的边缘。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Abel Rémusat,Jean-Pierre.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précédé du Discours prononcé à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ce Cours,dans l’une des Salles du Collége royal de France,le 16 janvier1815(Course Program of Chinese and Tartar-Manch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receded by th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ourse,in One of the Hal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France,January 16,1815).Paris:Charles,1815.
——.Iu-Kiao-Li,ou les deux cousines;roman chinois(The Two Fair Cousins:A Chinese Novel).Paris:Moutardier,1826.
Bergounioux,Gabriel.“‘Aryen,’ ‘indo-européen,’ ‘sémite’ dans l’université française (1850—1914)”(“Aryan,” “Indo-European,”and the“Semitic”in the French University[1850—1914]).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History,Epistemology,Language),tome 18,fascicule 1,1996.La linguistique de l’hébreu et des langues juives(The Linguistics of Hebrew and Jewish Languages):109—126.
Bournouf,Eugène.“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sanscrite”(Sanskrit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a Revue des Deux Mondes(Review of the Two Worlds),1erfévrier 1833 (February 1,1833).
Buffon,Georges Leclerc de.Histoire naturelle(Natural History),t.2.Paris:L’Imprimerie royale,1749.
Charle,Christophe and Jacques Verger.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XIIe—XXIesiècle(History of Universities,12th—21st Centuries).Paris:PUF,2012.
Chevrel,Yves,Lieven D’hulst and Christine Lombez,eds.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XIXesiècle(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in the French Language,19th Century).Paris:Verdier,2012.
Condillac,Étienne Bonnot de.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Essay on the Origin of Human Knowledge).Paris:Vrin,2014.
Condorcet,Nicolas de.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Paris:Flammarion,1988.
Courant,Maurice.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japonais,coréens,etc(Catalog of Chinese,Japanese,and Korean Books,etc.).Paris:Ernest Leroux,1902.
Crosnier,Alexis.Théodore Pavie,le voyageur,le professeur,l’écrivain,l’homme et le chrétien(Théodore Pavie,the Traveller,the Teacher,the Writer,and the Christian Man).Angers:Lachèse,1897.
Demiéville,Paul.“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Historical Overview of Sinological Studies in France).Tokyo,The Toho Gakkai,1966,n° 11:56—110.
Du Halde,Jean Baptist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Paris:Le Mercier,1735.
Étiemble,René.L’Europe chinoise(The Chinese Europe),2 t.Paris:Gallimard,1988—1989.
Foucault,Michel.L’Archéologie du savoir(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ris:Gallimard,1969.
Julien,Stanislas.Simple Exposé d’un fait honorable odieusement dénaturé dans un libelle récent de M.Pauthier(Explanatory Note on an Honorable Deed Hideously Distorted in a Recent Libel against Mr.Pauthier).Paris:Benjamin Duprat,1842.
Keevak,Michael.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Mignolo,Walter D.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Coloniality,Subaltern Knowledges,And Border Thinking.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Pavie,Théodore.Choix de contes et nouvelles(Selections of Fairy Tales and Short Stories).Paris:Benjamin Duprat,1839.
——.“Études sur leSy-Yéou-Tchin-Tsuen,roman bouddhique chinois”(Studies onSy-Yeou-Tchin-Tsuen,a Chinese Buddhist Novel).Journal asiatiqu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57,cinquième série,t.IX:357—392 ;et t.X:308—374.
Renan,Ernest.Questions contemporaines(Contemporary Questions).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1868.
——.“Rapport sur les travaux du conseil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Report on the Works of the Board of the Asian Society).Journal asiatiqu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7esérie,tome 12,1878.
——.De l’origine du langage(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InŒuvres complètes(Complete Works),t.VIII.Paris:Calmann-Lévy,1958.
Romano,Antonella.Impressions de Chine.L’Europe et l’englobement du monde (XVIe—XVIIesiècle)(Impressions of China:Europ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16—17th Century]).Paris:Fayard,2017.
Said,Edward W.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
Schwab,Raymond.La Renaissance orientale(The Oriental Renaissance).Paris:Payot,2014.
Van Damme,Stéphane.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I.De la Renaissance auxLumières(Hist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I.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Paris:Seuil,2015.
WU Huiyi.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siècle.Les jésuites traducteurs de textes chinois et le renouvellement des connaissances européennes sur la Chine (1687—ca.1740)(Translating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Jesuit Translators of Chinese Texts and the Renewal of European Knowledge about China[1687—ca.1740]).Paris:Honoré Champion,2017.
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CAI Tieying.Xiyou ji de dansheng(The Birth of theJourney to the West).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
张西平:《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2卷第3期,第411—427页。
[ZHANG Xiping.“Zhongguo wenhua de shijiexing yiyi—yi qimengsixiang yu zhongguo wenhua guanxi wei shijiao”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Culture).Guoji bijiaowenxue(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no.3 (2019):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