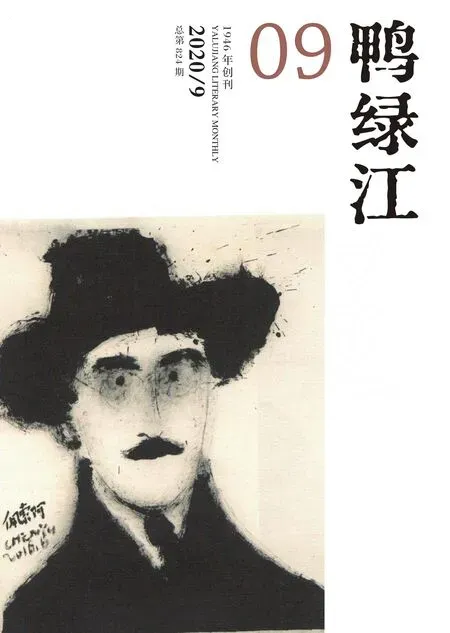天真汉与好故事(评论)
——读梁鼐的《哈布特格与公牛角》
2020-11-17曹霞
曹 霞
一个古董商人,骑着一匹黑色的骡子,在辽西大地上像幽灵似的游荡,在密匝的村庄和广袤的原野留下了重重的足迹。小说一开篇,梁鼐就准确地摁下了“在路上”的叙事枢纽,并让小说一直在漂泊、隐秘、魅惑的质感中滑行,让主人公不断遭遇意外、遭遇故事,直到最后与自己的使命劈面相逢。这样的气质不难使我们往远处想到欧洲的流浪汉小说,往近处则是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格非的《锦瑟》,洪峰的《极地之侧》……
找到《哈布特格与公牛角》所受的叙事影响并不难,它几乎带有一眼可被辨认的“先锋”痕迹。但是,在距离中国先锋文学三十年的今天,谁还要在先锋的形式里打转,将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实验当作目的,那显然并非良策。梁鼐当然志不在此。于是,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一种奇特而有趣的身份“错位”:古董商是一个有名的憨货。他很少做成生意,骡子背上的褡裢里经常空空如也,但他从不感到羞愧和焦虑,反而兴致勃勃地和人们拉呱、调笑、聊天,仿佛他的目的是收集话语,而非收集古董。
一个不以挣钱为目的的可疑的古董商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小说家很快就慷慨大方地向我们抛出了答案。商人在行进途中遇到了一位老妇人,那是他死去母亲的幻影。她不断向他重复着临终前的遗嘱:寻找父亲。商人也向着虚空重复当初的承诺:找不到父亲,决不归乡。二十五年前,父亲杨文生带着母亲做的葱油饼和家里所有的积蓄,与朋友罗喜来一起去内蒙贩牛,从此下落不明,踪影全无。为了尽快打听到父亲的下落,杨文生的儿子将自己扮作古董商人,走街串巷,搭讪闲聊。
综上所述,你可以将这个小说称为“寻父记”。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哈布特格与公牛角》的任务不是设置关于古董的谜语和解谜,它另有目的。我们的好奇心被高高挑起:商人怎样去寻找父亲?他最后有没有找到父亲?找不到如何?找到了又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关涉生命、血缘和伦理的困境。
在此,我们不妨略微将话题岔开,去看看梁鼐另外两篇小说《低级趣味》和《少年宝音的心事》。这两篇小说都以聪明调皮的少年为主人公。《低级趣味》在非正常的家庭关系和纠葛之外,庄重而令人忍俊不禁地开启了梁大平的成长之旅。《少年宝音的心事》通过宝音为聋哑妹妹萨仁“偷狗”的风波,牵连起广阔深厚的亲情,以及身处乌拉山深处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奇遇”。不难发现,这两篇小说除了主人公的年龄相似之外,还共有着精神上水晶般的纯粹:一种天真的执着,一种惊奇的发现,以及一份庄严的承诺。不独哥哥对妹妹和奶奶有所承诺,就连奶奶养大的那头名叫格日乐的熊也信守承诺。在一家子遭到狼群包围时,格日乐如约而至,用小山般的身体保卫恩人和亲人。
我们完全可以聪明地指出,梁鼐是个“笨”作家。他不厌其烦、靡费笔墨所书写的,无非是一个“信”字。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信”。我们信速度,信科技,信流量,信天方夜谭般的财富奇迹,唯独对于人性中最基本的、文化中最底线的那个道义之“信”、人伦之“信”失去了信任。但梁鼐仿佛与我们这个金光闪闪的时代绝缘,或者说,他即便看到了我们的那些“信”,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这样的“信”对我们来说是奇迹,对他来说却是常识。人间如此艰难多舛,造物主的恩典只够覆盖极少数人,但是,这完全不能动摇和侵蚀他的信念。
于是,梁鼐单纯、执着而坚韧地信着。在此,我们可以在心理学和行为实践的意义上将古董商人看作是长大后的宝音。他信守对母亲的承诺,风餐露宿,浪迹辽西。可以想象,如果他一直找不到父亲,他就会一直找下去。这种“重然诺”的特质并非仅仅是道德修为,它更多地来自与生俱来的天真、诚实、豁达和自我修复的力量。可以说,天真是一种天赋,而非后天习得。
小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梁鼐和他笔下的古董商人一样,都是可爱的天真汉。他们大规模地动用生命的权利,只为履行一个答应(或许会有人说,天哪,这真是生命的浪费)。小说的魅力还来自于另一重力量:好故事。作者借用了先锋小说迷宫叙事的外壳,通过罗喜来之口讲了关于杨文生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内容截然不同,在终极指向上相互矛盾。这种自我消解的叙事方式也让人想到马原、余华、孙甘露的元小说、互文本等实验手法,但它们在叙事目的上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第一个故事是杨文生和罗喜来到了内蒙,两人均为吉日嘎的妻子敖登动了心。罗喜来信守自己定下的行规,不与做生意的人家的妻子有瓜葛。结果是杨文生与敖登互生情愫。敖登送了杨文生一个自己做的荷包做定情物,蒙古语叫做“哈布特格”。吉日嘎发现后非常愤怒,约定以摔跤来确定奥登的去向。杨文生毫不畏惧,接受了这场必输的挑战,差点被摔死。在罗喜来的帮助下,这对有情人骑马逃往蒙古边境,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关于“爱情”与“真情”的故事。
在得知商人是杨文生的儿子、此行就是来寻找父亲时,罗喜来立即推翻了自己讲的这个故事,又另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到阜新低价贩到了一头凶猛的公牛,准备赶往一百里外的屠夫家卖个好价钱。公牛不肯往前走,罗喜来把它抽得皮开肉绽。公牛发起了最后的反抗,杨文生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住了公牛的进攻,被血肉模糊地挂在了公牛角上。罗喜来感到无法向杨文生的家人交代,于是将他埋在自己家门口,从此再也没有外出过。这是一个关于“仁义”与“道义”的故事。
两个好故事,各自拥有隽永的意象。鲜亮打眼的“哈布特格”与乡村常见的“公牛角”,分别作为两个故事的核心意象被提取出来。这不难理解,梁鼐是生活在汉文化中的蒙古族作家,就像川西的藏族作家阿来,“非汉性”元素为他们的小说带来了陌生化美学的擦亮和照耀。“哈布特格”所关联的“情”发生在蒙古族地域,“公牛角”所关联的“义”发生在汉族地域。事实上,这两个意象被作者赋予了同等的心之重量,跨越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界限,绽开了情深义重的朴素花朵。
最后,听从罗喜来的建议,古董商人准备带走父亲。在父亲的坟里,他意外地发现了“哈布特格”,虽然颜色已经黯淡,但依然结实漂亮。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和他一样陷入巨大的困惑:在第一个故事里出现的哈布特格为什么出现在第二个故事里?杨文生到底是和敖登私奔了还是为了保护罗喜来而被公牛角刺死了?我以为,究诘故事的真假并无必要。天真汉梁鼐要做的是将两个好故事合而为一,将来自不同地域的“情与义”开作一朵并蒂莲。一个对人世间持有“信”并坚执于此的人,就这样在两个相互守望、共同增殖的故事里,走出了一条自我完善的生命通途,收获了一种美满圆融的精神馈赠。
小说只有短短万字,却密实而迤逦地建构起了一个接近完美的结构和叙事。它以天真为底蕴,以故事为双翼,通过质感极好的文字,在亦真亦幻之间衍展出了一个重大的叙事变化。如果说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是着力于“解构”的话,那么,梁鼐则着力于“建构”。他要将那些曾经被深度消解掉的承诺、情义、信与望、爱与守重新拾掇起来,建成他自己的叙事之塔。在小说最后,古董商人将父亲怔忡不安的骨骼装入褡裢里,“我抖了一下骡子的缰绳,带着我的父亲在月光下奔跑起来。”这个结局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它消除了所有的心结怨恨,弥平了生命的匮乏和创伤。
这是天真与情义对于庸常世故的较量、征服、震撼。作为一个新作家的作品,《哈布特格与公牛角》堪称出色,呈现出了成熟小说的迷人质地。要说缺憾的话,那也同样是作为新作家的问题,就是梁鼐目前还无法完全摆脱前人的影响。这并非缺点,而是写作的必经之途。对于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叙事形式,而是能否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及其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梁鼐“建构”的有效性,我愿意看到这样的写作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洗去庸俗陈腐之气,呼应那一场场遥远、新鲜而古老的伦理召唤。